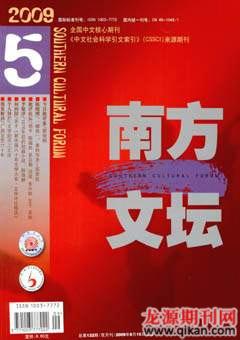《武训传》批判:对旧文艺及知识分子的规训
曹 霞
作为对“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①,文学批评致力于发掘文艺事实中的审美因素,并做出理性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分析,这决定了批评的审美实践特征和自主原则。但在“十七年”的文艺批判运动中,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遭到了阻断,成为国家机器对文艺和知识分子实行规训的方式之一。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在这一总纲的指引下,文学批评被赋予了加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思想政治功能,被规定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和“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②。随着20世纪50年代批判运动的日益扩张,文学批评的“去本体功能化”愈演愈烈。
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文艺批判的对象是孙瑜的电影《武训传》。在权力意志和文学批评的“合谋”下,这次批判清理了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旧文艺”和“旧思想”,对知识分子形成了隐性的规训制度,确立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模式。
一、“新旧”力量的多重“修复”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孙瑜一本李士钊的《武训画传》,希望他能够将武训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以教育和激励人民。孙瑜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所感动,以此为主线草拟了《武训传》的剧情,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歌颂了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③ 这是一个“民间”武训的形象。
1947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王瑞麟的协助下,《武训传》被纳入该厂的拍摄计划,该厂时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管属,这也是电影后来被批为“国民党反动派用以反人民、反革命”的原因。1948年1月,孙瑜写完分场剧本后,寄给阳翰笙、蔡楚生和赵丹等人,赵丹见山东同乡如此忍辱负重修义学,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接受了扮演这个角色的任务。电影从1948年秋开始拍摄,到11月,在拍摄到三分之一时,“中制厂”陷入经济困难,宣布停止拍摄。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购买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已经拍成的拷贝,孙瑜也加入了昆仑。但当时昆仑正在赶拍《三毛流浪记》并筹拍《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没有排上日程。1949年12月,在没有适当剧本可供拍摄、不能停工待料的紧急情况下,昆仑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从开始拍摄到再度开拍,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7月,孙瑜受邀北上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他被“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和“秧歌飞扭,腰鼓震天”的全新情形所激动,对“武训其人其事”发生了疑问: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的成立晚宴上,孙瑜就《武训传》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武训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都被地主拿过去了④,这些都促使孙瑜重新评价“义学”和武训。回到上海后,他和昆仑同仁决定将“歌颂”改为“批判与歌颂并行”:武训终生艰苦行乞兴学却劳而无功,但仍然肯定他艰苦奋斗的精神。郑君里建议将周大由张举人家的车夫改为被打散的太平军军士,沈浮主张周大可以被“逼上梁山”。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艺术事业纳入了国家体制,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环。1950年1月4日,昆仑影业公司邀请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夏衍和于伶等人讨论《武训传》剧本。作为经验丰富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夏衍和于伶意识到了武训的“不合时宜”。夏衍提出“武训不足为训”的警语,于伶建议不如拍摄解放区模范老师陶端予的影片⑤。陆万美认为,武训的悲剧和问题在新社会中实际上已经解决,但他艰苦兴学的精神对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些鼓舞作用。如何使电影同时达到对人物的“批判”和“歌颂”呢?陆建议修改电影开头和结尾,由一个老人在武训出殡时对孙儿讲义学故事改为1949年后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一百一十一周年纪念会上对小学生讲武训故事。这样既可以“结合现实”,又可以“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⑥。之后,孙瑜和昆仑公司的老板任宗德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案,申请到了贷款。
旧文艺要想在新文化中存活,必须顺应时代意识形态的流向,修剪抚平与之冲突的“枝节”。《武训传》之所以得到拍摄许可,就在于孙瑜尽量按照新意识形态的要求对剧本进行了大量删改。他吸取了陆万美的意见,加上了“女教师”这一重要角色,接受了郑君里和沈浮关于周大的意见,并且增加了李四和王牢头这两个人物,周大在他们的协助下打出牢狱,带领农民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和“行乞兴学”形成“一文一武”两条线,贯穿始终。
在影片中,新与旧的衔接任务由“女教师”担任,她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宣讲者。在影片结尾,女教师给小学生讲故事时,肯定武训“坚韧地斗争”的精神,同时否定他“个人的反抗”,而周大由于没有组织广大群众,报仇也没有成功,女教师由此得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中国的劳苦大众才能得“解放”的结论。这段台词与故事的叙述层明显形成“断裂”,却是电影的“点睛之笔”,它是1950年底全片拍摄完后、经过有关领导修改审定的,将意识形态的要求都融入了进去,可视为新社会对旧文艺的“修补”和“添加”。经过“新旧”力量的多重“修复”,《武训传》与李士钊的《武训画传》已相去甚远,阶级情感分明,阶级对立色彩浓厚。
1950年底,电影拍摄完成,先是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和文化局副局长于伶都认为这是昆仑的重点片,是国家贷款资助拍摄的,最好还是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华东局第一号人物饶漱石看完电影后,满面笑容地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说“好,好”,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了。1951年2月,《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和北京公映。周恩来、胡乔木等人都看了,毛泽东没有去。放映完后,朱德微笑着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仅针对一个艺术处理提出建议:武训在庙会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就把这个镜头剪短了。
公映结束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接踵而至,多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也试图在武训苦行僧式的生活里读出新政权的进步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孙瑜在北京逗留的十天里,遇到的很多人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特别有益于教师安心于教育事业,《武训传》还被《大众电影》评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二、权力意志的介入
权力是文化霸权的核心,它是“特定主体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源或优势而得到的支配他人或者影响他人的力量”⑦,这里的“特定主体”一般指那些因成就、威望和个人魅力等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的领袖人物,是具有“特殊的力量或品质”的“卡理斯玛”(Charisma)⑧。权力意志的运作具有极大的威力,一旦“异质”出现,就能迅速调动国家机器,发动从机关单位到舆论阵地和文艺干部等组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被批判对象的性质步步升级,批判运动层层深入。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意志起到了指导、统领和制订方案等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面临着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变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时起就具有了浓郁的民族国家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⑨ 1950年至1951年,国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以保障和巩固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变成执政党以后,不少人的“警惕”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发生了混乱,社会思潮纷纭复杂。不仅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散播“毒素”,有些经过延安整风洗礼的知识分子也未能保持正确的阶级立场,这使一向重视“思想站队”的毛泽东极为不满,认为非无产阶级思潮妨碍了政治经济建设和树立新的思想文化权威,更不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予以清除。
葛兰西在分析现代国家形成的时候,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暴力统治的机器,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⑩ 他认为,除了以强制性机器维持政治与社会秩序外,国家还要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使之在心理上达到“同意”和服从{11},后者的统治更具有弥漫性的力量。柄谷行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政治性机构更多地存在于“文学”那里{12}。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教育和宣传等非暴力手段,可以层层传达“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声音,塑造个体的情感取向和文化想象,引导民众完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武训传》及其“颂歌”恰逢其时地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批判和清理的机会。毛泽东专门调去影片看了之后,对江青和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13} 他指示胡乔木组织对《武训传》的批评。从1951年3月底起,对于武训和《武训传》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认为这样的讨论将是“教育者自身必须首先受教育”的“很实际很生动的范例”{14}。贾霁批判了武训“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以及“近似于‘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的路线”,断定影片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15}。杨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运用典型的毛氏推理法,指出应从“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呢还是妨碍了它”的实践效果检验历史人物的作用,他说,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武训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不仅毫无积极作用,而且非常“有害”{16}。这就指向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像武训那样“投降”,还是像周大那样“革命”?是走阶级调和路线,还是阶级斗争路线?两种不同的政治话语产生了强烈冲突,从而将文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他们的观点与后来的社论如出一辙。为使批判更具文化合法性,《文艺报》还重刊了鲁迅谈武训的文章《难答的问题》,这篇文章意在批判国民党政府借武训故事推行奴化教育,却无意中为毛泽东发动《武训传》批判提供了“依据”。贾霁、杨耳、江华的文章还被5月16、1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杨文的题目《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被改成质问句《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更具针对性和批判性。在权力意志的介入下,批判运动溢出了文艺问题的讨论范畴。
在批判过程中,《人民日报》社论起了关键作用。社论原为胡乔木所起草,毛泽东并不满意,只留用了第一自然段的两句话和那个长长的名单。在毛泽东看来,《武训传》的“旧”不仅在于它诞生于“旧社会”,而且在思想意识和宣传指向上都非常“旧”,辨不清“歌颂”和“暴露”的对象。社论从“封建/反封建”角度评价武训,称“行乞兴学”的行为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十分“丑恶”。社论高屋建瓴地剖析了《武训传》“不纯”而驳杂的质地:武训的行乞兴学是向地主阶级的“投降”,影片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扬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改良主义胜利了,武装斗争(周大)却失败了。在毛泽东看来,两种政治话语的交锋淹没于“千古奇丐”的感人义行中,不仅一般观众难以辨别,就连“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没有站稳“阶级立场”{17},这说明“阶级斗争”须臾不可放松。
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并不是主要目的,“改良主义”只是毛泽东竖起来的一个“靶子”,他所要做的是剪除旧文艺及知识分子思想的旁枝杂叶,进行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改造。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长长的名单,共有四十三篇赞扬文章、三本关于武训的书,一共四十七位作者,包括孙瑜、赵丹、端木蕻良、金紫光等文化名人。在毛泽东看来,《武训传》的“旧”与“新”时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大相悖离,却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这比电影本身更令人警觉。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武训传》一样质地驳杂,以致对于落后思想的歌颂和赞扬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如果不加规训和清理,就有使新中国倒回“旧社会”、无产阶级阵营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险。他对那些留恋旧“上层建筑”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警告他们如果不尽快与“新文化”接轨,势必会丧失“批判的能力”,以致让“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的批判力度和表达方式都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姿态,“难道……吗?”的连续追问句表达了严重的质疑和愤怒,而“我们的作者们”则暗含讥讽之意,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逼使他们怀疑原有的思想意识,重新思考自我认同的归属。
毛泽东通过对《武训传》的批判,重申了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路线的绝对正确,以此暗示:如果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坚持革命道路?还是坚持改良主义道路?这是划分不同阶级立场的标准。毛泽东将对《武训传》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性高度,其措辞之严厉,批判之苛刻,无形中划出了一道界线:凡是肯定《武训传》的一律是“反动宣传”,而保持沉默者则被定为“承认或者容忍”“反动宣传”,这两种都是“错误”的。
虽然人们当时还并不知道社论是毛泽东写的{18},但《人民日报》本身就代表了意识形态官方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刊登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毫无过渡地将“讨论”转换成了“批判”:“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该做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19} 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了批判活动,文化部电影局、教育部等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单位“讨论”和“学习”,胡绳、周扬、范文澜、袁水拍、何其芳等根据社论观点发表批判文章,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20} 给影片定了性,徐特立、夏衍、孙瑜、赵丹等人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发表过“颂歌”的《大众电影》、《文汇报》、《大公报》等做了公开检讨。从社论发表的1951年5月到8月,批判和自我批判文章共八百五十多篇{21},构成了由上至下的具有布置性策划性的批判格局。权力意志的介入主宰了批判运动的走向,意识形态机器积极配合,这种高速运作的方式不但具有良好的弹性和自我调节功能,还能高效吸附同等走向的社会资源,清除不同方向的“异类”。
1951年6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主要成员有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化名李进)等人。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指示说,武训本人和义学都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歌颂?还是应该反对?{22} 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三人执笔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经过了毛泽东的多处修改和加写,他认为原稿对武训的判定不够明确,大笔一挥,武训就成了“依靠封建统治势力”的“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23}。《武训历史调查记》印证了社论的“正确”,而且比社论更“有理有据”地证明了武训的“罪大恶极”,再次掀起批判热潮,为知识分子指明了自我批判的基调和自我认同的方向。
三、文学批评的双重功效
在《武训传》批判中,党内高层、文艺领导和知识分子沿用社论的观点,批判旧文艺和旧思想,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批判文章以文艺问题为起点,可以说具备了文学批评的形式,但其内里却是“政治化”的阐释,从两个方面完成了与意识形态的“合谋”:一方面强化了毛泽东的党内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清除了旧文艺的影响,使知识分子将思想改造内化为自我监督机制。
党内高层如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进行了内部检讨,在上海“文化广场”作国际形势报告时,周恩来公开提到自己对《武训传》的拍摄要应负一部分责任。徐特立和马叙伦将自己从前对武训的表扬称为“盲目的”、“不可饶恕的”{24},他们从“教育”角度阐释了对武训的新认识,指出武训的教育是“奴隶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是“使人民解放、使人民做主人的教育”,应认识到武训精神表现了“反革命思想和当前革命运动的抗拒”{25}。
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和政务院主管文教科技的郭沫若虽然以无党派人士参政,但他一直以特殊党员的身份与中共领袖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指责和周恩来等人的检讨使他大受震动,他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之前他受陶行知影响,一直高度评价武训:1943年应陶行知之约,在武训纪念会上讲话;1945年12月领衔发起武训107诞辰纪念会;1945年12月1日为《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题词:“武训是中国的斐士托洛齐{26},中国人民应当到处为他树铜像。”他痛批自己的行为,说自己以前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武训,盲目称赞过这个“奴化教育”的化身,如今,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种为《武训画传》题辞的行为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27}。除了检讨之外,郭沫若还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读后感,“重新再检讨一次”。他称赞《武训历史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肯定它“把武训其人及其事揭露得可谓一清二白”,“澄清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根据《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戴的“帽子”,他进一步做了发挥:“(武训)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28}以郭沫若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背景,这篇读后感可视为他的“思想献礼”。党内高层的行为为知识分子做出了“表率”。
对旧文艺的清理涉及允许旧文艺出台的文艺领导,只有在他们检讨自己的行为后,才能印证批判的合理性。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要求夏衍写检讨,当夏衍流露出“激动”情绪时,周扬却“平静”地告诉他要明白问题的严重性,理由就是社论是毛泽东写的。在上海市文化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夏衍以华东局和上海市文艺领导的身份做了检讨,他说《武训传》暴露了上海文艺界和自己“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的错误,表示要吸取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和脱离现实的错误倾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文艺理论,深入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的现实,创造出好作品{29}。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黄源、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伯韬和文化局副局长于伶都写了检讨。他们的行为产生了示范作用,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榜样。
对那些被社论点过名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顺应批判潮流,认清和改正“错误”,才能重新被接纳。在批判运动一开始,他们主要批判自己对武训的“歌颂”,表达对武训和电影的“新认识”。但是,在批判者看来,这种批判方向显然是错误的、不够深刻,还没有触及“灵魂”和“思想”。孙瑜一开始检讨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在于“学习不够”,忽略了武训的“非革命的本质”{30},被袁水拍、丁蔓公等人指责为“粗枝大叶”、“口是心非”{31}、“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32}。李士钊称自己是“思想上犯错误较严重的一个”,主要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与狭隘的爱国思想的错误”{33},也受到批判者的否定:“这篇东西与其说是‘检讨,毋宁说是辩解。”{34}在批判者看来,并非孙瑜等人对武训的认识出了错,而是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深挖思想根源。
《武训传》的作者固然要检讨,那些“歌颂者”也逃不掉相同的命运。在江青的“你是文艺界的老人儿”、“希望你带个头”{35} 的半劝半逼下,金紫光批判了自己从前的“错误”态度,说在“看了许多批判武训的文章之后”,有了“新的认识”,称《武训传》表现了对农民武装斗争的歪曲和“向封建统治者屈节妥协的改良主义倾向”{36}。与金紫光文章同版发表的还有端木蕻良以致编者信件形式所做的自我检讨,他从武训的“逆来顺受”和“利他主义”谈起,批判武训“用他的行为实践了统治者的思想”,是“统治者所肯定的示范人物”。他们的检讨与社论在同一天发表,因此不可能读到“许多批判武训的文章”,而是受意识形态的直接引导。他们的检讨令批判者极不满意,“编者按”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检讨极不深刻,因为他们并没有说明他们原来的意见是怎样的,究竟错误在什么地方。”{37} 其实,意识形态需要知识分子做的并不单单是自我反省,而是要他们将自己“批倒批臭”,褫夺他们的个人尊严,让知识分子在痛苦的“蜕变”中,抛弃自我,向意识形态靠拢。
检讨“不深刻”也就意味着对社论理解不深刻,对批判的性质和方向理解不深刻。在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的压力下,孙瑜等人将对武训的批判毫不留情地转向了自我批判,表明自己的“新立场”。董渭川检讨自己犯下“原则性的错误”有着“长期的原因”:一、全部思想建筑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二、不自觉地陷在“教育万能论”中,三、被“进步的”包袱阻碍了进步。他借金克木的话,将自己比作是“在黑窟窿里蹲惯了的猫头鹰”,不习惯在“阳光”下飞行,称自己站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38}。在严峻的批判形势下,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批倒批臭”,才能获得重返“人民”阵营的许诺,可他们就此被打上了“原罪”的烙印,只能以“带罪”之身凄惶栖于“人民”阵营的角落,此后,每遇一次运动,其“罪行”就被翻检出来,再次“赎罪”或“陪绑”。在社论发表一年之后,孙瑜还在继续做检讨,他以社论和批判者的观点为依据,说自己“错误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实际上作了他们的代言人”,他还引用周扬在1951年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对《武训传》的批判,称自己的错误为“改良主义”和“个人奋斗”,批判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立场”问题:“我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抱着自己错误的主观成见去看问题。”{39} 这份检讨以毛泽东和周扬等人的论点为论据,具有先天的“正确”性,加上周恩来的干涉,孙瑜总算暂时过了关。
在《武训传》批判中,被批判者的自我否定与社论的结论殊途同归,成为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的最后环节。知识分子在痛苦的质疑和否定中“清洗”思想,调整姿态,以沉痛的自我批判和对毛泽东的衷心颂扬加入到“大合唱”,从对武训的“盲目”歌颂者转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力争“脱胎换骨”,早日回归“党”的“怀抱”。意识形态、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认识”终于“合围”,文学批评也实现了一次政治功能的预演。
《武训传》批判确立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模式:以脱离文本的政治索隐为主要方法,以权力意志发难——意识形态机器全力配合——相关人员进行检讨为主要模式。这次批判对旧文艺的清除可谓干净利落,《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等影片被禁演,1952年只有两部电影,还不到1951年的十分之一,文化界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40}。《武训传》批判开启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41} 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痛切地认识到,只有“洗澡”才能“过关”,成为“此心光光地”{42} 新人,否则只能带着“不洁”和“污垢”等待下一次更严厉的“清洗”,或被打入另册。经过各种运动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痛苦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之中,这种扭曲比政治惩罚和肉体消亡的教训更加刻骨铭心。
【注释】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3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96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③④⑥孙瑜:《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载《春秋》1996年第3期。
⑤孙瑜:《对编导电影〈武训传〉的检讨》,载《解放日报》1952年6月3日。
⑦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1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译,3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⑩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译,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葛兰西:《致卡西尔的信》,余其铨译,见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222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13}{35}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88—89、103—10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4}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15}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16}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2期。
{17}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如无特别说明,毛泽东对《武训传》的评价都引自这篇社论。
{18}姚文元在1967年第1期《红旗》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才第一次公开说《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毛泽东写的,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套红重刊该社论,作者正式署名“毛泽东”,《文汇报》等同时刊登。
{19}《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20}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载《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
{21}张明编;《武训传研究资料大全•附录》,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2}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23}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4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24}马叙伦:《我过去表扬过武训的自我检讨》,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3期。
{25}徐特立:《〈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3期。
{26}裴士托洛齐是瑞士专为穷人孩子办教育的人道主义教育家。
{27}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7日。
{28}郭沫若:《读〈武训历史调查记〉》,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9期。
{29}夏衍:《从〈武训传〉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0期。
{30}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6日。
{31}丁曼公:《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
{32}袁水拍:《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7日。
{33}李士钊:《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31日。
{34}张立云:《检讨乎?辩解乎?——对李士钊自我检讨的意见》,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
{36}金紫光:《重新认识武训》,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7}《重新认识武训•编者按》,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8}董渭川:《武训问题给我的教训》,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12日。
{39}孙瑜:《对编导电影〈武训传〉的检讨》,载《解放日报》1952年6月3日。
{40}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陈荒煤,陈播主编的《周恩来与电影》,2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41}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42}焕南:《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0年7月23日。
(曹霞,供职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