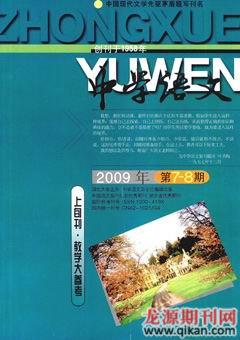水乡夜色凉如水
周兆梅
《社戏》在鲁迅小说中别具一格,是他一生孤寂、冷漠的心灵里唯一的安慰,充满着美妙的诗情,它与《故乡》互相映照,互为补充,是鲁迅小说抒情艺术的双璧。《社戏》语言精练、深刻,富有浮雕性和传神性,不仅有诗一样的韵味,而且还具有风清骨峻的内在力量,这也是鲁迅加进民族语言的重要因素。
《社戏》渗透着双喜、阿发们真挚友情的喜悦。随着平桥村那只有说有笑的航船的前进,豆麦水草的清香,山影月色的秀丽,依稀歌吹的迷人,远近渔火的悦目,景象迭出,妙趣横生,其运笔所及,简直写尽水乡夜色,曲尽人情之极致,这正是:水乡夜色凉如水,坐看灯火歌迷离。
一、谴词凝练平凡中见奇崛
《社戏》中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谴词凝练,于平凡中见奇崛。我们知道,语言是文本的媒介,文本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文本具有最本质的意义,它规定文本的性质,限制着文本的自由。
《社戏》虽是小说,却有诗一般的语言,它不像一般小说那样靠故事的曲折离奇来弥补语言的不足,而是在语言上捕捉稍纵即逝的感觉,靠语言去穿透,去滋润。例如:文中因为早上叫不到船,“我”不能去看向往的社戏,这一天“我急得要哭”,不钓虾,东西也少吃,然而,晚上,“吃过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少年们兴致勃勃,来给迅哥儿讲戏,“聚拢”一词,体现了孩子们与小客人“迅哥儿”的亲密无间,“叹息”、“同情”细微地表现出小主人们对“迅哥儿”不能看戏的惋惜,及对“迅哥儿”不开口讲话失望情绪的理解。且看下面的叙述:
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在这迟疑中,双喜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双喜的“大悟”引起了众少年的“大悟”,并立刻“撺掇”,让“我”实现心愿,然而,母亲、祖母又顾虑重重,双喜又忙打包票,给“迅哥儿”母亲、外祖母吃定心丸,让“迅哥儿”终于如愿以偿。平常的语汇,发生了奇崛的效果,把一群少年叹息、顿悟、化解疑虑刻画得真实、自然,景情相生,形神毕肖,使人感到每一句话都是从生活深处走来的,都带着生活的清新气息。
何谓佳句,用谢榛的话说,就是“颂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四溟诗话》),佳句应是:清爽流畅,抑扬动听,色彩明丽,含蓄隽永。要求文佳,必先求句佳,要求句佳,必先求字佳。鲁迅的《社戏》便是如此讲究炼字,即着一字而境界全出。他善于从丰富的词汇中选取最准确、明朗和生动有力的语汇,把事物描写和表达得恰到好处。
二、珠圆玉润浮雕感兼传神性
《社戏》语言中一个显著特色,是它的浮雕感和传神性,生活本来是有立体感的,是有生命的。惟有浮雕感和传神性的语言,才能写出它的真实面目来。而这,也正是鲁迅小说的文体特色。
别林斯基认为:“可以算作语言优点的,只有正确、简练、流畅,这是纵然一个最庸碌的庸才,也可以按部就班地从艰苦的锤炼中取得的。可是文体——这才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
而鲁迅正是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天才作家,他的《社戏》中每一个词语都珠圆玉润,具有一种诱人的力量。《社戏》中“阿发”、“双喜”两个人物只着上简单的几笔,就声情并茂,惟妙惟肖。
你看,这群水乡少年美妙的心境描写:
他们摇船摇得饿了,要上岸偷罗汉豆吃,偷谁家的呢?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各偷了一大捧。
阿发的纯真、率直、毫不掺假,一尘不染的心灵随着鲁迅的几笔勾勒、便定格在作品的人物画廊中。偷盗本是不足为训的行为,在这里却是多么神圣的事情,阿发因自家的豆大得多,主张偷自家的,表现出胸无芥蒂的无私;双喜却担心再多偷,阿发娘知道了要哭骂的,流露出顾全大局的友爱。在这种无私和友爱的“偷盗”中,体现了作者对他们心胸纯洁、重情重义的热情赞扬。
鲁迅对水乡少年的心境描写,主要运用率真的对话使文章趣味横生,抓住“偷罗汉豆”这件事的一个瞬间,将对话艺术化,在活脱跳达中发散出深深的意蕴。语言是小说的魔术棍,能幻生种种奇观,语言在浓与淡、拙与巧、奇与正,典雅与朴实、肃穆与活泼、沉滞与轻盈、华丽与清新等等之间,既存在对立冲突,又隐含着某种契合,鲁迅《社戏》中的可贵之处就是能够打通语言两极的气脉,融会贯通,达到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化境,体现了他独有的语言魅力——浮雕感和传神性。
三、辞精气爽骨体中具风力
《社戏》语言特点之三是辞精气爽,有风骨。风骨是艺术语言的内在功力。南朝人刘彦和说:“辞之待骨,如林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又说“奇正反,心兼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因此,“风骨”作为一个文体范畴,是指发挥语言艺术内部的义与辞、刚与柔、奇与正的相互辅翼,相互制约的作用,使作品写得辞精气爽,深刻动人,既有骨体,又具风力。
在《社戏》中,船向赵庄飞进时,作者描写的景色是: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文笔清新流动,景色清新秀丽,草香、月色、水气,写得那样明秀,那样迷蒙,又那么轻盈飘逸。只有作者对双喜、阿发们的纯朴友爱感到无比亲切,而现在又坐在他们的船上去看自己喜爱的社戏时,才可能有对自然景物的这种亲昵感受。因此,这段文字在我们眼里,简直分不清作者是在写景,还是在抒情,因为情景已交融为一了。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连山像踊跃的兽脊向船尾跑去,说明船行飞快,以此衬托出我焦灼的心情。迷离的灯火歌吹,并非是从真的戏台传来的,但是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社戏的戏台,所以把风声当歌吹,以渔火为灯火。处处写的是诱人的景物,而又处处写的是欢乐而焦急的心情。作者把秀丽的文字和独特的美学感受写进自然景物中,使“秀语”有了骨,把景物写得非常有个性。人因景而美,景因人而活,这种美丽而富有生机的景物描写具有使人移情荡志的艺术魅力。
总之,思想是语言的灵魂,风骨是语言的筋脉,富有风骨的语言不是“躺”在纸上的,而是“立”在纸上的。能够迈开自己的脚步,走进读者的心灵。
《社戏》之所以能勾起读者的深思遐想,让读者受到作品中童年美好往事的强烈感染,是因为作者的素材本身就来自中华民族最深层的记忆和幻想,其创作过程也就是将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转化为诗一般的语言以重新显现。它那未被认识的边界可以伸展到无限远的地方。
[作者通联:湖北房县门古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