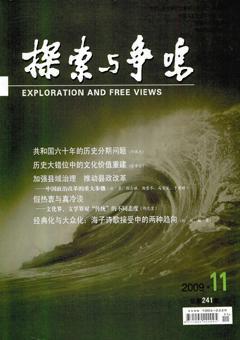假热衷与真冷淡①
内容摘要近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与20年前的文化热虽然在运作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价值取向不同。1980年的文化热是知识分子把政治改革失败的怨恨转嫁到传统文化,借助文化讨论的曲折叙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抛物线;而今天的“文化热”,则是集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细节与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演绎。今天的“文化热”只不过是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驱动下的人为制造的文化繁荣的假象。与文化界的假热衷相比,文学界则是真冷淡,这恰恰显示了这场“文化热”的本质:虚空的膜拜传统,是为了掩盖对未来的筹划的匮乏;而匮乏未来的筹划,必然一再求助于传统。
关 键 词 传统文化热 文化界 文学界 假热衷 真冷淡
作者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从学者到名流·从学界到民间·从国学到显学
近年来,文化界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热”。这话似乎有点语病:文化界内部当然每天都得面对文化,何热之有?但笔者所谓“文化热”,并非文化界内部主动“发热”,而是一股社会需求成为风气,突然热衷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界身不由己也被动地热起来。
所谓社会需求演成的风气,是指以强势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闻风而动的各地电视台为中心而波及全社会(书店、出版社、报刊、网络和学院),迅速造成以往只有政治动员才能生效的全民学习传统文化、关心传统文化的热潮。文化讲座收视率竟然超过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以往一贯很严肃的文化普及竟然赛过大众文化娱乐,精英文化竟然一夜之间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狂欢。电视文化讲座副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急遽飙升,一本书只要是“央视百家讲坛”某位坛主的演讲稿,开印就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册,成为理所当然的畅销书;本来在学界籍籍无名之辈,一旦登上某个讲坛“秀”一下,就成为当然的文化权威和学术明星,马上晋升(或自封)为教授。据说某位本来在书斋坐冷板凳的学者,自登上“百家讲坛”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流和公共人物,自此出门不戴墨镜,就害怕被人围观,而这位先生却在基本保险的公共媒体上频频露脸,对各种超出其专业领域的公共话题泰然地发表高见。
因为与大众媒体结合(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学者成了名流,学术走出学界而走向民间社会,传统文化再也不只是政治宣传的招牌和国家的文化名片,而被渲染为大众的普遍追求与精神寄托。本来一直是出版社沉重负担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书籍,也一下子成了文化产业链中被看好的一环,并被头脑精明的书商反复开发。最后,“五四”以来一直比较冷门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国学”,竟然无须任何权威干预,在经济利益主导一切的当下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
这一次“文化热”,使人们自然联想到1980年代后半期另外一场文化热。
20多年前那场文化热,是政治改革走到一定阶段的变相延伸。当政治改革无法按原来的速率深入下去时,剩余热情就只能转移到文化界,借助文化讨论的曲折叙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抛物线,结果只能是被政治权威叫停,由此积蓄的乃是未被实现的政治理想,而非任何形式的经济效益。曲折的政治隐喻必然走向宏大叙事,气势恢宏的本质论描述、概括、总结和未来学展望乃至潜在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呼求,成为20年前那场文化热的最高呈现方式。惟其如此,文化故事的讲述者、书籍读者、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都是所谓“社会精英”,而非今天大众集体的参与。20年前文化热的价值倾向很明显,是和“五四”前辈那样把政治变革失败的怨恨转嫁到传统文化,断言政治改革必须最后诉诸文化的更新,所谓文化热其实是文化批判热,参与者们所关心的乃是文化故事宏大叙事的本质论结果与必然推导的政治运用,不是如今以学术外衣包装好的集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细节与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演绎。
但两场性质不同的文化热,在运作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20年前那场文化热之所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主要是自上而下启蒙与教训的结果,它紧紧依赖“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创设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模式;那么眼前这场新的“文化热”,看上去增加了诸如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新的运作方式,骨子里仍然借用了这一传统的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不仅如此,它还把这种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在全球资本和后现代文化工业的语境下推向极端,变传统的诱导模式为后现代的恐吓逻辑——眼前的这场“文化热”告诉大众:跟后现代文化工业赛跑,也就是跟时间赛跑,跟生命赛跑;谁拥有正在热播的文化讲座的信息,谁就拿到了时尚狂欢的入场券,谁就抓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方向,其文化生命的质量与档次就获得保护。文化,不再是潜移默化、润泽心灵的精神营养物,而是必须及时抢购的时装与随身携带须臾不可或缺的救心丸。
在这场旨在对大众实行文化恐吓和文化收编的文化热中,重要的是被抽象把握的文化象征本身,而不是文化的实体内容。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典籍、人物、故事、典章、制度、文物之类之所以取代人类文化交互形成的文化公共体、未来文化展望而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并不只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结果,而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简单可操作性。
学院文化的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场“文化热”的发动者是权威媒体、头脑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的网络,但“资源”始终在高等院校。各种文化讲座的主讲人(纪连海、刘心武等个别例外)绝大多数都是学院(大学和社科院)的教授、博导与学术权威(至少也是学术新秀)。
学院的学术资源进入公共空间并非不经过过滤和选择。换言之,学院的资源并非全方位地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的发动机,公共空间在接纳和利用学院资源时也改造了学院的文化形象,甚至影响到学院各学术部门的原有平衡,促使后者在短时间内重新建构。其中有三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中学”压倒“西学”。“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与人文学科的重心是“西学”而非“中学”,这是对晚清维新改良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反动的结果。尽管解放以后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口号下“中学”一直受到重视,但从来没有压倒过“西学”。这不仅表现在投入资源之大小悬殊,也表现在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和世界观来自“西学”而非“中学”。很长一段时间,是“西学”领导“中学”而非“中学”领导“西学”。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国家在“中学”方面的投入不断提升,大型学术研究立项计划纷纷向“中学”倾斜,“西学”(除了与“西马”有关的课题)不知不觉失去了过去的领导和主导地位,成为真正封闭在学院内部的纯学术操作,和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建构运动失去有机联系。尽管没有清楚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无疑极大振奋了“中学”,在古典文学、传统史学、古代哲学、古代社会制度、古代科学、古代习俗礼仪(尤其节日庆典)、历代人口经济地理和交通演变、古代建筑、传统医学及宗教各领域,学术研究都欣欣向荣,“研究梯队”日益强大,研究资金日渐充足,社会关注也越来越可观。甚至不少地方和部门还直接把所谓“传统智慧”运用于管理、商业和日常生活,最后反映到大众文化领域,由权威媒体骤然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传统文化热,实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第二,“大传统”压倒“小五四”。“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很容易被简单阐释。比如始终有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中断了传统文化,使之发生“断裂”。其实这是极不公平的。如果说传统文化有所衰落,那也是传统文化自身运行的结果,其衰落早就发生了(章太炎等许多现代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在宋代就已经开始衰落),而且这个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也就是说,衰落仍在继续。为何衰落?其因应该在传统文化自身。如果传统文化果真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它就不会衰落。衰落之罪不能怪到“五四”。反之,若没有“五四”,单依靠“五四”以前“中学”自身的研究方式,传统文化不可能获得现代性研究、保存、整理、阐释乃至所谓“创造性转换”与推广。
“五四”所开启的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本身毕竟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复兴与延续,而是一种异质的新文化阶段,二者之间的区别远远胜过认同。正是基于这一层了解,许多学者主张“五四”以后任何一种文化运动,哪怕极端的认同传统的复古运动,都应该纳入特殊的中国现代性范畴来考察。可是,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产生了一种假象,好像今日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传统”因素应该压倒“五四”并取而代之。对今天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了解“传统”(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文化传统)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解“五四”(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五四”)。传统节日、文化象征和典籍经常被纪念、被保护、被阐释,而纪念“五四”的活动甚至连“虚应故事”也谈不上了。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有没有“五四”运动这回事也成了问题。关于传统,人们总能说点什么,但关于“五四”,尽管过去才90年,已经相当茫然。有学者甚至指出,既然传统有几千年,“五四”至今不到百年,二者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几千比几十、数百比一二三某个位数。具体来说,比如写一本《中国文学史》,先秦到晚清应该占99%的篇幅,“五四”至当代,1%的篇幅足矣。这种浅薄的见解起码忘记了,“五四”不是传统文化之外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恰恰是传统文化运动内部衍生的一个必然结果,二者之间的比重不能以单纯的年代长短来衡量。“大传统”压倒“小五四”,确实是近来比较流行的一种文化想象,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想象不仅以自身的传统鄙睨自身的现代,更以自己的传统鄙睨世界的现代,陡然发现祖宗原来还有大笔被忽略的遗产,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上也急遽膨胀起来,不再“拿来”,而急忙“送去”了——目前正以“大跃进”形式为世界各地送去孔子学院的豪举便是这种文化想象的必然结果,而奥运会开幕式更集中表述了传统压倒现代、“死人”代替“活人”的文化状况。
第三,“孔子”压倒“鲁迅”。“中学”压倒“西学”,“传统”压倒“五四”,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或象征就是“孔子”压倒“鲁迅”。这里仍然是以年代之长短而论价值之大小。“孔子”几千岁了,“鲁迅”才一百多岁,在许多人眼里,前者当然要胜过后者!所以,尽管鲁学成绩斐然,鲁迅著作俱在,而孔子的事迹渺不可寻,孔子著作只是断简残篇,孔子研究的诸多领域更只在猜测悬想之间,但社会上俨然似乎更了解孔子而不知道鲁迅,孔子成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文化名片。“送去”的时候,拿出的文化名片是孔子而不是鲁迅(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400多家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最高机构是“孔子学院”而非“鲁迅学院”)。
传统想象与自我认同
新一轮文化热,所热的对象和内容原本无关紧要。在后现代条件下,不管讲什么,只要运用文化煽动乃至文化恫吓手段,一定有人倾听和追逐,正如末世纷纷出笼的各个领域众多假先知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缺乏追随者。80后的抄袭写手不是还为粉丝所裹挟而宁肯在经济上赔偿被抄袭者也不愿在事实上承认抄袭或者向被抄袭者道歉吗?这种古怪的逻辑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需要文化,不管文化是什么。
然而,“文化热”所“热”的主要还是传统文化而不是别的,其中颇有玄机。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开放状态,总趋势是后发型东方现代化国家主动学习世界和西方的心态占主导地位。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主要方法论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众所周知,无甚异议。但与此同时,回归传统、弘扬传统的呼声也从来没有消歇,各种各样的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乃至急不可耐的“送去主义”始终是“拿来主义”的逻辑补充,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会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而已。比如,晚清的“中体西用”、整个现代时期不绝如缕的各种“复古运动”、十教授的文化本位论、傅斯年“东方学在中国”的叫喊、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应运而生的战国策派和新儒家,以及在延安发动的民间文艺、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的建构,在沦陷区“小品文”的兴盛、1980年代“文化寻根热”直至21世纪新的传统文化热——从这个角度,实在可以对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归热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历次传统文化回归热,并不是真的要回到传统。鲁迅早就辛辣地指出,那些假装迷恋往古的遗老遗少们比谁都更加懂得享受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他们的复古只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富有欺骗性的生存策略而已。所以重要的是要看清传统文化热或包含的对于现代乃至当下中国的自我想象。
一个民族,如果整天沉湎于传统,而忘记“向前看”,本来就值得警惕。但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与现代时期的复古主义有所不同。尽管现代复古主义者也懂得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但也并不能一概否认其怀古复古的认真和严肃。真有人相信只要复古,就天下太平,文化昌明,人性改善。许多复古主义是理想主义和悲情主义的全身心投入,他们顽固乃至变态地“玩古”,却仍然值得同情。今天的“文化热”却并没有那种严肃认真的样子,“文化热”的制造者们根本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群大玩家,他们并不相信传统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是因为在经济领域产生了一些暴发户,他们要领导一种文化潮流,本以为自己只会挣钱,但是在一群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的提醒下,忽然发现,原来老祖宗倾废的旧宅或根本就不存在的想象的祖屋,竟是诗书礼乐的渊薮,赶紧翻箱倒柜,清理遗产。清理出来之后,并不加以批判的理解,而是用后现代的新材料合成迷乱的时装赶紧穿在身上,自娱自乐的同时还顺便以此傲视别的据说是没有遗产的邻居们。
据说美国60年代中产阶级勃兴,催生了提倡“细读”的“新批评学派”,后者及时满足前者的文化需求,教他们怎样阅读经典;现在中国的暴发户面对像砖头一样扛回家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通鉴红楼以及为小皇帝们预备的三字经之类,却没有时间去“细读”,于是就有学者们披挂上阵,走上各种讲坛,叫他们来“悦读”。这种“悦读”不仅是自己高兴,也与民同乐,那些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的社会底层渴望在文化上走一条捷径,与暴发户们平起平坐,所以群众性的“悦读”,正好可以用现成的文化共同体来填补贫富悬殊造成的巨大心理鸿沟。
假热衷与真冷淡
这样一来,也就显示了这场“文化热”的本质:虚空的膜拜传统,是为了掩盖对未来的筹划的匮乏;而匮乏未来的筹划,必然一再求助于传统。
远交近攻、远大近小、远实近虚,神化传统和虚化现代,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化运动内部并非隐秘的冲动。今天的这场“文化热”,只不过是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驱动下的人为制造的文化繁荣的假象。对文化的全民热衷只是一种假热衷,而假热衷必然伴随着真冷淡。证据是:文化界这场“文化热”并没有取得文学界的应和与配合。相反,文学界对这场“文化热”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
文学是民族心灵的写照,民族心灵必然依托民族文化,文学也必然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时期的真实面貌。文学和文化水乳相融,不可分割。因此,很难想象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化,也很难想象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学。
然而如上所述,文学反映文化,是反映特定时期文化的真实面貌,不是片面迎合文化界某种不真实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当文化界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比较符合文化的真实面貌时,文学和文化就同步发展;当文化界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背离文化的真实面貌时,文学就必然与文化界的步骤背道而驰。文化界热得很,文学界则冷得很。
今天正是如此。
1980年代以来,复苏的中国文学和同时复苏的中国文化一度呈现同步发展态势。尤其1980年代上半期,“诸神归位”,学(文学)文(文化)并重,古今中外文化信息不分先后彼此一起涌入中国文学,使后者获得了斑驳杂色的文化形象。
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潮,相应催生了“寻根文学”,一时间中国文学的努力方向似乎就是要使自己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稍早一些时候,作家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口号,也很自然地得到多数的赞同。其实“作家学者化”就是要求文学作品更多地具有文化含量,因为“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作家队伍与整个现代时期作家队伍的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没有后者那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是没有文化或只有相当低的文化就因着时势需要而被推到作家位置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让文学回到文化根基,让作家取得和学者不相上下的文化素养,自然成了文学界的自觉追求。
但这个趋势很快中断了。随着冰心、汪曾祺、孙犁、巴金、林斤澜、张中行等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现代作家或直接继承了现代文学血脉的老作家纷纷谢世,“学者化作家”的典型虚位了。剩下来的作家队伍,主角是“知青一代”中年作家,他们在“文革”时期读了不少书,成名后也一直发奋“补课”,但毕竟没有童子功,很快“内囊就空下来”,显出疲乏荒歉的样子,又不得不保持高产写作,文化标准自然就放低。知青作家如此,比他们更年轻的60后、70后、80后、90后作家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更可想而知。这些作家占领文坛,“无文的文学”(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文学)必然大行其道。
学术界有没有文化,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因为学者“终日孜孜”,多少总能弄出一点死板的学问来吓唬人,但这种死板的学问不等于活的文化,它不与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灵本体相调和,是没有生命的摆设,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
经过文学创作的中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就不同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经过作家心灵的调和,经过作家所熟悉的那一部分民族生活的过滤和检阅,带着生命的气息,就能反映一段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于是就会出现看似吊诡实则非常自然的情况:在文化界热闹非凡地炒作文化以至于仿佛无处不文化的时候,文学界反而显得基本没有文化或者对文化热极端冷淡。文化界的文化是炒作出来的伪文化,文学界的没有文化或者对文化人极端冷淡,才是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文化工业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人为制造文化繁荣的假象,但文学必须诚实地传达出代表民族多数人的精神状态的作家们的心中所本有的内容。这就做不了假。
作为“无文的文学”又一个范例,不妨看看目前创作力相对比较旺盛的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他们普遍有一种趋向,就是丧失了与完整的人类思想传统(包括本国传统文化)积极对话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传统已死,没有对话价值,时间就从他们站立之地开始(或即将到他们为止),历史一开始就以他们为中心,只有他们看到的和经历到的当下生活才值得凝视。于是,在他们中间展开了一种片面的文学竞赛,就是看谁更及时、更鲜活、更丰富地捕捉当下生活的新现象,而他们所用以捕捉和凝视当下生活新现象的思想和语言资源,恰恰又只能取之于当下流行智慧和流行话语。结果,这种文学竞赛变成了拼生活、拼信息。但这样放弃与传统积极对话的当下生活信息的片面展现与竞赛一般的争抢报道,注定是扁平的传奇故事与“段子”集锦的结合。
当然,也会有相反的形态,就是少见多怪,因为被真实的空虚所追逐,慌忙从迎面碰上的随便一种传统的碎片中抓取一点两点,迅速装修门面,或者当真就作为终极的依靠。所以70后作家传奇故事和段子集锦的写作方式之侧,也有那种突然不知道从那里得来的一星半点文化的碎片作为装饰,比如,煞有介事地说点过去某个朝代的故事,神秘兮兮地演绎某种毫无根基的文化仪式,或者在已经不通的白话文里头掺和一点高考恶战中作为剩余物资保存下来的那点文言文的花拳绣腿。如果说前者是拼嗅觉,后者就是拼幻觉:完全拒绝传统,和破碎的传统意识一样,都会堕入绝对虚妄中。
不管哪一种情况,目前这批青年作家的写作,都可以视为“十七年”和“文革”之后“无文的文学”的又一个范例。他们其实更应该放下“生活”,拿起“书本”。我的意思是说,放下虚幻的“当下中心主义”,建立健全的历史和时间意识(也是健全的存在意识),由此返回当下,才有新发现。
中国文学真要有所发展,必须认真调整自己与文化母体的关系。目前这种对人为制造的“文化热”保持冷淡固然是好,但还不够,更应该积极地迎上去,撇开虚假的“文化热”,自己主动地去接触、去拥抱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也使传统真正活在自己的血液中。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不是掉书袋,也不会是扁平的似乎忘记时间忘记传统的当下生活的被动记录,而是从联系着过去也面向未来的活的文化当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活的文学。
“文化热”并未贡献活的创造性文化,而对“文化热”持冷淡态度因此似乎无文化的灰烬般冷寂的文学,倒可能蕴含着值得注意的活的文化的火种。文学不仅作为试金石照出了“文化热”之无文化的本质,它也像一片休耕歉收的荒地,倘有丰收的希望,也只能在这里,不再别处。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在2008年底“北京论坛”的发言稿,发表时有局部修改。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