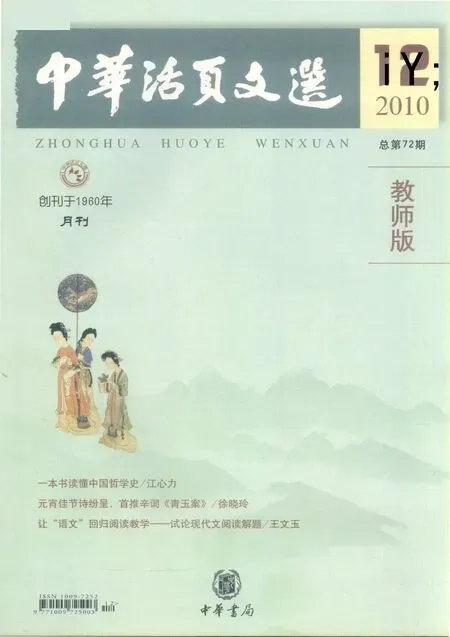浅谈《故事新编》创作的油滑误区
王 倩(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实验中学)
浅谈《故事新编》创作的油滑误区
王 倩(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实验中学)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以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剖小说中存在的自以为是“油滑”的弊端。
那么什么叫“油滑”呢?便是“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救赎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即在历史的回顾里,融进了现代生活的语言、细节和情节等内容”,将古代和现代错综复杂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写作方法。
对历史小说中的油滑,鲁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他也明白“随意点染”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弄不好便会滑入反历史的歧路。因而,他一再否定《故事新编》的审美价值:“《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取。”“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居多……”这些近乎否定的自评,是鲁迅以往创作小说时所不曾有过的。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战士对自身创作的失误所作的最诚恳、最严肃的解剖。事实上,油滑的消极影响,在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已经被证明了。作为一代文豪,鲁迅的文学风格、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等往往为他人所模仿、沿袭,因把握不住“随意点染”的尺度而在历史小说中出现的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时有所见。茅盾对此有过精当的评述:“历史题材的作品,近年来也颇多了。”“有的是继承着《故事新编》,这或者也可以尝试,可是就现在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亦失其功刺之目的。”
可是,多少年来,一些评说家不愿潜心研究油滑的实质,或视而不见,或简单地曲解为是作者的谦辞,对油滑的表现方法大加褒扬,笔者以为不安,以下就 《故事新编》里的油滑,谈谈浅见。
首先,笔者认为,油滑的产生,是鲁迅作为革命家和文学家对立统一的产物。作为文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士,他始终坚持和形形色色的腐朽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行为作韧性的战斗。《故事新编》的创作动机就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们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激烈的现实斗争和急切的革命功利性,使这位伟大的文学家难以平静地在艺术技巧上精雕细镂,又囿于自身的创作个性,杂文式的冷峻犀利,嬉笑怒骂,就不自觉地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走向油滑的误区。
我们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事件、人物为题材,以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为原则,借助恰当地虚构而创作出来的一种小说体裁。史迹、人物是创作历史小说的现实基础,故事情节的演绎、主题思想的形成,则是其“上层建筑”,“博彩文献,言必有据”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史迹的考证、挖掘,去孕育历史小说真实性的生命。但在《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中,取材于史实,即历史上实有其事,且古籍史料上可考的只有三篇:《采薇》《理水 》见诸 《史记 》,《非攻 》取材于 《墨子 ◦公输盘》。而且,它们也并不是纯粹的史实。而《补天》取材的是《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羿的神话串缀而成的。《铸剑》取材于《列异传》中关于干将莫邪的传说,可是原文很简单,许多都是鲁迅根据想象“点染”而成。《起死》则是根据《至乐篇》寓言演化而来的,至于《出关》的情节,鲁迅是根据章太炎《诸子学略论》中关于老子出关的揣测演绎而来的。很明显,这不是史实,而是章太炎的设想而已。对此鲁迅也明白地表示:“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习者,老却是‘无为而不为'的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以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也明确承认:“《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原来鲁迅先生,并非是围着古代传说而真的写起“历史小说”来,而是借“历史小说”之名,达到讽喻,揭露黑暗现实的目的。我们来看,《故事新编◦序言》中的这一段话:“第一篇 《补天》——原先题目作 《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做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惠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塑造,的确产生了联系现实斗争的反封建意义,扩大了作品的主题,但却影响了描写的舒展,使小说前后的风格不够和谐,由认真的虚构陷入了油滑的戏谑。鲁迅“对于自己很不满”。
事实上,在《故事新编》中,这种“对号入座”,直接以作品中人物、事件暗指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具体人物、事件的影射手法还不少。《奔月》篇就是鲁迅在和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的论战中产生的。鲁迅对此说得很明白:“那时就作了一篇小说,和他(高长虹——引者)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高长虹作为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在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鲁迅在《奔月》里塑造了一位盗名窃誉的小丑逢蒙,对其加以讽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其中引用的一些语言——“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你打了丧钟”“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等,却不免有油滑之嫌,从而在艺术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次,笔者认为,油滑的产生,是因鲁迅在对历史的回顾里,融进了现代生活的语言、细节和情节等内容。“以今天的生活去演义历史的生活。”“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处。”古人现代化的荒诞,将《故事新编》引入艺术的误区。
一、现代生活的语言
郭沫若在论及历史剧的语言时认为:“历史剧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同共通的最为理想。”共通,就是用白话,但又不是现代化。“根干是现代语,不然便不能成为话剧,但是现代的新名词和语汇则绝对不能使用。”他举例论及战国时代打仗,“就不能用‘飞机'‘坦克'‘毒瓦斯',古代中国人不能说出‘古貌宁'‘好都幽都'”,“今语为古所无的字则断断不能用,用了就是成了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郭老论述的是历史剧,对历史小说语言的要求,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且来看《理水》中的这一段议论:
况且,另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 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疗治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鄙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曦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远,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御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
“OK!”
上述文字中的“维他命 W”“OK”“蒸馏”“雪茄”等还有在《故事新编》中大量出现“古貌宁”“好都幽都”之类的音译外来词,以及“海派会‘剥猪猡',我们都是文明人”之类的现代国语,虽加深了作品的讽刺意味,但同时也不乏戏谑成分,影响了艺术的真实性。
二、现代生活的细节
同样的道理,细节的选择,也一样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大环境的制约。脱离古人古事孤立地将历史上的某一细节现代化,势必使它失去现实的根据而成为荒诞的空中楼阁。我们来看《起死》中的这两节文字:
“庄子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汉子愕然,放慢了动作。不多久,从远处跑来了一个巡士。
……
他跑进来,是一个鲁国大汉,身材高大,制服制帽,手执警棍,面赤无须。”
上述文字中的“警笛”“警棍”等现代生活的细节,从表层上看,似乎增强了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然而,若进一步作全面的考察,由于它失却了艺术的真实性,则不可避免地使小说步入油滑的误区。
三、现代生活的情节
王瑶在论及《故事新编》时说:“绝大多数都承认它是历史小说的人,对作品有关现代情节的作用及其表现历史人物的关系,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为什么?我认为是情节现代化的荒诞性破坏了历史真实性。我们且来看《铸剑》后半篇第四节,几乎全是荒诞的描写。且不说被豢养得不知其所以然的第六个妃子,会发狂似的哭嚷:“阿呀,天哪!咱们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唉唉唉!”曾经在国王膝上坐着,撒娇得特别扭了七十多回的第九个妃子,因见金盘里并放着三个头骨,也是焦急地问:“咱们大王只有一个头。哪一个是咱们大王的呢?”就是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急的手足无措,各自转圈子。算是最有谋略的老臣,伸手向鼎边一摸,浑身一抖,也只好立刻缩了回来。调集了铁丝勺、漏勺、金盘和
擦桌布等,由武士们协力打捞;可是头骨有三个,无从辨认哪一个是大王的。从胡须上辨别不出来,从后枕骨上也辨别不出来。结果只好把三个头骨和国王的身体一道放在一口金棺材里去埋葬。“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这样的描写,对于揭露奴才们的丑态,剥落侏儒、老臣的面具,指出其真相,确是大快人心的。但由于情节过于现代化,其荒诞性无形中破坏了书本的历史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