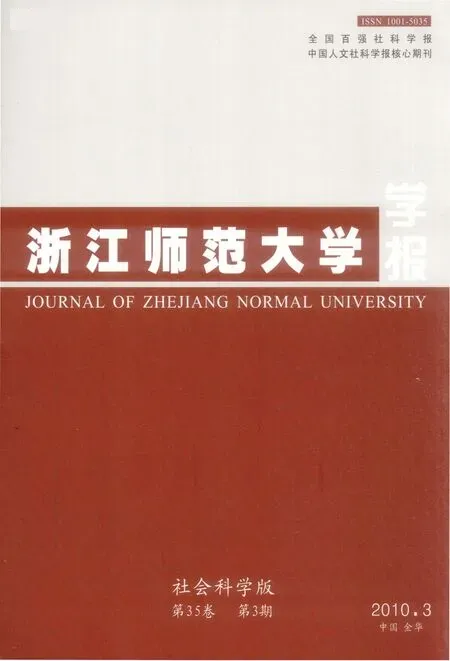印度两大史诗的活态考察*
胡吉省
(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外贸学院,浙江金华 321002)
印度两大史诗的活态考察*
胡吉省
(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外贸学院,浙江金华 321002)
印度两大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艺术。艺人说唱具有即时即型性。写定本的固定作用,导致活态艺术的消逝而成为标本。线性的起始与终点,消融于原始意识、集体意志之中。史诗及其说唱,规模在于情景,其“原始”性,在于艺人自我意识的消磨和群众的集体参与、迷狂。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史诗的艺术魅力是不可企及的。
史诗;即时即型;坐标考察
史诗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势必有时序的起止。而作为活态的集体创作、集体流传,表现在艺人说唱上,具有即时即型性。写定本的固定作用,导致活态艺术的消逝而成为标本。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其魅力则是不可企及的。
一、线性的起始
史诗的创作、写成和流传,是个动态的过程。散落各地的短歌、短的叙事诗和赞歌,必定是史诗的起始状态,燎起史诗烈焰的星星之火。但在伶工代代口耳相传的歌吟中,时有增删。长年累月汇聚成史诗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短歌涌现、加入。即使熔铸为“善书”以后,在没有用文字记载为文本之前,仍有变数。史诗作为“伶工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乃是动态的抑或活态的、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然而这个动态的抑或活态的事物,终究有个形成和存在的过程,也就势必具有可以追溯的线性时序。
季羡林先生说:
有没有一个“原始的”《罗摩衍那》呢?从理论上来看,当然是应该有的。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只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都有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原始的”什么什么。象《罗摩衍那》这样的作品,尽管被很多学者称作“伶工文学”,原来只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写定本;在传承过程中,你加上一句,我加上一句,你删掉些什么,我删掉些什么,时间悠久,变化万千;但是,长江大河,始于滥觞,《罗摩衍那》也必然会有一个开端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个“原始的”《罗摩衍那》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是“真正的”、“绝对的”“原始”《罗摩衍那》,那恐怕只有天晓得了。[1]23
探究“原始”的史诗,我们都会习惯性地指向线性时序,并习惯性地把它的起始源头归于最“古老”的部分。沿着线性时序探源,就会发现无论是哪种史诗艺人的说唱,每次都是汹涌澎湃的长河掀起的一组浪花而已,史诗长河即便有源头可探,源头之水也每天都是新的。事实上,史诗起始状态的那些散落各地的短歌、短的叙事诗和赞歌,和长河源头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起始状态并不是史诗内容所涉最远古的部分。在《摩诃婆罗多》中表示吉祥的颂诗里,在顶礼膜拜那罗衍、那罗和智慧女神时,规定要唱一部名叫《胜利之歌》的诗。学者们的说法是,这部名叫《胜利之歌》的诗就是《摩诃婆罗多》的核心部分。《摩诃婆罗多》里曾经写道:这部《胜利之歌》是一部历史,“它是以‘胜利’为名的历史传说”。它的第二阶段是名叫《那罗多》的阶段,其中只写了战争,还没有把一些插话包括进去,那时它只有二万四千颂,这也就是由护民仙人叙说给镇群王听的部分。诗中说“没有插话的二万四千颂叫‘婆罗多’,包括了插话的传本叫‘摩诃婆罗多’。”[2]10-11《摩诃婆罗多》的第一阶段是《胜利之歌》,更多的成分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更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门槛上,它的源头起始于人类文明的门槛。人类文明门槛上的史诗之泉,喷涌而出,向四周散射、漫溢(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类门槛上的星星之火,燃起漫延四周的烈焰),浸染古老神话乃至全部原始文化从而使之焕发活力(换一种说法就是将全部原始文化熔铸其中成为史诗生命的有机构成)。史诗之源其实就是人类文明之源,而人类从动物界进化从而走向文明门槛,也有一个线性的时序。此时序之源被彼时序之源涵盖并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追溯,以至混淆了此时序之源与彼时序之源。按照印度传统的说法,“最初的诗人”蚁垤仙人在“三分时代”,即在罗摩出生之前早就创作了《罗摩衍那》,[2]1或许便是如此。
二、线性的终点
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也必定有一个形成的终点。史诗自身的活态性变化与史诗产生的影响是两回事。《罗摩衍那》《童年篇》第二章第三十五颂说:“只要在这大地上,/青山常在水常流,/《罗摩衍那》这传奇,/流传人间永不休。”第七篇《后篇》第三十九章第十八颂说:“但有世界永远在,/我的故事将长存。”这是就史诗的影响而言的。
同时,史诗形成的终点,与后世学者的编纂,也是两回事。《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Adikavya),作者蚁垤被称为“最初的诗人”(Adikavi)。季羡林先生说,无论怎样,《罗摩衍那》在流传过程中,歌唱的伶工随时随地都会插入一些新的诗歌,也可以删掉一些。时间不同,地域不同,长短上就随之而异。等到写了出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本。最早的印刷本出现以后,可能对《罗摩衍那》的内容、语言等起了固定的作用。现在出的所谓精校本,固定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伶工文学的特点也因之而逐渐消逝了。[1]7-8史诗形成的终点似乎在于印刷本的出现,也就是史诗不再作为活态的事物而只是作为标本之时。
印刷本的史诗,最早的作者是许多学者或史诗中所称的“苏多”。《摩诃婆罗多》中的“苏多”与《摩奴法典》所说的一致,是婆罗门女子与刹帝利男子的婚生子。而在《罗摩衍那》中,“苏多”是支持刹帝利的婆罗门,其职责主要是担任帝王的御者和歌手。他们编纂史诗主要是为了颂扬自己所依附的帝王,也努力取悦于其他听众。这些既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又了解国王、贵族、武士等的政治斗争生活的自由人,其身份和性质与蚁垤不同,他们所谓编纂史诗,主要的是文献编纂和标本修理,与蚁垤说唱史诗是两回事,可以说“苏多”只是继承了蚁垤的遗产。
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门槛上的产物。“门槛”本身是一个过程,规定了史诗的线性时序。而史诗的线性时序又不等于“门槛”的线性时序。史诗的起始点在“门槛”坐标上,是难以测定的。史诗起始的喷涌性、散射性,史诗形成的燎原性,都基于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随着集体意识的瓦解、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等等,史诗也就失去了生产的土壤。因而,史诗在人类文明门槛上诞生,可以说是一种“爆发”。“门槛”的终界,应该也就是史诗形成的终界。跨越了文明门槛之后,便不再可能产生新的史诗,而只能是原有史诗的继续流传。行走于“门槛”和文明社会之缘的民间艺人的熔铸本,则是史诗形成的标志。
行吟歌手,即季羡林先生所谓伶工,藏语称“仲堪”,到处游行采撷、吟唱,边整理边传播,边传播边收集,口耳相传,形成一定规模后,教给自己的弟子,弟子们又会有自己的本子。事实上,形成一定规模,就是史诗的形成。同样,印度《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传说是毗耶娑,他有五个弟子,每人都有自己的本子。但是传下来的只有一个本子,这就是毗商波耶那本,据说是由罗牟诃沙那苏陀和他的弟子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据说只有两个弟子罗婆和俱舍。他把《罗摩衍那》教给他俩,他俩就到罗摩朝廷上去唱。后人又编了一个故事,说罗婆和俱舍本是罗摩的儿子,这个故事被写成了晚出的《罗摩衍那》的第一篇《童年篇》和最后一篇第七篇《后篇》中。[1]7无论弟子多少,无论弟子们的本子如何百花齐放,但是都不会改变毗耶娑、蚁垤史诗的主干。“毗耶娑”、“蚁垤”、“荷马”等等,是集体约定俗成的确认史诗形成的符号。他们的本子,就是史诗形成的标志。而他们的本子和弟子们的本子,都是艺人说唱史诗即时即型的体现而已。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本子,一旦留下文字记录的文本,便是史诗标本中的一个、化石中的一块、照片中的一张。由此说来,史诗形成的终点,如同史诗的起始状态,也不是固定的一点,而是多点多样的。
伶工在说唱史诗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会插入一些新的诗歌,他们是传唱者、创作者、收集者、整理者,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媒介,是口耳相传的渠道。当一个史诗作品被写定,口耳相传的动态被凝固,活态的物体成为标本,伶工文学的特点也因之逐渐消逝了。无论怎样解释“艺术生产”,史诗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原本是动态的、集体的、全民族的情感涌动,不是个人独立的面对客观世界思考的成果。史诗的“作者”,决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生产”的作者,只不过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代表而已。季羡林先生说,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材料或根据来证明蚁垤确实存在,他确实是《罗摩衍那》的作者。反过来,我们也还没有可靠的材料或根据来证明蚁垤并不存在,他不是《罗摩衍那》的作者。如果同《摩诃婆罗多》和它的所谓作者毗耶娑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摩诃婆罗多》内容庞杂,新旧并陈,内容和文章的风格都不统一,而作者又名为“扩大者”,可以断定,毗耶娑决非《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但是,《摩诃婆罗多》除第一篇和第七篇外,内容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是统一的,如果说它有一位作者,而这位作者就是毗耶娑,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讲得通的。那么,蚁垤就确实是《罗摩衍那》的今天我们理解的这样意义的作者吗?那也是不可能的。在《罗摩衍那》流传演变的过程中,蚁垤也只能像古希腊的荷马那样是一个伶工,他可能对于以前口耳相传一直传到他嘴里的《罗摩衍那》做了比较突出的加工、整理工作。使得这一部巨著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得到了较大的统一性,因此他就成了“作者”。在他以后,《罗摩衍那》仍然有一个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1]10不过,蚁垤的传本确实是《罗摩衍那》形成的标志。蚁垤的传本,只要进入说唱,在不同的弟子或其他什么艺人仍会有变数,但这属于后来长期流传中的演变,都是说唱史诗即时即型的呈现。史诗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口头艺术,它的生命存在于集体意识、集体意志之中,它的形成,作为活态的口头艺术,原本却是无形的,却也得到集体的感知和认同,以“毗耶娑”、“蚁垤”等称号标识。史诗的形成的终点,是史诗不再作为活态的事物而只是作为标本之时。史诗已经熔铸为“善书”却由于流传的多样性,致使史诗形成的终点不以关合为一点为标志,而以散漫多点为特色。
三、规模的度量
史诗演变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长。这一规律,或许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最原始的并不一定就是比新版的短。季羡林先生认为歌词可长可短,完全取决于当时听众的反映。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也就是这些诗被看成是“善书”的时候,这些诗就用文字记载了下来。随着地区的不同,使用的记载手段、字母等也不同,长短和内容也就逐渐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不同伶工家族写成的定本也随之而异了。季羡林先生的议论,参照藏族史诗《格萨尔》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格萨尔》主要依靠说唱艺人在民间的口头传播,以藏、蒙两种文本和藏、蒙、土、纳西等民族语言的说唱形式流传为主。在国内流传于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间。这部世界上最长史诗的发祥地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在藏族地区流传最为广泛,民间有“每一个藏族人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的谚语”的说法。
根据中国佛经译文,我们甚至也可以提出一点有关《罗摩衍那》发展演变的设想。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第五卷第四十六个故事同罗摩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这里是舅舅抢夺王位,是一条龙把王妃劫走这两点而已。但是没有提罗摩的名字以及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的名字。补充这一点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杂宝藏经》第一卷第一个故事,叫做《十奢王缘》,在这里提到十奢王 (十车王),提到罗摩,提到罗漫(罗什曼那),提到婆罗陀 (婆罗多),提到灭怨恶(设覩卢祗那)等等,并且提到国王的几个夫人。婆罗陀的母亲是第三夫人。她要挟国王废罗摩而立婆罗陀。结果罗摩被流放十二年,终于复国为王。这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王妃(悉多),没有猴子,也没有罗刹或龙。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就同《罗摩衍那》完全一致,连那些细节都无不吻合。因此,如果我们假设,上面这两个故事原来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后来,在发展演变的某一个阶段上,两个故事合二为一,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罗摩故事,不是完全合情合理吗?[1]26
我在这里还想提出另一个假设。唐玄奘译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第四十六卷里说:“如《逻摩衍拏书》有一万二千颂,唯明二事:一明逻伐拿(逻波那)将私多(悉多)去;二明逻摩将私多还。”根据这个记载,当时的《罗摩衍那》只有一万二千颂,而今天通行的本子则约二万四千颂,是当时本子的一倍。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一、从唐朝到现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罗摩衍那》的长度增长了一倍;或者二、《罗摩衍那》有两个本子,一长一短呢?这个问题只是在这里提一提,如何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1]26-27
季羡林先生的假设,或许就是伶工们根据说唱时的现实需要留下的选本而已。扎巴生前自报能唱42部《格萨尔》,玉梅自报能说 70多部,而老艺人桑珠自报能说近百部,才让旺堆自报能说唱 148部,达哇扎巴自报能写 120部。但是每位艺人每次说唱都只能是某个片段。因听众们要去干活,或登程赶路,只好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向艺人告辞。据扎巴老人说,因为篇幅太长,他讲了几十年,每次都只能讲几段最精彩的部分,顶多半部或多半部,很少从头至尾完整地讲一部。从说唱《格萨尔》故事的情形来看,艺人或在庄园里,或在田间地头,或在辽阔的牧场,或在贵族家的高楼大院,或在贫苦农奴家低矮的小屋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也不分春夏秋冬、风暴雨雪,都可以表演。固然艺人们说唱的内容一般没有什么限制,自己想讲哪一部、最擅长讲哪一部,就讲哪一部,同时也要看听众或施主的爱好和需要。季羡林先生的假设情况,或许也有这样的可能:艺人根据不同需要不同环境下留下的史诗片断,或者同一个艺人留下的详本、略本?
艺人的说唱,都有即时即型的性质。如果说史诗如同长江大河,艺人的每次说唱都是随时激起的浪花;如果说史诗有如游龙,艺人的每次说唱都是游龙随时呈现的姿态。而史诗某部分的说唱及其传本,则类同于“特写”镜头了。因此,活态的史诗,是民间集体智慧、集体理念、集体生活的显现,其生命并无童年、青年、老年的刻痕,其形态也没有昨天简陋、今天壮实、明天枯萎的周期。甚至于没有今天艺人说唱是新本而昨天说唱的就是相对“原始”的界域。而所谓传本,也只不过是瞬间定格而已。我们今天阅读的史诗作品,是一段被凝固了的历史,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标本。
四、魅力的界定
艺人之于史诗,需要一定的媒介触动才能入梦、顿悟、掘藏,而史诗的真正作者和传承者是民间的集合群体。艺人的说唱,实质上是民间集合群体创作、流传史诗的导入者、触发者,艺人并不能创作出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史诗作品。我们现在从《格萨尔》的说唱状况来看,不同的艺人,却唱出了、写出了大体相同的《格萨尔》故事。如果不是这样,各人唱各人的,各人写各人的,各不相同,互不相关,也就不成其为从远古流传至今的英雄史诗,在文学史上也失去了“活化石”的价值和意义。在民间,凭着自己的艺术天赋和丰富的生活积累,能编、能讲许多故事、号称“故事大王”、“故事背篓”的故事家,也不乏其人。但是,没有专门学习、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能讲出大体相同的故事,吟诵同一部史诗,而且不是几百行、几千行诗句,而是几万行、几十万行诗句,是几部、十几部、几十部厚厚的书。虽然每位艺人的每次说唱,几乎效果不同,但是其故事主干都是集体公认的标准。如果从这个角度剖析,艺人的每次说唱都是新鲜的,即时即型的,故事主干则永远都是“原始”的,因而所谓最“原始”的,就是效果最好的说唱;所谓最“原始”的史诗作品,就是原始意识、集体意志最浓烈的,其一是“托梦”艺人的作品,其二是“顿悟”艺人的作品,其三是“掘藏”艺人的作品,等等。[3]
西方的梵文学者,后来也有受了西方影响的印度梵文学者,他们的原则是越古越好,《罗摩衍那》第二篇至第六篇比第一篇和第七篇要好,因为它们古。他们幻想中的“原始”《罗摩衍那》比第二篇至第六篇更好,因为它更古。但是老百姓却偏偏喜欢那不古也真的篇章,这真叫做没有办法。[1]24,25
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如同比史诗更为原始的活态的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神话,神话中“图腾、天体神、与人同形同性之神,前后依次产生,但并不意味着互相代替,而是‘互渗’始终。原始意识作为社会心理结构和个体结构崩溃是文明社会以后的事。因此,从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到祖先崇拜,确实有一条线性的进化过程,而过程本身则是互相粘附、交织、融合,尤其是,祖先崇拜是自我意识反思的产物,反思又将进化的线性过程加以追溯。例如,我们现在所见到并据以考察研究的图腾神话,实际上并非最初的原始形态而是流传演变到人类文明门槛上的纷繁复杂的混合体”。[4]史诗的创作、写成和流传,是个动态的过程。然而这个动态的抑或活态的事物,既然有形成和存在的过程,也就势必具有可以追溯的线性时序。这种时序,却并不呈现前后的替代、否定之否定从而循环往复,而是在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集体流传过程中,消弥了史诗起始源头的具体标示;史诗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引起的后世对于史诗的依附和追溯,又模糊了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的创作终点。
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5]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说史诗是艺术生产还未作为艺术生产出现时产生的形式。无论如何解释“艺术生产”,史诗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是肯定的。恩格斯则指出:“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6]至少,史诗是人类文明门槛上的特产和遗产。
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史诗原本是原始意识状态下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口耳相传的动态的抑或活态的艺术,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个人创作所无法比拟的。所谓最“原始”的史诗作品,就是原始意识、集体意志最浓烈的;所谓最好的史诗说唱艺人,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集体的意志,以集体的潜意识影响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各阶层人物。艺人原创的过程就是个人化解为集体的过程,个人的自我意识消磨得越干净,其创作才能越接近“原创”,而艺人的“原创”,只能在说唱时群众的集体参与和迷狂中实现。[3]史诗的集体性即全民性、全人类性,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高度融合性从而反映社会的全面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个人创作或阶级社会所谓的“集体创作”所不可企及的,诚如马克思所说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
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艺人说唱的即时即型性,决定了史诗作为伶工文学的动态抑或活态,以及说唱艺人消磨个人自我意识的努力和群众参与的迷狂。史诗有可能随着说唱艺人的逝世而导致某种魅力的消失;有可能随着群众基础的丧失而导致说唱艺人的不可作为;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史诗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史诗产生的许多文化事象也在随之消失,导致某个民族突然遗失原始史诗。而史诗的历史范畴性、说唱的即时即型性,导致了现代社会对史诗“抢救”的不可能性。现代社会对于史诗的“抢救”,即便是对说唱艺人的录音,也只能是比较“原始”的艺人遗音,用声音制作的活态史诗的标本;如果是原封不动的文字记录,则是用文字制作的活态史诗的好标本;如果有人按照现代理念“整理”史诗艺人留下的遗产,那就不是“抢救”而是摧残、破坏了。
[1]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2]拉·斯·赫拉.摩诃婆罗多[M]//季羡林,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胡吉省.试论史诗艺人原创的迷狂原始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1):128-131.
[4]胡吉省.死亡意识与神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4-105.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4.
[6]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
(责任编辑 周芷汀)
A Survey of the Oral Trans mission of the T wo Ancient Indian Epics
HU Ji-sheng
(Jinhua Radio&Television University,Jinhua321002,China)
As a historically culturalphenomenon,the t wo epicsof ancient India,Mahabarata and Ramayana, belong to the categoryoforal art,characterized by i mprovisationalperfor mance.The birth ofwritten texts has resulted in the fossilization of that for m of art as an artistic speci men.It should,nonetheless,be noted that both 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the t wo epic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ri mitive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will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herein.The attractiveness of epics and their perfor mance lies in the scenario and at mosphere they created,in their“pri mitiveness”,and in the carnival participated in and enjoyed by both the actors and the audience.As a historical heri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epics are second to none in artistic char m.
epics;i mprovisational;a coordinate-method survey
I109.9
A
1001-5035(2010)03-0049-06
2010-03-02
胡吉省(1960-),男,浙江金华人,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外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