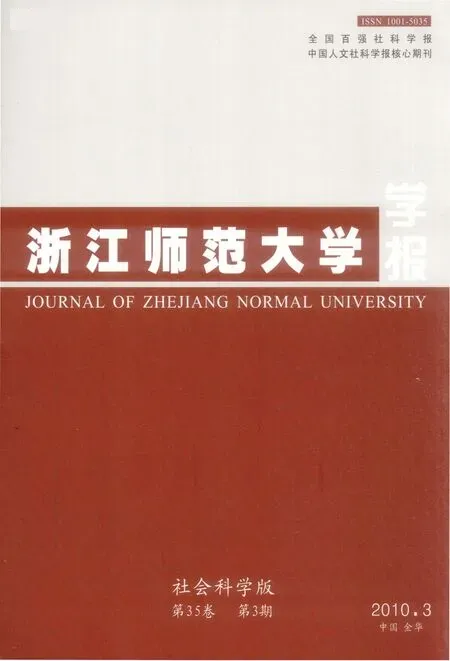从“戴着脚镣跳舞”到“自为的存在”*
——关于译者主体地位演进的哲学思考
唐小田, 唐艳芳
(1.吉首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从“戴着脚镣跳舞”到“自为的存在”*
——关于译者主体地位演进的哲学思考
唐小田1, 唐艳芳2
(1.吉首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从哲学层面对西方翻译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指出西方传统翻译观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后现代语境下传统译论解构的必然性。这种解构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从长期遭受压制、屈服于各种外部权力话语,跃升至与作者和原文本平起平坐乃至超越后者的地位。西方翻译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与哲学思潮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联。
形而上学;后现代语境;译者主体
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与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基本上是相呼应的,但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随着哲学研究在 20世纪的语言转向,二者之间的同步特征越来越明显。翻译理论之所以能够摆脱数千年传统的桎梏,很大程度上是同哲学领域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作一反思,论证传统翻译观的形而上学本质,并探讨译者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以及后现代语境下主体获得解放的必然性。
一、西方传统翻译观的形而上学本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形而上学对此的看法始于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的“洞穴”说,认为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真正的人和影子的关系一样,虽然有产生“影子”的存在,但人的思维不可能彻底把握存在。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存在是超越现象的,而人的思维只能把握住现象,因而对于存在,人们只能猜测,但不可能真正认识。换言之,思维能够把握的充其量只是存在的投影。这种单向的认识很容易导致不可知论,使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努力 (或曰能动性)遭到贬抑和抹杀。但由于形而上学并不否认客观存在,因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它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并与同时代的辩证法思想一道成为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 19世纪中叶西方现代哲学全面拒斥形而上学,才逐渐走向式微。
人类的翻译实践以及对翻译的认识,在时间上虽然先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但从一开始就有着哲学的特征。早期的翻译主要发生于宗教领域,这一点中外皆然,但宗教在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我国,这就使得西方早期的译论很难摆脱神秘主义色彩。对宗教的顶礼膜拜使《圣经》的原文希伯来语成为“神的声音”,其形式被认为与意义同样神圣,除了具有“通神”天赋的神职人员可以作一些口头阐释之外,绝不容许任何篡改,因而当时也就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这种以不可知论突出宗教神秘感和威严性的做法,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宗教的敬畏心理,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宗教的进一步传播,而后者则是宗教机构所不愿意看到的。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禁锢的冰山开始消融,于公元前 3世纪出现了圣经早期的希腊语官方译本《七十子译本》(The Septuagint)。当时所谓的 72位学者各领“神谕”、彼此译文一字不差的说法,本质上不过是以新的不可知代替旧的不可知,以便树立译本在新语境下的神学权威。《七十子译本》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牢固地确立了它自身作为“一切翻译实践和翻译思考的精神母体”的地位,并使翻译和翻译研究两千年来难以摆脱追求绝对真理的“忠实”情结。[1]因此,西方翻译研究的哲学基础,从一开始就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体,其核心思想就是文本意义 (亦即哲学上的存在)超越于思维之外,只有具备与神对话能力的贤哲们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西方宗教文本翻译所确立的这种形而上的标准,寄生于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并随着中世纪基督教统治地位的强化而如日中天,对后世翻译的方法论和评价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集音、形、义于一身的、独特而复杂的系统,因此语言之间的转换从一开始似乎就面临着何者优先的难题,而 20世纪之前关于翻译的争鸣和探讨也大多是围绕着去留取舍的标准与原则等展开的,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直译与意译的旷世之争。但假如从哲学的视角来观照西方翻译史上的种种思潮和论争,就会发现它们共同的形而上学立论基础。也就是说,无论持哪一种翻译观,人们都相信原文某个方面(音、形或义)的“存在”是确定的。比如,持直译观者就认为原文的形式必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就会把重心放在形式特征(如句式结构、语音特征等)上,而将语义等要素置于次要的位置。由于语言之间在音、形方面的差距比较直观,随着翻译史上著名的“阿诺德 vs纽曼”论战中阿诺德意译观的取胜,以语义为核心的通顺翻译观 (“翻译即译义”)在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直接导致了翻译后来遭到普遍贬抑并走向边缘化的结果。[2]29但这只能说明主体思维对客观存在的某一方面的认识获得了加强,西方传统译论在本质上并未摆脱形而上学的镣铐,而且,翻译研究之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走不出直译意译二元对立的怪圈,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其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 20世纪解构主义的“意义消解”才告终结。可以说,正是哲学研究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才彻底击溃了传统翻译研究赖以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使 20世纪的西方翻译理论焕发了新的活力。
二、后现代语境下传统译论的解构
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传统的“科学—哲学—世界观”一体化结构的动摇以及社会思想领域的“认同危机”,以拒斥形而上学为重要特征的实证主义登上了哲学的历史舞台。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将人类理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和科学阶段(实证阶段)。在孔德看来,形而上学阶段只是一个解体性的变化和过渡阶段,因为“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3]6差别仅仅在于它并不运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所以,“归根结底,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3]8由于形而上学的这种绝对性和不变性特点,孔德认为它对于“究极本原”的探求是绝对办不到的。赫胥黎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指出形而上学属于不可知之域,因为对世界本原、存在、实在问题的探究本身是超出经验之外,无法回答的,哲学不应越出可知的经验去探究形而上学的问题。[4]卡尔纳普则通过语言表达的逻辑分析来尝试消除形而上学,他将语言的作用区分为表达作用和表述作用,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如同抒情诗一般,只有表达作用而无表述作用,只可表达一时的情感,但欠缺经验和认知上的意义。“形而上学命题的非理论的性质,本身不是一种缺陷;……危险在于形而上学的这种欺惑的特性。它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在给予知识;而实际上并不如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5]后现代性开端时期的里程碑式人物尼采更是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认为不可能有永恒的真理,这就从根本上击溃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尼采对生命意志 (亦即权力意志)的阐释,也将哲学研究的范围从外部世界和知识转到了价值观的研究。
西方哲学的发展史由三个重要的阶段构成:古代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近代关注的是认识论,到 20世纪则转为语言论。[6]哲学的语言转向,同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从认识论到句法语义分析的转向(简称语义学转向),以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从句法语义分析到语用分析的转向 (简称语用学转向),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塞尔等为代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至此虽已告土崩瓦解,但人们对“存在”的认识和探索在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过程中却始终挥之不去,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可谓道出了语言研究的哲学情结以及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必然性。事实上,20世纪语言学及翻译研究的长足发展,一方面是哲学研究对语言的关注和转向的结果 (哲学研究对句法和语义分析的关注导致语义学研究的发展,对语用分析的关注则带来了语用学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则又为哲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是以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与其说是语言学理论,不如说是哲学理论 (或哲学家的语言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虽然植根于语言学,但却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哲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从批评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所建立的解构主义理论,同样具有哲学的性质和价值。
解构主义理论在后现代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哲学思想的源流来看,它应当是继承了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和否定。巴特和福柯的“作者死亡”(乃至“文本死亡”)的宣言,与尼采对永恒真理的否定可谓一脉相承。对于翻译研究领域来说,解构主义不啻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因为它将传统翻译研究赖以安身立命的“意义中心”这一形而上学的假设前提击得粉碎。意义的消解不仅来自巴特、福柯、德曼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更有德里达这位 20世纪解构主义大师的贡献。德里达从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意义转换入手,提出了意义“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认为意义不仅在原文本里就有不确定性,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也由于时间上的“延滞”(deferring)和空间上的“异化”(differing)而变得更为不确定。[7]从本雅明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德里达的“延异”、德曼的“来世”(afterlife),到韦努蒂的“抵抗”(resistancy),解构主义从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对传统翻译研究一系列方法论和评价体系的拆解和否定,并将 20世纪的翻译研究从现代语言学时代推进到了后现代文化学研究时代。尽管后现代理论总体上看重的是人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似乎并不特别关注个人的主体性,[8]但对于翻译研究领域而言,一旦原作者和文本被确定为不在场,长期遭受压制和禁锢的译者主体性就会大放光彩,因为传统翻译规范对于译者的束缚,主要就是通过这两者实现的。因此,后现代语境下译者主体的解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三、译者主体的解放
形而上学重视对“究极本原”的孜孜探求,强调存在相对于思维的不可知性,这实际上也是对主体的排斥和轻视。传统翻译研究以此为基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译者主体长期遭到压制。德莱顿在讨论他的翻译三分法时将逐字直译(metaphrase)比作“戴着脚镣在钢丝绳上跳舞”,[9]原本是讽刺其为愚不可及的做法,但反观整个 20世纪之前的情形,译者不幸恰恰就是钢丝绳上戴着脚镣的舞者。形而上学支配下的翻译过程,在罗宾逊看来就是译者向自身理性意愿之外的各种力量、尤其是原作者及/或原文本屈服、妥协的过程。[10]193对译者主体的压制早期来自原作者和文本,在西方宗教鼎盛时期,以宗教的权威制约译者的主体性,迫使译者亦步亦趋地紧贴原作进行逐字对译,成为作者和原文的奴仆,并造成译文佶屈聱牙。对于不愿意就范的译者,即以种种手段进行打压甚至迫害。当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法国翻译家多雷的“一言获罪”——他在翻译柏拉图的一篇对话时,因为添加了人死之后“万事皆空”(nothing at all)这一原文没有的内容而被指控亵渎上帝,于 1546年被处以火刑,成为翻译史上继廷代尔之后又一位因为“误译”而殉难的译者。[2]22随着中世纪神权统治的终结,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等洗礼,逐步强大起来,对非宗教文本及他者文化译介的需求大大增加。此时对译者主体的约束又从原文为中心这一极端走向了译文为中心的另一极端,要求译文通俗易懂,不带任何翻译腔。韦努蒂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指出 20世纪前的西方翻译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译者的“隐身”(invisibility)史,读者看到的大都是流畅通顺的“透明”译文,从而失去了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同时也使源语文化进一步边缘化。[11]韦氏提倡的“抵抗”式翻译策略,从表面看是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但由于这一策略是通过彰显译者主体地位的途径来贯彻的,因而可以看作是继其他解构主义倡导者之后为译者主体解放树立的一座里程碑。
译者主体的这种解放,完全可以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体系中找到理据。胡塞尔在其代表作《逻辑研究》一书中,从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概念出发,强调人的意识是一种主动向外投射的活动,认为哲学研究需要改变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他指出,由于意向活动很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意向对象的性质和意义,因此重要的不是由客观对象出发研究,而是要从现象学上的还原入手。对于翻译研究领域来说,这实际上是为译者的主体性提供了合理性辩护,也为当代描述翻译学理论及阐释学理论对译者主体行为的解释奠定了哲学基础。20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萨特在其 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将存在区分为自在的存在 (être-ensoi)和自为的存在 (être-pour-soi),指出前者就是形而上学所谓的“存在”,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后者则是主体向外投射的趋势,即奔向自在的存在,正是后者才使自在的存在有了意义。自为的存在不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面貌的存在。[12]在萨特看来,人注定是自为的存在,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也正是在主体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才能赋予对象以意义。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1927年提出的“一切研究……都是此在 (Dasein)的一种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性”的延伸和阐发,[13]7因为二者本质上都是对主体在反映客观世界方面的作用和地位的肯定与重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之所以能完成从客体 (翻译文本及其社会文化因素等)研究向主体(即译者)研究的重大转变,与哲学研究领域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以当前翻译研究领域对译者主体地位的关注程度,似乎完全可以套用海德格尔的话:“一切翻译研究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支配者状态上的可能性。”
但主体性犹如一柄双刃剑,过度张扬则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和唯我论的泥淖。萨特在肯定主体作为自为的存在的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12]当代译者主体性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罗宾逊认为:“译者并非取作者而代之,而是成为与原作者非常相似的一位写作者,但仅仅是因为二者都是利用自身语言和现实世界的经历进行写作,方式十分近似。”[10]3这就说明,彰显译者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翻译的操作过程,因为即便作者死亡,其作为对象主体的地位和影响依然存在,而且出版商和译文读者作为一个更大的对象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对译者的主体性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译者个人主体地位的提升,“交互主体”也是其关注的内容之一。所谓“交互主体”(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是指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它既包括多元主体性,也意味着主体性是在与其他主体对象之间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发生的,因而其实质就是主体间的共在。[14]交互主体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在于避免由于主客二元对立导致的唯我论倾向,这与形而上学以客体的不可知性排斥和压制主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翻译而言,交互主体性意味着在承认译者主体作用的前提下,探讨译者作为自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 (In-der-Welt-sein)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In-Sein)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13]146可见,交互主体性并非否定主体性、令翻译研究重回形而上学的老路,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
四、结 语
从“戴着脚镣跳舞”到实现“自为的存在”,译者主体地位的这一历史演进,既是人们在翻译领域探索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飞跃,也与后现代理论对主体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除了直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和文化转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哲学层面来关注和思考译者的行为,从而大大提升了译者主体的地位。这种对主体的重视,也是翻译研究的哲学转向的重要环节,预示了其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
[1]许钧.翻译的哲学与宗教观[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7-8.
[2]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3]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托玛斯·亨利·赫胥黎.方法与结果[M].谭辅之,译.上海:辛垦书店,1934:213.
[5]鲁道夫·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句法[M].傅季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2-13.
[6]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4.
[7]Davis K.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FLEP, 2004:14.
[8]凯思林·希金斯.尼采与后现代的主体性[M].王晓群,译//汪民安,陈永国.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98.
[9]Baker M.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New York:Routledge,2001:153.
[10]Robinson D.Who Translates?: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M].New York: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1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54.
[12]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2.
[13]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4]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16.
(责任编辑 钟晨音)
From“Dancing on Ropeswith Fettered Legs”to“Être-Pour-Soi”: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tatus
TANG Xiao-tian1, TANG Yan-fang2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Jishou University,Jishou416000,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Nor 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 present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Probing into the metaphysical essence of traditional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it proves the inevitable deconstruction of the latter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One of the outcomes of the deconstruction,it argues,is the unprecedented emancipation of the translator,who,having been subject to various externalpowers in the history,finds him/herself equalwith and even superior to the original author and/or ST.This development of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t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n the last century.
metaphysics;postmodern context;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059
A
1001-5035(2010)03-0092-05
2010-03-10
唐小田(1970-),男,湖南郴州人,湖南吉首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育学硕士;唐艳芳(1971-),男,湖南永州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