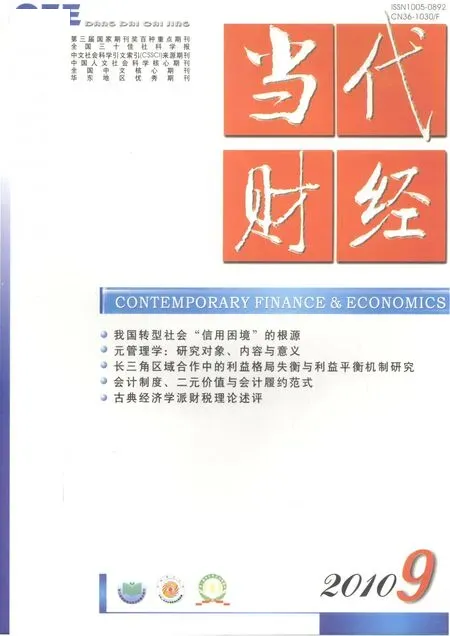环境税“双重红利”论及其启示
兰相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环境税“双重红利”论及其启示
兰相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双重红利”论认为,征收环境税可以实现“效率红利”、“绿色红利”的双重目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上“双重红利”论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一些争论和质疑,实践上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环境税所产生的“效率红利”与“绿色红利”相比也难以实现。虽然“双重红利”论在我国的存在具有某些约束条件,但是,可以借鉴“双重红利”论为我国环境税制提出改革思路,即立足我国实际,将环境税制改革与整体税制改革相结合,以实现既促进改善环境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红利”目标。
环境税;双重红利;效率红利;绿色红利;税制改革
环境税作为一种市场管制工具,其优点和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环境税的研究日益丰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不断深入,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Double Dividend Theory)是近年来环境税效应研究的新成果,但它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和争论。如何评价这一理论,对一国设置与实施环境税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改革与完善整体税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这种“双重红利”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双重红利”论的有益成分,考察“双重红利”在我国的存在性以及该理论的适应性。
一、征收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双重红利”理论
随着全球性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税收制度的“激励扭曲”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正如《1993年欧盟增长、竞争与就业白皮书》指出:“我们正在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对人力资源使用存在不足”。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20世纪90年代,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综合性税制改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初步尝试,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之一。Bovenber(1999)和Goulde(1995)很好地解释了“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开征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目标:[1]一方面开征环境税,可以将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实现内部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环境状况改善,有效地控制污染,即环境目标,也称为“绿色红利”。另一方面,开征环境税之后,可以利用其收入来降低现行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增加更多社会就业等。这有助于实现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目标,即非环境目标,亦称为“效率红利”。总之,要取得环境税的“双重”效应,必须在税收收入循环收益和经济损失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环境税有关“超额收益”的文献资料颇多。这些可以视为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最初萌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Pearce首次提出用炭税(carbon tax)收入来减少现行税收的扭曲效应,因而这种税收间接地促进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税收中性的改革可以在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获取额外益处,征收环境税随之就会产生这样的“双重红利”。[2]“双重红利”概念的提出随后激发了众多环境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围绕环境税对税制的效率影响这一主题论证“双重红利”假说是否存在,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论。事实上,90年代欧盟进行的环境税改革主要倾向于实现环境税的“第二重目标”。与此同时,许多环境经济学家从多角度力求对环境税“双重红利”展开深入研究。至今为止,对环境税受益的阐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弱式双重红利论”、“强式双重红利论”以及“就业双重红利论”。[3]
(1)“弱式双重红利论”,是指通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税收收入,用来减少原有扭曲性税收,降低超额税收负担。Tullock(1967)最先提出这种以环境税收来替代其他税收的思想。此后,欧美环境经济学家(Reptto,1991;Pearce,1992)进一步发展了此观点。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所得税是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所得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征收所得税通常会抑制人们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产生超额税收负担。所以,降低所得税的呼声很高。在实践上,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实行减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为维持较高的公共支出水平,必须有其他收入来补充所得税减少的收入。基于此,一些环境经济学家提出,开征环境税收一方面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这种税收收入可以弥补减少扭曲性税收的不足,实现“双重红利”的目标,因而环境税改革是一种两全其美之选择。
(2)“强式双重红利论”,是指通过环境税改革,可以达到提高现行税制的税收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增加社会福利是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而界定福利水平必须利用各种综合性指标来测定,其中,改善环境是其重要指标。环境税改革既可以通过减少扭曲性税收的方式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提高税收效率,同时也可以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的整体福利水平。
(3)“就业双重红利论”,是指环境税改革之后,环境税既可以增加就业,又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这种观点认为,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减少与劳动力相关的税收,提高雇员的税后收入,从而减少雇主的劳动力成本。所以,环境税既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从而达到增加就业的目的。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环境税改革进程中,受“双重红利”理论的影响,坚持了税收中性化倾向。环境税中性改革从两个方面推进:①一方面,从微观层面上针对纳税人,保持税收总体负担的中性,增加环境税,降低诸如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另一方面,从宏观上保持财政收入的中性。例如,随着污染的逐步治理,环境税随之减少,这就要从其他税种中寻找税源。随着环境税的增加,这就要随之降低其他税收的水平。
二、一些经济学家对环境税的研究和发达国家的环境税实践
对于“双重红利”理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绿色红利”的存在性,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赞成“弱式双重红利”可能存在。至于“就业双重红利”和“强式双重红利”,经济学家存在很大争论,理论文献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结论。
Bovenberg和R.A.de Mooij(1994)最先对“双重红利”假说提出质疑。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这两位学者提出“双重红利”的两种效应:“税收交互效应”(tax-interaction effect)和“收入循环效应”(revenue-recycling effect)。[4]税收交互效应是指对污染性产品征收环境税,引起污染性产品价格上涨,降低劳动所得的实际购买力。如果劳动供给弹性为正,那么劳动供给就会减少,进而腐蚀收入循环效应。收入循环效应则是指政府将环境税收入用以降低劳动所得税后,使得失业率降低,劳动者的供给意愿增加。这里暗含着同所得税一样,征收环境税就会产生扭曲效应,很可能使原本预期的“双重红利”不存在。由此,Bovenberg和R.A.de Mooij认为,如果环境税的收入循环效应小于税收交互效应,则就业会减少,“双重红利”就不存在;如果环境税的收入循环效应大于税收的交互效应,则环境质量改善,就业增加,于是,“双重红利”假说成立。这一重要结果已成为一个“焦点”,并引起了对“双重红利”假说的种种质疑。
为保持收入中性,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4)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在引入环境税的同时调整劳动力供给税收。两位学者认为,来自环境收益的效用降低了,这说明在模型中没有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5]Parry(1995) 直观地解释了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Bovenberg和R.A.de Mooij的最优税结果。他通过论证认为,在次优框架下与最优框架相比,进行环境税改革的效应会有两个显著变化。第一,通过一般均衡交互作用,通常会放大污染税的效率损失。实际上,开征环境税一方面会影响污染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会影响如劳动力市场等其他市场。例如,对家庭征收污染税会引起清洁产品的消费替代污染产品的消费,还会降低实际工资,这将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进一步恶化劳动力市场上已存在的税收扭曲。这种效应被称之为“税收相互效应”(tax-interdependency effect)。第二,环境税收入并不一定以一次总付税(a lump-sum fashion)的方式循环,但是,可以用来减少已经存在的扭曲性税收。这将会提高作为筹集收入工具的税收效率。这种效应被称之为“收入效应”。Parry还认为,税收相互效应在可信的假设下经常大于收入效应。[6]这就说明,环境税改革将会带来正的总成本,无法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R.A.de Mooij进一步总结了当时有关环境税改革效应的一致观点,那就是“鉴于第二重红利处于争论中,第一重红利(即一个更清洁的环境)仍然是引入污染税的一个最充分理由”。[7]
从各国环境税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都进行了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目标的综合税制改革。例如,1991年瑞典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了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使得两者占GDP的比重分别从2.8%和22.5%降低到1.9%和19.5%;1996年10月英国开征垃圾填埋税,每年收入达4.5亿英镑,用来降低2%的社会保险支出;自1997年起,芬兰减少的所得税和劳动税(1997年减少56亿芬克)部分被新开征的生态税和能源税所补偿(1997年增加14亿芬克)。②但是,从这些国家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远比其他效应更为明显。2001年Bosquet利用CEG模型,对30多个OECD国家的环境税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这些OECD国家开征环境税后,从短期③和长期来看,废气排放量分别下降了6.02%和13.08%。这充分印证了环境税是改善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从开征环境税对于企业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效果来看,虽然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税收收入用来降低与劳动力和资本有关的税收,从而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和就业量,但其效果都不是非常理想,大大低于环境税开征对于削减废气排放量的预期。具体而言,在有关OECD国家开征环境税后,其就业量从长期和短期来看仅分别增加了0.77%和0.34%,企业投资水平从长期和短期来看仅仅分别提高了0.44%和0.37%。总而言之,开征环境税的“绿色红利”较其“效率红利”更易实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没有环境改善效应那样明显。
三、“双重红利”论在我国存在的约束条件与局限性
在理论上,环境税的“双重红利”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现行税制结构来看,环境税的“双重红利”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从我国税制结构来看,目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2004年所得税占总税收的19%,为近年比重最高),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基本在60%以上,所得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不是很大,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税收中所占比重也不是很大。[8]这说明我国尚不存在依靠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
(2)从我国环境保护的隐性负担来看,政府选择环境保护政策工具不仅要考虑实现环境保护目的,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实施这一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各种成本。比如,征收环境税后有可能加重企业税负,降低这种行业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所以,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开征环境税提高社会福利,应该考虑更广泛的内容。
(3)从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上看,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替代效应也不是很大。所以,环境税有利于增加就业和降低扭曲性税收的作用在我国没有明显的效果。[9]
(4)从我国环境税制的现实来看,目前大部分税种的税基、税率和税目都没有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角度来设计,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据测算,1997年和2004年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6%和7%。在环境税收比较成熟的丹麦,1997年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就达到了10.03%;2002年废气费用和治理废水费用分别为69.8亿元和71.5亿元,同年的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10]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现行税制还有待绿化。
事实上,实施环境税收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种功能权衡:一是环境税的矫正功能,二是环境税的收入功能。如果对某些劳务或商品征收的环境税具有较强的矫正能力,那么征收环境税就会改变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改善环境条件,通常会导致缩减以相关污染物为征税对象的税基,从而减少税收收入。此外,如果某种税的收入功能较强,则可能达不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四、我国环境税制的改革思路及目标定位
虽然环境税“双重红利”论对我国适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但我们可以借鉴它的有益成分,为我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一条有益思路。即立足我国实际,把环境税制改革与整体税制设计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红利”目标。
(1)我国在实行费改税、环境税改革时,应该牢牢树立绿色理念。将税负从对资本和劳动的征收最终转移到对污染和资源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征收较高的税收,就会使贸易、工业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需求。税收收入的改革将对企业总体税收负担保持不变。环境税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将其纳入到国家的税收征收体制之中。
(2)逐步开征一些环境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人经济行为,促进环境的改善,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税收手段相比,征收排污费有一定内在缺陷,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将是改革方向。污染税的计税依据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数量和浓度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状况及环境目标的变化而变动。[11]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递增或者递减,税率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另外,适当增开其他环境税种。如噪音税,可以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用于隔音设备投资;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
(3)在绿色税制改革趋势下,受环境税“双重红利”论的影响,“强式双重红利论”在一定程度上比“弱式双重红利论”更适合我国实际。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环境收费较低,同时我国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国家宏观调控日趋弱化,不存在征收环境税导致减少其他税收的客观环境。只是宏观上从财政中性来看,不必照搬国外的做法,可以根据我国实际税收负担,坚持基本保持原有税负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环境税的税负水平。对于“就业双重红利论”,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还不是主体税种以及我国独特的个人收入分配现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加之社会保障税还没有开征,因此,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就业双重红利论”至少还不适合于我国。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就业、所得税对整个税收制度影响的日益增强,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环境税所固有的“双重红利”作用将会逐渐显现出来。
注 释:
①在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改革中,经常提到环境税中性这一问题,或者称之为财政中性。即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将由其他税的减少来平衡纳税人的总体负担。
②数据引自http://www.oecd.org.2005,Database on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es.③这里的短期是指少于10年,下面OECD国家环境税的有关短期也是一样。
[1]F.J.Andre,M.A.Cardenetee,E.Velazquez.Performing an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in a Regional Economy——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Approach[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5,39(2):375-392.
[2]Pearce D.The Role of Carbon Taxes in Adjusting to Global Warming[J].Economic Journal,1991,(101):407.
[3]Goulder L.H.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the Double Dividend:A Reader's Guide[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995,(2):157-83.
[4]Bovenberg A.L.,R.A.de Mooij.Environmental Levies and Distortionary Tax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085-1089.
[5]Bovenberg,Van Der Ploeg.Environmental Policy,Public Finance,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A Second Best World[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4,55(3):349-390.
[6]Parry Ian W.H.Pollution Taxes and Revenue Recycling[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5,(29):64-77.
[7]R.A.de Mooij.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the Double Dividend[J].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2000,(viii):89-90.
[8]应 燕,江 云.就业困境的经济学分析与税收政策选择[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51-55.
[9]付伯颖.论环境税“双盈”效应与中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政策取向[J].现代财经,2004,(2):8.
[10]梁燕华,王京芳,袁彩燕.环境税双赢效应分析及其对我国税改的启示[J].软科学,2006,(1):71.
[11]周全林.我国开征污染税研究[J].当代财经,1998,(7).
Double Dividend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Tax and Its Enlightenment
LAN Xiang-ji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Hubei Wuhan 430074,China)
The“double dividend”theory holds that levying environmental taxes can realize the double goals of“efficiency dividend”and“green dividend”.However,the“double dividend”has been challenged and questioned in theory by some environmental economists ever since the 1990s;in practice,the“efficiency dividend”generated from the levying of environment tax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to realize compared with“green dividend”.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doubledividend” theory hassomerestrictsin China,itprovidessomeideasforChina’s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that is to say that we should combine the environment tax reform with the reform of the overall tax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omestic conditions,so as to realize the“double dividend”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overall tax reform,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tax;double dividend;efficiency dividend;green dividend;reform of tax system
责任编校:周全林
F810.424
A
1005-0892(2010)09-0029-05
2010-05-20
兰相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