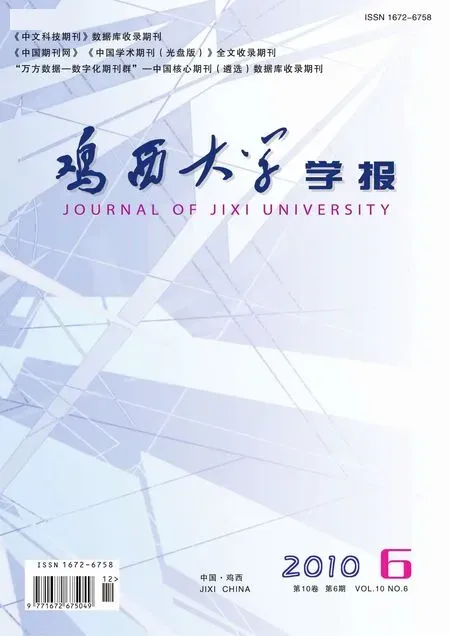梅尧臣以文为诗的特征体现
李 萍
梅尧臣以文为诗的特征体现
李 萍
梅尧臣诗歌中的以文为诗体现为意义层面的和形成层面的。所谓意义层面的以文为诗,体现在意识指向上“尚理趣,善议论”的特征,还体现在以典故入论上。形成层面的以文为诗则体现在诗歌谋篇布局的散文化上;诗题的长短变化上;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上,特别是引虚字入诗上。除用量多外,梅诗还偏爱某些虚字,如我们考察出梅尧臣自嘉祐二年以后便常用“不”“无”“莫”等否定词煞尾;最后还体现在梅诗节奏的与众不同上。
梅尧臣;以文为诗;诗题长短;虚字入诗
“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并非梅尧臣始创,自唐代杜甫开始就有了“以文为诗”的倾向,到了白居易、韩愈手中,更有所发展。梅尧臣等人承流接响,把其作为突破唐音、自成宋调的一大法门,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加以发挥,使之成为梅诗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梅尧臣的以文为诗分为两个层面:意义层面的和形成层面的。
所谓意义层面的以文为诗,指的是梅诗在意识指向上“尚理趣,善议论”的特征。与韩杜等人以文为诗的背景不同,梅尧臣处在“明道致用”的复儒思潮中,处在偏重策论的科举制度中,处在实行“台谏制”的社会官制中,处在于困顿境遇上下求索的个人生存状态中,还处在诗歌创作的学唐与变唐的关键转折点上。所以,与韩杜以文为诗的内容相比,梅尧臣更多了对社会人生及生命本体的自觉反省与哲理思考,“尚理趣、善议论”的特征体现得更突出、也更广泛,甚至到了“触处生议”的地步了:如对朝廷内部的争权斗争,对西夏与宋的战事,对官吏的欺压百姓了,甚至对生物景物等等都要议论几番。比如闲暇时欣赏年轻女子跳舞感慨议论到“老大而今莫那伊”(《观舞》),[1]看到舟人斗鸡感慨议论到“从来小资大”(《晚泊观斗鸡》)等。
对这种以议论为诗的做法,后人有一些非议之辞,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2]中以“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委婉地表明他的不赞成态度,屠隆在《文论》中则以“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3]直截了当地批评以议论为诗的做法。其实,诗歌作为言志抒情的工具是不可能完全排除议论的存在的,只要不以逻辑思维完全替代形象思维,使其诗歌既有理趣又有情韵,从增加诗歌表现手法上讲还是值得肯定的。以梅尧臣的《秋思》为例:“梧桐在井上,蟋蟀在床下。物情有与无,节侯不相侯。寥寥风动叶,飒飒雨堕瓦。耳听心自静,谁是忘怀者。”该诗旨在说明:时序之哀乐缘于人心之欢戚,内心静定者任物象动摇能不受其影响,进而推崇心定神静、不役于物的禅理境界。在这首诗中,梅尧臣并未只枯燥地去议论说理,他还运用了形象描写的表现手法,其中“寥寥风动叶,飒飒雨堕瓦”的景物描写对仗工整,形象逼真,与理趣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情韵,所以这类诗也是值得肯定的。
梅尧臣意义层面上的以文为诗还体现在以典故入论。如在《醉中留别永叔子履》中诗人发了一通“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的感慨之后,便引用了张翰见秋风起而思故乡鲈脍的典故,写到“江湖秋老鳜鲈熟,归奉甘旨诚其宜”;以比喻入论,如《咏秤》中诗人以秤星徒列无用比喻加强民众的道德伦理规范是如今当务之急。迨至梅尧臣在形象描写上的基础上加深立意、于物象之中探求宇宙人生哲理时,这类诗就成了理趣诗,如《惊袅》一诗:“惊凫虽避人,终恋旧所泊。尽背船头去,却从船尾落。须知取势高,不是初飞错。”以惊凫为取势之高被迫飞到船尾,暗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生哲理。又如 “看取有心常不展,亦知随分坼佳苑。无端大叶映莲幕,却笑菖蒲罕见花”(《依韵和行之都官芭蕉诗》)和“我心岂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须深红”(《公度以余尝语洛中花品而此邦之人多不敢言花于余今又风雨经时花期遂过作诗已见贻故次其韵》)等都是理趣诗中的精华之句。当然梅尧臣在具体运用以议论为诗创作手法的时候也会犯一些议论太多、形象不足的毛病,如他的《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感遇》、《古意》全诗,几乎是纯粹议论了,但这类诗歌毕竟是少数,并不影响梅尧臣以议论为诗的整体成就。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梅诗在形成层面上的以文为诗,即狭义的以文为诗: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歌创作中,导致诗歌在结构、句法、句式、节奏、语言以及诗题等外在形式上的变化。
首先,以文为诗带来了诗歌谋篇布局的散文化和诗题的长短变化。以《希深惠书言与师鲁子聪永叔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为例。此诗由交代游嵩缘由开头,然后一一描述所经景点:初经的是缑氏岭,再过的是轩辕关,又到的是礼神祠等等,洋洋洒洒,铺陈直述,最后全诗以感叹未能同游收尾。整首诗从行文的铺陈到结构的严整,俨然一篇“押韵之文”。此外这首诗的另一特点就是诗题较长,总共二十一个字。这也可以算成是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在诗歌题目上的表现,因为诗题一长,其记述的性质就越强。如梅尧臣作于康定元年的一首《己卯岁,紫微谢公赴南阳,过叶县,陪游兴庆精舍,题名壁间,西去。庚辰岁,余来按田,因访旧迹,衋然于怀,故作此谣以志其悲》(标题太长,为便于理解,加以标点)。该诗诗题共四十九个字,将作者的缘起、时间、目的以及心态等都交代得很清楚,犹如一篇短文。这类长诗题在梅诗集中是比较普遍的,但也不是创作伊始就是这般,而是逐渐加长的。通过对其诗题长短变化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梅诗从学唐到变唐、从探求个性到确定个性的一个过程。因为唐诗的题目一般以三两个字居多,宋诗的题目平均来讲比唐诗要长些。所以从总体上讲,诗题的长短也是唐诗和宋诗的一大区别。而梅尧臣以三两字居多的诗题多集中在洛阳三年,即梅诗艺术个性形式的第一阶段“学唐人平淡处”时期。[4]景祐以后诗题普遍增长,五六字、七八字者不在少数。至庆历年间梅诗艺术个性已确立,出现了许多二三十字以上的长题,甚至在庆历六年(1046)出现了高达七十七个字的最长诗题。这种在诗题上的改革是处在学唐阶段的诗人所不敢的。
其次,以文为诗还带来诗歌语言的日常化。语言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它讲求简洁、精练、有意韵。到唐代,诗歌语言除在音节上讲究平仄押韵之外,还在语序上讲求非正常语序,因为这样能造成诗歌意脉的“顿挫”与“断层”,增强诗歌的朦胧性,增加诗歌的品味回旋的空间。到了宋代,梅尧臣以文为诗,于语序上求新求变,一反唐诗语序的颠倒置换,引散文的正常语序、平实语言入诗:“梅天下梅雨,绥绥如乱麻”(《五月十日雨中饮》)、“君来何所闻,君去何所见”(《依韵公择察推》)、“扬州太守重交情,我欲西归未得行”(《依韵和戏题》)、“当时永叔在扬州,中秋待月后池头”(《寄淮阳许待制》)、“昔闻醉翁吟,是沈夫子所做;今听醉翁吟,是沈夫子所弹”(《送建州通判》)。这种白话语言比起白居易的“平白晓畅”是有过之无不及,无怪乎王礼堂在《冬夜读梅圣俞》中说“滑眼看不下,滑口读不入”(《西庄始存稿》卷十六)。
梅诗语句的日常化还体现在虚字的入诗上。所谓虚字,据《马氏文通》所讲“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比如介词、副词、助词、连接词等都可以归为虚字。在正常句法结构中虚字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或作为连接的枢纽,或调整语句的节奏、舒缓文句的语气,或使音节活泼不板滞、增加作品的美感。但多用在散文中,很少用在诗句中。以文为诗使诗歌打破了诗与文的这种语言界限,在梅诗中可以看到许多虚字,如“及”、“已”、“与”、“唯”、“中”、“焉”、“然”等。它们的大量出现虽然使诗歌少了几分意境上的清空朦胧、想象上的缤纷多彩,但也使诗歌多了几分意象上的张力与运动和思维逻辑上的严密与清晰。以《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为例:“去年君到见春迟,今日寻梦是夙期。只道朱樱才弄蕊,及来幽圃已残枝。飘英尚有游峰恋,著子唯应谷鸟知。把酒聊能慰余景,乘欢不厌夕阳时。”全诗总共五十六个字,就含“只”、“才”、“及”、“已”、“尚”、“唯”、“聊”、“不”等虚字八个,平均一句一个。除用量多外,梅诗还偏爱某些虚字,如“或”字和“不”、“否”、“莫”、“无”等否定副词。我们考察出梅尧臣自嘉祐二年以后便常用“不”、“无”“莫”等否定词煞尾,“数峰来枕席,曾不愧移文”(《答陈五进士遗山水枕屏》)、“而我无羽翼,安得与子游”(《往东流江口寄内》)、“莫贳远公酒,余非陶令贤”(《访矿坑老僧》)。这些虚字的使用使梅诗呈现出严整而又有活力的诗美特征,仍以《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一诗为例。如果把其中一部分虚字抽出来,这首诗后几联就成了“朱樱才弄蘂,幽圃已残枝。飘莫游峰恋,著子谷鸟知。把酒慰余景,乘欢夕阳时”,如唐诗一般的意象的平面叠加使诗人的形象若隐若现、情绪的转变模糊不清。而加上原来的“只道”、“及来”、“尚有”、“唯应”等词则使整首诗“词调流畅”,意脉畅通,增强了诗歌的内在逻辑,凸现了诗人的主体意识,使整首诗呈现出一种凌云健气之美。
再次,以文为诗还带来了梅诗节奏的与众不同。这主要是由体式的灵活与句式的参差引起的。梅诗历来以五言取胜,五言诗占其诗总量的74%,[5]其次以七言诗较多,此外还有个别几首杂言诗和四言诗。但在某些诗作中,梅尧臣“文随情变,诗随意改”,并不拘泥于体式的整饬与统一,常常在四言中杂五言(如《闵谗狡》),在五言中杂七言(如《百舌》),在七言杂三言(如《五二道太丞立春早期》)。这样就使诗歌于整饬中有变化,于变化中见整饬,具有了散文的流动形式和灵活的表现力。在句式上梅诗也多用散文的灵活节奏,于五言上二下三、七言上四下三的正格之中,间用上一下四,上一下六等诸多次格。如以五言诗为例,有上一下四格,如“或反授人柄”(《依韵和丁元珍见寄》)、“物以美好见称”(《和瘿盃》);还有上三下二格如“君比众最笃”(《送韩持国》)、“十一月将雪”(《和江邻几咏雪二十韵》),在许多正格之中偶用一处次格的做法,使整首诗顿挫有加、不至于太顺太滑,恰如高山瀑布直流而下,撞遇山石棱角,不期而遇却激荡起水花无数,不失为一种别样的美。
[1]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屠隆.由拳集[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
[4]李萍.论梅尧臣诗歌的艺术个性[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5]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147.
ArtisticCharacteristicsofMeiYaochen’sProse-styledPoems
Li 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i Yaochen's prose-style poems are reflected in two levels, namely, the level of meaning and the level of diction. The level of meaning refers to the tendency to prefer the abstract ideas and make comments, and to support his arguments with allusions. The level of diction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of his poems, the variation of titles in length the choice of daily words and functional words in particular and the rhythm as well.
Mei Yaochen; prose-styled poems; change of titles in long and short ; function words used in poems
ClassNo.:I206.2DocumentMark:A
宋瑞斌)
李萍,硕士,一级讲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研究方向:唐宋文学。邮政编码:210046
1672-6758(2010)06-0081-2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