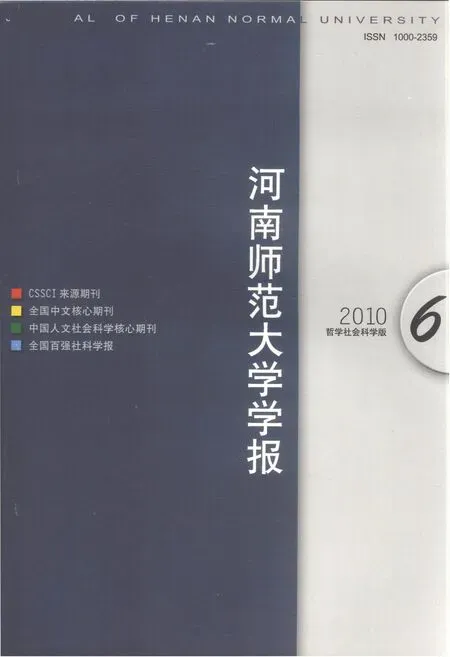人的本质存在与超越发展
——柏拉图人学思想初探
杨建坡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人的本质存在与超越发展
——柏拉图人学思想初探
杨建坡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柏拉图的idea思想,使世界二分,开辟了西方形而上学人学传统。柏拉图认为,由于人的本性由灵魂决定,灵魂又由理性所主导,所以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人的灵魂来自理念世界,其自在自为、永恒不朽的特性使得人们通过回忆和灵魂的转向可以认识理念世界,从而发展自身。柏拉图的人学思想建基于idea思想之上而具备了超越性层面,使人的发展也具有了追求超越的特性,教育是对现实人的一种实现,也是对最完善的“理念”人的超越追求。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结构和灵魂结构是相一致的,国家、个人和灵魂具有承载关系,因而灵魂的教育是国家正义的基础。
柏拉图;人;本质;发展
卡西尔在《人论》中开篇即表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1]4。而对人自身的认识是一直伴随着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只是在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任务之前,哲学的主要目标是探求世界的起源问题(向外观察,世界是什么?),即便是这样,哲学也没有“忘记”对人自身的反思(向内观察,人是什么?)。卡西尔指出:“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1]6可见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哲学思想发展。那么,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柏拉图来说,其人学思想自当极其丰富。
一、idea与“二分世界”
在柏拉图的著作里,我们似乎不能发现其对人性的详细论述,尤其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进行专门讨论。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理念论,把世界分为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把人看作“理性动物”的思想起源,从而影响到近代以降的对人的本质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海氏认为在提出“人是什么”问题之前,必须对“是”本身的意义进行思考,而“是”的意义必然是在是其所是的过程中展开的,因此“是”的意义必须在一种是者所是的过程中进入,由于人这个是者的特殊性,就成了海德格尔揭示是的意义所选定的特殊是者。可见人的本质规定和存在存在内在逻辑关联。理念论看似和人的本质规定无关,实则不然,柏拉图正是从理念论(idea)出发通过对灵魂结构的规定来规定人的理性本质的。
“理念论”(idea)是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理论,是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所谓“理念”,柏拉图使用的原文是idea,出自动词idein(看),其本义为“所见之物”即形,转义为灵魂所见之物。哲学初创时期,古希腊人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也是哲学概念的形成过程,这些概念既有其直接感性来源,又具有丰富内涵,这也是后来被逐渐抽象化了的概念所无法表达的。因此,将idea译为“相”不无道理,也有国内学者为确保“idea”概念的原初丰富性而主张音译为“意第亚”,我们这里循常例仍然沿用“理念”的译法。由于idea含义的丰富性,将其译为“理念”就侧重于idea的“超验理性层面”,将其译为“相”则偏重idea的“直观呈象层面”[2]。idea的超越层面意义重大,是柏拉图思想的核心,它将世界二分,即将世界分为耳闻目睹的经验世界和具有永恒实在性的“idea世界”,而“idea世界”是超验的理想设定的应然世界,正是这个“idea世界”成为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主流追求的目标,是现实流变世界的奠基,基督教对理想“天国”的追求、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探究、符号文化世界对意义空间的无限延展等这些超越性所追求的无不是“idea世界”的化身。而“idea世界”的直观呈现层面则为我们认识“idea世界”提供了可能,人可以通过心灵之眼去“看”理念世界。
柏拉图的“线喻”,认为可以把我们的认知对象世界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可见的领域,另一个是可知的领域。可见的领域包括影像的世界和事物的世界,即现象的、经验的、事实的、杂多的世界。而这个事实经验的世界,恰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捉摸不定的意见世界。真正作为具有永恒实在性的可知世界,则包括数理推论的知性领域以及更高的“idea”本身的理性领域,“理念世界”不是作为肉眼的对象而是作为心观的对象而显现的。“理念世界”同经验世界一样具有可知性。
“经验世界和可知的idea世界的区别并不在于一个是看的对象,一个是推理的对象,而都是可视的世界,只不过一个相对于肉眼,一个相对于灵魂”[3]58。为了更好地说明对“理念世界”的认识,柏拉图提出了“洞穴喻”,描绘了被禁者对两个世界的认识经历和感知体验:“被囚禁的人除了能够看见被火光投射在他们面前洞壁上的各种阴影之外,既看不见他们自己及同伴,也看不见那些举起的物品……在那个较上的世界中要能看清事物,这需要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辨认阴影最容易,其次就是看人或物体在水中的倒影,再次就是事物本身……最后,他就能够直视太阳儿沉思它本身了。”进而柏拉图指出,“每一个人的灵魂确实具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和看见整体的器官……整个灵魂也必须转离这个变化的世界,直至它的眼睛能够从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我们称之为善的至为明亮者……这并不是要把视力赋予灵魂,灵魂本身就具有这个能力”[3]59。
柏拉图的“idea世界”是具有直观的可知性的,是具有确定性的永恒的世界,人具有认知“idea世界”的能力与可能性,只不过这种认知是通过纯粹的灵魂的回忆而获得的,需要借助灵魂的转向。这种对“idea世界”的纯粹灵魂的回忆,或多或少地存有事实经验的提示。“但idea世界绝对超越了这个事实性的经验世界,并且在起源性和事在性上都高于现实经验世界”[3]59。在柏拉图看来,现象世界是建立在“idea世界”的终极实体之上的,现象世界只不过是“idea世界”的微弱反映而已。“idea世界不仅是一个确定的知识世界,更主要的是一个终极实体世界”[3]59。在柏拉图那里,人的地位似乎基督徒的角色,生活在作为派生并流转变换不定的经验世界里,就像洞穴里的囚徒一样是亟待拯救的,并且人由于是神创造的物品中最好的,也就有了被拯救的可能和潜质。人的独特性正在其灵魂与肉体的结合,而灵魂是来自理念世界的,是永恒不朽的,这也就为人追求理念世界提供了可能。而人的本质规定也就主要地由灵魂的结构来决定。
二、人的存在本质
柏拉图没有对人的本质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其“灵魂论”来看,他是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他在《斐多篇》和《斐德罗篇》中对“灵魂”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尤其在《斐德罗篇》中通过“灵魂马车喻”对灵魂的本性进行了形象的说明:“让我们把灵魂比做一股合力,就好像同拉一辆车的飞马和一位能飞的驭手。”并进一步说明,凡人的马车“有两匹马拉车,有一位驭手驾车……有一匹是良种骏马,而另一匹正好相反是杂种劣马。因此我们的驭手要完成任务就非常困难,经常会遇到麻烦”[4]。马车能否顺利前进取决于驭手对马匹的控制,也就是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调控。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明确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并且分有等级,理性居于支配地位。在《蒂迈欧篇》中,灵魂被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5]。在柏拉图看来,“灵魂”是自动自为、轮回不休的,它来自理念世界,客居于人的身上,人只有通过灵魂的不断磨炼和升华(转向)才有可能认识理念世界。所以,人的本性由灵魂决定,而灵魂又由理性所支配,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人的本质是理性的,这也正是逻各斯精神在柏拉图这里的深刻体现,也为亚里士多德明确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开辟了道路。
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人学时,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作为“理性人”思想的代表。在海德格尔看来,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传统形而上学人学渊源于古希腊,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存在论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第一个完整体系。柏拉图把理念看作是现象界的来源和本质本身,这种二分世界的存在论解释支配了近代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柏拉图的这种把存在解释为理念并由此把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理论看上去与人学无关,其实不然。柏拉图正是由此出发来规定人的本质的,他对人的灵魂的分析便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灵魂是由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真正的人必须以理性支配激情和欲望。这里所用的理性,实际上也即是理念本质在人身上的体现”[6]。
“理性人”是卡西尔的功能性定义“符号人”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意义的“Dasein”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性的概念式思维模式,但是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并非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人”的理性意义。“人是理性的动物”的思想根源在于前苏格拉底时期所塑造并成为西方哲学基本精神的“Logos”(逻各斯)和“Nous”(努斯)精神。在希腊语中,“Logos”是说话的意思,“Nous”是心灵的意思,这两个概念在中西方都翻译为理性,所以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逻各斯的含义,就是注重话语的规范、语法、理性的分析、逻辑的分析;一是努斯的含义,是超越宇宙之外的能动精神,是超越世界的能动性。所以理性就包含这两种含义。源出于柏拉图idea意义上的“理性人”就获得了的超越性和实现性的双重意蕴。这一意义又远丰富于后世的高度抽象的、僵死理性的铁一样的规定性。
三、人发展的多重维度
认识即回忆和灵魂转向。柏拉图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中最好的。人由肉体和灵魂构成。人的“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7]82,并存在于理念世界中,认识理念世界中的许多东西,以至于可以洞察最高的理念。但当灵魂和肉体结合投身为人时,由于惊恐和骚乱(因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就失去了对最高理念的认识和记忆。又由于灵魂受到现象世界中各种理念的阴影的刺激,逐渐地又把已遗忘了的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回忆起来。因此,柏拉图认定,认识不是对物质世界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认识真理就是接近最高真理的理念。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回忆理念世界的过程。由此柏拉图便进一步得出结论,“学习……就是恢复固有知识”的过程,“学习只不过是回忆”[7]82。如此,人的发展进步就维系于灵魂的转向和灵魂的回忆,人的发展具有了可能性和路径。灵魂的回忆是人认识理念世界的唯一途径,灵魂转向是灵魂“回忆”理念世界的必备技艺,因此,这就为人追求真理、把握真理提供了一条道路,为实现人的本质存在提供了途径。
由于知识分为多个层次和不同类型,人们在认识知识和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还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和掌握相应的技巧。柏拉图的“洞喻”中所揭示的不停的回身转向就是一种心灵逐步认识理念世界的必要技艺,也即“灵魂转向”。与“线喻”所揭示的两大世界四个层次相适应,人的灵魂也有四种不同的功能,从低到高依次为猜想、相信、推论和理智。猜想的对象是影像,由此产生的是人们的偏见和成见。相信的对象是具体事物,由此产生的是感性认识,因其对象的变动不居,所以感性认识也不具有可靠性和确实性。推论的对象是数理理念,它的活动特点是不得不先设定一些假设,并且视之为不证自明,然后由假设开始,通过逻辑推理继而达到答案。推论活动的成果是正确的,不过由于它依赖假设,因而前提的真假难以确定,故上升不到第一原则即善的理念。理智的对象是伦理方面的理念,它的特点是“不是将假设作为开端,而是直截了当地作为假设,作为阶梯和跳板,旨在超越它们,达到不要假设的领域,达到全体的第一原则。并且在达到这种第一原则以后,又回过头来把握以这个原理为根据的、从这个原理引申出来的东西,从而达到终点。它不用借助任何可感事物的帮助,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从理念开始,再从理念到理念,最后下降到理念而终止”[8]。它比推论更精确、更真实,获得的是真理性的一般认识,最终把握到善的理念。柏拉图把认识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未违背其将理念与事物进行区分基本原则。认识的发展过程并非自低向高的递减发展,而是灵魂的不断转向。正如“洞喻”所揭示的那样,囚徒不可能通过洞壁上的影像认识其身后的事物,除非转过头来;人们也不可能认识到太阳是万物的主宰,只有被拉出洞外。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也是如此,认识的过程是灵魂的四种功能依次转向的结果。于是,先天性在此不再像回忆说那样表现为具体的知识,而是表现为认识的功能。
人的发展具有二维性。人发展的本质在于其超越性,在于把人从单纯的适应自然界的物理层面,提升到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意义空间,使人能自由地把握对象和自身。“idea”具有超越和直观两个层面的含义,这就决定了柏拉图人学(教育发展意义上的)思想对构建理想国家的现实意义和对人的发展的本质的超越性追求,人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当下的功利、实用,它还有更高意义的追求,这个追求是人的自由发展的“idea”世界的“人的理念”,也即最完善的那个“人”的追求,具有实在意义和终极意义,哪怕这种追求要历尽千辛万苦,也要不断地实现灵魂的转向。柏拉图在“洞喻”中描绘了人对“idea世界”的追求历程和“idea世界”的实在的、清晰的图景,时刻激励人们追求超越。人的本质及目的理应建基在一个更高的和更令人向往的一个实在世界的基础上,人的发展教育要有更高的追求,要帮助人发现真实的自我和实现最高意义上人的本质。
在柏拉图那里,人的发展与国家正义相统一。基于对“idea世界”的追求,柏拉图致力于“理想国家”的建构,在《国家篇》和《法律篇》等篇章中,柏拉图描绘了其“理想国家”的完美图景。按照柏拉图的设计,在那个“理想”的国家里,存在神用不同的金属造就的三种人:哲学家、军人和劳动者(农民、手艺人)。哲学家是治国者,是神用金子造成的,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灵魂中理性部分(灵魂中的高级部分)最强;军人是奴隶主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和国土的保卫者,是神用银子造成的,具有“勇敢”的美德,意志在灵魂中占主要成分;手艺人、农民是生产劳动者,是神用铜铁造成的,具有“节制”的美德,情感(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在他们灵魂中占主要分量。奴隶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属于上述三等中的任何一等。柏拉图认为,智慧的特点在于能“妥善谋划”,使国家成为“真正智慧的国家”[7]110,因此哲学家最适合于担任国家的治国者。勇敢的特点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法律,坚定不移”,“为国家效力疆场”[7]111,因此军人最适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土。节制的特点在于能使各个等级的人“在谁该统治谁的问题上”易于“意见一致”[7]114,因此农民、手艺人最适于从事体力劳动,供养哲学家和军人。柏拉图还认为要把一个国家“安排得当”,光有智慧、勇敢和节制还不够,必须还要辅之以“公道”(公正)的美德才行。公道是每个等级都应具有的美德,它的特点在于使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做自己分内的事情”[7]117,这样社会必然是“安宁”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就是公道的”国家。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结构和灵魂结构是相一致的,国家、个人和灵魂具有承载关系,灵魂的教育发展是国家正义的基础。
[1]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3-68.
[2]高秉江.idea与“象”——论直观和超越的兼容[J].哲学研究,2007,(11).
[3]高秉江.胡塞尔的Eidos与柏拉图的idea[J].哲学研究,2004(2).
[4]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60.
[5]柏拉图全集:第3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1-282.
[6]刘敬鲁.论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批判[J].哲学研究,1997(9):66.
[7]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苗立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13.
B502.232
A
1000-2359(2010)06-0012-04
杨建坡(1979—),男,河南西华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新乡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代西方认识论研究。
河南省教育厅规划课题“现象学视角下的高校素质教育研究”(2009-JKGHAG-0609)
2010-07-12
[责任编辑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