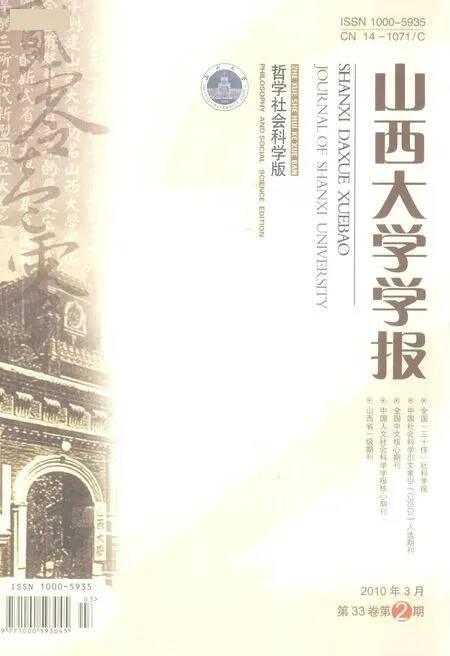超越于意识之外
——弗洛伊德论文学起源和读者接受理论
史 维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超越于意识之外
——弗洛伊德论文学起源和读者接受理论
史 维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学起源和读者接受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他相信一部文学作品是作家无意识心理的外部表达,艺术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白日梦,是他内心深处无意识欲望的变相满足。从生理层面上降低了文学本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这无疑是对西方文学传统中文学起源论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精神分析从心理无意识的角度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作出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卡塔西斯”,并且扩充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阈”、“文本召唤结构”等术语的理论内涵,从而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无意识;本能欲望;文学起源;读者接受
20世纪的西方文坛是“文学理论批评的时代”。在这流派纷呈、主义迭出的批评理论当中,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在其临床医学的基础上开创了以潜意识为基本内容的精神分析理论 (psychoanalysis),它原本是为精神病人治病的一种方法,在 20世纪将之广泛运用到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作者和作品人物的批评分析当中,形成了精神分析批评 (Psychoanalytic Criticis m)的文学理论。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其主要理论是包括潜意识在内的人的心理结构、释梦、白日梦、升华说以及人格结构等主要内容。
一 白日梦幻想与艺术创作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整个人类取得的最高成就甚至整个文明的造就也是与这种无意识冲动和刺激分不开的。作为作家精神活动的文学创作,在他看来也与这种潜意识的活动密切相关,他相信一部文学作品是作家无意识心理的外部表达,艺术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白日梦。
基于他的无意识和释梦理论,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说:
许多富于想象的作品和天真的白日梦模式相距甚远,但我仍不能放弃这种推测: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不间断的、一系列的过渡事件与白日梦相联系。[1]63
对于作家生活中童年时代的记忆的强调——这种强调或许令人不明所以——归根到底来自于这种假设: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1]64
根据弗洛伊德,白日梦或者说幻想源自于儿童时代的游戏,成年人则靠幻想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羞于启齿的愿望。这种将作家的艺术想象和创作,看做是儿童游戏在成年之后另一种方式的替代的观点,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弗洛伊德把艺术比作神经官能症,而把艺术家比作神经病患者,“艺术家跟神经病患者一样,受到格外强大的本能需要的压迫,使他由现实转向幻想。然而与别的幻想家不同,艺术家知道如何对自己的白日梦加工、塑造与软化,使之为别人所接受”,[2]这是因为,弗洛伊德注意到如同梦一样,文学创作也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sublimation)。通过作家一系列的艺术加工和处理过程——复杂的置换 (displacement)和浓缩 (condensation)的形式——作品表现作家无意识的内容。因而可以把释梦的规则拿来运用到对文学的解释上,即“文学并不是将无意识的内容直接翻译成代表无意识原本意义的象征性符号,而是将作者内心无意识的欲望、冲动和动机置换成与其本来面目不相关的意象,通过这些意象使这些无意识内容得以顺利释放或表达。”[3]在当时的文艺思潮和社会背景下,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论断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 文学起源的再阐释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学创作进行论述并非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开始,早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源头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明确地将诗歌这种艺术性的创作归结为神灵附体带来的灵感。
紧接着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模仿”这一概念,他说:
作为一个整体,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4]47
在随后的西方文学主流传统当中,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人类精神建构、负载价值观念和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具有崇高的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然而,弗洛伊德将作家的创作在本质上解释成作家自己的白日梦、幻想,从中可以读出弗洛伊德实际上对艺术发生和起源论的另一种理解和阐释,不过他的这种解释与上述西方传统的文学思想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用一种欲望和无意识本能冲动的人性解释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文学产生源头的来自于理念或高于历史的神圣性,文学生产成为受到心理结构中无意识领域里各种生理冲动的刺激,同时又由于外在社会中的道德限制和良心谴责而无法直接表达或满足,因而以迂回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的产物。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幻想的内容主要是野心的欲望和性的欲望两类。文学创作的动因就是人生命中这些幻想和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而这些欲望中最强烈的是性欲,换言之,本能的性欲是艺术家从事创作的根本动因。而“美”这个概念就植根于性冲动中,人类的审美活动则围绕着性冲动来进行,从性欲中获得美的享受。[5]
由此看来,艺术家从事文学创作,纯属性本能冲动进而升华的结果。弗洛伊德从生理层面对文学艺术做了一番解释,解构了以往文学的崇高性和神圣性,无疑是对西方文学传统的一次偏离和反叛,为文学的起源和发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和可能,而这对于传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家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不仅如此,在弗洛伊德看来,甚至整个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与人的这种潜意识活动中的生理冲动密切相关,文明实质上成为人类生理欲望的“升华”的结果。
三 文学接受的再阐释
既然文学文本中存在着作者的幻想,文本本身就是幻想的凝聚,读者从中能够寻求快乐的源泉。那么读者面对文本时是如何接受的呢?换言之,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为什么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文学给予读者的快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的定义说:“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4]63也即所谓“净化”(katharsis),在公元前五世纪,katharsis大概是指一种医疗手段,后来既可指医学意义上的“净洗”和“宣泄”,又可指宗教意义上的“净涤”。根据陈中梅先生的注释,“在定义所包括的内容中,‘净化’(katharsis)是《诗学》现存部分没有作过说明的唯一的一项内容。”[4]67他在随后对 katharsis作的评论中说:“亚氏亦把情感归为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同意柏拉图提倡的对某些情感绝对压制的办法。如果说产生情感的机制和它的工作效能是天生的 (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情感的表露和宣泄却是可以控制和调节的。有修养的人不是不会发怒,也不是不会害怕,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或事,在正确的动机驱使下,以适当的方式表露诸如此类的情感。”[4]227如果说在亚氏那里还没有对 katharsis在心理机制的层面上作出具体准确的解释的话,那么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这里,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所谓的情感宣泄作一个较为充分的诠释。
在作家作品的展示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层面,作家通过艺术作品这种载体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幻想和白日梦时,必须用艺术的技巧来克服读者心中的厌恶感,而读者在对作家的这种白日梦进行接受和解读时,也就能从这虚构的作品中得到乐趣和满足。
当一位作家给我们献上他的戏剧,或者献上我们习惯于当作他个人的白日梦的故事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极有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产生。作家如何达到这一目的,那是他内心身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精华在于克服使我们心中感到厌恶的效果的那种技巧,这种厌恶感毫无疑问地与一个“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产生的隔阂相联系。我们可以猜测到这种技巧的两个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他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俘虏我们这些读者。我们给这类快乐命名为“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作者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在我看来,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甚至有可能,这种效果的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1]65
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从中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考察,作进一步的阐释。首先,弗洛伊德是基于他的无意识理论和心理动力本能理论,从无意识和本能的角度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做出说明的。按他的看法,人在由婴儿向成年过渡的过程中都要经历性的四个重要阶段,即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和青春期,这四个阶段对于成人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而人在这几个成长阶段所经历过的生理快感的体验都将在内心深处积淀下来并潜在的对自我施加影响,其中主要是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而不为自我所意识。读者在进入文本之前,已经带着自童年时代起所经历过的这些快感体验,当其沉醉于文学阅读时,就如同重温童年时代的旧梦,在梦中重新获得幼年时代的快感体验,再次获得无意识欲望的满足,这同样是一种“移情作用”,将无意识欲望的满足转移到文本阅读,因而这里的情不仅包括读者的意识层面,更重要的是也包含了无意识层面,而后者是传统文学批评所不曾关注的,正如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诺曼·N·霍兰德 (Nor man N. Holland)教授所说的:
在我们生命的非常原始的层次上,我们与文学作品融为一体:我们感到其中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发生在我们内心。我们幼童时期的口唇满足的体验构成了一种基质,为我们后来涉及文学时那种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的心态打下了基础。[6]
也就是说,读者对作品的欣赏和接受是基于自身心理无意识中已经存在的幻想和欲望,对作品的阅读只是释放读者自己的“精神紧张”,满足受到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主要是在生理层面上的审美感受。因此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使得对作品的审美与欣赏降格为一种心理欲望和本能的满足。审美感受成了一种低层次的欲望满足,是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由愉悦。正如上文所言,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而言,“‘美’这个概念植根于性冲动中,而人类的审美活动则围绕着性冲动来进行,从性欲中获得‘美的享受’”。不仅作家在做白日梦,读者同样也在做白日梦,只是两者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获得快感的体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亚氏说的“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人的无意识中未满足欲望和本能冲动的一种宣泄和释放,进而达到平静和净化。
第二,将弗洛伊德的这种读者阅读联系接受美学理论来看。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快感,称之为“前期快感”(或叫“预感快感”)(fore-pleasure),从而激起读者内心更大的愉悦,引发心中张力的释放。如前所述,这种心灵的愉悦来自于读者对作家幻想——无意识中未满足欲望的实现——的理解和接受。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体验作家未满足欲望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读者自身欲望和冲动的变相满足。换言之,作家通过创作来空想和满足愿望,而读者则通过阅读来空想和满足欲望,并且读者的这种形式“用不着自我责备或害羞”,避免了道德自责感和羞耻感。
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批评家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其理论主张中着重分析了“期待视阈”这一概念,“期待视阈”在他那里主要包括“某一历史时期所有的对于一个文本的批评性词汇和评价”[7],另,
期待视野是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接受的前提条件,它包括读者从已阅读过的作品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对不同的文学形式与技巧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主观条件,如政治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生活的经历和经验、艺术欣赏水平和趣味、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和素质等。姚斯认为,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期待视野会在以下方面
具体地表现出来:一,对不同形式、技巧和
风格的作品的兴趣与需求;二,对一部文学
作品的不同的审美感知能力和理解水平;
三,将作品审美现实化的不同方式。[8]378
换言之,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理解文本之前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一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范围和限度。“期待视阈”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读者而变化。接受理论的另一位德国批评家伊瑟尔 (Wolfgang Iser)受到波兰文学理论家罗曼·英伽登的影响,即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充满间隙和不确定因素的“图式化结构”,需要读者的想象和加工来填充,进而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术语,意指文本中的空白点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文学作品本文的基本结构,因而使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它们在阅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作品被读者接受并产生作用的根本出发点,是沟通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和前者向后者转换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站’”。[8]760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阈的阅读期待,促使读者运用自己的个体体验、价值体系和哲学观念去填补文本中的空白,连接空缺,从而打破原有的阅读期待,形成新的读者视阈,并且获得对文本的新的意义。
在他们原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同样可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维度给他们所提出的术语和问题注入新的内容。即将读者的无意识欲望冲动和快感体验纳入“期待视阈”的范围,而将“文本的召唤结构”的内容看做是作家未满足欲望的提出和实现。姚斯在讨论期待视阈时认为它主要有两大形态:一是在既往的审美经验 (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期待视阈;其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 (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阈。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期待视阈还应该包括读者自身的心理结构尤其是无意识活动的广大领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一个个体,既包括作家,也包括读者,都有一个复杂而隐秘的无意识心理层。这个无意识层面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其中包含着人的各种本能、欲望、冲动等。尽管无意识是混乱的、盲目的,但却是广阔有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动力。对于作家而言,以性欲为主要内容的无意识是促使作家创作的根本动因;同时作家这种欲望、冲动在作品中的实现也使作品具备了一种“文本的召唤结构”。而对于读者而言,这种无意识则应成为读者内心潜在的“期待视阈”的一部分。
因而,读者阅读作品就是想要在作品中寻求自己内心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而作品中以作家的欲望及其实现为主体内容的“文本召唤结构”则是促使或者说吸引读者去阅读的动力。姚斯将作品的理解过程看做是读者的期待视阈对象化的过程。读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阅读的文本作出反应:他们或喜欢它,赞美它,或厌恶它,或迷惑于它等等,这些情感表现揭示出读者的诸多心理方面,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本“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9]在于文本中所包含的幻想是否契合读者的无意识幻想。当读者的期待视阈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相吻合时,自己的幻想得到了满足,获得了快感,阅读就会比较顺利地完成,读者的本能欲望在他阅读作者作品的过程中实现了,同时这一过程也就是审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部作品由此也被读者认为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当一部作品不仅符合一个读者的期待视阈,而且符合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期待视阈时,这部作品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著作。例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按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三部作品里面的“杀父娶母”情结是人类无意识中所共有的,因而才能被不同的时代和人群所接受,成为伟大的作品。正如德国学者汉克·德·博格 (Henk de Berg)在论述弗洛伊德时所言:“《哈姆雷特》这一戏剧的流行,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即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以自己的情感卷入到这部剧作的中心冲突当中。”[10]这里所指所谓的人童年时代心理中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有些人曾成功地克服了这一情结从而顺利地进入到成人阶段,而有些人则未能成功地克服这种情结而从中遭受到心理痛苦。不管文本的读者是那一种情况,重要的是这些读者至少都曾经在童年阶段有过“俄狄浦斯情结”,“既然童年时代的经历对于我们之所以成人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部剧作在所有的时代和地方对于读者都有巨大的魔力,就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最黑暗的童年时代的欲望,了解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剧中的英雄主人公、诗人和读者观众,由于他们内心共有的根源冲突,因而都被这种冲突产生的情感所深深打动。”[10]从中不难看出,以人心理中各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和快感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无意识领域在“期待视阈”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 20世纪西方众多思潮中一种,对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维度,对文学领域中的一些传统问题提出了一些崭新而独特的见解,如果将这些观点与同时代和后来的文艺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就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新问题,并且会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提供新的具有启示性的解释和补充。
[1][奥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 [M]//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七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2][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刘 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11.
[3]Rivkin,Julie and Michael Ryan.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M].Blackwell Publishers,1998:125.
[4]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美]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M].王宁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序言.
[6][美 ]诺曼·N·霍兰德.文学反应动力学[M].潘国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93.
[7]Charles E.Bressler.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Upper Saddle River,N.J.: Prentice Hall,2003:65.
[8]乐黛云,叶 朗,倪培耕.世界诗学大辞典[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9]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9.
[10]Henk de Berg.Freud’s theory and its us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M].Rochester,NY: Camden House,2003:87.
Beyond the Consciousness——On the Literary Genesis and Reception Theory by Freud
SH 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The unconsciousness theory in psychoanalysis by Freu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genesis and reception theory.Freud clai ms that a literarywork expresses the writer’s unconsciousness,and the artistic creation is the writer’s daydream that in disguised form satisfies his inner instinctive desires.This undoubtedly degrades the literature’s spiritual contents and aesthetic value,which brings about great impact on the literary genesis in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On the other hand,psychoanalysis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ader’s re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ciousness and can be a proper di mension to deepen the Aristotle’s ter m Katharsis.In addition,it is an expansion of theoretical terms in acceptive aesthetics such as horizonsof expectation and calling structure.
unconsciousness;instinctive desire;literary genesis;reader’s reception
book=68,ebook=241
I0-05
A
1000-5935(2010)02-0068-05
(责任编辑 魏晓虹)
2009-12-18
史 维(1979-),女,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在读博士,从事欧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