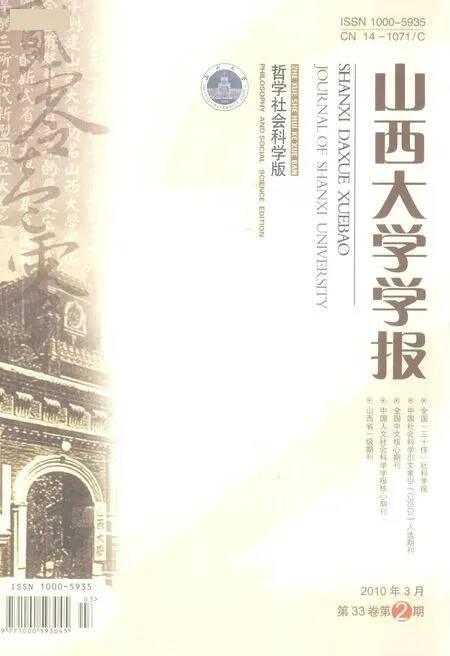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研究
沈沛龙,申毅刚
(1.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6)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研究
沈沛龙1,2,申毅刚1
(1.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6)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文章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创新已经过渡到制度创新阶段。在制度创新体系中,组织创新较业务等其他创新层次更高。要进行组织创新,需要将合作金融机构做成农村金融的主体,加快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进程,打通民间剩余资金的制度通道,强化监管创新,体现农村金融特色,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性。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一 引 言
始于 2003年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实质上是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一次新的制度创新过程,从央行的“花钱买机制”,到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革的三分天下,无不说明制度创新已成为影响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体系内,信用社产权改革圆满收官,管理创新棋至中盘,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都表明出以新的农村金融机构成立为主的组织创新开始成为改革的主角。在 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将“加快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放在了首位,凸显了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性。
多位学者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曾从不同角度对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周小川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人民银行要重点研究放宽准入,鼓励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创新等涉及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1]郭力认为,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上,现有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也需要以组织机构的保障为前提,因此,需要金融机构的创新。[2]张晓山认为,多元化的组织创新需要发育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作为依托,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3]李春生从功效体系角度出发,提出地方供销合作社应发挥网络、设施和信誉优势,积极参与到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创新中来。[4]本文对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和监管创新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二 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的地位
(一)组织创新是制度创新的更高阶段
根据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North)的解释,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变革。制度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这些收益在现存制度安排下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人为的、主动的变革现存制度中的阻碍因素,才会获得预期收益。[5]组织创新作为制度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同样服从这个规律,组织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创新的成本成为创新的原始动力。组织创新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企业内部的组织创新,一为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
在农村金融领域,相比较传统的业务创新,组织创新是更高层次的创新,它一方面联系着企业的管理层面的创新,如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再造对相应的管理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产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采用新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对产权创新和改革的冲击。组织创新的这种特点,成为系统性制度创新在后期阶段的必经之路,但同时也因为组织创新苛刻的前提条件而成为制度创新的难点。
组织创新的前提条件主要为:一,产权关系的明晰。因为组织创新要涉及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如果在产权上不能够明晰,将会增加创新的成本,甚至会产生负的激励效应;二,市场化环境的形成。组织创新所遵循的原则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要考量创新前后的收益和所付出的成本,以获取创新的动力,这就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在计划体制下,价格扭曲是制约创新的最大制度阻碍。如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企业的存在是由于节省了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只有在完全市场环境中才能计算出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才有企业创新的冲动。
在农村金融领域,上述两个前提条件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在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中,首要的着力点就是产权的改革和明晰;其次是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在新的农村金融理论范式指导下,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市场化进程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存的市场体系,为下一步的组织创新创造了条件。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使得组织创新具有独特性
我国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开始于 2003年,其宏观背景是新的中央决策层将“三农”问题提上了国家战略关注点,作为服务于三农经济的农村金融,开始进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2003年,我国农村金融最大的主体——农村信用社——开始了深化试点改革;2005年,小额信贷公司开始试点;2007年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后挂牌,村镇银行破局……经过几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国农村金融的多样化市场主体已经基本建立,为下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组织架构。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其中蕴含的深层次问题也开始逐一显露,迫切需要继续进行组织创新改革。
以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农村信用社为例,在 2003年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对农信社的定位是“市场化”,但同时又规定农信社支持三农工作的责任。这是一个基本矛盾的改革,农信社要想市场化,就会逐步脱离三农领域;要支持三农工作,就不能以市场化来指导改革。这极大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问题日益严重。再则,2003年的改革方案中,只是给了农信社一个改革大纲,缺乏细则。之后,农信社又似乎淡出了央行和银监会的关注视野,使得基层信用社要么囿于风险,固步自封,不敢改革;要么钻政策的空子,随意改革,酿成风险。
再以小额信贷公司为例,这是我国在农村金融领域最大的创新,但命运多舛。不仅在成立时央行与银监会存在认同上的不一致,在实践中也遭到歧视,尤其是“只贷不存”的特征,使得开办人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有些更成为给其他金融机构打工的“二级银行”。虽然银监会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转化成村镇银行的具体办法,但在实际运营中不断遭遇阻击,转化标准一再提高,不仅使中央政策大打折扣,也挫伤了投资人的积极性。
此外,农业发展银行的角色缺位,合作金融的止步不前,邮政储蓄银行的定位模糊等都对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消极影响。因此,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创新重点。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组织创新具有独特意义
2008年 9月,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形成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造成巨大影响。在农村金融领域,先是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普遍惜贷,原本供应“三农”的资金被大量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随后为应对危机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农村金融市场也迎来了资金相对充盈时期。纵观这一过程,农村金融基本是被动地迎合货币政策,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金融积累了新的风险。因此,发展根植于农村本土的金融组织如合作金融,就成为必然,而这一领域目前还处于相对空白。
另一个层面上,有效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可对外来的风险冲击形成对抗作用。一个地区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越是合理化、多元化和专业化,其对抗外来风险的能力就越大。以美国为例,在次贷危机中,投资银行的损失最大,全军覆没的几乎是单一的投资银行;其次是商业银行,资产大幅缩水;损失最小的是各类小的专业化银行,如联邦土地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相比之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就比较单一,一旦遭遇系统性风险,难免出现崩溃局面。因此,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发展更多的专业化农村金融组织,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
在监管协调方面,金融危机也提出了警告,现有僵化的金融管理体制不仅在预测危机方面全面失效,在危机的应对上也存在着沟通成本过大等问题。以我国为例,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存在着业务交叉区,这就为合法违规提供了制度激励,必须予以重视。
三 组织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金融市场结构
(一)合作金融机构将会成为农村金融的未来主体
农村金融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大背景。近年来,随着国有化的快速推进和商业资本大力介入,农民被迫从加工、运输、零售、流通储藏、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等领域退出,只能获得部分种养殖业的收入。在这个背景下,持续的“三农”利好政策,并没有给农民的收入带来提高。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真正主人,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这就需要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这也是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
在研究了大量现实素材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三农”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长期以来缺乏话语权,这使得惠农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让农民组织起来,即合作化。这里的合作化同 1950年代末的集体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是业务上的合作,不涉及产权,其特征可概括为: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非赢利性。[6]这正是“双层经营体制”灵活之处和核心所在。经过组织化、合作化的农民,才是现代化的农民,才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知道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上传自己的诉求的农民。因此,农民的合作化是未来“三农”工作应该坚持的主流政策。
在合作化的背景下,再来审视农村金融工作,答案就很明确,实行合作化金融。这里有两层关系:只有具有合作化金融参与的农民合作组织,才是稳定的合作化组织。缺乏金融这个内核,任何合作化组织都难以长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实行合作化金融,不仅可以激发农民的生产和还贷积极性 (借周围人的钱,还贷态度上自然不同于借银行的钱),还可以避免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甚至可以吸纳城市资金。实行合作化金融制度,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成了农民,农民也就真正掌握了话语权,农村资金的融通实现了错位发展和良性循环,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金融风险。在实践中,合作金融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现代金融市场不可缺的一部分,在金融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拥有信用社 11 000多个,社员 7 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不乏两会议员。[7]
在理论上,合作金融也符合目前世界范围内占据主流的农村金融发展新范式的要求。新范式体现了金融系统观理念,以市场化为核心。认为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不应取消,而应当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结合起来。而其理论先驱的微观金融革命和技术,更是在提供小额贷款方面具有优势,适合在农村地区广泛应用。[8]合作金融制度十分符合农村金融发展的新范式要求,原因有三:强调合作农民内部的资金积累,不仰仗外来的资金;不以盈利为目标,合作金融的盈利部分主要用来解决合作社内部的活动,如社员培训等;以提供小额贷款为主,是典型的微观金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合作性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工作的最佳突破口,要充分利用中央文件中关于“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利用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政策,围绕合作性金融这一主题,尝试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农村金融制度体系,合作金融机构也必将成为农村金融的未来发展主体。
(二)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进程有待加快
民间金融在我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远远超过正规金融。有了农业文明,就有了民间借贷,这是农村经济体系内生性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有其体制和历史的必然性。民间金融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在动力的情况下自发成长、壮大,充分说明农村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和环境,也从侧面说明仅凭正规金融机构是难以达到农村金融长期、稳定、充分发展的,这一点必须得到肯定。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偏见,民间金融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法律、政策层面也没有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民间金融只能偷偷摸摸地发展。发展至今,不仅有规模适中、经营规范、组织完备的民间金融机构,也有浑水摸鱼、违法经营、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组织。但必须承认,民间金融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在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温州,据温州市银监分局 2009年 3月的调查,在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由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是 54∶18∶28,而2006年三者之比是 60∶24∶16,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达 2 200亿元。[9]这说明,在从银行获得贷款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民间融资。
从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外经验来看,承认民间金融的地位,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正规化引导,纳入政府的统一监管范围是必须的,这就需要在立法上进行改革,给民间金融机构以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
由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各有优劣,从而使得它们有可能业务互补,形成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共存的格局。如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机构面临三大劣势:制度劣势,由于是体制内产物,受到的监管或者管制较多,相应的利益攸关方也多,常面临“船大难掉头”的局面,这在我国尤其明显;成本劣势,涉农贷款普遍具有数额少、交易次数多的特点,对正规金融机构而言,一笔小额款项和一笔大额款项的交易成本是基本相等的,这就加大了经营成本;信息劣势,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同时,民间金融也存在自己的劣势,主要是可用资金数额小和风险控制问题。这样优劣势共存和互补格局的存在促使双方进行相应的业务组合,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在保证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扩大农村金融资源的供给,比如“转贷”业务等。
民间金融合法化进程的加快,将会大大改善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形成良性竞争的格局,是基于存量改革前提下的组织创新突破,也会加快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三)民间剩余资金:制度通道是关键,组织创新是载体
在农村地区,一方面是金融资源供给普遍趋紧;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民间资金积累相当深厚,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要么闲置,要么“消费性内耗”和外流,存在极大的资金浪费。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的民间资金积累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受惠于体制变迁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我国的乡镇企业发展曾经独树一帜,贡献显著;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随着宏观经济紧缩时代的到来和自身技术、管理方面约束,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的乡镇企业能坚持住,并做大做强外,大部分的乡镇企业都处于倒闭状态。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些乡镇企业主手中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二是资源性行业的积累,尤其是 2003年以来,伴随着全球能源产品的涨价,分布于我国农村的各种小铁矿、小煤矿等小企业在短时间内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以山西省最为典型,形成了独特的“煤老板”现象,据初步估计,约有 4 000亿元的资金沉淀在山西民间,且大多在农村地区。
因此,在政策上进行积极创新,降低农村金融类机构的进入门槛,打通民间剩余资金良性循环的制度通道,加快组织创新的力度,提倡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主体发展,将这部分沉淀的资金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源供给,能极大地缓解现时农村金融资源供给的紧张状态,并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格局的形成。
民营资本利用积累的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同其他社会资本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民营资本发迹于当地,甚至借力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系统,对当地的社会生态、传统文化、人脉关系等比较熟悉,对贷款流向的一些农业项目也不陌生,这样可大大减少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信用风险,有利于贷款的回收。但面对的挑战依然不少,比如,金融知识的匮乏,政策解析的模糊,“只贷不存”的资金压力等等,但最大的难题还是制度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金融知识的普及,因为这部分民间资金的所有人普遍存在学历低、知识储备少的现象,再加上以前从事的不是金融行业,所以不能贸然鼓励他们投资农业;二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要谨慎,政府主要在于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法制环境,并严格按照《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保护资金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三是体制的变迁要因势利导,要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和改革。
民间剩余资本的“金融化”过程,不仅表现为一个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不断丰富和多元化的过程,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农村金融市场“有进有出”的局面,这对于未来持续的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具有示范和标本意义。
四 监管创新为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金融与标准化、市场化的城市金融在社会属性、目标追求、运行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体现在监管上,表现为对不同的主体要有不同的监管模式。现在的主导思维模式是用对城市金融的标准化监管来适应于农村金融,这势必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必须体现监管的差异性,进行监管上的创新,只有在监管上创新了,才能为接下来的组织创新创造条件。
(一)农村金融的监管要体现农村特色
农村金融的主要服务产业是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农业表现出弱质产业特征:生产周期长、回报率低、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等等,这使得各国政府对农业进行大力扶持,包括对农村金融。在这个背景下,如果用基于城市标准化的金融监管模式,不仅会使农业项目得不到贷款,即使得到了贷款,在后期的金融服务中效果也会降低。这就要求在监管体系上不仅要有金融监管部门,也要有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参与。这样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才是一个富有弹性和创造力的监管体系。
以农村金融发达的美国为例,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典型的“双线多头”模式。尤其是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它直属于美国农业部,负责监督美国农业信贷机构,这种组织制度较好地保证了农村资金用于农村和农业,并根据不同阶段农业的不同发展目标,调节农业信贷的方向和规模。而我国的农业部门则没有这种职能,只要是金融机构,都由银监会监管,不管是偏远山区的信用社还是都市金融中心的商业银行,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监管体系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甚至会产生制度扭曲效应,使更多的农村金融机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转变。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农村金融,有必要在监管体系上进行创新。尝试在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贷款方向进行把握的基础上,把农业、林业、水利等“涉农部门”加入到“涉农金融业务”的监管体系中。
(二)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要有制度基础
在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还处于“分业监管”阶段,不同的监管职能分属中央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风险、明确责任,是经过历次金融业危机后逐步发展来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监管制度。但我国的农村金融处于起步阶段,过于成熟和稳定的监管制度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形成,同时,部门间职能划分不明确,也让“监管内耗”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
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小额贷款公司是 2005年5月人民银行为了响应“新农村建设”而做出的创新之举,应该说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积极性,当年的试点省份很快成立了各自的小额贷款公司,但作为金融企业监管机构的银监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发出声音。直到 2006年 12月,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才初见端倪,但通篇不见小额贷款公司的字眼,这种状况让已经营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不清楚自已的位置。2008年 5月,距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整三年之际,银监会和央行才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准生证”才姗姗来迟。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和协调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组织创新的运作。
再以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运营为例,当初宣传的时候是金融机构,民营资本也是冲着这个金字招牌去投资的,进去了才发现是个“非企非金”的四不像。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大多流向了农村,却不仅不能享受如农村信用社一般的优惠政策,也不能享受银行的待遇。在税收上,小额贷款公司被当作一般工商企业来纳税,而银行是按利差所得纳税,形成了不平等竞争和政策歧视,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
因此,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协调必须有制度基础。在创新理论上,越是在创新活跃的领域,越要采取包容性大的监管措施,监管的成熟度和创新活动要逐步进行,一开始就实行僵化的监管制度,会对创新形成制约。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有贷款抵押等具体业务创新,也要有组织创新和监管创新。在农村金融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组织创新将会具有更大的作用,是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更高阶段。就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而言,金融供给主体的单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只有积极进行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降低农村金融业的准入门槛,依据农村金融需求特点成立更多新的金融机构组织,形成农村商业化金融、合作化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共同发展的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困境。同时,成功的监管体制创新将会为农村金融的机构运营和业务创新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也能为相应的组织创新提供政策支撑。只有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体系的最终完善,才会形成一个持续的激励机制,呈现出“加速创新”的局面,也才能实现我国农村金融的大发展。
[1]周小川.研究放宽准入鼓励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EB/ OL].(2008-10-23).http://u.peoplex2.com/25137/ 20090915142149.htm.
[2]吴红军.加快农村金融组织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 [N/ OL].金融时报,2009-02-05.
[3]张晓山.农村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 [J].理论视野, 2008(5):16-19.
[4]李春生.海峡两岸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讲话 [EB/OL].(2008-12-02).http://www.Chinacoop.com/print.aspx?id=18547.
[5]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s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张 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闫永夫.中国农村金融业[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8]Claudio Gonzalez-Vega.Lessons for Rural Finance from theMicrofinance Revolution[M]//Promising Practices in Rural Finance:Experience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2002:53-65.
[9]温州市银监局.温州地区民间融资调查[R].2009:3.
Rural FinancialOrgan iza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SHEN Pei-long1,2,SHEN Yi-gang1
(1.Faculty of Finance&B anking,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Taiyuan030006,China; 2.Applied Econom ic Research Institute,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Taiyuan030006,China)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develop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at present the reform of rural finance in our county hasmoved to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age,and in the system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innovations,such as business innovation.So,we should carry out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make the coope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main body of the rural finance,accelerate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private finance,open the institution channelof the private surplus funds,enhance the innov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finance,and ensure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rural finance;institutional innovation;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book=93,ebook=220
F830.6
A
1000-5935(2010)02-0093-06
(责任编辑 石 涛)
2009-07-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078);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晋规办字[2007]2号)
沈沛龙(1964-),男,山西襄汾人,山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方向的研究;
申毅刚(1982-),男,山西高平人,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工程与农村金融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