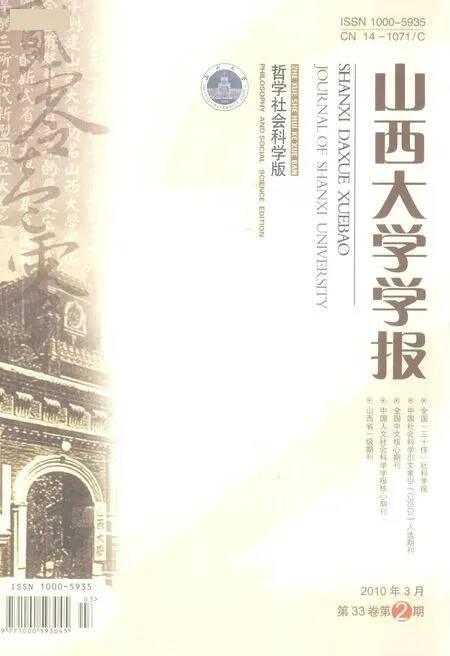再论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类工具书的立目
——以《新华语典》惯用语选条为例
吴建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山西太原 030006)
再论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类工具书的立目
——以《新华语典》惯用语选条为例
吴建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山西太原 030006)
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问题,既是汉语语汇学必须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语典编纂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常见惯用语工具书的收目做了分析比较,并结合《新华语典》惯用语的编写实践,给出了惯用语工具书收条的可操作性标准。认为,在“语”、“词”分立的前提下,“叙述性”是惯用语界定的首要标准;惯用语字数不受“三字格”限制,可以向多音节延伸;但应遵从公众语感,不接纳两字组条目。
惯用语;界定;《新华语典》;立目
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问题,既是汉语语汇学必须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语典编纂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在编写《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出版)过程中,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在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编写《新华语典》惯用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人们对惯用语的认识仍然大相径庭。因此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常见惯用语工具书的收目
在确定《新华语典》惯用语语目之前,我们先考察了市场上常见的以“惯用语”命名,且影响较大的6本工具书 (《中国惯用语》总 8 000条,《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总3 000条,《汉语惯用语大辞典》总 14 500余条,《汉语惯用语辞典》总 6 000条,《惯用语小词典》总 4 700条,《常用惯用语词典》总2 300条),并对其所收条目做了比较分析。
比较的结果令人吃惊:各本的收条,可谓五花八门,各行其是。其中 A字母收条情况:6本观点一致,都收录在内的条目仅有 1条:挨闷棍;5本收录的有 5条:挨黑枪、矮三分、矮一头、安钉子、安乐窝; 4本收录的有 11条:挨板子、挨千刀、挨枪子、矮半截、矮一截、爱面子、碍面子、安根子、安心丸、熬日月、熬心血;3本收录的有 15条:挨不上边、挨不上来、挨烙铁、矮一半、爱脸面、碍声名、安翅膀、安骨头、安乐死、安下脚、熬出来、熬到头、熬干灯、熬干血、熬尽油;2本收录的有 27条:阿Q相、阿木林、阿土生、挨肩儿、挨壳子、挨闷棒、挨闷雷、挨日子、挨软棍、捱上门、矮冬瓜、矮二寸、爱八哥儿、碍手脚、安本分、安坏心眼、安琪儿、安蛇足、安眼目、暗得灯、暗门子、熬不住、熬出头、熬灯油、熬点灯油、熬九九八十一难、熬月子;有 112条仅有 1本收录 (略)。
值得注意的是,高歌东、高鹏编纂的《惯用语小辞典》[2]以三字条目为主,表明其对惯用语的认识与高歌东、张志清所编《汉语惯用语大辞典》[3]有所不同,范围有所缩小,似乎又回到了 20年前的观点[4]5;而王德春在《新惯用语词典》[5]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常用惯用语词典》[6],虽然在语目上有了较多的调整,但收条原则尚未改变,“AA制、矮冬瓜、安心丸”等名词或体词性组合依然被收入在内。
我们同时考察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关于惯用语的两本教材。一本是苏向丽编写的汉英对照本《汉语惯用语学习手册》[7],这本手册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是对外汉语教材的一个新的尝试,但遗憾的是,在其所收的 300条“核心惯用语”中,被《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 5版)标为名词的就有 120余条,如“白眼儿狼、半边天、绊脚石、变色龙、丑小鸭”等。而“喝西北风、捅马蜂窝、八字没一撇、换汤不换药、干打雷不下雨、雷声大雨点小、不管三七二十一”等常用惯用语却没有收入。这就使其在实用方面打了折扣。另一本是郑伟丽主编的《惯用语教程》[8],这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语汇与文化”对外汉语系列教材中的一本,适用于汉语水平考试6级及以上水平的外国留学生。该教程选编了 570条“最常用的惯用语”,其中收录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问青红皂白、吃不了兜着走”等多字条目,但也同样收入了“安乐窝、八辈子、白眼狼、半边天”等名词,还收入了“拆台、吃透、吃香、下台”等两字组条目。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什么是“惯用语”的问题,目前尚未尘埃落定。
二 关于“语”、“词”分立
毋庸置疑,惯用语是“语”不是词。但是,“语”和“词”区分的问题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这就给惯用语的界定带来了难度。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汉语中“语”和“词”的界限在哪里,一直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首先是什么是“词”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甚至在汉语中究竟有没有“词”这样一个语言单位的问题,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从赵元任的“音节词”、“结构词”[9]894,到吕叔湘的“短语词”、“语法的词”、“词汇的词”[10]498,再到徐通锵的“字组”[11]365、冯胜利的“韵律词”[12],几代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孜孜不倦地观察和探讨“词”的问题,一步步将研究推向深入,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说明了词汇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艰难性。
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语”的研究一直包含在“词”的范围之内。什么是“语”?“语”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语”是不是“词”的等价物?不同的工具书所给的答案并不相同;不同的研究者也持不同的看法。鉴于此,温端政提出了“语”、“词”分立的主张。[13]他认为,“语”不是“词”的等价物,它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大于词的语言单位;“语”虽然和词一样,都具有整体性,但“语”不是概念性的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如果说“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那么“语”则应当定为“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成语和惯用语。汉语里所有语的总汇,叫做语汇。[14]17“语”、“词”分立的主张,为“语”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也为语类工具书的编写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赵元任先生曾经说过:“哲学家和科学家似乎专门喜欢用违反常情的方式来给词下定义。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想给词下定义,而是试图设立精确的概念。他们只是想用紧凑而成形的词来做概念的标签。一旦新的用法站住了,词典当然要记录在案。”[9]891《新华语典》的编写,就是试图将“语”、“词”分立观点“记录在案”的一次实践。
三 《新华语典》惯用语的立目标准
(一)“叙述性”是首要标准
按照语汇学理论,“语”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14]17这一点,与表示概念的“词”截然不同。在界定惯用语时,我们首先从语的“叙述性”这一根本特点入手,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
经过反复筛选,我们为A字母选定的条目是:
挨板子、挨不上边、挨打不记数、挨当头棒、挨黑枪、挨了巴掌赔不是、挨了雹子又挨霜打、挨闷棍、挨千刀、挨日子、挨一刻似三秋、挨一天算一天、挨砖不挨瓦、矮八辈、矮半截、矮三分、矮一头、矮子队里选将军、矮子面前说短话、爱财不要命、爱面子、碍面子、碍手脚、安钉子、安眼目、按倒葫芦瓢起来、按定坐盘星、按葫芦画瓢、按老方子吃药、按老皇历办事、按着葫芦抠子儿、按着牛头喝水、熬出苦井又跌进了火坑、熬干血、熬胶不粘做醋不酸、熬了星星盼月亮、熬过初一等十五、熬日子
可以看出,我们认定的惯用语,都具有叙述性,也就是说,都带有谓词性成分。据此,以往多数人认为是惯用语的“安乐窝、安心丸、安全岛”等,因其鲜明的体词性被我们认定为词而请出了惯用语的行列。
这一看法,与马国凡、高歌东先生曾经指出的,惯用语多数是“动宾结构词组”,其核心部分“是三音节的动宾关系固定词组”中的“动宾关系”[4]5有相似之处,但是范围扩大了很多。
至于如何区分惯用语和同样都具有叙述性的其他语类,我们认为,可以分层次来认识。[14]71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惯用语和歇后语在形式上的区别十分明显,一般不易混淆。例如同样是形容你看我我看你,彼此尴尬或束手无策的神情,惯用语说“大眼看小眼”,歇后语说“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惯用语和成语的区别从形式上看也比较明显,那就是四字惯用语是非二二相承的,成语是二二相承的,例如“吃大锅饭”是惯用语,“吃苦耐劳”是成语。
惯用语和谚语有时在形式上不大好辨别,就需要从语义层面来区分。惯用语不具知识性,只是描述一种情况或状态,而谚语以知识性、哲理性为基本特征,以传播知识、传授经验为目的。每一条谚语都会告诉人一个道理或者对人进行某种警示和劝诫。这一点,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得理不饶人”指人占了理就揪住别人的缺点不放,描述了人的一种态度,不含知识成分,是惯用语;而“得理让三分”则告诫人即使占理也不能把事情做绝,应该留有余地,阐明了做人要有度量,能包容的道理,是谚语。同样,“得了便宜还卖乖”描述人实际上得了好处,却刻意掩饰并假意送人情,是惯用语;“得便宜处失便宜”告诫人不要太贪婪,得失总是如影随形的,在什么地方占了便宜,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吃亏,是谚语。
(二)不受“三字格”的限制
惯用语要不要受字数的限制?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惯用语多数都是三个字的。这一观点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影响逐渐扩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上述马国凡、高歌东所言[4]5;又如:“惯用语的形式,大部分为三字格”[15];“惯用语在音节组成方面,以三个音节为基本格式”[16]75;惯用语“在结构形式上以动宾结构的三字格为主体,……也有不少非动宾结构的三字格”[5]2;“惯用语的结构就是以三字格为代表的”[17];“惯用语是具有超字面意义功能,三言口语化习用短小的固定词组”[18]383。周荐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凡“三字格”都应该算作词,惯用语只能是非三字格的一部分俗语[19]。
温端政认为,惯用语在结构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表示完整意思的句子,一类是不表示完整意思的词组。“后一类惯用语,从字数上看,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还有十来个的,如‘碰钉子’、‘喝西北风’、‘坐山观虎斗’、‘拆东墙补西墙’、‘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等等”[20]4。孙维张的认识与此大体一致:“汉语惯用语的结构形式的特点不在于是否短小,也更不是什么‘三字’结构”,“少则三字,多则七字、八字不等,甚至有十几个字的”[21]199。
我们认为,温、孙的观点是符合惯用语实际情况的。从“叙述性”和“描述性 (描绘性)”出发认定的惯用语,突破了三字的束缚,这就“使得惯用语的界定从‘三字组’和‘意义双层性’的纷争中跳了出来,在语汇的大家族中,具有与歇后语、谚语和成语完全不同的区别性特征,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可操作性”[1]11。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对《现汉》(第 5版)所收的三字条目以及三字惯用语作了初步统计。见表 1。

表1 《现汉》三字条目相关统计表
统计表明,在《现汉》(第 5版)所收三字条目(不含两字加儿化的条目)中,可以确定为惯用语的占三字条目总数的比例还不到 8%。其余的条目多数被《现汉》(第 5版)加了词性标记,其中,标记名词的多达总数的近 80%。
郑庆君认为,汉语三字格多为偏正式的,“由于偏正式中的中心成分主要为名词性质,因此‘定 +中’型便占据其中优势,这反映了汉语三字格的词性化倾向——名词性质。同时也表现出三字格的词汇意义特征:多是表示事物 (具体的抽象的)名称的词语”[22]。我们的统计结果印证了这种观点。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在“语”、“词”分立的观点被更多学者接受以后,《现汉》中的少数惯用语也将会从“词典”中脱离出来,纳入到“语典”之中。《词典》收词,《语典》收语,名副其实,各司其职,这对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汉语,促进语言学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武占坤在《汉语熟语通论》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时代在变,语言事实也在变,惯用语的形式,除尚保持三言的主流外,分流变得五花八门,‘四言形式’、‘五言形式’的惯用语,变得亦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惯用语特点的五言式的俗语句可以视为惯用语,那么多一个字的六言式,甚至多两个字七言式的俗语句就不惯用,不能成为惯用语吗?你有什么雄辩的理由来说这一字之差就有惯用不惯用的区别呢,所以我对惯用语总的定义去掉字数三言的限制是赞同的。”[23]122武先生的话代表了一些学者对惯用语在认识上的转变。
这里还涉及惯用语和“狭义俗语”[24]的区别问题。事实上,惯用语和所谓的“狭义俗语”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仅从字数上人为地把它们分为两类,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对“俗语”这一术语的浪费。不能否认,在“语”的家族里是有“雅”、“俗”之分的,保留广义“俗语”的概念,而取消“狭义俗语”,摆脱其与惯用语的纠缠,对“语”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说利大于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辞典的收目》[1]一文中已经做了阐述,此不赘述。
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对《新华语典》惯用语条目作了甄别筛选,初步选定了 6 884条。表 2是我们对所收惯用语条目字数的初步统计:

表2 《新华语典》惯用语条目字数统计表
可以看出,三字组的条目在总条目中只占了1/4的比例。因此,我们认为,三字组条目是惯用语家族中的大户,但是,并不是“多数”或“大部分”。惯用语并不是“以三字格为主”的,它的字数多少不等,少则三字,多则十余字,甚至有少数条目达到十六七个字,例如“白昼吃饭不知饥饱,夜晚睡觉不知颠倒”、“自个儿挨饿,倒把白面卷子送给别人吃”、“在河里的人不着急,在岸上的人倒急坏了”等,都可以纳入惯用语的行列。
(三)不收两字组条目
我们说惯用语不受“三字格”的限制,往上可以向多音节延伸,那么往下是否也可以持宽容态度,把“吃醋、出血、吹牛、帮腔、露丑、碰壁、说嘴、松绑、跳槽、砸锅”等两字组条目收纳在内呢?在第一部分列举的一些惯用语工具书中,也或多或少都收入了这类两字条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在《新华语典》惯用语编写中,采取了一律不收的做法。这样处理,主要基于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参考了《现汉》(第5版)的做法。《现汉》(第 5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给词标注词类,大于词的单位,不作任何标注。“双字条目,除极个别难以归类的 (阿门、南无)之外,一律标注词类。其中有极少数条目从语法角度看是词还是词组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从词汇角度看都可以算作词,因此都标注了词类。”“惯用语 (穿小鞋、人来疯、活见鬼、开门红)、成语……都看作非词,不做任何标注。”[25]《新华语典》惯用语不收双字条目,与《现汉》第 5版的体例保持了一致。
第二,从语感来说,两字条目更容易被普通读者认为是词。普通读者不会像语法学家那样分析两字条目的成分是自由还是黏着,能否插入扩展,成分能否平行周遍地替换,成分义加结构义是否等于整体义,等等。这一点,可以从王立所进行的 3次分词抽样调查中得到证明。从王立的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十分倾向于将”双字组合“认定为词,反映出公众词感的一致性”。[26]吕叔湘先生说:“从词汇的角度看,双语素的组合多半可以算作一个词”,“拿到一个双语素的组合,比较省事的办法是暂时不寻找有无作为一个词的特点,而是先假定它是词,然后看是否有别的理由该认为是短语。”“在这里,语素组合长短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10]495-496王立关于“双字组合”认定为词的公共调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吕叔湘先生此说的正确与睿智。
第三,从这一类两字组的发展趋势来看,固化进而词化不可避免。“双音词有三类主要历史来源,一是从短语降格而来,二是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三是从本来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27]6从短语降格而来的一些两字条目,正处于“词化”过程中,可离可合,扑朔迷离。从音节的角度将其与“语”暂时区分开来,顺应发展趋势,符合公众语感,比较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
赵元任先生曾经说过:“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学者都同意,对于所研究的对象语言,不应该刻意去寻找在我们从前就碰巧会说的那种语言中十分熟悉的那些东西,而应该确定我们实际上碰到了什么,并给它们以适当的名称。”[9]891我们对《新华语典》惯用语立目的思考,力求理解和体现前辈的这一思想。
[1]吴建生.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辞典的收目[J].语文研究,2007(4):10-17.
[2]高歌东,高 鹏.惯用语小词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
[3]高歌东,张志清.汉语惯用语大辞典 [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
[4]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5]王德春.新惯用语词典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6]王德春.常用惯用语词典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7]苏向丽.汉语惯用语学习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郑伟丽.惯用语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9]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M]//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汉语语法论文集.第2版.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徐通锵.语言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一章.
[13]温端政.论语词分立[J].辞书研究,2000(6):1-10.
[14]温端政.汉语语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汉语惯用语简说[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6):87-101.
[16]高歌东.惯用语再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17]李行健.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前言.
[18]王 勤.汉语熟语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9]周 荐.惯用语新论 [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 128-139.
[20]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前言.
[21]孙维张.汉语熟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22]郑庆君.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J].山西大学学报,2003(1):68-71.
[23]武占坤.汉语熟语通论 [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
[24]王 勤.俗语的性质和范围[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4(4):107-111.
[25]徐 枢,谭景春.关于第 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J].辞书研究,2006(1):25-35.
[26]王 立.汉语“字/词”公众语感的测量[J].语言文字应用,2002(3):53-59.
[27]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节词的衍生和发展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Re-discussion about the Defi nition of Idioms and Its Entry i n Idiom D ictionary——In the Case of Idiom Selection in CompilingXinhua Idiom D ictionary
WU Jian-she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hanxi Social Science Academ y,Taiyuan030006,China)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properties and scope of the idioms is notmerely a theoretical problem that is necessary to be solved in Chinese idiomology,but a practical problem involved in lexicography.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this paper provides practical criteria of idiom dictionary,in comparison with contemporary idiom dictionaries and concrete practice in the compilation ofX inhua Idiom D ictionary.It ismaintained that narration is the primary standard of the definition of idioms,providing the separation of"word"from"idiom".Accordingly,idioms can be extended to multi-syllables rather than restricted to the three-syllabic format.However,it is suggested that two-syllabic items should be excluded following the language sense of the native speakers.
idiom;definition;X inhua Idiom D ictionary;entry
book=83,ebook=215
H16
A
1000-5935(2010)02-0083-05
(责任编辑 郭庆华)
2009-08-31
山西省社科院重点科研项目(09SKY-ZD)
吴建生(1954-),女,山西万荣人,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山西方言和汉语语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