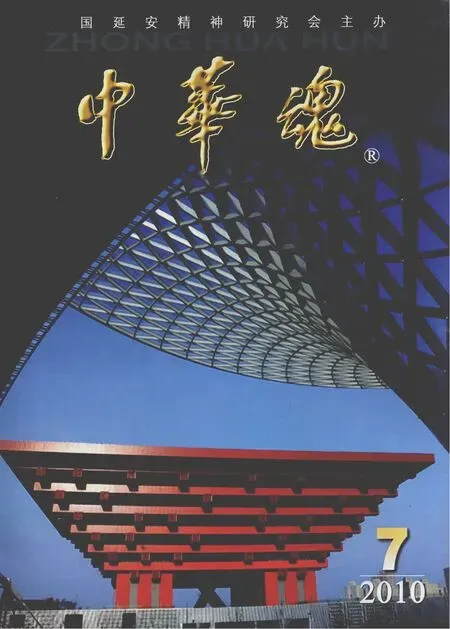从父亲与毛泽东见面赠书说起(上)
——也谈善于学习的毛泽东
文张 复
从父亲与毛泽东见面赠书说起(上)
——也谈善于学习的毛泽东
文张 复

1
许多年前,我学习毛泽东著作,看到在 《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里有这样一段话:
“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 《再论民族问题》。……”
我问父亲:“爸,主席写 《新民主主义论》时认识你吗,他怎么在书里提到你的名字呢”。
“哦,主席那时不认识我,我是1940年5月到延安后才认识主席的”。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回忆起往事……
1939年8月底,周恩来途径迪化 (今乌鲁木齐)去苏联治疗伤疾,在新疆曾面对面地与盛世才周旋过。他深知新疆环境险恶,到苏联后托同在苏联治病的毛泽民,回新疆后转告父亲和茅盾可以去延安。直至1940年5月初,父亲与茅盾才在毛泽民的运筹和安排下,利用种种借口,巧妙地摆脱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魔爪,转道兰州、西安去延安。他们走后不久,张学良的好友、也是邀请他们去新疆工作的杜重远即惨遭杀害,至今连尸首也找不到。
1940年5月26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父亲和茅盾随朱德等人从西安一起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经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的安排,父亲与茅盾在延安南关的招待所里住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即去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张闻天是父亲留学苏联时期的老同学,见面后格外亲切,父亲与毛泽东则是第一次见面。
父亲回忆说: “主席长时间以来有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他先去看望茅盾,他与茅盾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去看望我时做了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来到我的住处,他身材高大,湖南口音,衣着朴素,两人的话题从我留学苏联的见闻,苏联的理论家、哲学家米丁、罗森塔尔、尤金等,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及其知名文化人士的状况,谈到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关于殖民地革命的一些著作、观点,以及我翻译、编辑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兴致高时,还手里夹着烟卷在窑洞里来回走几下,看得出,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界的情况,对苏联的少数民族问题,对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其观点十分熟悉,他还由这些著作、观点谈到了中国革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等等。”毛泽东与父亲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一个通宵。
在父亲简短的口述回忆中,提及了毛泽民,我想他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中谈到毛泽民的话题不会少,一是危急时刻,毛泽民积极筹划和安排父亲与茅盾撤离新疆脱离险境,二是毛泽民在苏联治病期间,应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写了许多资料,真实地向共产国际陈述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是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他刚回到新疆时间不长,毛泽东会挂念处境危险的这个胞弟,他曾深情地对人说过:“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
滞留在新疆的毛泽民最终未能逃脱盛世才的魔爪,于1943年惨遭杀害,与他一同被害的还有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等人。
那次见面过了一周,毛泽东又在两三个人的陪同下来看望父亲,随后他托人把自己三四个月前刚出版的 《新民主主义论》和1938年5月写的 《论持久战》两部著作亲笔签名赠给父亲,还特意把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第四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手稿给父亲留下,意思是要父亲对此一章节提一些意见,以便日后该书再版时考虑作些补充或修改。
父亲回忆说,毛泽东的谦虚、好学、博学,以及他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的能力,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么,你翻译的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那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我问父亲。“这本书是1938年底在汉口由生活书店出版的。”父亲回答。也就是说,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毛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找到并且熟读了这本书,还在写作 《新民主主义论》时参考和引用了其中的观点。
父亲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初期,他联系中国的国情,有针对性地搜集了一些斯大林谈有关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以及殖民地革命的资料,其中一部分翻译、编辑成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父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中国地广人众,民族众多,在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抗战的今日,怎样彻底实现中山先生民族主义——对外求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对内实行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更引起各方的注意。以此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实在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
不可否认,斯大林在其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述中,有简单化的倾向,个别论断甚至有缺陷,对中国革命也有过错误的意见。但是,斯大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后来多次赞扬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认为他的这一论断正确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和主要形式,“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而斯大林写的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在发表的当时,就被列宁称之为在民族理论文献中“首屈一指的论文”。
毛泽东著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影响,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毛泽东在书中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的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它使人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一个东方大国的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2
那一次,毛泽东同时送给父亲的另一本书是他在1938年5月写就的 《论持久战》。这本书似乎仍然与父亲有“缘分”。
1937年底上海沦陷,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汉口,父亲与邹韬奋、金仲华、钱俊瑞等由香港到达汉口后,除了与邹韬奋等抓紧出版 《抗战三日刊》外,他还与胡愈之、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钱俊瑞、柳湜、杜重远等组成和充实了书店编审委员会,他们出版了一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籍,还着重出版了一大批抗日救亡方面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著的 《论持久战》,此外还有宋庆龄著的 《中国不亡论》、叶剑英著的 《武汉广州沦陷后的抗战新局势》,还有其他学者著的 《战时的日本问题》、《论抗战期中的文化运动》、《近六十年的中日关系》等。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撰写的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在抗战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市场。《论持久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的时候,《论持久战》在人们面前那样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 《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父亲来到延安以后,才有条件看了不少毛泽东写的著作。来到延安半年以后,他在1940年12月29日延安出版的 《解放周刊》上刊载的 《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榜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节里由衷地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不仅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恩、列、斯的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的 《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除了 《联共 (布)党史》而外,这是中国共产党现在跟世界上其他各兄弟党比较,可引以自傲的地方。”
为什么毛泽东能写出 《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从而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还要从大革命失败后说起。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最初的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没有达到预期占领中心城市的目标。毛泽东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他认为必须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出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在敌人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在全国中心大城市起义暴动夺取政权。这条独特的中国式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这条独特的中国式道路在理论上最好的阐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早期实践中最好的表述之一。
就在井冈山根据地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党中央领导层突然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愤青”,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0日退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开始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这次战略转移基本是无准备的仓促上路。加上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领导者采取消极避战的军事逃跑主义路线,使中央红军再次蒙受巨大损失,至突破敌湘江封锁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仅剩3万多人,其伤亡减员之大,在红军战史上是空前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简称遵义会议),检查、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实行的军事指导路线、方针及战略战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重掌“帅印”后马上面临重大考验。这就是如何率领全军迅速摆脱四面包围之敌。1935年1月19日,也就是遵义会议仅仅结束两天,从这一天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5月9日渡过金沙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3万多人,四渡赤水河,北渡金沙江,转战几千里,大小战役战斗40余次,歼敌1.8万余人,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的企图,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此,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革军委的领导下,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为什么毛泽东能在井冈山多次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什么毛泽东又能带领红军在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简单地说,就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读无字书,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制定战略战术,不教条,不盲从,不机械。
毛泽东常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大革命失败后,他发动秋收起义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几仗,及时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法书,更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指挥打仗是靠 《孙子兵法》,靠 《三国演义》。据毛泽东说,那时他还没有读过 《孙子兵法》。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最主要的是他有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他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的,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
回首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党从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自己独特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回首丧失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损失大半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要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中,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同时,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以极深的印象,毛泽东到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后,提到这场争论时说过,“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读书学习的一个高峰。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不可能出版齐全,长征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就尽可能地广泛地收集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在马、恩、列、斯的原著中,毛泽东读得最多、最下功夫的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其中,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的列宁的 《两个策略》、《“左派” 幼稚病》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许多批语,还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圈、点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 “二读”,某年某月 “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哲学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了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外,他还批阅了许多中外学者撰写的哲学著作。斯诺在1936年10月写的《西行漫记》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连续写出了 《实践论》、 《矛盾论》两篇哲学名著,他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必须研究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特殊性。
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艾思奇、何思敬等人发起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其宗旨是研究、学习和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40年6月21日,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艾思奇、周扬、范文澜等五十多人出席,会上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茅盾和父亲也出席了这届年会,父亲还在张闻天、朱德、郭化若之后作了发言。会后,毛泽东在延安西北饭店,用他的稿费,摆了几桌简单的酒菜,请代表们吃晚餐,以示庆祝。父亲在延安经常参加“延安新哲学会”举办的各类报告会或座谈会,父亲回忆说,看到经常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艾思奇、周扬、何思敬、吴亮平、郭化若、范文澜、柯伯年等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为了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商议后决定,1938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由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任院长。
父亲1940年春到延安后,中央分配他去中宣部工作,并在抗大、女子大学等处讲课,同时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她的回忆录中说:“马列学院成立了一个编译部,专门从事十卷本 《马恩选集》和十卷本 《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闻天亲自指导,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有张仲实、王思华、何锡麟等,他规定任务,每天译一千字,一年三十六万字。生活上对他们很照顾,派了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人每月发四元五角,那时政治局委员们也只有五元钱。闻天得到了外文版的书刊,就亲自送到编译人员的住地。编译部在马列学院的后山,他总是不怕劳累,爬山走去。”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对理论学习是多么重视。
也是在创办马列学院的这一年,1938年10月,为了在特殊的复杂的中国环境下更好地担负起党在抗战中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学习”一节中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在联系实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不仅因为历史就是过去的实际,还因为博大精深的东方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会给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因素和新的活力。
也是在“学习”这一节中他又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接着,毛泽东继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