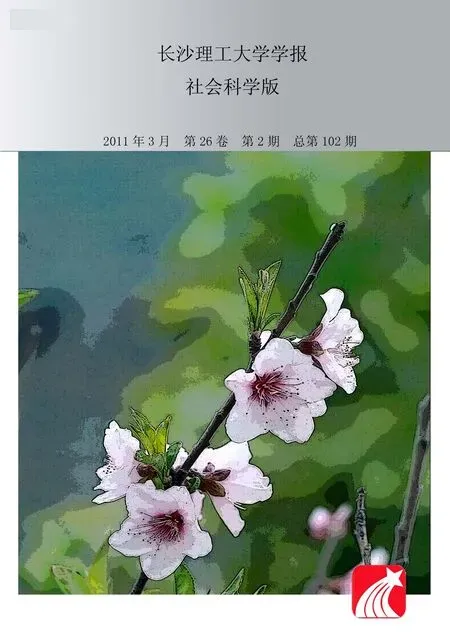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
綦保国
(仙桃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仙桃 433000)
官营工商业在中原汉地起源很早,《国语·晋语》中就有“工商食官”的记载。“工商食官”是西周时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即主要手工业和商业部门由官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业制度。[1]官营工商业制度经秦汉,历唐宋,虽时有变迁,但官府直接经营管理大量工商业经济,为皇室贵族和各级政府提供各种消费品和奢侈品,为国家财政节约开支并获得大量利税收入,一直是中原汉地历代封建王朝经济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大蒙古汗国建国之初,国家机构虽然已经产生,但更多的是一种军事组织机构,而不是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将征服和掠夺视为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还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但随着汗权的扩张,国家的大量财富汇聚到汗权的控制之下,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日益突显。特别是征服中原汉地之后,汉族地区的中央封建集权文化和经济管理制度,日益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重视,并逐步得到采纳和仿效。其中,中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就是伴随着“黄金家族”共有财产权的形成及管理体制的官有化,而在这一时期被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并付诸实施的。
一、成吉思汗时期官营工商业制度的萌芽
大蒙古汗国建国之后,随着掠夺财富的积累,蒙古社会对生活必需品及奢侈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不断的征服战争,对兵器、战车等战争器具也需要不时地补给。因此,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大蒙古汗国早期,蒙古社会的工商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基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私有财产制度,工商业的经营主体并不是国家,而是私营工商业奴隶主。
在早期的征服战争中,蒙古统治阶级就十分重视保护手工业工匠,实行“唯匠屠免”的军事政策。但对俘获来的大量手工业劳动者,大汗经常将他们如同掠夺到的财产一样,由各部落蒙古贵族象占有无主财产一样占有和使用,或者象分配猎物一样分配给他们属有。正如《史集》所载,蒙古军队攻陷一座城后,“分出手工业者和工匠,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分配与各蒙古亲王贵族为奴”。[2]成吉思汗在攻陷撒麻耳干后,把三万有手艺的人挑选出来,分给了他的诸子和族人。①蒙古军兵临费纳客忒城下,在允准该城乞降后,他们将“士卒和市民给分为两队:前者悉数被歼,有的死于刀下,也有的死于乱箭,而后者则被分配给百户、十户。工匠、手艺人、看猎兽的人,分配(给百户、十户)”。[3]在早期征服中原的战争中也是如此,“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4]“命镇海世掌焉”,实际上就是将这些工匠赐予给镇海作为其投下私属人口,并归其世袭拥有。
在将俘虏的手工业工匠进行分配并组织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成吉思汗本人拥有的大量工商业,一是中原汉地旧有的大量官营工商业落入地方政府的世官世侯之手。这两种形态的工商业都为后来蒙元统治者发展官营工商业提供了基础,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看,这两种工商业也是元初官营工商业的萌芽形态。
成吉思汗除了把大批俘获的工匠分赐给蒙古贵族亲王外,自己还拥有庞大的私属工匠。这些工匠一部分从事各种民用手工业生产和建筑,一部分则编组为匠军,生产、修理武器或者在行军、攻战时开辟道路、架桥、造船。例如,在成吉思被拥立为乞颜部首领时,就曾命令古出沽儿管修造车辆;到成吉思称汗时,他又将古出沽儿管理的手工业部门扩充到一千户。[5]匠军在太祖西征花剌子模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军种,“高闹儿,女真人。事太祖,从征西域;复从阔出太子、察罕那演,连岁出征,累有功,授金符,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匠军”。[4]再如,“(张荣)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庚辰八月,至西域莫阑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子奴婢,袭佩虎符、炮水手元帅,领诸色军匠”。[4]从一月造船百艘的速度上看,张荣所领军匠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元初官营工商业制度形成过程中,更具积极意义的一种工商业形态是汉族世官世侯们所把持和拥有的中原汉地旧有的官营工商业。所谓世官世侯,时人当时评论说:“诸侯如史、如李、如严、如张、如刘、如汪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唬将劲卒,茬习兵革,骑射驰突,视蒙古、回鹘尤为猛鸷。”[6]太祖初征中原时,目的只在掠夺,对经济恢复与建设并不重视,因此,将征服后的各项行政和经济管理事务悉数付诸当地诸侯“便宜行事”。例如,太祖曾经授刘敏“安抚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道、司天等事,给以西域工匠千余户”。[4]因此,燕京路的官营盐铁诸业的经营管理权甚至所有权均落入了刘敏之手。又如,“太祖,丙戌,赵柔……以功迁龙虎卫上将军,真定涿等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总管”。[4]再如,“太祖十六年,(李)全叛宋,……太师国王孛鲁承制拜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杨州,败死。亶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4]直至世祖中统二年(1261)仍“命李亶领益都路盐课”。[4]由于缺乏系统的正式的税赋制度,大小诸侯把持这些盐场、银冶,只是将很小一部分利润贡献给蒙古大汗,大部分则归自己属有。有些诸侯食髓知味,甚至表示:“愿辞监军之职,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岁献织币,优游以终其身,于臣足矣。”[4]
二、窝阔台时期官营工商业制度的草创
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汗位,“国家财产”的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国家财产”成吉思汗的汗有财产随之解体消散,取而代之的“国家财产”不再是窝阔台汗的汗有财产,而是“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这种财产权的公有性或者说共有性,为窝阔台汗时期官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财产权制度基础。
为了经营和管理“黄金家族”共有财产,太宗在1231年设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建立了管理国家经济和经营官有工商业的专门官僚机构。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230年,太宗就命耶律楚材“举近世转运司例,经理十路课税,易司为所,黜使为长”,[7]“始置十路徵收课税使(所)”,成立了经营、管理国家经济的地方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地方政府财赋的征收和官营盐铁等手工业的生产经营。耶律楚材本人身受汉文化影响,对中原旧制官营工商业制度十分推崇。耶律楚材在课税所所用之人,“凡长贰悉用士人,……参佐皆用省部旧人”,[4]即为中原儒士及金代中书省遗臣。因此,元代的官营工商业思想及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深受中原汉法特别是金代律令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为了改变“官无储待”的财政状况和解决“岁赐”及“南伐”之需,耶律楚材主张恢复和重振金代中原的官营课程禁榷工商业主要是盐铁业。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的建议,于1230年春正月“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4]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在1230年元政府就先后设立了河间课税所,“置盐场,拨灶户二千三百七十六隶之”;益都课税所,“拨灶户二千一百七十隶之”;并“立平阳府征收税课所,从实办课”,经营解州池盐。[4]官营铁冶业在稍后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太宗丙申年(1236),立炉于西京州县,拨冶户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1237),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一千煽焉。”另外,在檀、景等处,太宗也在1236年拨户于北京煽炼。[4]官营课程禁榷工商业的设置和营运,很快取得了实际的财经效果。1231年秋,窝阔台至云中,十路课税所“咸进廪籍及金帛”,窝阔台看后,大赞耶律楚材贤能,“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自此,财经钱谷之事,事无巨细,皆先决于楚材。[4]
另一方面,官营造作手工业在此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太宗七年(1235),城和林,作万安宫。因为营造和林城和万安宫等宫殿的需要,大量的汉地手工业工匠被迁往漠北和林,从事官营造作手工业劳作。据《史集》记载,为建造各种建筑“彼(窝阔台)自契丹发来各色工匠,令于彼大部分时间居住之福地哈刺和林建一高耸之建筑,承以高大之柱,使与如此崇高之国王之决心相一致。……此等建筑皆采取尽可能优美之式样,饰以各种彩画”。在宫殿建成之后,窝阔台又命“杰出之工匠打造储酒之金银器皿,形如象、狮、马等动物之形状,皆置于大桶之下,满贮酒及马奶。其前又各置银盆,酒及马奶自此等动物之口中流出,而至盆中”。[2]大量的宫殿建筑业和金银器皿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官营手工业劳动人口,以致在漠北和林形成了一个汉人工匠生活区,“城里(和林城)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9]
除了在和林城聚集有大量满足蒙古统治者生活需要的官营手工业之外,地方政府也大量设置和经营手工业局院,造作织品、军器等政府消费品。牙剌瓦赤治理西北河中地区时,“各城建立了为官家工作的大作坊‘科尔霍纳’,最早见于记载的这种作坊,是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途思的科尔霍纳。为这样的作坊建筑了特别的大房屋。这些作坊生产衣服、武器、军队装备和玻璃器皿等物”。[10]中原地区更是如此,例如,太宗四年(1232),直脱儿“收河南、关西诸路,得民户四万余,……八年,建织染七局于涿州”。[4]军器制造业一直受到元太宗的高度重视,精于制造兵器和铠甲的手工业工匠往往被委以重任,授予管理官营手工业的官职。例如,浑源人孙威,“善为甲,尝以意制蹄筋翎根铠以献,太宗亲射之,不能撤,大悦。赐名也可兀阑,佩以金符,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4]蒙元军器工业的发展,为蒙古军东征西讨取得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金天兴二年(1233),金哀宗总结蒙古军取胜的原因时,感叹说:“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4]
窝阔台时期,对官营造作手工业的管理立法也初具规模。“时工匠造作,靡费官物,十私七八,楚材请皆考核之,以为定制”。[4]同时,对于工匠的口粮,也开始有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匠人每造作呵,验工程与粮有来。”[11]另外,在耶律楚材陈时务十策中,“选工匠”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工匠户籍制度,即把工匠从一般民户、军户、站户等户籍中分立出来,单立匠籍,加以管理,有可能起始于此。太宗时,对重要手工业品的样式已经作出了具体且严格的规定,例如太宗六年(1234),谕条令曰:“……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论罪,即聚财为更娶。”[4]这种产品程式的规定,应该既适用于私造织品,也适用于官营工商业品。
官营工商业制度,在太宗窝阔台时期仍然还处于草创之初,当时这些制度既不完备又不稳定。例如,太宗初定天下课税格,定额为银1万锭,即五十万两,然而“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4]这种课税“扑买”制度既不符合元代“定其岁入之课,多者不尽取,少者不强取”的课税原则,同时,也表明窝阔台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官营工商业的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甚至根本就不想由政府经营官有工商业或由政府承担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责,而只是简单地将天下税课“扑卖”给富人和商人,直接获取超经济的政权利益。“扑买”制度遭到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但太宗不为所动,“姑令试行之”,楚材竟力不能止。
三、忽必烈时期官营工商业制度的建立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府召集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建元中统,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地方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中原汉地已经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然而,在忽必烈即位之初,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可以说是外有未戢之兵,内有不贰之臣。在国家经济基础方面,由于连年征战,文治多阙,人们流离失所,逃散在战火及鞭笞之下,经济生产破坏十分严重。
从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来看,一方面,忽必烈政权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用以平定阿里不哥漠北之乱和稳定汉地诸侯和蒙古诸王分裂势力之心;另一方面,国家急需休养生息,以苏民瘼。这种国家财经困窘在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与离中书左丞之职赴大名等路宣抚之任的张文谦之间的一段对话中可见一斑:“(张文谦)语文统曰:‘民困日久,况当大旱,不量减税赋,何以慰来苏之望?’文统曰:‘上新即位,国家经费止仰税赋,苟复减损,何以供给?’文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十之二”。[4]在这种“何以慰来苏之望?”与“何以供给?”的矛盾中,国家急需一种“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不赋百姓而师以赡”[12]的经济制度。无庸置疑,这种所谓的“差发办而民不扰” 的经济制度就是中原汉地自古有之,而又被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所推行的官营盐铁等工商业制度。
当然,世祖忽必烈及王文统、阿合马等理财大臣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方面,以蒙古守旧势力、汉地世官世侯为代表的权豪势要之家出于自己的工商业利益必然坚决反对官营工商业制度。另一方面,以许衡、姚枢、窦默等为代表的义理派儒臣政治集团,他们格守儒家的政治观念,死抱“义理至上”的“仁政”宗旨,坚决反对理财派大臣“与民争利”,对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的理财派大臣口诛笔伐,百般阻挠。
蒙古诸王贵族是私分国家财产的急先锋,又是自由放任工商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死守蒙古旧制,企图将落后的蒙古奴隶制强加于中原汉地,仍然对分疆裂土的分封制及掠夺、贡献等经济制度抱有幻想,甚至遣使入朝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4]汉地世官世侯,作为地方割据势力,“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4]他们必然反对中央集权,而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则是忽必烈政权加强中央经济集权的重要举措之一。例如:史天倪之子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或请运盐按籍计口,给民以食,楫争其不可,曰:‘盐铁从民贸易,何可若差税例配之。’议遂寝”。[4]而江淮大都督李亶在中统二年仍受命“领益都路盐课”,地方的官营工商业仍然还落在颇具权势的地方诸侯之手。忽必烈登基后,两件重大的事件改变了上述政治局面,一是阿里不哥称汗于和林,忽必烈一方面依托汉地丰富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切断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出兵击败阿里不哥,使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败;二是山东世侯李亶趁北边战事,发动叛乱,占据益都,并企图策动中原其他诸侯响应,但被忽必烈迅速镇压,并采取系列措施:罢世侯,置牧守,分兵民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极大限制和削弱了数十年专制地方的大小诸侯势力。这两件政治事件的最终影响是巩固了忽必烈新政权的政治基础,为新政权发展官营工商业经济扫清了政治障碍。历史无数次证明:政权强,则官营工商业经济强;政权衰,则官营工商业经济衰;政权亡,则官营工商业经济亡。
在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义理派儒臣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大臣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世祖时的官营工商业制度就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并日臻成熟和完备的。义理派儒臣政治集团曾经在协助忽必烈应付蒙哥大汗及阿里不哥的政治威胁及“论立体统、张布纲维”以恢复中原传统文化和典章制度方面有过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官营工商业经济方面,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与忽必烈此时所需要的、同为中原文化之源的法家“专盐铁”“官山海”的经济思想相去甚远。他们坚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的理论信条,主张“德者本也,财者未也”,认为代表国家与民争利都是政治小人,“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13]他们解决国家经费窘迫的指导方针是“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国家诸般日用供给自然都够用了”。[13]他们的指导方针可能十分完美,但却提不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来保障国家经费的收支平衡,以解世祖发动平内攘外战争的财力、物力所需。难怪“窦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怿而罢”。[4]
在发展官营工商业经济的道路上,世祖忽必烈既得不到勋贵世侯的支持,也无法获取儒臣士大夫的理解,太宗时的耶律楚材早已驾鹤西去,“少时读权谋书”的“布衣”王文统又因李亶事件迅速凋零,世祖只得依靠色目家奴阿合马、“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的商贩卢世荣以及西蕃译史桑哥。尽管如此“力小任大”,但建立官营工商业制度、发展官营工商业经济的历史成就,就其产能及产值来说,并不比历史上任何王朝稍有逊色。以官办手工业为例,有学者认为:元代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大,产品多,远远超过宋金时的官手工业”;“元代的官营手工业一度得到大规模发展。……元政府建立起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全国共设立大小工业局院三百一十余所,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七十多处”。[14]元人苏天爵更是认为:“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至于官营禁榷工商业,《元史》有时也评论:“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4]以盐课为例,高树林先生认为:“元朝盐课,在官府财政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比唐、宋王朝又有了更多增长。”[14]唐、宋时盐课收入一般占财政收入不到一半,或者“实居其半”,但元代盐课有“国家经费,盐课居十之八”的记载,元人袁桷也评论说:“国朝定煮海之赋,倍于前代”。事实上,忽必烈对官营工商业的发展及产生的财经效果也是十分满意的,至元初,帝(忽必烈)谕(廉)希宪曰:“吏废法而贪,民失业而逃,工不给用,财不赡费,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为相,朕无此忧。”[4]这表明在世祖即位后不久,官营工商业制度的运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本上可以保证工可给用,财可赡费,而吏不废法而贪。到桑哥为相时,桑哥曾经集诸路总管三十人,导之入见,欲以趣办财赋之多寡为殿最。帝曰:“财赋办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库,岂少此哉!”[4]这一方面表明国家府库比较充裕,忽必烈对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十分满意,另一方面表明至元后期忽必烈对官营工商业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
自1206年太祖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经太宗窝阔台汗推行汉法,草创官营工商业体制,到世祖忽必烈全面采用汉法,系统地巩固和发展官营工商业经济,期间虽几经周折,但最终在元初全面建立了一个以“黄金家族”共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十分复杂、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伴随着元代官营工商业的兴起,与之密切相关的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体系也逐步建立。
[注释]
①《世界征服者史》,第140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86页。《史集》记载的工匠数量是“千名”,与《世界征服者史》有出入。
[参考文献]
[1]曾代伟.中国经济法制史纲[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2][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5]鲍思陶(点校).《元朝秘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郝文忠公陵川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从刊(91册).
[7]杨奂.还山逸稿[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8][波斯]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M].周良霄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9][英]道森.出使蒙古记[M].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前苏联]B·R·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肖之兴译)[M].
[11]大元通制条格[M].郭成伟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2]盐铁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3]许衡.许文正公遗书[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高树林.元朝盐茶酒醋课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1995(3):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