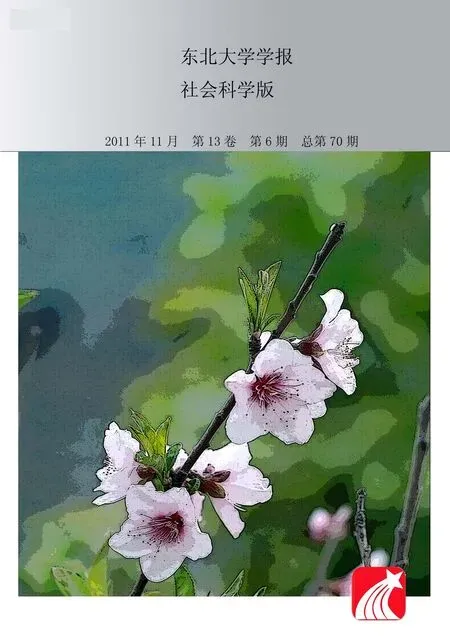论马尔库塞的美学救赎之路
朱春艳,张 丽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189)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批判思想较为激进,热衷于领导并参与革命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被奉为“学运先知”、“青年造反之父”。运动最终失败,马尔库塞也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激进革命转向审美救赎道路的探索上来。由此,有学者评价其晚年走向了乌托邦主义。诚然,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看,连哈贝马斯都承认自己的理论具有乌托邦色彩,马尔库塞当然不能例外,但如果从马尔库塞理论的兴趣点来看,他晚年转向美学是其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不仅仅是其理论的乌托邦特质使然,审美救赎理论本身也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单向度意识控制批判是美学救赎之路的理论起点
对单向度社会中人的爱欲本质受到压抑的剖析和批判是马尔库塞美学救赎道路探索的理论起点。正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单向度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已经成为受工具理性全面控制并维护这种控制的机器,马尔库塞才将工具理性对人意识的控制、人的压抑心理机制看做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根本原因,得出了摆脱意识控制、实现以意识革命为主导的整体革命才是实现单向度社会救赎的根本道路的结论。
单向度相对于双向度而言,是指仅仅具有肯定的维护的向度,缺乏否定的批判的向度,双向度是指具有肯定同时具有否定的批判的向度。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全新时代意识,其基础是理性主义”[1],而“理性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工具理性是技术演化的结果”[1],因而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造成的单向度性,尤其是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思维意识进行的控制,是工业社会现代性最显著的弊端。纵观当代工业社会,单向度性已经全面表现出来:经济成为建立单向度社会的控制基础;政治领域内消除了对立的政治面,统治成为资产阶级内部轮流坐庄的游戏;文化领域内,大众文化的产业化低俗化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生活于单向度社会中的人,依赖于高科技生活方式,被单向度社会同化了,成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程序一体化的人;单向度思维方式在思想领域成为普遍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压抑性的社会心理机制,人从此被“一体化”进了单向度的社会,成为维护单向度统治的机器,而丧失了自我认识的能力,失去了否定的本质力量。
思维具有单向度性、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了当代社会的压抑性的心理机制,则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的重点。马尔库塞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研究当代工业社会人们的单向度思维方式,指出思想的一维性是决定人们的一切行为失去批判性超越性的内在原因,是单向度社会得以维持的内在机制。他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使人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科技反过来控制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内化到精神领域,控制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思维向度单一化,失去了反抗能力。资本的统治使用了更加隐秘的工具,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取代了政治强权力量,在社会内在机制的深处以及社会最广泛的层面上控制了人们的思维。现代社会的理性表现形式被工具理性所控制,借助大众传媒控制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精神灵魂的方方面面,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在这样的单向度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进步的批判的力量和意识,人本身应该具有的否定的思维也被工具理性控制了,难以认识到自己被控制被奴役的现状,甚至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人从此再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摆脱工具理性的控制,将感性重新植入理性形式之中,实现新感性的回归。
二、艺术的革命性整体性引导性特点是美学救赎之路的逻辑前提
马尔库塞的美学救赎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深入剖析,致力于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对人的本质的控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感性来对抗工具理性的控制,建立人类以及社会新的存在方式,通过突出意识革命重要位置的整体性革命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艺术对当代社会思维解放具有革命性作用。
一方面,强调新感性的解放,有着现实的背景,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因素,却具有现实的意义。艺术美学的现实作用来自于现时代背景下对新感性回归的呼唤,当代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对全社会的控制现象掀起了当代哲学对人性复归的呼吁,一种充满感性美的田园生活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风潮。马尔库塞崇尚艺术的革命价值,实际是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工具理性控制的人的本质的真正追求。虽然,马尔库塞过于强调感性的作用,出现了“矫枉过正”式的激进表现,最终将艺术家推上了革命主力军的地位,使其美学实践陷入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主义,但不可否认感性对于重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促成全社会的新理性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新感性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是美学救赎在当代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就是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现代价值。
另一方面,艺术的作用也存在着矛盾:所谓的真正的艺术不仅保有人类的双向性,同时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对社会不满的工具,成为人们反抗社会的避难所。人们在艺术中发泄自己的批判否定的维度,使艺术具有了双向性,也成为双向性存身之地。然而研究艺术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他们有着理想,却陶醉在艺术中不能自拔,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艺术在一个侧面纵容了这种逃避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失去站出来对抗现实的勇气。人们因为有了发泄之所而增加了容忍度,艺术就这样从反面成为维护单向度社会更加持久的工具。
其次,当代社会革命具有整体性特点。
马尔库塞对社会革命理论的探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一样,突出革命的整体性,突出主体的意识革命。马尔库塞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性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已经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种现象造成了革命形势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革命动因的变化,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纯经济的阶级分析扩展到了更加全面的社会原因分析之中,通过对当代工业社会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新的压迫统治形式的发现,改变了原有的革命主因转而认为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本质的压抑控制才是革命的社会内在因素,也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动因。二是革命任务的变化,因为革命动因发生了变化,革命的任务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的革命任务从反抗经济的阶级的剥削转变为实现人的本质爱欲的解放方面,工业化带来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满足,也就使得革命的任务不再是物质的追求,而是爱欲的解放。三是革命道路的变化,革命动因革命任务的变化,阶级的对抗已经变得模糊,以实现爱欲解放为目的的全人类的解放,不再是无产阶级自身的任务,而成为全人类的革命,这一革命是整体性的革命,走的是一条以意识革命为先导的“第三条道路”即和平斗争道路。四是革命主体的变化,当代工业社会阶级界限的模糊,整体性革命强调的意识革命所具有的先行性特征,使得革命的主体必然区别于阶级革命的主体,从无产阶级身上转移到“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工业社会‘新左派’肩上”[2]4。
上面四个方面的变化是工具理性对全社会的控制所导致的,四个方面同时出现并且相互交叉相互促进,共同处于一个发展进行的过程之中,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马尔库塞指出,这些处于一个整体中的变化都源于工具理性控制了人们的思维,而“现代大革命的客观趋势是自由在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和需要的扩大”[3]。因此,马尔库塞就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单向度社会的分析得出了摆脱工具理性的意识控制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最迫切需要,得出了美学救赎的社会革命理论。他认为,革命的原因归结于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而革命的任务就是摆脱这种控制,而摆脱这种控制的途径则是通过美学艺术对全社会进行新感性教育,这样则将艺术家最终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位置。马尔库塞将意识革命放在整个革命的突出位置,这实际是对工具理性控制的现实社会的回应。将美学救赎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统一于改造现实单向度社会的道路之中。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控制之下革命形势的客观分析,以及对革命意识的重要性的深入剖析对于当代社会主体意识的全面发展,改变单向度的控制,实现革命的批判的意识的回归具有现代意义。
第三,艺术在当代社会革命意识兴起中具有先导作用。
马尔库塞在自己的社会革命理论中,强调艺术对革命的重要作用,实际是强调了艺术的革命的批判的内涵中所代表的对感性的追求,对于革命意识的重要性。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出现衰退的迹象,这使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陷入了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也体现在认识的局限性上面,“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5],时代的发展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更给了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灵魂。马尔库塞从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出发,不仅将自己的理论发展旨趣放在实现全社会的、人的所有潜能的全面发挥上面,更致力于对现实的社会发展进行历史的发展的剖析批判,寻找最终的美学救赎之路,是对人类意识解放的宝贵探索。马尔库塞能够基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新的探索,审美艺术中所包含的否定的批判的感性的革命因素,将审美形式的革命推上了改变现实世界的主力的宝座。马尔库塞看到了感性对当前社会革命所起到的作用,将这种艺术在精神领域所掀起的革命,植入新时代的革命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
三、审美形式对社会心理机制的改造是美学救赎的必经之路
马尔库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后的革命者,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而走上改良道路。马尔库塞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实践的不懈追求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创作和革命活动之中,这是其区别于包括阿多诺、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其他重要代表人物之处。从其美学救赎理论看,这表现在马尔库塞赋予了美学理论以革命的实践的功能。这一功能不仅体现在马尔库塞美学产生的现实实践需要、革命目的等理论构建方面,更体现在马尔库塞晚年对于美学对抗工具理性、审美形式改造社会内在心理机制、审美理念改造技术体系等美学救赎的实践路径探索方面。
马尔库塞美学的宗旨是救赎。在他那里,美学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德国传统浪漫主义美学,也不再是希腊式的古典审美艺术,其功能就在于解放,是变革意识形态的武器和打破资本主义市场虚假需求的革命力量,从而他的理论中的美学成为了针对当代工业社会工具理性统治压迫成为新的压迫形式所创造的新的解放路径。马尔库塞从艺术对现实的反抗中看到了艺术的革命性。“即是说,艺术仅仅疏离与反叛现实是不够的,它还应承担重构现实的任务。”[6]在《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一书中,马尔库塞明确指出要“按照美的法则重建世界”,美学中的审美形式应成为现实的形式。“作为现实之形式的艺术的意义并不是对给定东西的美化,而是建构出全然不同和对立的现实。”[7]103马尔库塞建构美学救赎理论的路径,就是立足于对当代工业社会的革命目的、革命主体、革命道路等方面变化的深入分析,从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高度出发,寻找到根植于艺术之中的革命性整体性引导性的新感性特点,使现实的革命需要与艺术所具有的感性特质相结合。
马尔库塞美学的革命实践的特质,最终体现在马尔库塞美学救赎理论对于其具体实践路径的探索方面。马尔库塞将美学中的抽象范畴审美形式应用于现实社会的工具理性统治的社会内在心理机制改造之中,并强调了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具体的应用,也就是美学形式对于技术体系的改造。他求助于美学这一依然保留人的本质的唯一净土去解放人的爱欲,实现单向度社会向全面发展社会的转型。他全面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人的爱欲被压抑的状况,进而据此为资本主义社会寻求解决人的心理压抑、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方法,审美成为创造新人类的路径,即审美救赎。因此,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社会批判理论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所。
首先,艺术具有感性意识的品质。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唯有艺术保留了否定的批判的向度,在艺术活动中才能使人摆脱工具理性的控制,重新拥有感性意识,从而成为感性理性健全的全面的人,因此唯有艺术才能扛起反抗单向度社会的大旗。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具体论述了他的美学思想,“美学领域本质上是非现实的”[2]126,而人们在“审美方面的基本观念却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的,而不是观念”[2]126。因此,在艺术活动中,工具理性控制不了艺术的感性能力,人们在从事艺术活动的过程中仍然会突出主体的价值性取向,就是这种对感性的保留能力,以及人们在非现实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本质能力使得艺术活动有可能成为人们对抗工具理性的工具,在工具理性中植入艺术的价值性取向平衡两种理性,建立新感性成为可能。
其次,自律性赋予艺术革命性品质。马尔库塞为了将美学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他提出了美学具有自主性和自律性,“艺术通过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7]203-204。“艺术作品只有作为自律的作品,才能同政治发生关系。”[7]243马尔库塞是这样阐述艺术自律的:“审美的形式、自律和真理,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它们都是社会历史的现象,又都超越了社会历史的竞技场;当社会历史限制艺术自律的时候,它必定也破坏着艺术作品所表现的超历史真理。”[7]309艺术因此与现实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是相反的,艺术所建立的抽象世界是一个独立的自律的领域,它可以不依赖于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而存在,因而不受约束。因此,马尔库塞一直很重视艺术所具有的自主性,艺术所表现的是创造者自身的内心世界最深处的本能,艺术能表现出人的原始本质,即爱欲能使他们的艺术作品远离现实而具有一种新的感性,“所谓新感性,就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8],这种感性就是一种否认工业化社会工具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否定力量。他进而将审美艺术与革命联系起来,指出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他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换来一个解放的世界。
第三,艺术的革命性要诉诸技术改造的实践。马尔库塞没有止步于寻找艺术感性及其对政治革命的现实意义之中,他还致力于寻找艺术革命的技术实践道路,将艺术感性纳入技术体系之中,改造工具理性形成新的理性形式。他提出,工业社会的现有技术体系是现代性弊端的根源,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主体应用于客体的技能,而成为了一种“组织、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形式,是普遍的思维和行为形式的显示,是社会控制和主导的工具”[9]。要改变这样的社会存在的形式,需要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形式中植入艺术感性,形成新的社会存在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中,艺术“能够以其反升华的政治的生存形式,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即成为生产技术中的一个因素,成为物质和知识的需求借以发展的水准。在这里,艺术改变着科学技术和现存体制;艺术的合理性及其构想生存的能力推动着对世界的科技改造”[8]。艺术感性就这样进入技术体系之中,改变人们对于技术体系的认识形式,恢复人的主体性在技术社会中的地位,从而打破现有的理性形式,重建社会存在形式,人们重新审视技术的应用和人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现有的社会存在和认识思维方式,重新确立感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这种新的以审美形式存在的社会存在方式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是一种新感性,也是一种新理性形式,这种存在方式具有双向的维度,是体现人的全面本质,促进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形式,人不再是被技术控制的客体存在,重新成为自身的主体。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启发人类重新发现自身的主体性特征的意义,而且能够通过对技术体系的改造而成为具有现实的政治革命意义的力量。
马尔库塞通过厘定艺术的感性特质,发现艺术潜在的政治意义,建立起艺术感性实际应用于技术体系对抗工具理性形成新理性形式的整个逻辑体系,完整地论证了美学救赎道路。在这一理论中,马尔库塞强调新感性的恢复对人类解放的作用,并详细论述了艺术感性在建立新的审美的社会存在和思维方式中的政治实践作用。这表明,西方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昭显出一个社会之“应然”的状态,这也是在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同时也视其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意义所在。二者共同构成了美学救赎之路的理论论证,也昭示了美学救赎之路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成岗.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技术理性”建构----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诠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26(7):43-48.
[2]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 黄通,薛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 江天冀.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3.
[4] 恩格斯. 致威·桑巴特[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42-743.
[5]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37-338.
[6] 鲁献慧.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及其审美拯救思想析评[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22(5):59-62.
[7]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 张之沧. 论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4):37-38.
[9] Marcuse H.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M]∥Kellner D.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vol.1. London: Routledge, 1998:3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