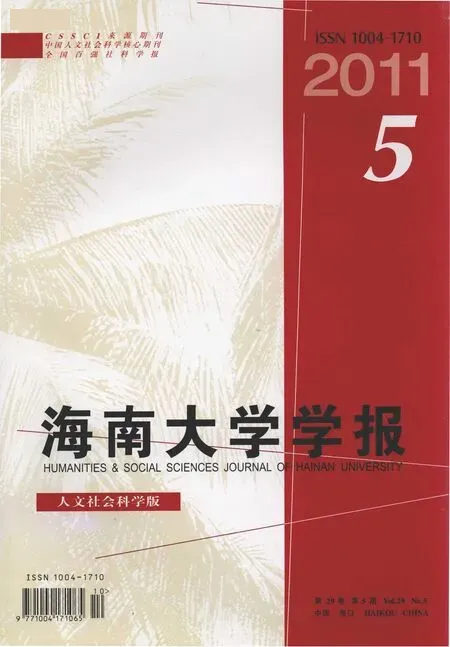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旷凌云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旷凌云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被害人;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就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问题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之贯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颇受青睐①笔者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率”,搜索结果中有一半以上显示的调解率超过60%,有些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率甚至高于90%,如河南省温县法院从2008年至2009年8月底共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53件,全部调解结案,调解率达100%。,其具有的轻刑化效果和对被害人受损民事权益的救济效果相当明显。据福建省华安县法院统计,该法院从2000年至2002年共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6件,其中调解率占64%,判处非监禁刑的占68.3%,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执结率98.2%;同比判决率36%,判处监禁刑100%,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结率37%[1]。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立法粗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制度的正确适用与功能发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提上日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200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要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强化诉讼调解。2010年《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5条特别指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要在调解的方法、赔偿方式、调解案件适用时间、期间和审限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争取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为正确适用法律和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造条件。”本文拟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加以分析与论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有助于该制度的完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现状与特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除了受刑事法的调整,还要适用民事法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刑民交叉”特色。然而,这一特色却造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既不受刑事立法的重视,也得不到民事立法的垂青。刑事立法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作为一种民事司法调解应当主要由民事立法来规定,而民事立法则致力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的完善,忽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特殊性,没有为其制定特别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调解的程序规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一直不受重视。理论界普遍认为“调解是最典型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反程序外观”[2],它比较灵活、方便而简捷,只要当事人达成合意就行了,无需拘泥于一定的程序规则。也就是说,“调解程序制度的价值应当是能够使纠纷获得妥善解决而非程序保障”[3],因而要求调解在程序上合法意义不大。上述两方面原因造成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相当粗疏而简单,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刑事立法来看,《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若干问题解释》)只有第90、96、97、101、169、205条6个条文涉及到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概括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调解人和调解时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主持调解;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庭调解。二是调解的基本原则,也即,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三是调解的适用范围。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均可适用调解,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除外。若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仍可以进行调解。四是调解书的制作与生效。在审前阶段,调解成功的案件并不制作调解书,在审判阶段,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达成协议并当庭执行完毕的,可以不制作调解书,但应当记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即发生法律效力。五是调解与审判的关系。在审前阶段,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在审判阶段,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判决。其次,从民事立法来看,《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也没有特别规定,只有2004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21条提及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程序规则的适用,即“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依照本规定执行”。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唱主角,两大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持漠然态度。二是以参照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关规定为主,少有特别规定。三是过于简单,操作性弱。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适用范围、方式、期间、效力等,立法均没有具体规定,留待法官在实际适用中的自由裁量。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立法没有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特殊性为之设计专门的规则,加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立法本身存在差异与冲突,这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适用普通民事诉讼调解规则时容易产生“水土不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功能发挥。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适用范围较为模糊,容易引发争议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现行刑事立法仅是概括地规定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均可适用调解,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除外。那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主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时,其案件范围有无不同?立法对此没有明确。另外,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之影响下具有轻刑化效果,当事人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解决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能导致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例如,有的认为判死刑的案件不宜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否则无异于宣告富有的犯罪人可以“以钱赎命”[4];有的认为如果案件广为社会关注,因调解可能造成“拿钱买命”、“以钱赎刑”等不良社会评价和影响的,不宜对之进行调解[5];还有的认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的,不能适用调解。
(二)调解的期限过短,限制了调解合意之形成
调解的过程是当事人多次谈判与磋商、调解人反复说服与教育的过程,必须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保障。正因为如此,《调解规定》放宽了法院调解的时间限制,规定法院在答辩期满前至裁判做出前均可进行调解,只要不超出民事诉讼的审限即可。但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而言,调解的期限仍显过短,客观上不利于当事人达成调解合意。主要表现在:
第一,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较之普通民事纠纷而言更为尖锐,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也更为强烈,而且相当多的犯罪案件发生在非熟人之间,当事人在案发前少有密切的社会联系,因此,调解的难度往往高于普通民事纠纷,可能需要多次调解才能成功②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泰州市两级法院2003年度共调解审结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04件,其中多次调解的占86%。参见薛剑祥:《刑事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适用》,《华东刑事司法评论》2006年第8卷。,理应需要更多的时间保障。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最长仅为4个半月,远远低于民事诉讼的1年3个月的最长审限。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从收案到结案审限仅20日,更是难以满足调解的时间需要。
第二,受“先刑后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官在刑事部分基本查清之后才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根据《刑诉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69条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一般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进行。如此一来,庭审中留给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时间更显不足。有些法官为了在审限内尽快结案,不愿意多花时间进行耐心而细致的调解工作而倾向于判决结案。当然,法官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可以根据《刑诉法若干问题解释》第99条之规定在刑事案件审判后将附带民事案件交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但这样一来,调解轻刑化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调解协议则难以达成。
第三,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害人为了避免调解协议履行中的风险,以拿到赔偿款作为在调解协议签字的条件。那么,在现行立法规定的调解期限过短的情况下,被告人及其亲属难以及时筹足赔偿款项,如此也不利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三)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特殊,自愿原则受冲击
自愿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调解的正当性基础“并非来源于解决方案严格基于法律而形成,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6]。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虽然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地位平等,但因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其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实际上并不平等。这直接影响到调解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刑事被告人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态,而且大都限制了人身自由,难以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加之刑事诉讼立法对被告人聘请律师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活动设置了种种限制,因此被告人无论在话语权方面还是收集信息抑或谈判交涉能力方面,远远不及普通民事诉讼被告,在与被害人交涉的调解过程中,是居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这种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势必影响到当事人谈判磋商的自主与自愿③有学者通过调研还发现,许多案件多次调解无法达成协议,但只要对被告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无一例外地都能接受调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中的自愿原则存在问题。参见薛剑祥:《刑事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适用》,《华东刑事司法评论》2006年第8卷。。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通常处于被羁押状态,而被害人则可能因身体伤残或精神痛苦而难以或者不愿意直接面对被告人,故而两者之间很难有直接的对话与协商;加之被告人的个人赔偿能力大都较弱,能否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往往取决于其亲属的赔偿态度和赔偿能力,因此,调解往往不是直接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展开,一般是当事人的亲属代为参与调解。这就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像普通民事诉讼调解那样表现为直接性磋商,而是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对此种情况采取了默认态度,往往不会进行严格的委托手续方面的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亲属特别是并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的被告人的亲属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当事人的本意,实在不容乐观。
(四)调解人权限过大,危及调解的公正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一样存在着调解人的双重角色混同的问题。作为调解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保持消极性中立,通过为双方当事人磋商创造条件、提供机会等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作为刑事责任的追究者,上述刑事司法机关则更具有积极能动性,运用刑事司法权力主导诉讼进程,并依法对与追究刑事责任相关的事项作出独立决定。此双重身份使得刑事司法机关在主持调解时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决定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较之普通民事诉讼调解而言,此种强制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更为明显。这是因为:
首先,现行立法对当事人的知情权保障不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调查取证的权利实际受限,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资料主要集中在刑事司法机关手中,而当事人很难获得谈判磋商所需的足够的信息资料。在这种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当事人难以自主进行理性决策,往往盲目听从调解人提出的方案,故而调解的公正性值得怀疑。
其次,吸引双方当事人进行谈判磋商的最大筹码是调解具有轻刑化效果。但对于该调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刑事量刑这一关键性问题,并不由当事人决定,而是属于相关刑事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加之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调解与具体量刑幅度的关系且对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监督不力的情况,因此,该问题基本上属于相关刑事司法机关单方面的自由意愿。在这种局面下,当事人若拒绝刑事司法机关提出的调解方案,就会顾虑重重。那么,一旦调解人的态度成为达成调解合意的决定性因素,调解的正当性就会动摇。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合意并不纯粹,即合意是在某种外部压力影响下得到的话,合意本身就不能使纠纷的解决正当化”[7]。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若干对策
针对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上述不足,笔者认为,现行相关立法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适用范围方面
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是所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但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除外。
从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之所以能影响到刑事处理结果,是因为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便意味着基本上满足了三项条件:(1)被告人真诚悔过;(2)被告人积极赔偿;(3)被告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这些条件一方面弥补了犯罪所导致的民事损害,减轻了犯罪的危害后果;另一方面弱化了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了其再犯的可能性,客观上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故而被视为从轻量刑情节。换言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是通向刑事部分之从宽处理的“康庄大道”。
鉴于此,无论刑事案件的性质如何,即便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大门也不应对其关闭;无论被告人有无赔偿能力,只要被害人对此明知的且愿意与之磋商解决民事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仍然可适用调解解决。当然,对于前者,刑事案件的性质不同,调解所影响的量刑幅度应当有别,立法应当尽量明确调解轻刑化的幅度范围,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对于后者,在民事实体法上,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有多样性,金钱赔偿仅是其中一种,刑事立法不应当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责任方式作过多限制,而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确定,比如被告人可以通过提供劳务或从事被害人要求的某种活动等方式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只要该合意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
其次,应当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中的适用案件范围予以区分。这是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第14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可以撤销案件或者不提起公诉从而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在司法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即可运用上述自由裁量权,使得这些刑事案件无需进入审判程序④例如,2004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轻伤犯罪案件在侦查、审查过程中,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可以撤案、不起诉: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协议;当事人双方和解,被害人书面要求或者同意不追究刑事责任。。然而,目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持的调解存在诸多弊病,暂不论调解人的中立性能否保证,调解能否贯彻自愿原则和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也存在疑问。因为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双方当事人难以获知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加之被告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根本无法亲自与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自主谈判。倘使不加限制允许所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调解,将可能导致“以钱赎刑”失控泛滥,大部分案件(包括一些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都可能借着这种方式偷偷私了,从而蚕食法院的审判权。鉴于此,立法一方面应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审前阶段的适用案件范围原则上限制为轻微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合意解决,应规定轻微刑事案件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在审前阶段虽然可以适用调解,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能决定其轻刑化效果。
(二)调解期限方面
考虑到刑事诉讼审判期限较短,立法应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时间适当提前,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审前阶段实行繁简分流,以减轻审判阶段调解的压力。这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第一,对于下列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在审前阶段实行先行调解:(1)轻微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2)当事人之间存在近亲属、朋友、同学等密切社会关系的案件;(3)被害人急需费用进行医疗救治的案件;(4)其他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
第二,改变现有立法将法院调解限制在审判阶段的规定,扩大法院调解的适用程序范围。对于公诉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当事人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主持审前调解,实行“先民后刑”。但法院调解提前至什么阶段,学者看法不一。有些认为是法院受理刑事公诉之后开庭审理之前,有些认为是在侦查机关立案后法院审判之前。笔者认为,一旦公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就可申请法院调解。也即,法院调解可以在审查起诉程序阶段进行。这是因为:(1)侦查阶段贯彻不公开原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获知案件的证据材料。而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事实得以查清,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印案卷材料,对案件事实有基本了解。(2)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述两点对当事人理性行使处分权以及提高调解的效率有着积极意义。
(三)当事人的自愿性保障方面
当事人谈判磋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博弈。为了避免这场博弈沦为“弱肉强食”的游戏,可从以下方面满足当事人决策的自主性和理性从而保障调解的自愿原则:
第一,构建较为便捷的当事人收集信息机制。为此,立法要重点强化当事人的取证能力之保障,完善当事人的取证手段。例如,对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调解,当事人有权申请调解人举行证据交换;被害人因客观情况无法收集到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赔偿能力等信息时,有权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上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等等。
第二,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相关制度以强化被害人谈判的筹码,避免以调解获得赔偿这一路径成为被害人惟一的“救命稻草”。一方面应明确被害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量刑的幅度(下文对此有详细论述)。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害人因担心“钱财两空”而被迫接受调解,且防止部分被告人以“判刑则拒赔”加以要挟,立法应完善诉前与诉中的财产保全、先于执行、国家救助等制度。
第三,在制度设计上应强调调解的直接性,要求刑事司法机关有义务创造条件促成当事人直接参与调解。为此,首先要改革会见制度。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仅其辩护人有会见权,被害人无权与其会见。要实现调解的直接性,必须改革现有的会见制度,为调解人主持当事人会面与磋商活动开辟绿色通道。无论是审前调解还是审判阶段的调解,征得被害人及其亲属同意之后,调解人通过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如提交相应法律文书、经相应主管机关审查等,应安排其与被告人会面谈判,未成年被告人在其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参与调解。其次应规范调解代理制度。对于一些保密性案件或其他不宜直接调解的案件,被告人亲属参与调解的,须征得被告人的书面同意,且代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由被告人本人签字认可。这样既能真正考察被告人的赔偿意愿与悔罪表现,又能因参与原则得到保障而容易获得双方当事人的认同,真正贯彻调解的自愿性。
(四)调解人的权限方面
如何科学界定并理性规制调解人的权限,直接影响到调解的品质与效果。为了化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司法机关同时作为调解人和刑事裁量权的享有者可能产生的弊病,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调解人权限:
第一,强化调解人的居中告知与释明职责。调解人应是双方当事人沟通的桥梁,应尽量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对话和协商的机会,为形成调解合意创造条件。考虑到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主要是一种间接性调解,参与调解交涉的双方未必是案件的亲历者以及待处分实体权益的权利人。因此,调解人为促进调解合意之形成,至少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1)调解过程中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调解的期限、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等。(2)根据当事人的需要阐明相关的法律、法规。(3)对当事人的主张作出评价并帮助其了解潜在的有利点与不利点,引导当事人提出合理的主张。(4)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不当主张,应说服教育其加以修正;对当事人提出的非法的主张,须予以制止。(5)依当事人的要求解释调解方案,等等。
第二,适当扩大调解人的范围。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可以邀请社会力量协助调解或者委托其调解。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调解人因为掌握“从宽处理”的筹码而导致的强制调解,也可以减轻公检法的办案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刑事诉讼审前阶段的特殊性,应当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委托调解制度制定特别的细则,如以不公开调解为原则、委托调解的案件范围应严格限定、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的主体宜加以特别限制等。
第三,适度提高被害人意愿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的影响力。一方面,立法应将司法解释中被告人悔过并积极赔偿且取得被害人谅解这一酌定情节上升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民事赔偿的,应当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另一方面,赋予被害人对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与量刑方面的建议权。2010年10月1日施行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该规定为被害人在审判阶段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依据,值得肯定。不过,它没有涉及被害人在审前程序中对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权,这有待以后立法完善。
第四,细化调解轻刑化的幅度以限制刑事司法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有学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赔偿数额参考标准及从轻处罚的基本幅度范围,再由各地高级法院结合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际,在规定幅度内确定本辖区的执行标准[8]。笔者认为,该建议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赔钱减刑”的暗箱操作与恣意妄为,较为合理可行。但是,它一味关注赔偿对量刑的影响力,而没有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其他因素,恐违调解轻刑化的本意,有可能异变成为刑罚明码标价,助长“以钱买刑”。更何况,金钱赔偿并非弥补犯罪行为所致民事权益损害的惟一方式。如前文所述,被告人真诚悔过、被告人积极赔偿和被告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是调解具有轻刑化效果的三项要素。为了凸显上述要素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重要性以及纠正司法实践中只看重赔偿的做法,立法宜规定上述三项要素原则上须同时具备才能产生调解轻刑化效果。当然,考虑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以及被告人赔偿对弥补被害人损失的重要性,且为了化解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赔偿能力有限而被害人索赔数额过高之间的矛盾,避免被害人故意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要求致使调解陷入僵局,立法宜规定被告人积极赔偿在影响量刑上占一半的比重,并且在衡量积极赔偿时,不简单以赔偿额高低为衡量标准,而应综合考量案件的具体情况、各种民事责任方式对犯罪所致损害的补救程度、被告人对赔偿的努力程度等因素。这一做法在域外立法中得到了认可。例如,《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34条将被告人“真诚努力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规定为“特别减轻事由”[9],《德国刑法典》第46条之(2)要求: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行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并将“行为后的态度,尤其是行为人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作为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之一[10]。《西班牙刑法典》第21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减轻的情况”包括“已经对罪行进行起诉,在诉讼进行的任何时候和开庭之前,给予被害人的伤害进行补偿或者减少其效力”[11]。在立法上有类似规定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与澳门地区等。
[1]王瑛,黄养华.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轻刑化功能的理论与实践[J].人民司法,2003(10):31-34.
[2]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7):1 -46.
[3]杨荣馨.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08.
[4]方文军.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平衡规则探微[J].法律适用,2007(2):19-23.
[5]张中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应把握六个特点[EB/OL].[2009 -11 -14].http:∥china.findlaw.cn/susong/xingshisusong/xshdmsss/2772.html.
[6]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J].法学研究,1996(4):57-68.
[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机制[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80.
[8]柴建国,王宇辉.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中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9-07-01(06).
[9]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6.
[10]德国刑法典[M].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7.
[11]西班牙刑法典[M].潘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
M ediation in Pertaining Civil Action to Crim inal Procedure:Problem s and Solutions
KUANG Ling-yun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ght-punishmentmovement of criminal justice,mediation in pertaining civil action to criminal procedure enjoys high favor among judicial practices in recent years.Inadequate attention,however,given by both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ivil legislation,resulted inmany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which influences its proper functioning.Themediation in pertaining civil action to criminal procedure being so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in general civil action,particularmediation procedural rules should be instituted in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ertaining civil action to criminal procedure;mediation;victim;compensate
D 925.2
A
1004-1710(2011)05-0053-06
2010-09-27
旷凌云(1981-),女,湖南祁东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08级民商法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司法制度。
[责任编辑:王 怡]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