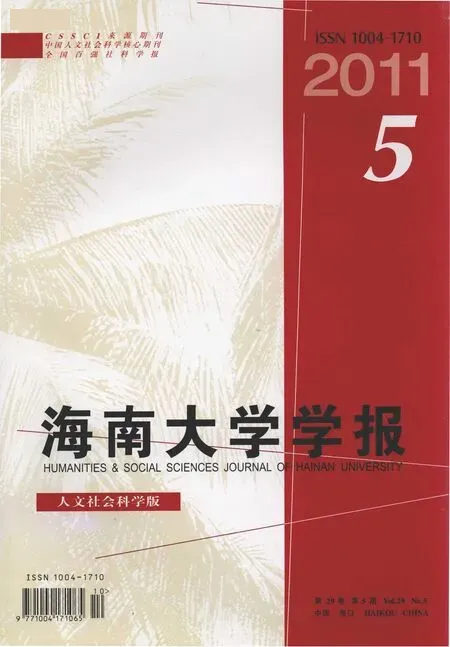论雇主单位在职场性骚扰防治中的作用
徐金锋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 311300)
论雇主单位在职场性骚扰防治中的作用
徐金锋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 311300)
职场性骚扰在中国是复杂的,问题的出路在于从“单位”语境下善加解读中国的职场性骚扰,同时吸取西方国家反歧视立法中雇主责任制的经验,致力于寻找适合中国的职场性骚扰防治策略,如何发挥单位(雇主)在职场性骚扰预防中的作用等更是其中关键。
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预防措施
职场性骚扰属于性骚扰种类之一,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而被西方国家所重视。作为现代劳动场所的文明恶疾,职场性骚扰会对被害人(主要是女性)造成严重的伤害,可能会导致其工作机会丢失,工作满意度下降等,且对单位而言也有诸多不利的后果,工作场所氛围恶化使得士气低落,效率降低,处理不慎又损及单位声誉等。
有关中国的职场性骚扰问题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有人开始关注,个别省份甚至在有关妇女权益保障地方立法中进行了专门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后对其是否进行立法亦为讨论之热点。而从职场性骚扰法律实践层面看,尤其是在1990—2010年间,诉诸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与民众调查中透露的潜在受害人群存在巨大反差,表明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复杂性,也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对解决此类问题时的困境。如何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善加解读,充分调动本土资源,适当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职场性骚扰解读
在我国,职场性骚扰作为一种特殊的劳资纠纷,其解读离不开本土固有的政治、文化、经济特质以及争端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只有在此语境下对问题的审视才可获得较为全面而理性的认知。
(一)单位文化与流氓罪
职场发生的性骚扰较与其他性骚扰的区别在于职场、单位因素,即单位文化。单位体制是1949—1979年之间形成的“新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在建国初期,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困境,在党领导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以空前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将几乎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合法存在的组织都纳入序列,在个人—单位—国家链条格局中,作为单体个人退守至家庭,社会中间层也不复存在。该阶段在单位中很少会发生性骚扰事件,原因在于一旦被发觉个人作风问题便意味着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的丧失。在单位体制中,觉悟、作风等是个人获取各种短缺的社会流动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约束与价值导向使得单位人在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生活选择。即使在事件发生后,单位作为资源的掌控者有权介入个人生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调解以图教化,其目的在于要求个人始终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生活规范,以达到单位有序状态。比如原《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便规定:“企业职工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遵守劳动纪律,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国有企业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的效力,可视为国家法律规范的延伸,对违规(性骚扰)职工的处罚如同行政处分无异。此外在单位中工作的身份甚至可以遗传,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离职退休之后可以由其子女接替,具有十分浓厚的身份特性。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公权力从企业组织中撤出,企业市场化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亦逐步活跃起来,作为个体的劳工权益意识复生,个体空间急剧膨胀,而由单位承载的调控管理体系则逐步衰退,但仍在一定领域内继续产生着影响。“有事情找单位、找领导”即使在当前仍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认识,可见单位已不仅仅是体制性的产物或者纯粹的经济组织,更是中国人感情投放与价值实现的依托。根据劳动法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存在从属性,人身、经济等皆从属于企业,此种从属性与前者依附特性正好吻合,可见当劳动者在为企业单位不断创造价值利润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单位所需要承载的对劳动者的照顾义务。
1979年《刑法》流氓罪条款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流氓的语言、动作对妇女进行调戏或者猥亵是该罪名的客观表现之一,同时流氓罪又是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按照当时的理解,所谓公共秩序乃是指“依靠法律所确立的公共生活规则所维系的社会有条不紊的状态(秩序)……只有在此秩序中人们才能有条不紊的生活、生产和工作”[1]。对于流氓罪,笔者认为79年《刑法》将公共秩序即社会整体利益置于首位,而非基于妇女个体权利为立法之基础,体现出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特点。第二,将生产、工作场所秩序等也纳入公共秩序规范要求,其范围十分宽泛。第三,犯罪嫌疑人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屡教不改的流氓行为本质上与现行对性骚扰行为表现认识相一致。由此可知在当时我国对于职场性骚扰这种性侵犯行为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政策,甚至将其作为《刑法》调整的对象,尤其是口袋罪构成中的“其他流氓行为”这一弹性规定,流氓罪曾一度被放大而招致滥杀之嫌①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流氓罪被分解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取消口袋罪无疑体现着刑法转而重视公民人权保障,但另一个现实却是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逐步淡出了刑法的视线,在旧法已废的思维模式下甚至导致警察不敢过问性骚扰事件,97年《刑法》中的侮辱罪要求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与性骚扰的一般表现亦相去甚远,法律规范出现了一定的真空状态,加上认定标准以及程度模糊,实践中取证困难等,也使得侦查、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事件时捉襟见肘。
(二)就业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用工体制改革方面,从倡导就业渠道多元化到实行新招工合同制度,从开展优化劳动组合到推广全员劳动合同制,传统的固定工、统包统配的模式被打破,转而以自主用工、双向选择的模式,大量职工被推到了劳动力市场大潮最前沿。在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原先计划单位中的冗员逐渐被剥离出来而成为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一些女职工较为集中的诸如纺织、轻工等行业。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的历史背景下,加上国家公权力从企业逐步撤出,对于女性提供的特殊照顾的政策保护伞也正逐渐减退。在高失业率背景②从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部分数据来看:2002年到2007年,我国城乡已登记的失业率为4.0%到4.3%不等,而在2000年该数据仅为3.1%。下,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往往需要在生命尊严与生活压力之间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
在实践中,真正诉诸于司法程序维权的职场性骚扰被害人很少,纠纷的解决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调解还是诉讼或者其他渠道,这同样取决于被害人如何选择。有学者指出:“禁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成本主要有国家成本、以雇主为代表的场所主成本、施害人的违法成本、受害人的权利成本等,上述数项主要成本在当前法律规定下的数值皆为零,故而妇女要想实现其免于性骚扰的权利将要付出的成本,几乎等于该项立法法律效益成本的总和”[2]。2005年8月28日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项立法将禁止成本主要强加给了受害者,仅此规定既不能实现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目标,实际上又给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创造了新的不公平。受害者只能在国家公权力机构获得帮助,受害者—行为人—国家三者之间没有缓冲地带,受害者需要支付高昂的精神性成本以及承受各种流言蜚语,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工作。故而对于被害者来讲主张权利可谓是非理性之举,由此便可理解多数受害者宁可忍辱不愿揭发被侵害的现象。
“无论是现在或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3]我国职场性骚扰问题在上述两种语境下的解读是复杂而真切的,在试图通过制度妥善解决职场性骚扰这样一个人性与社会痼疾问题时应当充分认识雇主单位、企业在反职场性骚扰中的应有作用,调用已有资源,使得相应制度更具有生命力。
二、职场性骚扰域外考察
对职场性骚扰的预防与治理,西方国家有关立法相对起步较早,尽管国情存在差异,但个别制度以及做法值得借鉴。
(一)美国
二战以后,美国大量妇女进入工作场所,职场性骚扰的问题同样困扰着美国。久病成良医,美国包括职场性骚扰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性骚扰是作为性别歧视来加以规范的,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从美国1964年制定的《民权法案》第七章(Title VII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1964)开始,通过多项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形成,使得美国在职场性骚扰防治立法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
《民权法案》系美国所有联邦反就业歧视法中范围最为广泛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法案,其规定:“雇用人不得由于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而对其为拒绝雇用、解雇或其他工作补偿、期限、条件或权利上给予歧视行为。”还专门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即“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简称EEOC)来专门处理相关案件。1976年在William v.Saxbe一案中,联邦地方法院首度判决,所谓交换性骚扰构成一种违法的性别歧视,而并非由于涉案管理监督者个人行为不检③413 F.Supp.654(D.D.C.1976).,从而首次提出“交换性骚扰”的概念。紧接着1977年联邦上诉法院在Barnes v.Costle一案中,也指出被害人因抗拒性骚扰而遭解雇的情形,是违反前述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规定④④ 561 F.2d 983(D.C.Cir.1977).。至此美国正式确立了第一类性骚扰,即“交换性骚扰”。
EEOC于1980年颁布的一项指导原则中明确将性骚扰分为交换性骚扰和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两大类,同时将“性骚扰”界定为“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示好行为;或要求性方面的好处;或其他具有性本质的口头或肢体行为,而(1)顺从该项行为是作为某位个人明示或默示的就业条件或情况;(2)个人顺从或拒绝该项行为,是作为影响该位个人就业决定的基础;(3)该项行为的目的或结果,会不合理干涉某位个人的工作表现,或会造成一胁迫性、敌意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环境”⑤Equal Em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Guidelines on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Sex——Sexual Harassment,29 C.F.R.∮1640.11(a)(1998).。该指导原则虽没有直接法律效力,但对美国各级法院在解决类似纠纷时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上述定义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后在1981年的Bundy v.Jackson一案中,联邦上诉法院认为,被害人虽未有如被辞退等有形经济损失,但其工作环境已显然被非法恶化⑥641 F.2d 934(D.C.Cir.1981).。之后在Henson v.City of Dundee案件中,联邦上诉法院更是列举了判断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的标准来确定雇主的责任⑦682 F.2d 897(11th Cir.1982).。联邦最高法院1986年在Meritior Saving Bank v.Vinson案中首度加以判决,首先肯定了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事件属于一种性别歧视,并且指出应从行为人之举动是否受被害人欢迎,而非是否出于被害人自愿来判断;以及雇主应当负有禁止性别歧视的政策和措施,否则便不能免除雇主的责任⑧477 U.S.57(1986).。上述判例共同构筑起美国反职场性骚扰法律体系。
在美国,雇主单位必须配套如下措施:(1)制定正式的禁止职场性骚扰书面政策声明并加以公示;(2)于企业内部建立申诉程序,对于此类正式申诉进行迅速、客观、完整而保守机密的调查,并且根据调查的结果作出决定,然后采取一定的补救行动等。雇主对于工作场所负有诸多监管责任以防范性骚扰的滋生,若未尽到上述监管责任或监管、保障措施不力甚至需要为职场性骚扰支付巨额赔偿,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如1997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性骚扰案件中,法院最后判决日本三菱公司赔偿3 400万美元,有300多名女工获赔。
(二)欧盟
欧洲理事会在1990年5月通过了一项《保障工作场所男女两性尊严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ignity ofWomen and Men atWork)。欧盟委员会在1991年11月27日又通过了《反性骚扰措施实施准则》,其中对性骚扰进行界定:“性骚扰是指违背意愿的性本质行为,或其他基于性的行为而影响男女工作时的尊严者而言,包括不受欢迎的身体、言词或非言词行为”。1993年欧盟成立后,欧盟诸成员国对1991《反性骚扰措施实施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吸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上述指令对各成员国内防治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于欧盟各会员国[4],深受欧共体1991年《实施准则》的影响,多数会员国在1991年前后对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于1992年开始逐步出台专项立法,如奥地利《待遇平等法》、比利时两项皇室命令(1992年9月、1995年3月颁布)、法国《刑法》及《劳工法》、德国《第二号平等机会法》等。其次,确立雇主责任,采用多法配合模式,并不局限于歧视、工作机会平等立法。如德国立法中《第二号平等机会法》、《德国民法典》及《柏林邦反歧视法》(地方法)等;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丹麦和芬兰两个国家,其并未对欧盟1991《实施准则》作出相应立法回应,而是另辟蹊径,除了制定《丹麦平等机会法》、《芬兰平等机会法》外,还制定了《丹麦工作环境法》,如《芬兰劳工保护法》中规定了“防治职场性骚扰乃是雇主应提供给雇员安全卫生环境义务”,《法国劳工法》也有类似规定。
可诱导表达IL-12的GPC3靶向性CAR-T细胞在免疫健全小鼠中的抗乳腺癌作用(刘 莹)(7):631
(三)借鉴
在比较上述域外立法后,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学习借鉴:
第一,关于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问题。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的关键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受欢迎”,之后再进一步探讨是以一般人(理性的人)的标准还是以理性的女人的标准。此外“交换性骚扰”、“敌意的工作环境”的划分方法同样值得借鉴学习。
第二,诸法共同规制与防范。前述国家几乎没有只以单一特定法加以规范的,通常包含劳动法、平等机会法、侵权法乃至刑法等。足可见上述国家并未单一将职场性骚扰认定为公法上或者私法上的事件。另一个特点是主要将其认定为劳资纠纷并通过劳动立法的方式来加以调整。
第三,明确雇主责任制。各国立法中始终强调雇主单位的作用,要求其积极承担预防、监管职责。确立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制,有利于改变雇主单位从被动支付赔偿转为主动预防,使其更具主动性地制定内部管理政策,落实防治措施,在企业内建立起合理的申诉渠道,在接到申诉后积极调查应对,以维护职场工作秩序等。
三、职场性骚扰防治中的雇主责任
笔者认为,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关键在于预防,尤其是如何发挥雇主单位的防控作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从立法、企业管理实践等多个角度积极探寻良策,主要集中在如何确立雇主责任制以及单位预防措施两个方面。
(一)雇主责任制立法要素
1.明确雇主的范围 1994年《劳动法》、2008年《劳动合同法》中未有“雇主”的表述,而以“用人单位”替代。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所指的“雇主”属于自然人雇用关系,其范围十分狭隘。有关雇主的界定,属当前争议问题之一。在2010年《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曾有专家提出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第二稿)》中明确使用了雇主一词,该条文稿第48条第2款规定:雇员在职场范围内遭受第三人性骚扰造成损害,雇主未尽保护注意义务的承担补充责任⑨2010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对性骚扰(包括工作场所性骚扰)作出直接规定。。仅就职场的雇主而言,笔者认为应仍以“用人单位”界定为宜,即《劳动法》所规定的“境内之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第一,避免雇主责任被扩大化,首先应将公务人员排除在外,尽管不少国家与地区(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皆将公务领域的性骚扰纳入相应防治法,然而按照我们现行对雇员或者劳工的理解,将雇用关系定格为“私法契约”关系较为妥当。第二,按2005年《妇女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可见有关单位的表述与现有劳动法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2.雇主作为 应当包含设施整备;监督教育;诚实处理;保护隐私;惩戒权等。
(二)重视单位的作用——预防措施
笔者认为,企业单位在预防职场出现性骚扰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1.明示雇主禁止性骚扰之声明 雇主单位可以通过企业网站、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入职学习培训等渠道表明本单位严禁出现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在该声明中还应当界定性骚扰的具体行为表现,一旦发生事件如何在企业内部进行申诉;声明应承诺受害者申诉及其相应调查等皆以专人、保密的方式进行,保证申诉者免遭报复;相关的目击者不会因为提供证据而被打击报复;置惩戒条款,告知何单位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性骚扰员工申诉制度,这些申诉渠道应对当事人待遇公平,何种程度的性骚扰将受何种内部惩戒(警告、降级、开除等)。
2.申诉受理与调查处理 未有正式结论前严加保密,负责人应表明绝无偏颇一方的意思,既有利于被害人敢于揭发,另一方面亦可促成嫌疑人能积极配合检查并澄清事实。设置专人负责处理此类投诉,在接受投诉后展开初步调查,尽量迅速搜集事实,同时对于积极提供线索者给予相应保障等。在处理此类投诉并调查过程中雇主的态度对于受害者十分重要,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积极处理,从而避免发生后续伤害。
3.合法限度的惩戒 在不违反劳动法强制性规范的基础上,雇主可以通过规章制度创制一定限度内的惩戒。但应当遵守如下规则:
第一,惩戒措施合法。笔者认为雇主依照劳动规章制度给予行为人惩戒的权力/权利应来自于劳动契约,但不得违背“公法责任不能通过私人契约加以转移”的基本法理,雇主对肇事者实施的惩戒(如开除、降职、罚薪)必须符合相关强制性的规定,如《劳动合同法》第42条等。
第二,行为危害与惩罚程度应相符。在充分调查形成结果后对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应给予不同的惩戒。比如初犯或情节轻微者一般采取口头或书面警告即可;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停职、停薪、降职等处罚;对于交换性骚扰或情节较重的敌意性骚扰,应开除免职等。同时对于被害人应恢复原状处理:如赋予其交换性骚扰中原先丧失的工资、未获晋升的职位或者其他应得利益等;敌意性骚扰中敌意、冒犯、胁迫环境消除并保证不再发生。
4.场景设置与企业文化 企业实践证明,职场内相互尊重、和谐互助的工作氛围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有条件的企业单位应提倡公开办公、透明工作关系,一方面可促进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减少性骚扰的发生。可限定上司与下属谈话的场地、时间、随同人员以及相应的拒绝权等。“雇主应提供劳动契约性的安全设施(例如职场、更衣室等),例如避免偷窥设施、偷拍,而在女性劳工夜间工作之际,雇主应针对男女设置不同休息室、厕所等设备,并确保女劳工通勤安全。”[5]同时雇主应在企业文化中着重倡导性别平等、相互尊重的风气,共同创建和谐的工作环境。
5.重视调解 调解最擅长解决熟人社会之矛盾,同时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认同底蕴与传统支撑。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纠纷毕竟发生在熟人之间,司法机关对这些纠纷的处理大都是公开进行的,诉讼将熟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对于信奉“家丑不可外扬”的中国人来讲有些不适应。同时,公开化又往往导致矛盾的升级,这是双方所不愿看到的。通过沟通、教育进行各种形式的调解,是处理此类纠纷的最佳途径。
可见,职场性骚扰问题的解决关键还在于如何调动企业单位积极性,采取各种措施提前防范,并制定规章加以惩戒。单位需要在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权益之间做出平衡,身为职场家父更需要其承担起维护家庭和睦之责。
[1]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74.
[2]郭慧敏,于慧君.“禁止性骚扰”法律成本的性别分配——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6(5):45-48.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1.
[4]焦兴铠.向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宣战[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187-447.
[5]许必齐,絲钰云.论劳资争议类型与处理机制[M].台北:台湾司法院,2003:237.
About the Effect of Emp loyer in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t W orkp laces
XU Jin-fe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Zhejiang A & F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China)
Sexual harassment atworkpla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most complicated issues in China now,and the outlet of the problem is thatwe should give it a clear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context of“unit”in China,absorb the experience from employer’s responsibility in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get committed to find out Chinese strategie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workplace,andmore importantly,bring the effect of employer’s unit into key play.
sexual harassment atworkplace;employer’s responsibility;preventivemeasure
DF 474
A
1004-1710(2011)05-0065-06
2011-04-12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A10ZF04);浙江省教育厅课题(Y201017800)
徐金锋(1979-),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法研究。
[责任编辑:王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