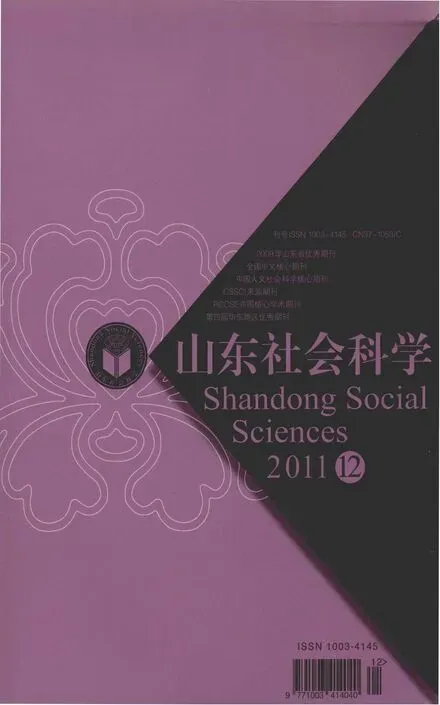文化创意产业:意义的生产与消费
陈小申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 100024)
文化创意产业:意义的生产与消费
陈小申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 100024)
文化关乎生命的“意义”或价值,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文化的变迁、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当下文化形态和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世界观;主体性;核心价值观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兴盛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只要稍加观察和留意,就会对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或者说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感同身受。对此,不少学者从大众文化需求、资本、政策等方面加以诠释,也得出了许多富有理论价值的结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需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生命活动”的“生活活动”的本能追求,尽管受到时间、支付能力、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其对某一产业而言是一个隐含、潜在的必要条件;资本追逐利润的人格化特性也不能想当然地左右有规律的产业格局的重构和产业的升级;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起的更多是一种顺水推舟、锦上添花的作用,行政命令或政策引导只能在符合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做多层次、多维度的思考。
一、文化之于生命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容易引发争议的“金苹果”,不同学科或专业背景的学者各有其文化的定义。尽管表述不同,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文化关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使生命富有意义,人类才创造了文化。对此,许多哲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思想。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具有特别的代表性,他认为:“在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里,‘文化’或‘一种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里,主要是指‘表意’(signifying)或‘象征’(symbolic)体系。”①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同时,雷蒙·威廉斯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能够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将文化与意义有机联系在一起。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直言“人是文化的动物”,是能够创造并使用符号表达其生存意义的动物,并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其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②[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美国文化批评家贝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文化是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符号形式的领域,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
的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经历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才是具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都在各式各样的心物交感中体认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意义产生于人们心灵的沟通的意愿,通过文化的体验和理解,复原它们所表征的原始体验和所象征的生活世界,正是理解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或扩展,使表达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使精神世界成为具有相关性和互通性的统一,使历史在阐释中成为现实。这也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潜在性和可能性。理解不是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人们存身其间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它构造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塑造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如果说文化是“表意或象征体系”,那么,审美文化则是这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感性是审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的根本规定性,但这并意味着它可以与别的文化领域毫不相干,审美文化总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宗教、政治、哲学、道德、科学、经济等文化领域纠缠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政治、科学、经济的派生物。
文化创意产业冠之以“文化”二字,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关乎“意义”的产业,关乎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产业,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是其内在的规定性的追求。与其他产业一样,其“产品”在为我们提供连续不变的世界图景的同时,重要的是也为我们描绘并帮助我们建构了自身的内在的私人生活:我们的幻想、情感和认同。这种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具体活动来分析意义被制造和再造的方式,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二、文化的转向与意义的迁移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相似性的一面。曾有人说五四运动仿佛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翻版,而当下的中国也似乎经历着西方工业革命后发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出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相继出现并产生弥散性的影响,特别是渐次迈过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2002年加入WTO等带有标志性节点之后,在全球化浪潮中社会转型处在进行时,文化转向不期而至,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极力批判的追求感官愉悦的大众享乐主义意识形态,注重游戏、娱乐、炫耀和快乐的消费文化。距离今天切近而遥远的80年代理想主义已经湮没,这个时候最关切的问题不止于所谓“改革共识”之类政治表象的问题,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维系一个共同意义世界的平台的消失,我们不但失去了与传统的关联,与神圣、崇高的关联,甚至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真正的关联。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并且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制造、左右着人们的口味、情趣乃至习性。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淡,文化生产本身日益成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很难找到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很难找到不体现文化意义的消费,文化消费演变为日常的商品消费。
对此,不少人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上加以分析并获得了不少的理论快感。其实,这种移植或照搬并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事实上,当我们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出现文化走向市场的附生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社会转型的社会很难契合。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正是文化单向、同质灌输,才常常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使文化异化的负面影响,但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和理解文化的内涵。文化不应只是“知识的和精神的”,或者说不只是阿诺德所推崇的“所思所言之精华”,文化也是“物质的”。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提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体制和日常行为。”文化分析就是一种暗含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澄清,同时,也“将借助于识文断字和其他高级交流之技巧的活跃的求知过程扩展到人民而不是只限于其中某些部分之要求。”(W illiams,1996:xi)在这里,雷蒙·威廉斯将文化与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创造意义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活动,而是我们所有人都介入其中的事情,所有人不分男女、贵贱、贫富、阶级等等,都在生活实践中创造意义,都是一种文化活动,诚如克罗齐所言,按其本性说来人人都是艺术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创造出为他人所欣赏的具有同等艺术水准的作品,也并不是都能“止于至善”即臻乎所谓“文化”的佳境。
这种“文化唯物主义”观念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具有天赋者的作品,也并非存在着绝对的品位和价值的等级划分,以经营符号性商品和信息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与以文化形式出现的材料生产中所涉及到各种活动相联系,包括创意、生产、再生产和交易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文化活动,都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这并不像某些传统人文学科那样试图提示出伟大艺术家灌注于其作品的复杂意义,而是聚集于文化产品的非刻意的复杂性。二是强调了普通消费者在文化消费中的主体性作用。消费者不是全然被动的主体,而是具有文化“生产”和“意义”再造的能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成为消费者可以亲近的中介,消费转化成一种体验和参与,一种更活跃、更真实的意义实现的活动,一种社会的体验与文化的认同。消费的动机不是来自于功能的使用,而是被文化的风格、价值观和审美所刺激的冲动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又深化了文化积累。这就由以往的“商品消费”转移到对“文化意义”的消费,能够从商品中以个性化的方式获取意义,从而建构起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文化世界,或者说第二种生活,一个没有地位差别或森严等级的世界,这种“自然状态”带来的愉悦,比一般的快乐远具解放的能量。
三、意义达成:传播技术的推动力量
信息传播技术是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意义生产、传播扩散的桥梁和推动力量,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已大大溢出技术的层面,它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
雷蒙·威廉斯从符号创作者及其更广的社会关系,把西方文化产业的变迁划分为三种形态或三个时代(era):1、资助(patronage),自中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诗人、画家、音乐家等受到贵族的资助,这一形态在今天也还有一丝存留;2、专业市场(market professional),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艺术作品”逐渐开始供出售了,文化生产中有了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发行中介和生产中介更加高度资本化,成功的符号创作者获得了“独立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缴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3、专业公司(corporate professional),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作品的委托生产变得专业化和更具组织性,创意除了直接销售,广告也成为了创意作品谋取利润的一个全新且十分重要的方式。①[美]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我们如果列出一份信息传播技术的重大发明与应用的清单,然后与上面雷蒙·威廉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的不谋而合的关系,能够感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发明对文化产业的促进或革命性影响。古登堡发明的机械印刷技术只是印刷故事的一半,许多为人忽视的发明创造所产生的影响就像指南针对航海的影响一样巨大。例如,1803年德国柯尼希发明、设计圆压式印刷机,一种用齿轮控制印版台升降和轴滚筒加油墨的印刷机,之后又得到进一步改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订购的这种结构相同共用同一给纸出纸结构的机器,速度每小时1600张。19世纪后半叶,机械印刷复制技术更是得到迅速发展。雷蒙·威廉斯所称的专业公司时代,也正是电子传播技术发明并逐步推广使用的时期,如电话、电影、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急剧扩充,与电视的普及相辅相承,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以当下的电子媒体技术为例。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使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不再仅仅是文字和书本,更多则是以声音、图像起作用的多媒体,某些非视觉的领域视觉化了,“世界即文本”的观念更换为“世界即图像”。图像在表意系统中已占有主导作用,成为整个意义系统的支配性力量,成为我们文化的日常表现形态。“媒介即信息”,电子传媒带来的“信息”其全部意义并非它所传送的声音和图像,而是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方式。电子图像表面看起来是自然之再现,但是它已是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拟态环境”,真正的现实迅速地退后甚至消失。人们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世界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传统的文化仪式所拥有的象征意味渐趋消失,对人生及意义的反思与情感冲动让位于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人日益成为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像不断切换的电视镜头一样,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
文化创意产业之产品意义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的作用下完成的。电视广告把人们想象中的美好图景以富有动感和感染力的音像画面呈现给观众,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仪式,把想象中的欲望和物质现实之间以及梦想和商业之间既新鲜又明确地结合在一起了。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广告对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了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并赋予其文化意义,通过意义传递把一般商品和属于文化范围的世界带到了一起。广告创意追求的是让观众一看便能发现商品与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这样一种效果。当这种象征性的共同点建立起来的时候,观众就会把他或她知道的一些属于文化范围内的特征归属到广告代表的消费品上去了。这样,“它将审美内容传播进了日常生活”②[德]沃乐夫冈·韦乐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版,第7页。,从文化到商品之间的特征转引便完成了。正是电视广告把商品的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或者说通过符号价值的强调,大众在消费过程中逐渐地消失于“符号”的海洋里。文化创意产业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生存和壮大的空间,把体现“意义”的文化元素注入到商品之中,换句话说,把浪漫、欲望、美丽、满足、归属感、科技进步和好生活“粘”到商品上,当尘世间的日常消费品和华贵、奇异、浪漫等文化特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再认真地辨认这些商品的原有的使用功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被符号和形象所吸引,使用价值就处于第二位了,并且这种以“符号价值”为前提的消费并不局限于某阶层,也不分男女老幼,而是大众普遍共有的消费方式,这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潜在的消费人群和广阔的市场,也意味着拥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G114
A
1003-4145[2011]12-0039-03
2011-10-28
陈小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