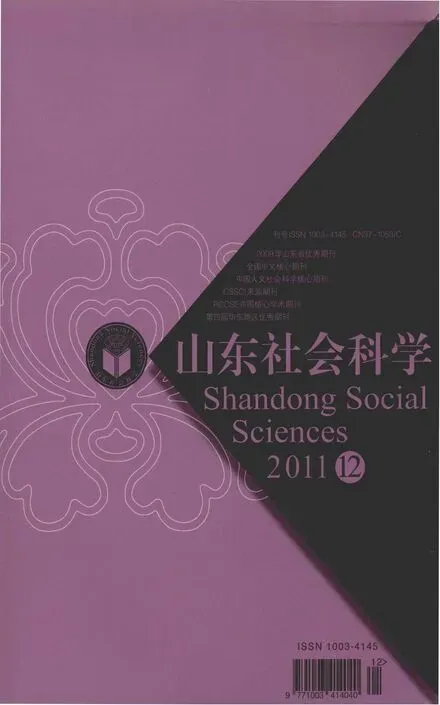论英美侵权法上的医疗特权
韩 冰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论英美侵权法上的医疗特权
韩 冰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医疗特权是医患关系由传统的医生家父主义向绝对患者中心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残余物,是对患者绝对中心主义的必要矫正,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界定应采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应当对医疗特权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侵权责任法》仅规定了绝对的告知义务,过于僵化,建议立法对英美法上的医疗特权制度进行借鉴。
侵权;告知;医疗特权
所谓医疗特权,是指当医生认为特定信息披露在医疗上为不当处理时,为避免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潜在损害,医生得故意保留该信息不予披露。医疗特权使医生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得以豁免,是有关医疗专业过失诉讼中重要的抗辩理由之一。医疗特权是在充分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前提下,对专业判断的有限保护规则。传统上,医生在医患关系模式中居主导地位,医生诊疗行为只须符合专业标准即为合法。大多数患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无保留地交到医生手中,医生对于诊疗行为具有广泛的权力。晚近以来,患者中心主义被提出,家父主义让位于患者自主和决策分享机制。医生须对即将采取的诊疗手段及其预期利益与潜在损害,向患者充分告知并进行公开讨论。患者中心主义强调患者的知情权在诊疗过程中的绝对价值,“告知后的同意”成为医疗诉讼中的重要诉因。但是,患者自主权的绝对化并未给患者带来真正的利益。医生可能会畏手畏脚,趋于保守;患者则有可能在冗长的程序事项中贻误治疗时机。其实,在医疗过程中,医生有义务以其独立最佳判断促进患者福利,选择最合适患者的治疗方法。医生在认为披露诊断或预防上的信息会给患者造成压力或损害时可选择不予披露。有人认为,医疗特权产生于医生在医学伦理上对患者健康所负义务与在法律上对其所负告知义务的冲突。也有人认为,医生不仅须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也同样须关注其心理和精神健康。笔者认为,医疗特权是医患关系模式由单边的医生家父主义向绝对患者中心主义转变过程中留存的残余物以及法律发展与社会生活相互作用、不断调适而产生的反弹物的混合,它的覆盖范围反映了医学专业行为标准与患者人权保护两种方向相反的利益主张在边界划分上的模糊性。
一、医疗特权的范围
医疗特权是在对严格的“告知后同意”的弊端进行纠正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是对患者绝对中心主义的矫正。但它仍维持对患者自主权予以尊重的基本理念,而不是向传统医疗“家父权主义”的回归。这里所谓的“特权”强调的是其例外性而不是至上性。因此,仍须对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作出必要限制。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即使对被视为“创设案例”的Canterbury v.Spence一案,学者亦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法官裁判意见表明,只要系争信息构成对患者的“威胁”,即无须披露。也有人认为,法官在该案中暗示,适用医疗特权的标准是信息披露是否会“阻碍合理决策”。还有人认为,只有在披露信息可能造成的损害“如果不是致病(pathohlogical)的,也必须是严重的(severe)”的情况下,才能免于披露。可以看出,由“威胁”到“严重损害”存在重大的程度差异,而所谓“阻碍合理决策”更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判断标准。所有这些说法,都未能对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作出有力澄清,如此一来,就会给医生留下过大的裁量空间。基于以上学说的模糊性和有限性,Van Oosten细化了适用医疗特权的理论,将其类型化为六种较为具体的情况:第一,披露会危及患者生命或影响其身心健康;第二,披露令人困惑或惊惧,可能会妨碍合理决策的作出;第三,披露会带来焦虑或悲痛,可能会妨害介入疗法的结果;第四,患者已经濒临死亡,披露是不人道的;第五,披露的风险大于或等于介入疗法的风险;第六,披露会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①F.F.W.van Oosten,The So-Called“Therapeutic Privilege”or“Contra-Indication”:Its Nature and Role in Non-Disclosure Cases(1991)10 Med.& L.31 at 32.这样的列举当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它对于医疗特权适用范围的类型化发展无疑是一个推动。医疗个案的具体情况不胜枚举,只有以这种概括加类型化的方法,才能较全面地涵盖各种不应告知的情形。
医疗特权的范围除了可以从正面列举外,还可以从反面通过排除规定予以明确。首先,若告知只是可能引发轻微损害,则不宜发动医疗特权。只有在征询告知或经告知可能产生较大损害时才可提出医疗特权而不予告知。有人甚至主张,只有为征询告知可能产生直接导致死亡的危险时才可以提出医疗特权,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显然过于苛刻了。其次,不能仅因患者可能会作出“不适当”的决定而发动医疗特权。因为所谓医生的合理医疗决定总能被认为是代表患者的意愿,或者患者只能在事先列明的有限“合理”选项中作出选择。再次,医疗特权也不能对患者应有的选择权越俎代庖。医疗特权的意旨在于基于人身生理特质的复杂性赋予医生自由专业判断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只有建立在患者自主决定的基础上才具备正当性。不能滥用医疗特权对抗告知义务,从而使患者决定权流于形式。因此,对于存在可替代方案的背景信息,医生应以患者可理解的方式充分予以告知,供其选择。例如,不接受手术而采取保守性治疗措施,不接受新研发、进口、昂贵药物而改用传统、国产、低廉药物,不在此医院本医师就医而改从彼医院他医生就医等。最后,医疗特权不能以对健康有利为由,剥夺患者对余生的安排权利。在一些患者被诊断罹患绝症的病例中,医生履行如实告知可能会对患者精神造成巨大打击,甚至意志崩溃,不利于病情的稳固。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有策略地向患者告知。健康上的正负并不是患者利益的唯一指标。相反,在余生不多的情况下,患者如能知晓自己的病情,早日在有能力的条件下安排自己的余生,以及对身后事项作出安排,才更符合尊重其人格自主的本意。至于因告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更策略的告知方式、更人性的心理辅导、更周全的看护制度来克服。
二、适用医疗特权的限制
基于医疗特权发动标准的模糊性,为防止其在实践中被滥用,有必要对适用医疗特权加以必要的限制。首先,发动医疗特权的举证责任在医方,医生必须证明不披露特定信息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医生须就上述Oosten所列情况以及患者自主权可能受到的损害等情况作出综合衡量。这一举证责任并不那么容易满足,因为大多数法官认为,医疗特权不应当被轻易援用,否则就会“将披露义务完全吞噬”,而法官的这种倾向性态度足以让医生们在动用医疗特权时有所克制。其次,如果患者主动要求医生披露特定信息,医疗特权通常不能援用。因为此时患者已经通过其请求行为暗示其对自主性的重视,医生对披露的利害关系进行权衡时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而不能对其自主性作一般性的推定。当然这条规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披露确定对患者构成巨大威胁,保留信息还是会得到法庭的认可的。第三,医生须评估特定时间患者对信息的需求与接受能力,考虑患者的个性特征和临床记录,依此决定适宜的披露方式。医生应谨慎地回答所有提问,努力减少负面效果;仔细倾听和回应患者所需,增进医患关系,防止患者蒙受就医压力与不适;不能因倾泻式的告知可能造成患者不安就豁免所有的告知义务,此时医生须就应以何种方式告知进行合理评估,这种评估可能比较困难,但却是在最后不得已援用医疗特权前所必须认真考虑的。第四,不存在完全的信息披露豁免,医生至少应告知患者其所拟实施的治疗程序的基本性质和结果。当认为暂时不应披露时,仍须继续关注和观察,选择适当时机予以充分披露。豁免的正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披露在延缓至适时后仍应作出。对此应作出明确的计划,以避免无限制保留。美国2006年6月伦理与司法委员会《关于医疗特权:对患者信息保留的报告》中指出:“医生应在潜在有害信息可获知前,就考虑披露问题,鼓励患者就接受医疗信息作出抉择”,②E.Patterson,Therapeutic justification for withholding medical information:What you don’t know can’t hurt you,or can it Nebraska Law Rev.1985;65:721.“医生应按患者的需要、期待及偏好剪裁其披露内容”,③W.Weston,Informed and shared decision -making:The crux of patient- centred care.CMAJ.2001;165(4):434 -9.“为尊重患者自主权,医生应向所有患者提供接受相关医疗信息的机会,向患者询问其愿意接受信息的具体范围及接受方式,医生应尽可能地满足这些偏好”。①B.Freedman,Offering truth:one ethical approach to the uninformed cancer patient.Arch Intern Med.1993:153:572 -6.最后,有些患者希望保留特定信息,有些希望家庭成员参与决策,或由家庭成员代理,医生须尊重其意愿。医院须向病人的配偶、亲属或关系人披露并征询其意见。医疗特权的使用涉及医生及病人的权益,为避免争议,宜在病历中详细记载。
三、我国法律关于医疗告知义务豁免的规定及评述
上述英美法国家医疗特权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医患关系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化的反映。医疗特权理论的发展,反映了法律对于医患之间就告知与自主的博弈与协调的态度更易,也代表着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新立法趋势,因此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和参照。
我国有关医疗告知义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之中。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②王 岳:《对于医生说明或告知义务保留问题(保护性医疗措施)的法律反思》,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1.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786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承认了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时享有知情权保留的特权,并认为此种保留是“一种对医疗正义的误解和歪曲”。但笔者认为,对上述立法进行规范性分析,并不能得出我国现行立法认可对知情权保留的结论。上述立法中但书的措辞与其说是对前半段所宣示告知义务的豁免和否定,毋宁说是在认可告知义务的基础上,对该义务的履行方式及效果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换言之,上述有关规定并不认可对知情权的任何保留,而是绝对地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
《侵权责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上述立场。该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显然,即使此前立法中真的曾经存在所谓“知情权的保留”,这一萌芽中的医疗特权观念也业已就此夭折。我国相关立法从未明确意识到医疗特权的特殊意义,而只是僵化地引入了绝对的告知义务。《侵权责任法》的条文表述则体现了对医疗机构履行“妥善告知”、“避免不利后果”的法定义务的舍弃。相同立场在不宜向患者本人告知时则要求其近亲属书面同意的规定中同样清晰可见。虽然绝对的告知义务能最大程度地尊重患者的知情权,进而保障其能对下一步的治疗和生活作出更加理性的预测和选择。但是,绝对的告知义务并非总是对患者有利,僵化地履行告知义务有时甚至会给患者以致命的打击。赋予医生在特定情形下享有医疗特权,对患者知情权予以适当的保留,应该是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尊重人权的立法选择。笔者相信,《侵权责任法》立法者的本意是善良的,意图通过绝对的告知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然而,事与愿违,《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极易成为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推卸、逃避责任的保护伞。实务中,医生将患者同意作为诊疗行为唯一合法依据与患者对于签署同意书的疏离感和抵触情绪,已经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害事故的发生。③如2007年11月北京的肖志军事件,丈夫拒绝签字无法实施手术导致母子双亡的惨剧。http://news.sina.com.cn/s/2007-11-24/113014378612.shtml。2008年3月浙江兰溪的周国书事件,妻子脾脏破裂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8/04/01/009368059.shtml.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在接受患者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承认医生在告知义务中的医疗特权豁免,并参照英美侵权法上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对其适用范围和限制作出合理的法律规制。
D913
A
1003-4145[2011]12-0076-03
2011-07-12
韩 冰,上海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法。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