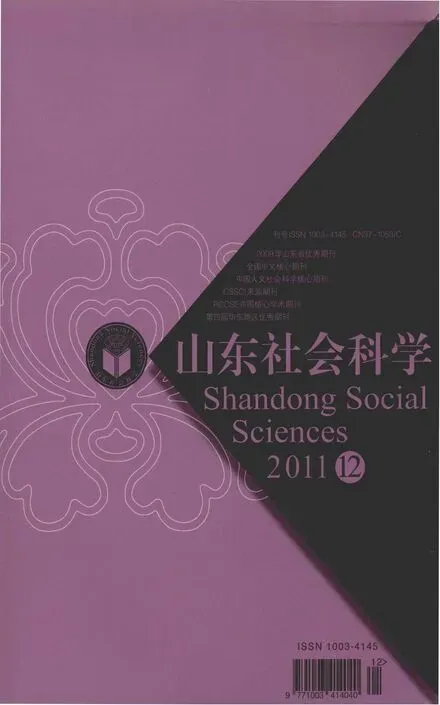学术自由略论
张献勇
(山东工商学院 政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学术自由略论
张献勇
(山东工商学院 政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学术自由是指以高校为代表的学术机构中的教师和学者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受外部强制的权利,由主体、对象、内容三要素构成。学术自由不仅为很多国家宪法所确认和保护,也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中国当前语境中,应注意认识和把握学术自由的主要问题:学术自由并不只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由,它不是绝对的自由,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应防止学术机构对个体学术自由的损害,以司法途径维护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要素;宪法规范;问题
一、学术自由的要素
学术自由,有时也称学问自由,中外学者对其概念一直颇有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者观察视角的不同。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学术自由的观念产生于19世纪初威廉·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学术自由观念是大学的核心”、“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性”等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学术自由包括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两个方面。教的自由是指,教师在专业上享有自由探讨、发现、出版、教授在其专业领域内所发现的真理,而且这种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亦不听从任何权威的指挥,任何主旨的政党及社会的舆论不得加以干涉。学的自由则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正确方法指导下,在专业学习上拥有探讨、怀疑、不赞同和向权威指出批评的自由,有选择教师和学习什么的权利和在教育管理上参与评议的权利。①张宝昆:《人的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外国教育动态》1988年第1期。可见,洪堡所作的定义是从学术自由的主体和内容出发的。日本宪法学者芦部信喜则从学术自由的性质角度做了考察,他认为,学问自由属于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学问自由的中心,是以发现、探究真理为目的的研究自由,这是内在精神活动的自由,构成了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并且,如果研究的结果无法发表,研究本身最终是无意义的,因此学问自由当然也就包括研究发表的自由。研究发表的自由,是属于作为外在精神活动自由的表达自由的一部分。②[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在学者的个别努力之外,一些组织也试图对学术自由加以界定。如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美国学院协会(AAC)联合发表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影响最为深远,基本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学术自由的理解。③周光礼:《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第39页。声明提出了学术自由三方面的内容:教师享有研究以及发表成果的充分自由;在教室中讨论其所选择之主题的自由及其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学校审查制度或纪律约束的自由。1988年,致力于教育、发展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大学会社,在利马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宣言》。在这一文件中,学术自由被定义为:学术团体成员——个人或集体——通过研究、学习、讨论、教学、讲座、写作、生产、创作等方式,发展、追求和传播知识的权利。①John Daniel and Nigel Hartley(edited),Academic Freedom 2,World Univercity Service,1993,p2.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对此三要素的分析有助于对学术自由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界定。
(一)学术自由的主体
学术自由的主体是指谁享有学术自由。需要厘清的相关问题有:首先,学术自由的主体是组织还是个体?可以有集体性或机构性的学术自由与个体性的学术自由,即学术组织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与学术活动中主体个人思想和表达自由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因而,组织和个体都可以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笔者认为,尽管学术自由的主体包括了大学等在内的学术组织,但从根本上说,学术自由是一项个体的基本权利,学术组织的自由权或自治权利是个体学术自由的引申、派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体的学术自由,是个体学术自由实现的一条途径或一种方式,而非个体学术自由的对立物。因而,个体是学术自由首要的和核心的主体。
其次,学术自由的主体是可能的主体还是现实的主体?从可能性上讲,所有的个体都有可能去从事学术活动,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但从现实性上看,并非所有的个体都在实际从事着学术活动,特别是将学术活动作为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职业而加以追求。进言之,在现实性上,对学术自由的主体亦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将学术自由的主体限定为学术组织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一切学术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者和教师们,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内有寻求真理并将其晓之于他人的自由,而无论这可能或给当局、教会或机构的上级带来多么大的不快,都不必为迎合政府、宗教或其他正统观念而修改研究结果或观点。”②[英]戴维·M·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自由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如“学术自由指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有不受不合理干扰和限制的权利,包括讲学自由、出版自由及信仰自由。”③《大美百科全书(卷1)》,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译,光复书局1990年版,第36页。笔者认为,虽然不宜将学生排除在学术自由主体之外,但学术自由的主体主要是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中的教师和学者当是无异议的。
再次,如将教师和学生作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凡承认学术自由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大学以外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是否享有学术自由,即能否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对此问题,在日本,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在适用于中小学的教师与学生方面应受到限制是得到承认的。④[日]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5页。
(二)学术自由的客体
学术自由的客体指学术自由的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即学术。具体看,学术自由客体有三类:⑤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1)从事学术活动的行为,包括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学术交流、教学、学习以及这些行为的辅助行为或派生行为(例如学术机构中日常生活的管理、学术课题申报和评审中的纯事务性工作等);(2)学术观点、思想,形成和表述这些观点、思想的方法,以及这些观点、思想和方法的载体(如书籍、论文、言论);(3)与学术活动不可分离的资源,如接近学术机构的机会、学术职位的占有和维持、开展学术活动所需要的适当场所、学术成果发表的途径、学术交流的渠道等。
(三)学术自由的内容
学术自由的内容是学术自由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自主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人不得强制。对组织的学术自由而言,要求免于学术组织外部的强制,实行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一种制度性保障,主要是为保障教师、学生的学术自由而提供必要的物资、管理及选择教师与学生的自主空间,从而免于学术以外的其他势力干涉。⑥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主要内容包括:(1)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理论上都被认为和法官一样,在职务上要保持独立性,不受上级行政当局的指挥和支配;(2)学校的行政、教授和研究人员的人事安排要有一定独立性;(3)学校(校园)的内部秩序、大学的设施和学生生活由学校自己组织师生来管理。⑦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而对个体的学术自由而言,外部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学术组织外部的强制,包括来自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宗教力量等的强制,其中主要是政治力量的强制;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学术组织内部的强制。而此种学术组织内部的强制属于学术组织自治或自主管理下的强制,是集体性学术自由意义上的强制。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和研究的需要,可对本文所要探讨的学术自由作一狭义界定:学术自由是指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机构中的教师和学者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受外部强制的权利。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规范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根本法、高级法。宪法规定的一般都是该国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在宪法中确认学术自由,反映了制宪者对于学术自由重要地位的认识。注重以成文宪法保障学术自由的典型国家首推德国。早在1848年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第152条和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20条中先后出现对学术及其教学自由进行的规定,这是最早在宪法中引进学术自由的条款。①杨克瑞、王凤娥等编著:《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发展——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一战后,魏玛宪法第142条亦保障艺术、学术及其讲授的自由。二战后,德国基本法第5条也规定了保障研究与讲学的自由。在德国,从普鲁士宪法、魏玛宪法、到德国基本法,无不保障讲学自由。
20世纪初以来,学术自由逐步成为不少国家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之一。据对世界上142个国家宪法的统计,规定学术自由的有34个。②[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各国宪法一般在“公民基本权利”这类章节设立学术自由的专门条款,这些条款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一)从基本权利的角度作出一般规定
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意大利、土耳其、越南等国家。如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33条:“艺术与科学自由,讲授自由。”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27条:“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学习、传授、解释和传播科学艺术的权利,有对科学艺术进行各种研究的权利。”越南1992年宪法第60条:“公民有权研究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改进技术、合理化生产,创作、文艺批评和参加其它文化活动。”这种模式旨在说明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
(二)从国家义务的角度作出一般规定
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较多,有西班牙、埃及、日本等。如西班牙1978年宪法第20条第1款:“承认并保护的权利:1.以口头、书面或任何其他复制的方式自由表达和传播思想、想法和意见。2.文艺创作、科技发明。3.讲学自由……”埃及宪法第49条:“国家保证公民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自由,并给予鼓励。”日本1946年宪法第23条:“保障学术之自由。”苏联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马其顿等国家也大多采用这种模式。俄罗斯联邦1993年宪法第44条:“保障每个人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其他类别的创作、教授自由。”匈牙利1990年宪法第70条G第1款:“匈牙利共和国尊重并支持科学和艺术生活自由、课程自由和教育自由。”克罗地亚1990年宪法第68条:“科学、文化和艺术创造的自由受到保障。”马其顿1991年宪法第47条:“保证学术、艺术及其他形式创作的自由。”这种模式意在强调国家负有尊重和保障学术自由的义务。
(三)在规定为基本权利的同时,禁止妨碍该自由的实现
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不多。如比利时宪法第17条:“教学自由。禁止一切妨碍教学自由的措施。”这种模式体现了制宪者对于国家权力干涉学术自由的高度警惕。
(四)既规定为基本权利,又加以必要限制
德国、希腊、马尔代夫等国家采用这一模式。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5条第3款规定:“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马尔代夫1968年宪法第16条:“在不违反教律和法律的情况下,有获得知识和传授知识的自由。”这种模式下,制宪者并不认为学术自由是一种绝对的基本权利,而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进行限制。
(五)既规定为国家义务,又进行必要限制
如巴拿马1972年宪法第100条:“承认讲学自由,除大学章程出于公共秩序原因而规定的限制外,不得有其他限制。”哥伦比亚宪法第41条:“保障教育自由。但国家可对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实行最高级的检查和监督,以力求实现文化的社会目标,使受教育者得到最好的智育、德育和体育。”这种模式下,国家负有承认和保障学术自由的义务,但由于国家义务又是国家职责,为防止其以承认和保障学术自由之名,行使限制和侵犯学术自由之实,而对其在方式和目的上进行规范。
(六)同时规定为基本权利和国家义务,并对基本权利作必要限制
如希腊1975年宪法第16条第1款:“艺术、科学、研究和讲授自由,促进其发展与提高是国家的职责。艺术学术自由和讲授自由并不免除任何人忠诚于宪法的义务。”
另外,还有不少国家的宪法尽管没有使用“学术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讲学自由”等语词,但是经宪法适用机关的解释,其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条款被认为逻辑地包含了学术自由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联邦国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1957年斯韦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为包含了对学术自由权的确认和保障。首席大法官沃伦籍由此案提出了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自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自由业已进入国际人权法领域。《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利和义务宣言》、《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等诸多国际人权法文件中有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意见自由等的规定,亦涉及到学术自由的一些方面。同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教师地位规约》、《科学研究者地位规约》均涉及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问题。此外,在世界大学会社、国际大学协会、国际大学教授和学者联合会以及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还诞生了许多直接针对学术自由的宣言、声明。例如,1988年《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利马宣言》、1988年《学术自由和学术社会责任达累斯萨拉姆宣言》、1990年《知性自由和社会责任堪培拉宣言》、1992年《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锡纳亚声明》、1993年《学术自由波兹南宣言》等等。①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这表明,学术自由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权利。
三、中国语境中的学术自由
我国1982年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本条实际上就是对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权的保障。②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可以认为是学术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表达。此外,《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该法并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这是学术自由第一次被写进我国的官方文件,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宪法、法律和文件虽然均对学术自由有所规范,但由于中国缺少学术自由的传统和积淀,要使纸面上规定的学术自由转化为实践中的学术自由,还需从多方面努力。以当下的中国语境,笔者认为尤应注意认识和把握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术自由不只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由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了科学研究自由,这里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不过,这只是一种通常的学理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并未对其作出正式解释。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学术自由程度,最重要的尺度不是宪法上是否作了规定,也不是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是否存在限制,而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预设了禁区。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提供多元化性,只服从真理,而不能强求学术活动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当然,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
(二)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学术自由并非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但基于学术自由的基本权利地位,对它的限制适用“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规则。即应受到来自于其它基本权利或宪法价值的宪法体系上的限制。当学术自由与人的尊严、平等权等其它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产生冲突,应依据宪法的价值秩序标准,并且保证宪法价值一致性,通过宪法解释来解决。在这类冲突中,学术自由对于与其相冲突的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不能永远居于优先地位。①李文章:《关于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外限制问题》,《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6期。前已述及,一些国家在宪法中将学术自由规定为基本权利的同时,又加以必要的限制,这就反映了学术自由的非绝对性特征。实际上,随着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将学术理由理解为绝对自由,很可能将对人的尊严、生存造成威胁。例如,产业技术研究的进步,所产生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以及遗传因子重组实验、无性生殖等遗传因子技术研究,以及体外受精、脏器移植等医疗技术研究的进展。消除这些尖端科技研究产生的威胁及危险,基本上应由研究者自主和自制。但是仅仅凭自制是不够的,有时为保护人的尊严等基本权利或重要宪法价值,需要对学术自由加以必要且最小限度的限制。
(三)学术自由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在政府规制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之间,应有相对确定的界限,明确政府能干什么与不能干什么。这的确没有一条公理可循,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规则不一。在中国,学术长期以来受到政府的不当管制和干预甚多,尤应反思。学术归根结底是学者的事情,政府能做的主要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这首先包括设定建立学术机构、选任学术人员的标准,处理有关这方面的纠纷;其次是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最后是设立尽可能少而精尖的奖励。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与使用、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等宜交由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自主处理。②郑永流:《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学术界》2004年第1期。
(四)防止学术机构对个体学术自由的损害
学术机构一方面为个体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条件和平台,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侵蚀学术自由的危险。特别是当前在各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等目标的冲动中,尤其容易实施某些违反学术规律、损害学术自由的措施。高校应尽可能地远离功利学术,主要通过激发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使其保持一种“不为一己之利所诱惑、不受世俗需求所驱使”的精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获得内心满足。高校虽然可以对学术成就突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给予表彰奖励,但对全体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数字化、教条式的定期定量考核,完不成任务的予以惩戒乃至降低待遇等,是有违于学术规律、有损于学术自由的。因为学术生命的本质在于创新,但是创新通常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要求一个教师或科研人员一年内有多个学术创新(通常以论文表现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必将助长学术浮躁和腐败。
(五)以司法途径维护学术自由
司法既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维护学术自由的最后一个屏障。尽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但对于这一自由的内容和界限还缺少来自司法实践的阐释。近年来发生的诸如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某高校教师因“没有教师资格证”被停课、上海某高校教师因上课时有批评时局内容被举报和侦查等一系列关涉学术自由的事件,本应是以司法维护学术自由的恰当契机,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未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些争端。由此可见,要将宪法“本本”上规定的学术自由贯彻到实践中,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G644
A
1003-4145[2011]12-0092-05
2011-10-25
张献勇(1970—),河南安阳人,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决策、执行、监督——高校内部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0873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陆影luyinga12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