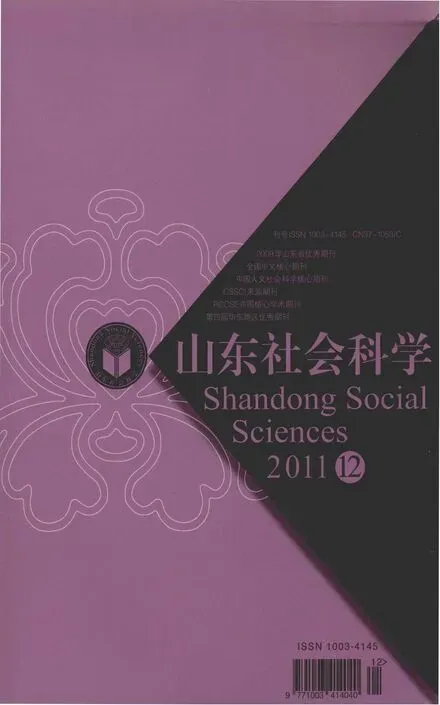从葆拉·马歇尔《寡妇颂歌》中的民俗事象说起
李 敏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从葆拉·马歇尔《寡妇颂歌》中的民俗事象说起
李 敏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葆拉·马歇尔的小说《寡妇颂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间传说和民间音乐铸就了小说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美学价值,同时这些民俗文化也因作品这个载体被赋予了更加久远的生命。
葆拉·马歇尔;《寡妇颂歌》;民俗事象
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1929—)是美国当代杰出的黑人女作家,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先驱人物。马歇尔的父母是加勒比海巴巴多斯的移民,祖先是来自非洲的黑奴,她本人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多米尼加人居住区长大,复杂的家族背景和多元的文化滋养使她的文学创作展现出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寡妇颂歌》(Praisesong for the Widow)是作者198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1984年获美国图书奖,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艾薇在美国梦的奋斗中迷失自我,而后又重返精神家园的故事。国外有关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研究已有相当规模,但国内评论界对葆拉·马歇尔的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其第一部小说《褐姑娘,褐砖房》(1959),而且数量不多,对《寡妇颂歌》这部作品也只是停留在简单介绍的层面上,研究上基本还是空白。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步和传承”①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民俗事象纷繁复杂,神话传说、民间歌舞、婚丧礼仪、节日庆典等皆在其中。至于民俗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以用法国艺术家丹纳的名言作一归纳:“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由心境和四周习俗所造成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即:民俗文化土壤是文学艺术产生所必备的条件。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历来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因此,从民俗学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一、伊博人的传说与口述传统
今天枝繁叶茂的美国黑人文学最初是在几近荒芜的文化沙漠上发展而来的。由于其奴隶身份,美国黑人很长时期内被排斥在以文字为标志的正统主流文化之外,因此,口头性(orality)便构成了美国黑人文化的主要特征。凭借着口耳相传,非洲的文化得以部分地保留下来,也正是在这个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口述文学逐渐产生、发展、壮大起来,民间传奇、神话故事、演讲、布道词、黑人歌曲等口述艺术构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的一幅独特风景。可以说,口述文学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奠基石,也是其独树一帜的魅力所在。
在《寡妇颂歌》里,作者马歇尔把民间故事和口述传统拉入对黑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审视中,这个民间故事就是伊博人的传说。伊博人的传说民间版本很多,选取下面三个为例:
黑夜是非洲之神,
用愿望和疲惫
织成一双翅膀,
哦,飞回家吧,飞走吧,
……
我的爷爷就飞回了非洲,
展开双臂,
飞回家去。
——罗伯特·海登(美国黑人)
有些人说黑人死了就能回到非洲去,这是谎话。人死了怎么还能回去?是活着的人飞回去了。那些西班牙人不再从那个部落贩运黑奴,因为很多黑奴都飞走了,生意不好做了。
——埃斯特班·蒙蒂如(古巴前黑奴)
非洲人不吃盐,他们说那些不吃盐的非洲人来的时候就像是些巫师——他们无所不知。知道他们为什么飞回去吗?他们受不了重活和工头的鞭打。他们就站起身来,唱着歌,拍着手,就这样,他们伸开双臂就这么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以实玛利·韦布斯特(牙买加人)①W endy W.Walters,“‘One of Dese Mornings,Bright and Fair,Take My Wings and Cleave De Air’: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Africans and Diasporic Consciousness”,in MELEUS,Fall 1997,p.1.
这三个不同的说法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民间故事,即黑奴的祖先是会飞的。从故事叙述者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故事流传面很广,实际上,在美国、拉美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黑人后裔中,这个传说几乎是妇孺皆知。可以说,“在任何一处受大西洋奴隶贸易波及的海滩,都会产生一个集体神话”②W endy W.Walters,“‘One of Dese Mornings,Bright and Fair,Take My Wings and Cleave De Air’: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Africans and Diasporic Consciousness”,in MELEUS,Fall 1997.p.2.。这个传说的版本多达上千种,仅在1940年出版的名为《鼓与影》的民间故事集里,就有27种之多。
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民间故事,名字是《上帝的子孙都有翅膀》。流传在康涅狄克州的故事讲述了几个黑奴不堪庄园主的鞭打,“把锄头往地里一杵,‘呱呱呱’叫着,腾空而起,变成秃鹰飞回非洲去了”③Meredith M.Gadsby,Sucking Salt:Caribbean Women Writers,Migration,and Survival,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6,p.25.。圭亚那人说他们的非洲祖先“把葫芦掏空,坐在里面,盖上盖子,就飞回非洲了”。古巴的一个前黑奴回忆说:“当时的情形是,他们的灵魂脱离了身体,在大海的上空游荡,就像蜗牛离开了自己的外壳。”④Lorna Mcdanie,l“The Flying Africans:Extent and Strength of the Myth in the Americas”,in New West Indian Guide,1990,no:1/2,p.29.Z.N.赫斯顿在她的民间故事集《告诉我的马儿》中对非洲人不吃盐的说法又提供了另一种牙买加人的解释:“过去非洲人都会飞,因为他们从不吃盐。很多人被掠到了美洲做奴隶,但是他们不做奴隶,飞回了非洲,那些吃盐的人留了下来沦为奴隶,因为他们身子太沉飞不起来。”⑤Zora N.Hurston,Tell My Horse,HarperCollins ebooks,p.46.非洲祖先飞翔的方式上也多种多样,有的飘在贝壳里,有的骑在鸟的翅膀上,有的用树叶驮着,有的像火球一样腾空而起,还有的在水面上行走如飞,如履平地。……
除了民间故事,还有很多黑人歌曲同样传唱着飞翔这个主题,从下面这些歌曲的名字就能窥见一斑:《借给我你的翅膀》、《我要飞走了》、《假如我有一对翅膀》、《双翼》,等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就曾将飞翔的主题应用于她的小说《所罗门之歌》里,她回忆说她是听着黑人会飞的故事长大的,“那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飞翔是我们的天赋之一,人们常常谈论飞翔,这在圣歌和福音音乐里都可以找到”⑥Thomas LeClair,“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at: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in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ed.Danille Taylor,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22.。
伊博人的传说是会飞的非洲人的又一个版本。在《寡妇颂歌》中,女主人公艾薇6岁到10岁期间每年的8月都去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泰特姆(Tatem)岛上看望她的曾姨妈康妮。康妮老人会定期带艾薇去一个叫伊博人登陆的地方。书中有着大段仪式化的描写:每周至少两次,日落黄昏时,老人会“庄重”地戴上帽子,系上腰带,沿着同一条路线,跋涉一个多小时。期间,老人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脚步坚定,从不歇息。她们最终来到水边一块空地上,泰特姆岛上的河水在此与大海交汇。在这里,老人每次都用同样的措辞、同样的语气讲述同样那个伊博人的故事:
他们就是给带到这里的……我奶奶说人很多,那会儿她还没你大。……那些伊博人一上岸就停住了,朝四周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他们那天看到的东西你我都看不到,因为我奶奶说这些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有着过人的眼力,能看到他们的前生后世。……然后,他们转过身去,一个不落……朝着河边走去……人们会以为他们走不远
的,因为他们是走在水上,再说,他们身上还有那么多铁镣……但是这些都没能挡住伊博人的脚步。我
奶奶说他们径直往前走就好像脚下不是水而是坚实的土地……他们还唱起歌来了……歌声在泰特姆岛
的另一边都能听到。……①Paule Marshall,Praisesong for the Widow,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83,pp.37 -39.
马歇尔讲述的这个伊博人的传说与民间版本有所不同。按照民间说法,这个故事发生在乔治亚州圣西蒙岛上的邓巴溪。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当地一个叫怀特的老人这样说:“贩奴船把伊博人带到那里,伊博人不喜欢那个地方,他们唱着歌大步地往回走,要回到非洲去,可是他们没能回得去,都淹死了。”②Meredith M.Gadsby,Sucking Salt:Caribbean Women Writers,Migration,and Survival,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6,p.23.按照另外两个说书人弗朗姬和昆比的说法,伊博人是被奴隶贩子以打工为幌子骗到美国来的,等他们发现上当了,他们决意死也不做奴隶,于是他们用锁链把自己拴在一起,唱着歌跳水自尽了。他们还说,至今人们还能在夜里听到邓巴溪水里低沉的说话声、恸哭声和铁链的叮当声。对此,古巴前黑奴蒙蒂如却有另一番说法:“有些人说那些黑人投河自尽了,这不是真的,他们把锁链拴在手腕上,可那锁链是充满魔力的。”③W endy W.Walters,“‘One of Dese Mornings,Bright and Fair,Take My Wings and Cleave De Air’: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Africans and Diasporic Consciousness”,in MELEUS,Fall 1997,p.16.奴役的枷锁在他的版本里变成了力量的源泉。
会飞的非洲人的故事千变万化,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飞越海洋或水域,飞向大洋彼岸的非洲家园,因为他们的根在那里。马歇尔让她笔下的伊博人回到了家乡,邓巴溪的伊博人却永久地留了下来,其实这些会飞的非洲祖先是不是真的回到了故乡,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飞翔故事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美国黑人对奴隶制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和对黑人民族性的坚守。然而,这个康妮老人精心守护的精神家园却在艾薇长大后对白人主流生活的盲目追逐中丢失了。
艾薇和丈夫杰罗姆经过30多年的打拼,成就了自己的一份家业,从哈雷姆的黑人贫民区一路奋斗到纽约州白原市的大房子里,完成了从社会底层到中产阶级的飞跃。然而也正是这个飞跃让他们脱离了黑色的文化沃土而落入了白色的精神荒原。婚后的最初几年,艾薇每年都会带丈夫到泰特姆岛伊博人登陆的地方,像康妮姨妈当年那样给他讲伊博人回家的故事,然而这个旅行很快就被各类求职、补习、加班等代替了。为了多挣钱,杰罗姆有时会同时打两份工。这个曾经风趣健谈、迷恋黑人音乐的年轻人,变得吝啬虚荣,甚至嫌弃自己的黑人同胞,还扬言要“把哈雷姆区的舞厅全关掉,把鼓都烧光”④Paule Marshall,Praisesong for the Widow,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83,p.132.;而艾薇自己也变成一个好妒忌、爱吵架的怨妇,记忆中倒背如流的伊博人的故事早已被那个挣大钱买大房的幻想给挤得无影无踪了。杰罗姆人到中年就一命呜呼,留下富足的寡妇艾薇在落寞中打发无聊的日子。
艾薇与杰罗姆的悲剧不是孤立的。多少年来,美国黑人文化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美国黑人也始终生存在社会的边缘。许多黑人因为自己的黑人身份而惶恐不安,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黑人性。有人会漂白自己的皮肤,拉直自己的卷发,以求在外形上更接近白人文化的审美标准;有人则在行为举止、话语方式上模仿白人,极力“白化”自己;更有人梦想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以期得到强势文化的接纳。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背离了自己的民族之根,走向了自我异化。他们选择的其实是一条不归之路。
口述文学的传承自然缺不了口述者,因此在美国黑人文学里,讲故事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母题,是美国黑人作家“把编神话、讲故事的口述传统创新为一个文学模式”⑤Joanne V.Gabbin,“A Laying of Hands:Black Women Writers Exploring the Roots of Their Folk and Cultural Tradition”,in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Afra -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0,p.246.。《寡妇颂歌》的结构就充分体现了讲故事这一口述传统。全书共分4大章。小说开篇,艾薇是一个65岁衣着光鲜、举止得体的黑人中产阶级妇人,正和朋友在豪华的游轮上享受着加勒比海的旅行。不想夜夜恶梦缠身,梦里早已过世的康妮姨妈气急败坏地要拉她去伊博人登陆的地方。这样几次三番让艾薇感到身心俱疲,只好中途在格林纳达下了船,可是因为误了当日回纽约的航班,她不得已要在当地住一晚上。第二章是以倒叙的形式展开的。在宾馆里,艾薇浮想联翩,和丈夫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一股脑地倾倒出来。虽然叙述视角始终是第三人称,但是大段的意识流独白让读者仿佛置身现场,亲耳聆听艾薇的倾诉,特别是在艾薇的思绪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她一连串的质问和情不自禁发出的有10次之多的怒吼声:“够了!”另外,这一章的标题是Sleeper’s Wake,此处的wake有着双重的含义,即可以解释为“苏醒”,也可以理解为“守灵”。“苏醒”是指艾薇经过反思,黑人意识开始觉醒,为下一章艾薇踏上回归之路作铺垫;“守灵”则是用言语的方式缅怀亡者,是对亡者的倾诉,因此艾薇讲述者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
伊博人的传说在小说里有着更多的讲述者。从事件的目睹者“我奶奶”到艾薇的曾姨妈康妮,这个接力棒又传到了艾薇的手上。小说的结尾,艾薇计划卖掉白原市的房子,在泰特姆岛上安家。她准备让两个外孙和他们的同学每年夏天都到岛上来。每周两次,她会带着孩子们到伊博人登陆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用康妮姨妈同样的话语讲:“他们就是给带到这里的。”这个故事在艾薇的子孙那里还会继续讲下去的,而这也正是马歇尔小说创作的意义所在。
二、民间歌舞:甩抖舞
民间歌舞是产生于民间并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非洲民族能歌善舞,歌舞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部分。不论是婚丧嫁娶、祭祖拜神、还是人际交流、抒发情感,非洲人都善于采用歌舞的形式。美国黑人继承了非洲祖先的音乐天赋,这一点从他们音乐创作的多样性和流行性上便可以看出,从早期的劳动号子、灵歌、布鲁斯、爵士乐到今天的说唱音乐、黑人街舞,无一不透出美国黑人非凡的音乐才华。对于美国黑奴来说,音乐的功能性尤为突出,音乐是他们抒发情感、祈求神灵、寻找精神慰籍的最佳渠道。在《寡妇颂歌》里,与伊博人传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外一个民俗事象是甩抖舞。
甩抖舞(ring shout)是流行于美国和加勒比海国家黑奴中的一个宗教仪式。美国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伊斯(W.E.B.Du Bois)曾经把传统的黑人教堂仪式归结为三个因素:牧师(preacher)、音乐(music)和狂态(frenzy)。牧师扮演的是灵魂引路人的角色,通过激情的讲道,引领信徒到达如痴如狂的境界。最具黑人特色的宗教音乐是灵歌(spiritual),灵歌内容上取自赞美诗和《圣经》,曲调上加入了非洲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灵歌属于即兴演唱,通常的表现方式是有人领唱、众人回应,这即是黑人音乐独特的呼唤—应答方式(call and response)。人们时而浅唱低吟,时而高亢呐喊,用歌声宣泄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这种状态达到高潮时,信徒的情绪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这时,“有人沉默不语,表情凝重,有人低语呻吟,有人身体完全失控,顿足、尖叫、大喊,横冲直撞,双臂挥舞,或出现幻觉或神情恍惚”①Allen D.Callahan,The Talking Book: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Bibl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63.。据说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神灵才能降临,信徒才能脱离罪恶获得救赎。《寡妇颂歌》里的甩抖舞就集中了杜波伊斯所说的这三种因素。
甩抖舞通常在祷告会之后举行,信徒围成单行的圆圈,按逆时针方向拖着脚步行走,或拍手或拍膝,发出类似非洲鼓点的节奏,其间他们会吟唱或是祈祷。领唱的人站在一边,边唱边击掌或顿足,为舞者提供伴奏。仪式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甩抖舞带有明显的非洲舞特征,“圆圈移动、脚步拖沓沉重、姿势和手势、站立的样子、双手伸出保持平衡或放在两侧、肩膀的晃动,这一切都源自于非洲”②Albert J.Raboteau,African Slave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4,p.71.。在西非的伊博人、约鲁巴人、伊比比奥人和中非巴刚果人的葬礼上,也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甩抖舞:逆时针行走,渐快的节奏,在最后的癫狂中与祖先的灵魂相会。
有关甩抖舞的记载很多,下面是美国内战期间北方军进入南卡罗来那州沿海岛屿时看到的一幕甩抖舞:
教堂内的连椅都推到了墙边,男女老少站在地板中央,随着灵歌歌声的响起,他们排成圆圈拖着脚步前行,他们的脚几乎不离开地面,身体的移动主要是靠肢体的用力拉扯……歌声和舞蹈都十分强劲有力,有时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单调沉重的脚步声让半英里内的人都无法入眠。③Allen D.Callahan,The Talking Book: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Bibl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66.
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甩抖舞中的步法有着严格的规定,随意挪脚或是走出舞步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在神面前跳舞是对神的极端无礼和亵渎。康妮姨妈还年轻的时候,一次她在甩抖舞上被人发现“双腿交叉”,这被看做一个舞蹈动作,所以康妮被赶了出来。一气之下,康妮不再参加任何教堂活动,转而把伊博人登陆的地方当成了她新的宗教。然而许多个夜晚,艾薇发现康妮姨妈悄悄站在教堂对面的路上,透过教堂敞开的门,贪婪地看着里面几个年长的人跳甩抖舞:
他们拖着脚步往前走着,脚上是干活时穿的沉重的鞋子,鞋底始终贴在地板上,每走一步,只有踵部抬起落下……发出一声声像鼓点一样准确而又复杂的击打声。夜越来越深,气氛也越来越热烈,击打声响彻整个泰特姆岛。
他们唱着:“驾着马车的人是谁?/哦哦哦”,要么拍手,要么拍打着膝盖、大腿或胸口,发出让人接应不暇的切分音节奏。他们晃动着肩膀,偶尔居然还摇摆一下他们不再年轻的屁股,他们恣意地扭动着自己正在衰老的身体,但是脚却从不抬离地面,当然更不会两脚交叉走出舞步来。
他们两臂上伸……墙上的灯光投射下围成圆圈的身影,他们一边用颤巍巍的声音唱着不成调的歌“你的命握在我手里/哦哦哦”,一边一个挨着一个拖着脚往前滑动。即使神灵附体攫住他们的灵魂,即使他们扭动的身体好似要腾空而起冲上夜空,他们的脚也会永远牢牢地钉在地上。①Paule Marshall,Praisesong for the Widow,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83,p.34.
这一幕让一旁的小艾薇感到“血液里有一股想要跳舞的冲动”,于是,她一边低声哼唱着一边学着挪着步子。但是遗憾的是,长大后的艾薇脚步越挪越远了。面对夹缝中的黑人文化,她选择了背弃和忘记,甚至当有人问她祖上是非洲哪个民族时,她竟然不知所措、无言以答。直到多少年后的一天,一次偶然的加勒比海卡里亚库岛(Carriacou)之行才让她迷途知返,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在格林纳达滞留时,艾薇偶遇一个名叫拉伯特·约瑟夫的人,后者告诉她他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正举办一个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他力邀艾薇一同前往,于是艾薇便随约瑟夫踏上了去卡里亚库岛的游船。
卡里亚库岛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西非黑奴后裔。每年岛上都有一个祭祖活动,称为大鼓仪式,或称民族歌舞仪式,届时生活在岛外的族人会从各地回到卡里亚库岛,以各具特色的祭奠形式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热爱。这个时候的卡里亚库岛就是一个缩微版的非洲大陆,积聚众多古老非洲民族的后代,浓缩了非洲绵长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对于艾薇来说,岛上的一切让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岛民像家人一样对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岛上的克里奥耳语让她想起了哈勒姆区的黑人英语和泰特姆岛上的快乐时光,在向祖先乞求谅解的祈祷仪式中,她甚至依稀觉得康妮姨妈就站在身边。泰姆奈人、芒戈人、肯巴人、昌巴人、班达人,这些陌生而又遥远的民族用他们的歌声和舞姿渐渐唤醒了艾薇沉睡多年的记忆。“一个喊声从院子一角响起,声音沙哑、无调、苍老……紧接着,其他喊声和鼓声回应过来,一个、两个、有时三个人边唱边加入到圈子里,尽情地舞动起来。”音乐变得越来越欢快,鼓点也越来越稠密,更多的人涌入跳舞的圆圈,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好像很多条手臂汇成一股从圈子里伸出来,把她(艾薇)拉了进去。”艾薇发现自己正随着人流按逆时针方向走着,“她的脚不由自主地向前滑动着,几乎不离开地面,只是穿着低跟鞋的脚踵每走一步就轻轻抬起”。第一圈,“她走得小心翼翼,好像脚下的地面真的是水,每走一步都是在试探能否担得住她的重量”。伊博人回家的情景在艾薇身上重现了。第二圈,她熟练多了,夸奖的声音从四面传来,但是艾薇已经浑然不知了,仿佛8月里那几十个燥热的夜晚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正和姨妈站在教堂对面黑黢黢的路上。夜幕下,她模仿着教堂里那些围成一圈拖着脚步走的老人,跳着那个不能称作舞的舞蹈——甩抖舞。那一瞬间,她感到万千条斑斓的丝线从周围跳舞的人的心里、眼睛里、肚脐里射出,进入她的身体,就像是母婴之间的脐带,把她和母亲连在了一起:
她开始舞动起来,就像脚自己找到了节拍,她的臀部也不由自主地扭动着。……她双臂下垂,两肩……用力前耸,再猛然收回,摆动的头高高昂起。……尽管她剧烈扭动着身体,却总是小心翼翼地遵守着那条古老的规则:鞋底决不离开地面。……她不知道自己的胳膊抬起来多久了,也不清楚走了多少圈了。……她感觉身体像是要腾空而起,飞向夜空。②Paule Marshall,Praisesong for the Widow,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83,pp.238 -248.
在歌声、鼓声、音乐声中,艾薇获得救赎从而涅磐重生。那一刻,流浪的女儿终于回家了。
《寡妇颂歌》里丰富的非洲民俗文化因子,构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美学价值。马歇尔曾说,美国黑人作家“担负着双重的责任:一是要利用目前丰富的民俗和历史资料,二是要用英雄的字眼来诠释这些资料”③Wendy W.Walters,“‘One of Dese Mornings,Bright and Fair,Take My Wings and Cleave De Air’: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Africans and Diasporic Consciousness”,in MELEUS,Fall 1997,p.18.。马歇尔所说的双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胸怀和文化担当。小说《寡妇颂歌》创造出的独特文化景观,是对其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塑。这种重塑在展现人类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人类文化的健康传承提供了可能甚或注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力量。
I106
A
1003-4145[2011]12-0164-05
2011-10-20
李 敏(1962—),女,汉族,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