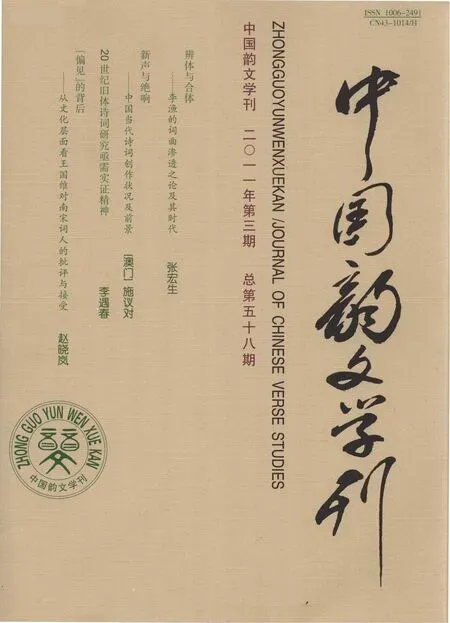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抒情与群体认同
唐元 张静
(防灾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系,北京 101601;北京语言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3)
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它究竟起源于何时。传统的认识中,由于李陵诗、团扇诗、古诗十九首等五言诗的创作年代和作者颇存争议,加之钟嵘《诗品》总序“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1](P11)的说法,班固的一首《咏史》被认作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五言诗。这个观点,在近些年得到了学者们的有力反驳。在赵敏俐先生的《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①见《北方论丛》1994年第 1期。另,关于文人五言诗起源的论争历程,可参见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 1期。一文以及众多学者的相关讨论之后,几乎已经题无剩意。在班固之前,五言诗体已经成熟,它的“质木无文”只是单篇作品的风格问题,并不能作为判断五言诗在当时还很稚嫩的依据。将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限定在某一人的某一首作品上面,一方面文献不足,一方面也并不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五言诗的发生与发展,是诗歌史的自然过渡,并没有确切的时日断限。对起源和真伪问题的过多纠缠和顾虑,曾经阻碍了对汉代五言诗的更多层面上的研究。在汉代,大部分的诗歌并不与某个具体的诗人附着在一起,放下这个定要知人论世的包袱,可以看到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更多特性。抒情和诗体认同方面,就值得更加细致地分析。
一 关于“文人”与“五言诗”的悖谬
如果我们把五言诗当作一个诗体来看的话,且不论团扇和苏李诗等等的真伪,单看汉乐府,其中就有很多五言诗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诗第六》:“今考西汉之世为五言者有主名者,李都尉班婕妤而外,有虞美人《答项王歌》(见《楚汉春秋》)、卓文君《白头吟》、李延年歌(前四语)、苏武诗四首。其无主名者,乐府有《上陵》(前数语)、《有所思》(篇中多五言)、《鸡鸣》、《陌上桑》、《长歌行》、《豫章行》、《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陇西行》、《步出厦门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怨歌行》、《上留田》(里中有啼儿一首)、《古八变歌》、《艳歌》、《古咄唶歌》(此中容有东汉所造,然武帝乐府所录,宜多存者)。歌谣有《紫宫谚》、长安为尹赏作歌、无名人诗八首(上山采蘼芜一、四座且莫喧二、悲与亲友别三、穆穆清风至四、橘柚垂华实五、十五从军征六、新树兰蕙葩七、步出城东门八。以上诸篇,或见《乐府诗集》,或见《诗纪》)。古诗八首(五言四句,如采葵莫伤根之类),大抵淳厚清婉,其辞近于《国风》,不杂以赋颂,此乃五言之正轨矣。”《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7页。。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大家却在斤斤计较一个五言诗的起源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把五言诗又加了一个限定,那就是所谓“文人”的五言诗。即是说,像班固、张衡、秦嘉他们写的才是文人的五言诗,乐府里的五言诗是“非文人”的。因此,乐府诗有了另一个界定——民间的①如江艳华《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源流与影响》:“民歌刚劲蓬勃的艺术精神、丰富不拘的体格形式、自然多姿的表现手段、清新鲜活的语言风格,都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而汉末文人效法乐府民歌五言体创造诗歌主流形式的巨大成功,又给他们提供了榜样与典范。”参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 4期。及陈天祥《试论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五言诗在汉初的高祖时代就已出现,它源于民间,后来逐渐传入宫廷和文人之中。”参见《名作欣赏》2005年第 10期。。这是一个很不严密的区分。首先,乐府不完全是民间的。乐府本就是一个朝廷机构的名称,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秦代时已有建制,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最为昌盛。乐府诗的来源有二,一是搜集的各地歌谣,一是组织文人进行的创作。即便是前者,也是经过了乐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的采集和润色,谐乐演唱的,这与《诗经》中《国风》部分的形成相似。所以,乐府诗当然与民间有很大关联,但它们的采集、使用和流传,都有着很多朝廷的因素。其次,乐府诗也有文人因素。汉代乐府诗中本就有很多文人的作品,而能够收集、整理、创作、编排这些诗的乐府职官,又为何不能被称作文人?再次,文人的也就是民间的。在汉代留下诗歌的作者们,大部分都并非皇亲贵戚、列土封侯,住在高墙深院里的,反而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生活于民间,创作于民间的,难道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写诗,曾有个一官半职,就变成非民间的人了?民间与文人的两分是对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错误认识。
乐府诗与文人五言诗确实不同,但并不在创作主体的截然差异,而是在于“歌诗”与“诵诗”的区别②参见赵敏俐《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6期。,简而言之,就是前者入乐,后者不入乐。在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诗体的新变往往是由新的乐曲声调来带动的,但是在乐推动了诗产生新的体式之后,又往往有一个趋向,就是这种新诗体对促生它的乐曲的脱离,而由诗与乐的综合性形态演变成诗句文本的独立形态。在汉代,诗与乐府分离之前,应该说,诗在谋篇布局上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声调、演唱、伴奏、舞蹈等与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形式所共同赋予的,诗歌的诗体文章艺术并不具备完整的独立价值。而被称作“文人五言诗”的不入乐诗体逐渐发展之后,汉语诗歌艺术开始在自身语言文字、篇章结构、音韵特性等方面的全面的规范化、主动性、艺术化的追求,不再依托其他艺术样式而存在。直到唐代,律诗体制的完善,汉语诗歌作为纯粹的诗语言的高级艺术到达了最高峰,具备了非常细致的规范性和艺术性。
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还有另一个问题:五言诗的起源是可以被限定的吗?刘勰就已经说过:“按 《召南 ·行露 》,始肇半章 ;孺子 《沧浪 》,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2](P66)其中,《行露》出自《诗经 》,《沧浪 》出自 《孟子 》,《暇豫 》出自 《国语 》,《邪径》见载《汉书》,可以说,五言诗其实一直都有。尽管《行露》这样的作品并非从头到尾都是五言句,但是,从《诗经》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诗歌艺术已经成熟的先秦时期,无论是四言句,还是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句,任何一种诗句的写作都已经没有障碍,《诗经》之所以以四言句为主,是由当时的诗歌风格和音乐结构所决定的,而并非诗人们不会写其他句式。汉代的五言诗,又不像后世的律诗有那样多的形式限定,片段的五言句与完整的五言诗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的鸿沟,它们之间的过渡是非常自然的。在楚汉战争的时候,就有了虞美人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3](P89)见载于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③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班固《咏史》最早的出处同样是张守节《史记正义》。,随后,又有 《舂歌 》、《李延年歌 》等 。除了所谓当时人写不出这种诗,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伪诗,而我们也不能说《和项王歌》就是最早的五言诗了,因为在以赋诗断章为习惯的先秦时期,《行露》的五言诗部分就可以被单独拿出来吟诵,那简直就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在它与汉代五言诗之间,并没有什么艺术上的界限需要着力地突破,所以在秦汉之际还有类似的作品也是很正常的。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兴盛时期不一样,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也不必将五言诗的起源限定在某一人、某一诗。与后来南朝、初唐等时期大张旗鼓的诗体革新不同,两汉时并没有班固或是谁的振臂一呼,而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完成了主流诗体的时代性变迁。
二 汉代文人五言诗由群体抒情向个体抒情的转化
汉代文人五言诗以抒情为尚,在诗由“言志”向“缘情”的转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①可参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它既没有像《诗经》那样沉积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容,具有不朽的民族诗歌奠基意义;也没有像楚辞那样充满着炽烈的宗教意识和爱国情感,放射着神奇的浪漫光彩。它只不过是一些无名文人关于个人生活的吟咏,是发目于普通人心怀的抒情短章。”《文学遗产》1995年第 2期。及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的抒情化倾向,始于东汉。东汉末期,一些愤世嫉俗的士人,便已突破汉大赋体物的传统,创作了一些批判现实的抒情短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可惜数量极少,不成气候。而产生于汉末的无名氏《古诗》,却全面出现了浓浓的抒情色彩。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文人,抒发了闺人怨别、游子怀乡以及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浓厚的感伤情怀。曹魏之声,近沿枚、李。建安诗风直接上承《古诗》,并使抒情化倾向铺延到辞赋、散文,形成了一股任情的潮流。”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69页。。而它们对诗歌发展的开创,不仅在抒情,更在于体现出由群体抒情向个体抒情的转化。汉代诗歌是以群体抒情为主流的,而在其中,也孕育着个体抒情的倾向,对后来的诗坛颇具引导性。胡应麟在《诗薮》中言:“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汉之诗也。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此“无意”[4](P22),正是汉诗之胜处,亦汉诗与后世相别处。后世之诗,皆有意,且与诗人个体的遭际心性紧密关联,汉诗的主流,或抒发普遍之心性,或虽抒写个人遭际而不以此为主观之目的。故汉诗之“无意”,正体现汉诗与后世诗歌之界限。汉诗背后,是一整个时代,而后世之诗的背后,是先有一个诗人,然后才是时代。后人仰望汉诗,却终于不能再造,非才不能也,而是诗歌创作的心态与追求已经不同了。从这一点上讲,《古诗十九首》是汉诗的绝代遗响,是代表汉代诗歌最高成就的高峰,却是类型化的群体抒情诗,而不是个人化的个体抒情诗。它们以无与伦比的成就终结了一个时代,而《咏史》以下的诸多文人五言诗,才是属于新时代的新诗。
1.汉代《古诗》的群体抒情性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无署名的《古诗》,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钟嵘《诗品》即说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P75),其后历代佳评仰慕,斑斑可表。《古诗》对后世的影响诚然十分巨大,但它的一个特性,却是与后世诗歌不同的,那就是群体抒情性。许学夷《诗源辨体》中说到:“汉魏五言,由天成以变至作用 ,故编次先 《十九首 》,次苏、李 、班婕妤,次魏人 。”[5](P65)“天成 ”与 “作用 ”之别,说来玄 妙,但诚如许学夷所言:“汉魏五言,由天成以变至作用,非造诣有深浅也。”[5](P73)这并非诗歌水平的高下之分,而是诗歌抒情取向的差异。《古诗》并不对应具体的作者,这与《诗经》、乐府以来的早期诗歌创作传统相一致,它所抒发的,是群体之情,而不是个人之情,不强调个性,而含有时代之同悲。这是建安以前诗歌的主流特征。毛先舒的《诗辩坻》即对汉代《古诗》的旨意有此概括:“《古诗》二十首:`行行重行行',谪宦思君也。`青青河畔草',怨不得其君也。`青青陵上柏',愤时竞逐,相羊玩世也。`今日良宴会',遇时明良,思自奋也。`西北有高楼',悲有君无臣,思自效忠也。`涉江采芙蓉',放臣思君也。`明月皎夜光',怨朋友也。`冉冉孤生竹',伤婚姻迟暮也。`庭中有奇树',感别也。`迢迢牵牛星',怨君臣意隔,不获自通也。`回车驾言迈',孤臣流放,自怨惩也。`东城高且长',悲时迈也。`燕赵多佳人',恋君也。`驱车上东门',伤时速迈也。`去者日已疏',小人日进,社稷将墟,贤者睹微而牵于时位,欲去不得也。`生年不满百',伤时逝也。`凛凛岁云暮',怨妇思夫,见于梦寐,因自述梦也。`孟冬寒气至',`北风',时气衰乱也;`众星',小人聚也;`蟾兔缺',君道亏也。君虽思旧见召,心衔恩遇,而惧罹于祸,怨思之志也。`客从远方来',孤臣见召,思效厥忠,义同胶漆也。`明月何皎皎',伤时将乱,欲遂归志也。”[6](P50)
可见,虽然因为不入乐,《古诗》在诗体上与乐府有了脱离,但是一诗咏一事,一诗抒一情这样的类型化追求,却与乐府诗的立题解题非常相似。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言:“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食覆言。初无可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7](P200)这种类型化、群体化的诗歌,与魏晋之后的诗歌的竞才逞奇、个性飞扬的面貌有很大区别。这并非汉代诗歌有什么实在的桎梏,而是时代风气使然。汉代乐府和古诗的作者,也有自己鲜活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自己与众不同的遭际感受打着自己的烙印去体现在诗歌里,而是往往隐去了具体事件要素,抽象出一个广泛的场景和情感,加以描写。《古诗》的这种抽象的写法,也在后人眼中加深了不可测度、无迹可求的天然高雅的神秘。而到了建安时期,个性化的五言诗创作完全展开了,个体抒情遂代替了群体抒情,诗歌之面貌,随之大变。如《文心雕龙·明诗》所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2](P66)而在建安之前的诗歌中,也有个体抒情的因素存在,它们仿佛星星之火,呼应着建安的燎原之势。
2.班固《咏史》的个体抒情因素
《汉书·艺文志》中,这样概括汉代乐府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8](P3024)在班固看来,在汉代创作中,能上承《诗经》传统的,是“代赵之讴,秦楚之风”这样的乐府歌谣。而他判断的标准,是讽喻——这是诗歌的真正价值所在。可以看出,班固依然是以“诗言志”的标准来判断诗歌的,所以他将汉乐府的价值也拉到了讽喻的一面,实际上,汉乐府当然不只讽喻一面,但是,汉代政府采集歌谣,确实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的,一些汉乐府的创作和整理,也是以此目的为前提的。班固的看法并不错,但是,诗歌的创作目的和实际影响往往并不一致,汉乐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继承了《诗经》的言志传统,更重要的是为崭新的诗体和诗思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班固的《咏史》毕竟是被确认、被公认的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所以它还是处在时代坐标上的一首重要作品。在这首依托在具体史事上的诗中,同样有个体抒情的可能性。它在体式上和个人抒情上的突破,已经露出了新时代的特征。所以,从班固自身对诗歌的理解来看,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旧的诗歌时代,但他却又有意无意间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路标。
班固这首《咏史》写的是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缇萦救父的事情: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2](P170)
这首诗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唐代张守节的《正义》和《文选》卷三十六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的注。缇萦救父的故事载于《史记·孝文本纪》,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汉书·刑法志》里也有记载。班固这首五言诗的内容就是对缇萦救父的故事的叙述。在著名的医生齐太仓令淳于意将要被处以肉刑之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儿子,因此不会有人在危难时加以解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向汉文帝上书,愿意牺牲自己而免除父亲的刑罚。引起汉文帝的感叹悲怜,因而废除肉刑。这八句诗,第一句交待了肉刑的由来,二到七句就是对事实的记述,有“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这样的描写句,最后一句发出“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正是钟嵘所说的“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1](P357)。这首诗语言朴素,基本上就是对史事的平铺直叙,与成功的五言诗作相比,确实显得质朴,甚至有些板滞。从文采上讲,钟嵘“质木无文”的评价是准确的。而在钟嵘眼中,最后一句的“感叹之词”,是这首诗的亮点,符合了他对诗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P1)的认识。这种感叹,不是生命易逝、游子思乡、君臣关系等汉代诗歌经常表现的感情,而有着另外一层潜在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咏史》诗很像是班固在编纂《汉书》时对缇萦的故事有感而发创作的,但是如果联系班固的生平,这首诗的创作却很可能还寄托着班固对自己的遭遇之叹。班固一生中曾经两次身陷囹圄,而他的晚年入狱,则与他不成器的几个儿子颇有关系,《后汉书·班彪列传》载:
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9](P1386)
班固的几个儿子不遵法度,因而与洛阳的官吏交恶,他的奴婢又得罪了洛阳令种兢,在失去了窦宪的庇护之后,种兢出于报复逮捕了班固,这位有着旷世之才的大文人就这样惨死狱中,命丧宵小之手。在班固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想起自己的几个不能施以援手的不孝子,想起自己也曾经是为皇帝器重的臣子,如果这首《咏史》创作于此时,相比于有着幼女冒险相救,有着汉文帝垂怜的淳于意,班固的处境显得何其悲凉!那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之词,就凭添了许多愤恨哀叹。如果这首诗并非创作于此时,当班固想起自己这首旧作,当我们将这首诗与这样的处境联系起来,就更是成为了班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令人心痛的预言。这首看来平淡的《咏史》诗,因为班固的身世,却有了一层深潜的凄凉味道。仅是这首《咏史》诗,就引出了一个与传统中盛世修史、忠君臣子所不一样的班固的诗人形象,这不正是班固寄寓在五言诗中的个体抒情因素吗?班固还有三个五言诗佚段存世:“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披百领,县官给衣衾。”“宝剑值千金,指之于树枝”。“延陵轻宝剑。”①孙亭玉在《班固文学研究》中认为后两段来自同一首诗,并将这两首残诗命名为《霍光葬礼》和《季札宝剑》,认为它们是与《缇萦救父》类似的咏史诗。《班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2](P170)显然也是类似于这首诗的咏史之作。班固在修史的同时,也写出了这样的咏史五言诗,尽管其艺术技巧似乎并没有达到如他的赋作和史传作品那样的高度,但是,这其中的情感却是与他本人的遭际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不仅为班固本人的艺术成就添了色,也表现出了诗歌发展的新趋向。
3.苏李诗的形成——个体抒情的追溯
苏李诗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一朵奇葩,它既不像《古诗十九首》那样可以径直抛开了作者谈而更加清音独远,也不像 《咏史》、《见志诗》、《秦客诗》等可以坐实了作者和时代去挖掘。千百年来,人们既不足以证明它们确是李陵、苏武所作,也不足以证明它们与李陵、苏武没有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扯之间,本来应该在诗史上据有重要一席的苏李诗折损了多少精气,它本身的艺术成就反而鲜有人问津了。其实,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诗歌史就是一个接受史。在苏李诗与苏李的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被传承了这么多时代以后,诗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分割。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也体现了后人在接受时的追溯习惯。这些诗,体制风格都与汉代《古诗》非常相似,也是可以归入群体抒情一类的,而它们在传承时与苏李的传奇故事结合在一起,又具有了个体抒情的因素。如上文所论述,苏李诗即便是苏李所作,在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气中,也不一定会署名,也很有可能从自身遭际中抽象出时代性的共同情感来抒发,所以,现存的苏李诗的形成,更大的可能,是后人在个体抒情的五言诗已经成为诗歌主流形态之后,对前人所作诗歌的追溯和落实。
在《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有一首李陵所作的骚体《别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3](P109)而五言体的苏李诗,被《文选》、《玉台新咏》、《古文苑》等总集所收,还有一些残诗见于各种类书所引。其中,萧统《文选》载有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3](P337)
从骚体与五言的李陵诗,可以看出,骚体《别歌》有“沙幕”、“匈奴”等明确地指示李陵个人遭际的字眼,所表达的意旨也具备李陵本人的独特性。而五言诗则没有这样标示李陵的特殊遭际的字眼,表达的别情,既可以是李陵的,也可以是所有人的,是与汉代《古诗》同样的群体抒情。可以说,苏李诗的真伪之所以被长久地质疑,与这种群体抒情的特质很有关系,因为人们潜意识就认为这些诗与李陵苏武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文选》都没有收,最早见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的班固《咏史》,之所以从来也不被质疑真伪,也与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史学家班固理应写咏史诗不无关联。在诗歌发展到诗与诗人有着很紧密的关系的时候,所有的诗歌都自然携带了他的创作者的一段具体人生。尽管鉴赏一首诗的好坏,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知道它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倾向,但是,一旦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对诗歌背后的人与故事的追索就不可阻挡了。所以,当钟嵘、萧统、刘勰不约而同地要为五言诗梳理一个源流的时候,当时诗歌的个性化已经非常普遍了,尽管他们也知道苏李诗与苏武和李陵的关系是存疑的,但这种关系却是被欢迎的。在此时的人们写作五言诗的时候有意识地体现自己的个性与遭际的情况下,他们在追溯前人诗作时,亦会想要去落实这些诗作的具体作者和情境。这些诗作,是否出自苏李之手,因当时作诗之情况,已不可确认,但在后人看来,苏李诗如果是苏李亲作,会显露更完整的价值。所以苏李诗等汉代五言诗,所关键之处,不仅在其是否流传之作者所亲作,而在后人如何看待与借鉴它们,在这一点上,苏李诗与苏李本人,已经无法分开了。
三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个人创作与群体认同
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已经无需再多纠缠,但是,传统观点上对东汉方有文人五言诗的看法,仅仅是一个该被纠正的误解吗?这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诗歌创作与诗体认同,并不是同步的。汉代的五言诗创作,不止一直都有,而且数量不少,也不乏佳篇,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些五言诗创作出来的同时,五言诗作为一个诗体的可靠地位就树立起来了。在文学史上,身份认同与艺术突破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往往会注重艺术突破,去寻求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最早”在哪里,实际上,“最早”往往是不经意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得到了足够的认同,可以建立源流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时此种文艺样式的创作、倡导者往往会向先贤追溯其同类作品,而塑造一种传承脉络,他们所抬起来的源头和榜样,在创作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后世的这些讲究。从这一点来看,《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作品并不足为奇,苏李诗亦如是。六朝时人对这些作品创作于西汉时期之判断,或有实际之依据,或乃一种积极的追溯,这有助于他们为自身创作在传统性上的认同而张目。
所以,五言诗的个人创作其实一直都有,尽管这些诗的作者并没有署名或者很难确认。但是,五言诗作为一种主流的诗体被诗人群体广泛认同,大量采用,还是要降及它真正得以爆发的建安时期。正如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所言:“五言之成立时期(东汉中叶迄建安)。五言在当时虽为一种新兴诗体,然在一般朝士大夫心目中,其格乃甚卑,远不如吾人今日所估计。与此后词之初起,正复相似。故在第三期,五言乐府虽已流行,而文人采用者则惟班婕妤一首。然其时四言之体,弊不堪用,虽为之而难工,复以一时潮流所趋,故一方面诋乐府为郑卫之声,一方面仍不能不窃取乐府之体以为五言诗。班固之《咏史》,傅毅之《冉冉孤生竹》,即此期产物。厥后文人五言诗,则有张衡《同声歌》、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宋子侯《董娇娆》等,皆乐府也。若秦嘉之《赠妇》,郦炎之《见志》,赵壹之《疾邪》,高彪之《清诫》,则皆徒诗也。迄建安曹氏父子出,而五言遂成为诗坛之定体焉。”[10](P23)辛延年、宋子侯这样的诗人,既没有苏武、李陵那样的传奇故事,亦没有戚夫人、班婕妤那样的特殊身份,也不像班固、张衡那样有别的建树,他们单以零星之诗作垂名后世,这在建安以前是很难想象的,而在这之后,则是常有的现象了。这并不是他们生前就凭诗作名满天下,他们的身后名,是此后学习、推崇他们的诗人所赋予的。胡应麟《诗薮》说:“昔人谓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窃谓二京无诗法,两汉无诗人。即李、枚、张、傅,一二传耳,自余乐府诸调,《十九》杂篇,求其姓名,可尽得乎!即李、枚数子,亦直写襟臆而已,未尝以诗人自命也。”[4](P131)诚然如此,在五言诗统领天下之前的这些诗作,并没有诗人群体的整体性主观追求,但由言普遍之志到言自己之志,从抒普遍之情到抒自己之情,这正是汉代文人五言诗开启一个新时代的着力之处。汉代人在五言诗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也为新的诗歌形式,塑造了新的诗人群体。
所以,事实上,汉诗,甚至汉代以前的诗歌,一直都有缘情的一面,但是,汉代诗歌的真正突破、独立价值的真正形成,还是要以五言诗的定型兴盛为标志,而群体抒情向个体抒情的转变,在此形成过程中作用很大,并且个体抒情的确认,大大激发了诗人群体对五言诗体的认同和广泛使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该把建安还给汉代,不仅因为建安本就是汉代的年号①曹道衡《两汉诗选》前言:“以建安属魏实有困难,因为在建安初年,曹操还没有封为`魏公',何来`魏朝'?”《两汉诗选》,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7页。,也因为建安文学正是汉代文学的发展所蓄势而成,建安文学是汉代文学这颗大树萌芽生长后所结出的硕果,它与汉代文学脉络相连,如果将建安与两汉断开,而作为魏晋文学的起点,反而是将建安文学视作了无本之末。
[1]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C].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5]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