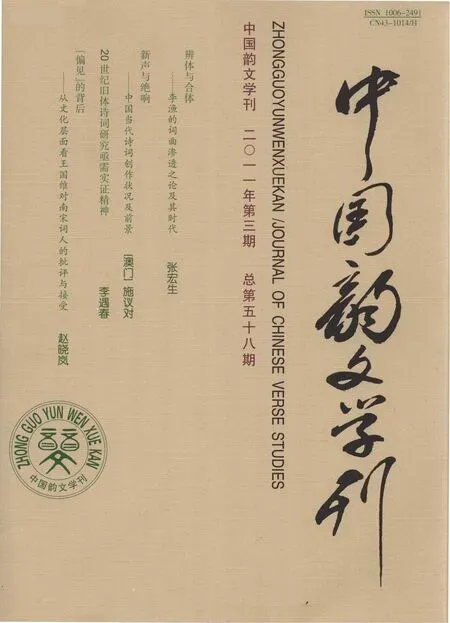“偏见”的背后——从文化层面看王国维对南宋词人的批评与接受
赵晓岚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宋词的整体评价颇低,著名词人除辛弃疾外,其他均多所诋斥,甚或是全盘否定。他的这种观点,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是偏颇之见。笔者在此不拟进行是非之辨,但以为,虽则王国维作出这一论断的主要标准是词之“意境”(或曰境界)的高下有无,然而在他据此所得出的这一“偏见”背后,实则隐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所秉持的观念,体现着他的文化眼光和文化选择。因此,从文化层面对他的这些词论进行观照,或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位大师的理解。
一
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所持的看法,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有精到的表述。他认为: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1](P154)
在这段话中,王国维分别用帝王派和非帝王派、近古学派和远古学派、贵族派和平民派、入世派和遁世派、热性派和冷性派、国家派和个人派的名称,从渊源、崇尚、身份、行为方式、性情表现、目标指向等方面说明了中国春秋以前两种不同的道德政治思想。由于前者大成于北地的孔、墨,后者大成于南方的老子,所以王国维又称前者为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而战国后的诸家学术思想,均是由此二派导源扬波,“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德政治思想作出了这种南北之分后,王国维于此文中进一步指出了双方当时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差异:诗歌为北方学派所专有,南方学派仅有散文文学。这是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学派的理想,是入世,是“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因此对现实的社会人生有深刻的体察,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题材和情感;而南方学派的理想是遁世,“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1](P155)因此多以散文的形式抒写其遁世无闷、嚣然自得的情志。
然而仅就诗歌而言,想象力亦为其重要的原质之一,南人在此方面的伟大丰富又远胜于北人。因此他又说:
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1](P156)
王国维于此处所论,实已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伟大作家和作品产生的原因:“大诗歌”之出,必须南北互通互融,将北方人的感情和南方人的想象合而为一,而“南人而学北方”的屈原正是融合了南北两种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肯定想象是诗歌的原质之一,将情感和想象的完美结合作为“大诗歌”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他仍坚持情感的基础性地位: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1](P157)
因此,他在文章的最后说:
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
他的这个结论,强调了北方入世、热情的文化对诗歌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未及于词,但诗、词既同为以抒情为主的“主观之文学”,那么自可对我们分析他词论背后的文化意义提供若干的启示。
二
王国维在南宋词人中,对稼轩推赏最多最力,或称其为南宋词人中唯一堪与北宋人颉颃者[2](P10),或云“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轩”。[2](P77)稼轩的《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一词,被誉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2](P20),甚而云“南宋只爱稼轩一人”[2](P75),其地位可谓独尊。然则从文化上看,辛弃疾与其他南宋词人相比,有何独特之处呢?
笔者以为,辛之所以如此受王的青睐,其原因正与屈原相同:他既具积极入世、热情豪放、坚忍勇毅、忧国忧民的北方文化精神,又熏染了南方富于想象的浪漫风气,当其将改变社会现实理想不能实现的抑郁牢骚发之于词,遂能成为“有性情、有境界”的伟大作品,呈现出“横素波、干青云”的宏大气象。
辛弃疾本为北人,出生于儒家文化昌盛的山东。而辛的祖上原籍陇西狄道,古来为征战之地,李唐王朝亦由此而兴。辛对自己原来的郡望十分自豪,曾自称“家本秦人真将种”(《新居上梁文》)[3](P103)。因此等内外之因素,辛弃疾积极入世、勇毅坚忍的北方人之情感特征十分明显。在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情感即表现为一种热烈执著的爱国主义,一生矢志于抗金恢复大业。尚在北方沦陷区的时候,他就对金人“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摧毁中原文化的行径感到“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美芹十论·观衅》)[3](P21);祖父辛赞有意识地对他进行的抗金复国的教育,亦深深扎根于心中:“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美芹十论》)[3](P1)正是这种深深扎根于心底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感情,使他后来才有聚集二千义军隶耿京“与图恢复”,以及杀义端,擒张安国,决策南向等一系列“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3](P267)的英雄经历。观其进呈君相的《十论》、《九议》以及其他奏疏,使人惊叹他何以会有如此深谋远虑的的战略思想,如不是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热情,视抗金复国为己任,岂能为此?而且他一再强调出兵山东的必要,《十论·详战》云:“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3](P54)其中除了对地理形势的战略考虑外,不排除他对故乡特有的热爱之情。再观其地方任上所作的一切抗金备战措施,真可谓为北伐中原耗尽心血。表现在词中更是一种缠绵不已的“西北望长安”的故土情结。纵览南宋词人群中,有北国家园沦陷之痛,又同时有真正驰骋战场经历的,除了辛弃疾,可谓绝无仅有(抗金名臣岳飞除外)。当时南方士大夫中虽不乏抗金有识之士,但相较辛弃疾这种与生俱来的家国一体的忠爱之情而言,理性的认识要多过切肤之痛。因此,辛弃疾的“北方人之感情”,既有特定时期中原人丧失故土故国之愤,又同时有其他词人所不具备的经过战火焠炼的坚忍顽强的收复之志,且具备封疆大吏独当一面的杰出才干。可以说,辛弃疾是真正用全副生命和全部感情写作的爱国词人,由此也造就出他“慷慨不可一世”的英雄之词。
辛弃疾二十三岁渡江南下,至六十八岁卒,期间沉沦下僚和闲退的时间居于大半,虽曾数度出任方面大员,但处境孤危,抗金复国之志难伸,事功难有大成,其间境遇,颇类屈原。而其“借歌词为陶写之具”的过程中,亦继承了屈辞中长于想象的南方感性文化精神。且不说其写山之“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写石之“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归朝欢》),写潮之“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写树之“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念奴娇》)等想象夸饰之作,也不说其写梦如《兰陵王》之类谲怪之作,单看词中最常见的月词如《太常引》写重磨飞镜、乘风斫桂,以浪漫手法寄托现实壮志;《水调歌头》与李白、苏轼相约天宇,共酌高歌,从意境的辽阔而言,当与东坡相视而笑,从想象的奇特而言,较苏轼中秋词更甚;而《木兰花慢》送月词更是充满奇思异想,就月亮的运行提出了天体学的问题,无怪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其“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2](P12)辛弃疾明言此词仿屈原《天问》,一骚一词,遥相呼应,亦可谓“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了。
如前所述,王国维是将屈原推为将“南方人之想象”与“北方人之感情”完美结合的诗人代表的。这种南北文化的结合,使屈原能取镕经意,自铸伟辞,成为先秦文学的最后总结和光辉代表,为后来的文学树立起新的范式。而将北方人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感情和南方人的浪漫想象力在词中加以结合的辛弃疾,同样也以其“大声镗鞳,小声铿鍧”之作,在词中“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王国维虽未明确将其定为宋词的总结,但屡云“南宋唯一稼轩”,其意已隐然在焉。
然而王国维之赏稼轩词,于“北方人的感情”和“南方人的想象”二者之中,实亦有所侧重。《人间词话》曾云:“稼轩之词豪”,[2](P11)又云“苏 、辛,词中之狂。”[2](P11)“词豪”之语,或启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所云:“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4](P3925)所谓的“吞吐八荒”之概,当是指其勇于任事、矢志恢复的英雄志气和特出才能,而“词中之狂”的“狂”,也是以进取作为其精神特性的。由此我们可知王国维论词所重,仍为北方入世进取的文化精神,这与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以诗歌为北方文学之产物的观点正相一致。关于此点,《人间词话未刊稿》中的两则词论可为佐证。一则云: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2](P24)
又云:
竹垞痛贬《草堂诗馀》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2](P24)
文天祥生当末世,一生殚精竭虑,欲回狂澜于既倒,补破碎之山河。虽不以词名家,但其词的慷慨悲壮处,不在稼轩之下。如《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此等词作,充溢着对国家、民族深切强烈的思想情感,政治家坚忍勇毅、顽强进取的用世之志明明可见,显属王国维所言“北方派”的文化精神。而他将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过等有北方豪雄之气和进取意志的词家排除在“极无聊赖词”之外,也同样说明了他在论词时对“北方人的感情”这一要素的重视。故有论者言:“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他的文学批评,绝非如 `今人'给他`包装'的那样 `卓荦'遗世、超然人间;忧生忧世、关注国运民脉,乃贯注于其毕生的学术(包括文学)业绩之中。”[5](P256)
三
王国维褒贬相参的南宋词人有二:一为姜白石,一为陆游。其中论白石尤多。
在《人间词话》中,王对白石的评价是“有格而无情”,[2](P10)“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2](P11)“犹不失为狷”,[2](P11)“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2](P10)又云 :“诗人对宇宙人生 ,须入乎其内 ,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2](P15)又认为他写景咏物之作,有“隔”的毛病:“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 》、《惜红衣 》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2](P8)“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著,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2](P9)“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数峰清苦 ,商略黄昏雨 '、`高树晚蝉 ,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2](P9)
白石所以得王氏如许之评,从南北文化的角度衡之,则因白石之文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南方派。白石为江西饶州人,晚生于辛弃疾约十五年,主要生活在宋孝宗隆兴至宋宁宗嘉定这一段宋金之间相对和平的时期,因此缺乏像稼轩那样在北方沦陷区的生活经历和战争体验。他于诗、词、书、乐等方面均有造诣,曾一度有用世之志,向南宋朝廷进《大乐议》和《圣宋铙歌》,但其事不行之后即未再求仕,而是在仕、隐之间奔走于公卿之门,布衣终身。观其一生行事,绝类王国维所言之“南方人”的文化特点:“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
如前所述,王国维以诗歌为感情的产物,南方人所长的想象原质(知力原质)于诗歌中“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于是,我们可知“白石有格而无情”之评正与其南北文化之论相应:“格”,南方的“知力原质”可致,故白石有之;“情”(按:指坚忍勇毅、积极进取、改作社会的入世热情),正为南方派所短,故白石无之。又因“情”在王氏的词论中居于基础的地位,为其“意境”说的核心构件,故王氏“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之叹,正恨白石虽具南方人之伟大丰富的想象原质(知力原质),却乏北方人之感情,故终不能如屈原般“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而其论白石写景咏物之“隔”,亦可由此得解:非技巧(知力的原质)之不工,实感情之未到。
但白石于文化上的大体取向虽是王氏所言的南方派,是趋向于先秦的遁世主义、个人独善,但南北之驿骑既通,时代既变,其遁世和独善的方式,自会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笔者在《姜夔和南宋文化》一书中,曾指出了当时南宋所独有的一种“江湖文化”: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出现了奔走江湖、趋向城市谋生的新的社会一业,一部分“士”成为江湖中的“闲人”,出现了非仕非隐的第三态。这种处于第三态的江湖之士,既不能“外王”以经世,又非“内圣”以修身,他们或为“训导蒙童子弟”的馆客,或作“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的食客,“明经”无所用,文艺之才成为依附他人、用以谋生的手段,既非仕宦而食官禄,又非渔樵自给。而白石终其一生,都处于这样非仕非隐的状态,依违于入世和出世之间,因此也属于“江湖”中人。这种江湖之士因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依附性,其人格的独立性往往大打折扣,时常会面临着“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的尴尬。[6](P477-488)或者正是从这个角度,王国维认为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对宇宙人生未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甚至批评说: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2](P29)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2](P27)
然而,白石其人,虽为江湖之士,却又与当时一般的江湖之士不同。笔者曾以“人在江湖,身能由己”概括其生平行事,认为“同与他同时代或后于他的江湖之士相较,他都以不同流俗的品格表现出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6](P488),“从姜夔的诗词中,看到的不是对名人、权贵的谄谀和媚态,而是文艺上的相知,人格平等的交往,甚至不时露出散淡的情怀以至于兀傲。”[6](P492)他“生活于尘世又不至于沉沦,始终保持超尘脱俗的雅趣;本为生计而依托于达官,却又拒绝送田捐官,不卑不亢;寄人篱下却不向某个主人出卖自由。”[6](P493)
那么,白石精神上的此点特质,究竟属南属北呢?王国维曾以“廉贞”概括屈子的性格,以为“廉”为南方学者之优为,“贞”则源于北方学派。[1](P156-157)观白石之行,其忠君爱国之热情自不如九死不悔的屈子,但在维护个人的人格独立方面,实亦当得一个“贞”字。由是观之,白石之文学精神,应是南北相混。然北少而南多,“北体而南用”,北方勇毅坚忍、改作社会之热情,转变为对个人精神独立和自由的维护。王国维大约有见于是,故论白石词,又称其“犹不失为狷”[2](P11)(狷者,有所不为),褒其“尚有骨”[2](P74),且云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气象,白石词略得一二[2](P7)。按所谓“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气象,实可于庄、列的散文中得之,为南方文化之所长,白石有之,正其宜也。然此一评语本为王无功称道薛收《白牛溪赋》之言。此赋今虽不存,但白牛溪为隋末北方大儒王通讲学之地,薛收为其弟子,因此其内容当与王通讲学传道有关。而王无功为王通之弟,曾三仕三隐。由此我们可知此赋实含南北相杂之文化因子,王氏称赏此种气象,亦与其南北文化相融方出“大诗歌”之论暗合。他之所以最爱白石词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2](P17),也许正因其具有“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这种峭拔孤寒的气象吧。
持此南北文化的视点,则其论陆游“有气而乏韵”[2](P10)之语亦可解释:气,即魏征于《隋书·文学传序》所言“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之“气质”,为北方的;韵,据叶嘉莹的解释,指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含蕴不尽的余味,即婉转曲折、深远幽微之美[7](P256),此种特质,为南方的。放翁生于北方,正当金兵灭辽后南下攻宋的乱世,有过“儿时万死避胡兵”的惨痛经历,故其如稼轩一样对家仇国恨有深切之感受,一生富积极用世之热情,于中原之恢复不遗余力,其“北方人的感情”发之于词,便具有了“豪壮典丽”[2](P74)的特色。放翁于南方的文化当然也有所接受,其诗歌即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其词也有一些深情婉转之作,但大略言之,其文化精神,是北多而南少,且未能如稼轩般熔铸一炉,故如叶嘉莹所言:“如果就放翁词本身来看,则其所短正在于过分偏于豪放发扬,因而乃缺乏了一种含蓄蕴藉之美 。”[7](P256)
四
在稼轩、姜夔之后的南宋词家中,尚有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等人为王国维所道及,王氏对他们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有“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2](P11),“若梅溪以下,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 '者也 ”[2](P24),“最恶梦窗、玉田”[2](P75),“玉田 、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2](P24)等诸多贬斥之语,且言 :“梅溪 、梦窗 、玉田 、草窗 、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 。”[2](P17)点出了“ 时代 ”、“才分”为梅溪等人之词“失之肤浅”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时代、才分对以上之诸人在接受南北文化方面究竟有何影响,并且进而影响到他们作品的面貌和王氏对他们的评价的呢?
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人,主要的生活时代,均在号称“中兴”的孝宗朝之后。南宋国势自孝宗朝后即呈“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势,衰颓难振,特别是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已只能偏安自保,再也无力北图。伴随着英雄主义精神的退潮,是偏安逸乐之风的盛行。此外,自思想界言之,则南宋中后期为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理学虽源于北方之儒学,但其中已混入了大量的佛、道等南方之学的成分,长于思辩,好谈“义理心性”,其价值的中心取向由追求事功之“外王”转向了重视精神的“内圣”。所以南宋的理学家中虽有外主抗战、内修美政之议,但终乏实干之才,往往能言而不能行。其影响于士林,于政治的表现是清谈之风日盛,然“美意虽多,实政未究”,以致理宗亦曾感叹“虚论诚无益于国。”(《宋史全文》卷三二)而日常生活中,则“在这种理学观念的熏染和规范下,宋代(尤其是南宋)文人士大夫大都追求一种高雅不俗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而与唐人的浪漫多情、外向热烈而不重理性的时代风格大异其趣。拿南北宋来比较,理学盛行后的南宋儒生士人比起北宋更加温文尔雅,举止`中节'而合`理',其文化行为(包括创作)更加重守道义,潇洒而又厚德,山水云林、清笙幽笛、品竹赏梅等等,成为主要的好尚。”[8]
丹纳言:“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9](P76)与南宋中后期这种偏安享乐的时代特点相应,北宋周邦彦一路讲究词法、字面、音律的词重新成为创作中的典则和时尚,以应歌合乐、宴会酬酢为目的词作大量出现,此即是王氏所言的词成了“羔雁之具”[2](P17)。又由于理学盛行的精神文化环境,使他们极力推崇“雅词”,要求词的意趣雅正,即或有身世之悲感,亦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刻意求雅的结果,是让他们的词作与北宋词人相比,失却了性情上的真实自然,于是便出现了“游词”之病:“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 。”[10](P799-800)梅溪 、梦窗 、玉田、草窗、西 麓等辈 ,其出身固有高低,但既处此时代的大环境中,自是概莫能外。如以王国维南北文化赋予文学不同精神质素的观点来看,他们于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性,亦如白石一般,主要为个人的、遁世的、冷性的,为南方派。王氏论词,既以“北方人的感情”为诗歌的第一要素,特别重视入世之热情,则这些人同为王氏所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王氏所说的这些人词作“ 肤浅”的另一原因——“才分”,则属于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言的“知力的原质”。这本为南方派之所长,但同为南方派,其间当又有高下之分。王氏言南宋中后期词人“肤浅”而不及于白石,显然是认为白石的才分要高过这些人了。此点,也可说明他为什么对白石持一种贬中有褒的矛盾态度。
概言之,王国维对南宋词家的接受与批评,说明他论词虽以“境界说”为旗帜,但所持之文化眼光,是与《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论诗的观点相一致的:即以诗歌为“北方文学之产物”,以“北方人之感情”为诗歌的基础,强调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精神和热情,特别推重融合了“北方人之感情”和“南方人之想象”的作家作品。因此,在清代的词论家中,比之重醇雅、声律的浙派和重比兴寄托的常州派,王国维的词论无疑蕴含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体现了更为宏阔的文化视角。
[1]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邓广铭辑校审定,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唐圭璋编.词话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5.
[5]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6]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7]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刘扬忠.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6).
[9]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0]金应珪.《词选》后序[A].施蛰存编.词籍序跋萃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