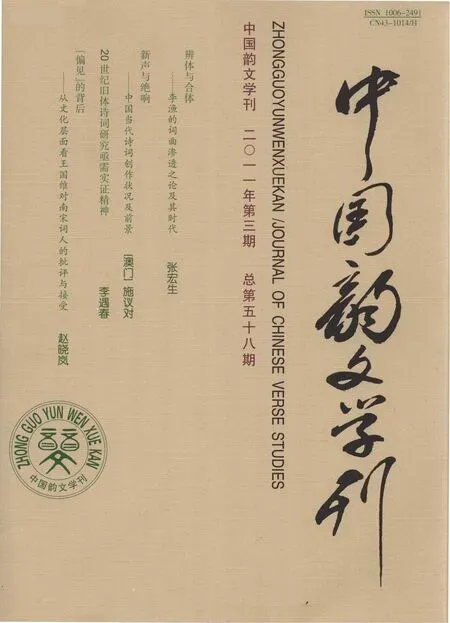明末清初西泠词坛与词学复兴
胡小林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一 词学复兴与西泠词坛
词滥觞于唐,繁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复兴于清。清代词学的复兴,既是清代词人对词学理论不断反思总结、臻于完善的过程,亦是近三百年来阵容庞大的词人,以数量惊人的词作和异彩纷呈的风格,而展现出来的自唐宋以来词学经验积累的释放,更是众多词学流派或词人群体之间互动融合、此消彼涨的历史。而考察清代词学复兴之肇始,不能不上溯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明末清初的西泠词坛。
唐宋以降,西泠(即杭州)一直是词学活动的中心地域,延至明末清初,亦是如此。明末清初的西泠词坛,是指明末清初在西泠一地进行词学活动的词人群体,既包括西泠本郡词人,亦包括宦游于西泠的词人,是一个以地域、家族、师承为纽带,以明末盟社为契机,同时浸润西泠的厚重词学传统,在明代后期词坛特定词学氛围中形成的词人群体。明末清初的西泠词坛,在词由元、明以来的衰弊,转向清代的复兴这一嬗递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它与云间词派、柳州词派、毗陵词人群体、广陵词人群体等一起拉开了清词发展史的序幕,于清词之中兴的贡献不可小视。
关于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的阵容,从陆进、俞士彪所编郡邑《西陵词选》可以管窥一斑,此选共收西泠本郡词人 185家,词作 665首,词集 58部。又根据明末清初其它词选如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邹祗谟、王士禛 《倚声初集 》、沈谦、毛先舒 《古今词选》、陆次云《见山亭古今词选》、卓回《古今词汇三编》、郑道乾《国朝杭郡词辑》等文献统计,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多达 351人,词集近百部,其中包括三部唱和集,是明末清初词坛众多的词派或群体中成员数量最多,创作亦最为繁荣的一个群体。
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不仅阵容庞大,而且成员也极其复杂。就籍贯言之,有土著,有侨寓,有宦游;就身份言之,有遗民,有布衣,有官宦,有方外,有闺秀。他们交游唱和,操持选政,进行各种词学活动,盛极一时。西泠词人群体的词学思想和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开放包容、异质共存的特点;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沈谦、毛先舒虽然在这个群体中具有一定的领导作用,可是沈、毛的词学观点也有互相9牾之处,并且,除沈谦、毛先舒之外,徐士俊、陆进、王晫等人在群体中也具有很强的凝聚作用,彼此的词学观也不尽相同。所以,从严格意义而言,西泠词人群体没有形成一个词学流派,但他们彼此之间亦有词学共识,气脉相通。
总而言之,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与其他流派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组织松散、风格多样,存在时间最长,包容性最强。同时,他们又区别于毫无关联的词人群体,群体内部的词学思想虽同中有异,却也自成体系。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称之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宗派;同时,也区别于纯粹因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一群词人。
二 西泠词人的创作分期
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以明天启五年(1625)卓人月、徐士俊定交,并唱和《徐卓晤歌》为形成标志,以清康熙六十年(1721)徐逢吉与厉鹗定交①徐逢吉与厉鹗最早有诗词唱和,是在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此即二人定交的标志和时间。此年,徐逢吉与厉鹗、蒋雪樵三人定交,同作《试天目茶歌》,详见厉鹗《试天目茶歌,同蒋丈雪樵、徐丈紫山作》,《樊榭山房集》,卷二(辛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75页。,并皈依浙西词派为解体标志,存在时间前后绵延近百年。根据西泠词人群体形成、繁荣、皈依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先导期、发展期、余波期。
(一)先导期 (1625— 1635)
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期,以天启五年(1625)卓人月、徐士俊定交为开端,以崇祯八年(1635)“西泠十子”形成之前为终结。在此十余年间,西泠词人群体的成员约有三十余人,他们的身份大多为科举仕进不甚如意,以诗酒结社为风雅之事的文士。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人,除了卓发之、卓人月父子与徐士俊之外,还有朱一是、陆钰、徐之瑞等人。西泠词人群体在这一时期的词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十部词集的产生,如徐士俊和卓人月《徐卓晤歌》、卓人月《蕊渊词》、徐士俊《云诵词》、朱一是《梅里词》等;二为词选的编选,如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
这一时期的西泠词人群体,敏锐地意识到了词体在明代的衰颓及其缘由,因此鼎力革除旧弊,率先担当起振兴词体的重任,他们不仅究心于词的创作,还利用词选这一批评工具,大力张扬自己的词学主张,形成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建构两方面齐头并进的格局。他们在主张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并举的同时,大力张扬稼轩词风,开明末清初词风嬗变之先声。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者,不仅继承了两宋以来西泠词学的传统,还对西泠一地的词学发展和清词的中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明末词坛一片凋零,词体已经进入其衰颓的最低谷,而词坛的其他词派或词人群体还未成形,尚在孕育之中。即使号称云间“三子”的陈子龙、李雯、宋征舆方才定交,但尚未形成气候。直至崇祯十年(1637),陈子龙进士及第,“云间三子”才作为一个文学团体逐渐扬名天下②详见浙江大学李越深 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云间词派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云间三子群体的形成”,其中提到,“云间三”子中的陈子龙和李雯,定交于崇祯二年(1629);而“云间三子”全部定交,则在崇祯七年(1634);“云间三子”的扬名,则在崇祯十年(1637)。。而此时,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期已经在词的创作和词选编撰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明末衰飒词坛可谓振聋发聩,独领风骚。
(二)发展期(1635—1672)
西泠词人群体的发展期,以崇祯八年(1635)“西泠十子”的形成为发端,以康熙十一年(1672)“西泠词社”成立前夕为终结。这一阶段共有三十七年,是西泠词人群体创作极度繁荣的时期,群体的成员从先导期的三十余人,猛增至二百余人。群体成员的身份也变得极其复杂,既有绝意仕进,隐居于山林的明代遗民,有仕途或偃蹇、或通达的官宦,也有或专心学问制艺、偶尔事词,或无心仕进,专力填词的士子,更有方外、宦游和闺秀词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团体,主要有“西泠十子”、“北门四子”、“严氏词人群体”、“冰轮二陆”、“东皋草堂词人群体”等。同时,先导期的领袖人物徐士俊依然健在,被西泠词人群体推尊为词坛耆宿。
(三)余波期(1672—1721)
这一时期,以康熙十一年(1672)“西泠词社”的形成为发端,以清康熙六十年(1721)徐逢吉与厉鹗定交并皈依浙西词派为终结。在此五十年间,尽管西泠词人群体先导期和发展期的成员,如徐士俊、丁澎、毛先舒、张丹等大都谢世,存者寥寥,但此时西泠词人群体的成员依然众多,大约有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人群体有:“东江八子”、“西泠三子”、姚氏昆仲、以仲恒为中心的词人群休、查氏词人群体、顾氏后进词人等。
这一时期西泠词人群体编纂了六部词选,包括陆进、俞士彪的《西陵词选》、陆次云、章昞《见山亭古今词选》、陆进、佟世南 《东白堂词选初集》、卓回《古今词汇》、卓长龄《正续花间集》、卓灿《历朝词汇》;同时也从事词话、词韵、词律著作的撰写,如张台柱《词论十三则》、赖以邠《填词图谱》、王又华《古今词论》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西泠词人发起的清初最后一次大型唱和活动,即王晫“千秋岁唱和”发生在这一时期,并刊刻了唱和之什《千秋雅调》。
这一时期西泠词人群体的总体特点是,词的创作依然繁盛,同时也进入词学理论的总结时期,逐渐形成了完备而成熟的词学理论体系,康熙十八年,查继超将西泠词人群体关于词调、词论、词律、词韵的四部著作,即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赖以邠《填词图谱》、仲恒《词韵》附柴绍炳《柴氏古韵通》,合刻为《词学全书》,标志着西泠词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
同一时期,清初词坛百派竞流的繁荣格局,随着各个词派或群体如云间词派,柳洲词派、广陵词坛、阳羡词派等的衰落,而逐渐消解,只有西泠词人群体以其庞大的成员数量和繁盛的创作,依然称雄词坛,与康熙十八年形成的浙西词派,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西泠词人群体的词风,也并非没有受到浙西词派的浸润,西泠词人陆进、陆次云的词作,已明显带有浙西词派的咏物之习,而徐逢吉与厉鹗的交往,则标志着西泠词人群体彻底融入浙西词派。
三 西泠词人的创作特色
自两宋以降,西泠一地词人辈出,如周邦彦、张枢、杨缵、张炎、马洪等人,均以词称胜一时。至明末清初,西泠词风复盛,不仅词人众多,而且创作极其丰富,仅《西陵词选》就收录西泠词人 185家、词集85部。正如西泠词人陆进在《西陵词选序》所说:“西陵山川秀美,人文卓荦。宋、元以来,以词名家者众矣。迄于今日,词风弥盛。”[1](卷首)与明末清初其他词派各有宗法,且词派内部词人的创作具有统一风格不同,西泠词人群体的词作呈现出多姿多彩、异质并存的特点。俞士彪《西陵词选序》:“(西陵词人)其间学为周、秦者,则极工幽秀;学为黄、柳者,则独标本色;或为苏、辛之雄健,或为谢、陆之萧疏;或年逾耄耊而兴会飚举,或人甫垂髫而藻采炳发。闺中之作,夺清照之丽才;方外之篇,鄙皎如之亵句。……可谓各擅所长,俱臻其极者矣。”[1](卷首)正是由于西泠词人群体词作具有千人千面的特点,传统研究范式即从整体上对其风格进行宏观把握和梳理,就显得过于粗疏,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这一群体的创作特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西泠词人群体中,抽取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词人词作,从个体切入,分别解析其词风的形成和演变,并将所抽取的词人,按照“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和 “学人之词”进行分类讨论。
首先,在西泠词人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词”有丁澎《扶荔词》、陆进《巢青阁集诗余》和丁介《问鹂词》等。其中,丁澎是西泠词人群体中间年辈较长、际遇最为坎坷的词人,其《扶荔词》三卷创作于康熙十年(1670)以前,是其身世与词风的完美结合。梁清标曾评丁澎《扶荔词》曰:“药园之词,流丽隽永,一往情深,所谓言近指远,语有尽而意无穷者。”[2]卷末梁清标以儒家诗教的最高水准“温柔敦厚”、“言近旨远”来评价《扶荔词》,准确地抽象出丁澎本人词为诗教之余的词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指出《扶荔词》婉丽多情与慷慨悲愤等多种风格并存的特色。尤其是丁澎被放之后的词作,明显带有稼轩词悲慨激昂的腾越气势,如《贺新凉·塞上》:
苦塞霜威冽。正穷秋、金风万里,宝刀吹折。古戍黄沙迷断碛,醉卧海天空阔。况毳幕、又添明月。榆历历兮云槭槭,只今宵、便老沙场客。搔首处,鬓如结。 羊裘坐冷千山雪。射雕儿,红翎欲堕,马蹄初热。斜亸紫貂双纤手,扌刍罢银筝凄绝。弹不尽、英雄泪血。莽莽晴天方过雁,漫掀髯、又见冰花裂。浑河水,助悲咽。[3](P3191)
此词作于丁澎被流放边塞之后,只有亲身经历过边塞酷寒与荒凉的谪客,才能如此真切地表达被放逐天涯的绝望与孤独。
其次,在西泠词人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词人之词”有沈谦《东江别集诗余》、沈丰垣《兰思词钞》和《兰思词钞二集》等。其中,沈谦《东江别集诗余》,具有绮艳婉媚之美,是明人《花间》、《草堂》词风的沿续。沈谦前期词作以《云华馆别录》为代表,内容上崇尚艳情,往往因刻意过深且纤秾有余,加之沈谦同时又是曲中作手,所以其词难免有曲化之痕,这也是沈谦词作备受后人指责的原因。如谢章铤有云:“沈去矜好尽好排,取法未高,故不尽倚声三昧。长调意不副情,笔不副气,徒觉拖沓耳,且时时阑入元曲 。”[4](卷八)其实,不单长调 ,沈谦的小令、中调,亦染有曲家风范。
沈谦后期词作虽仍旧崇尚婉丽情思,但其所作,已经非全然艳情,而且词风已经渐趋雅致,时见清奇俊逸,尤其赠答抒怀以及登临怀古之作,更是如此。沈谦曾与邹祗谟谈及自己词风的转变:“仆童年刻意过深,时多透露,前蒙登拔,皆其少篇。近亦幡然一变,将尽扫云华之旧,不知足下之许我否也?”[5](卷七)如以沈谦晚年所作《东湖月》为例:
甚钟灵。便珊瑚百丈老重溟。问谈天邹衍,凌云司马,此日敢纵横。骨带铜声敲不响,有黄金伏枥难行。只好衲衣持钵,绣幕闻笙。 山青兼水绿,对萧疏、白发转多情。笑磨厓天半,沉碑潭底,身后枉垂名。雾里看鸢非我事,尽优游下泽同乘。漫道出,堪作雨处亦关星。[3](P2017)
可见,沈谦词作风格,沿续明代词风的余绪,虽以婉句丽情为基本特点,但无伤大雅,间有清奇新疏之色。
沈丰垣《兰思词钞》、《兰思词钞二集》的词风,经历了由绮丽到慷慨的转变,折射出明末清初词风的嬗变历程。《兰思词钞》是沈丰垣前期词作的结集,多为闺阁之思、时令之叹,以及羁旅之愁,以绮艳多情为其特色,“笛”与“月”为这一时期词作的典型意象。吴仪一曾评《兰思词》曰:“洪昉思尝举遹声词`一床夜月吹羌笛'、`草白烟青,何处画楼吹笛'、`闭着窗儿自剔,不怕高楼吹笛',谓可称`沈三笛'。予谓沈词如`画屏飞去潇湘月'、`枕儿畔,挂一片、明河月'、`南楼过雁,一声唤起明月'皆警句,称`沈三月'较胜。”[6](卷首)
在后期,沈丰垣作词功力益进,词风也由秾丽转向苍劲。所以《兰思词钞二集》多言离情,兼有怀古赠答悼亡之作,主要以慷慨悲愤为特色。《兰思词钞二集》有《满江红》四十首,可视为沈丰垣后期词风的典型代表。如《满江红·十五夜,与高则原、朱景亭》:
人道元宵,浑不信、又逢佳节。我已到、中年之后,满怀萧瑟。闭户强斟桑落酒,开窗怕见团圞月。指梅花、结个岁寒盟,心如铁。 翠竹上,余残雪。帘影外、灯明灭。愿故人长健,月圆无缺。蹋地呼天伤往事,文期酒会成辽阔。待颓然、一枕学庄周,迷蝴蝶。[7](卷下)
此词自叙中秋佳节之时的孤独凄凉,以及中年以后萧瑟颓废的心境,与李清照《永遇乐》“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堪称同工。因此,陆进在《兰思词话》中,总论《兰思词钞》、《兰思词钞二集》曰:“昔东江沈先生与余札有云:`《兰思词》精思殊采,不愧淮海、屯田,惜不令程村见之。'今沈先生宿草矣,而遹声词益进。使东江读是编,其击节又当何如?”[6](卷首)
再次,在西泠词人群体中,学者型词人数量相当可观,这也与其他地域性词派或词人群体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词作数量不多,但佳作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学人之词”有毛先舒《鸾情词》、姚之骃《镂空集》和姚炳《荪溪诗余》等。毛先舒论词,非常重视学问胸襟的重要性,认为填词如作文,必须有根柢,而填词的根柢就是学问胸襟,二者为流与源的关系。他在《丽农词序》中指出邹祗谟词作的成就,根植于其学养的深厚:“虽然,余谓皆讠于士之学为之耳。盖讠于士负宏博才,其于文章,真能穷源极流者也,所著文抄、经术、史学,条贯纷纶,而便便出之,如云属河注。故虽作一词,皆有大气,精思贯其表里,而足以益人性情如此。”[8](卷一)
但是,毛先舒的词作,与其词学理论还有一定的距离,仍然囿于明代婉艳词风之中。《鸾情词》多写闺情艳想,其中别有寄托,风格则以绮丽旖旎为主,沈谦曾戏举毛先舒“不信我真如影瘦”、“鹤背山腰同一瘦 ”、“书来墨淡知伊瘦 ”,嘲之曰 “毛三瘦”[3]2183。当然,毛先舒亦有多首其所倡导的学问胸襟之词,其所作《水调歌头·七夕》、《兰陵王·秋日感怀》等词,皆是气吞五岳、胸怀万卷之作品。如《望海潮·吴山伍公庙作》:
山川磅礴,激为俊物,作人须是英雄。战国未成,春秋之末,江南特地生公。佳气最高峰。看丹青别殿,香火行宫。北望苏台,杜鹃无血洒东风。难平浩气如虹。现银涛白马,驰骤江中。却怪为谁,心惊铁弩,潮头忽尔回东。不屑与争锋。但眼中竖子,付与奇功。千古兴亡,且将孤啸对冥鸿。[3](P2196)
此词以春秋末年的伍子胥为引,慨叹昔日英雄,今已荡然不存,千古兴亡事,唯留孤鸿鸣,词句中隐藏慷慨的社稷之悲,具有直贯长虹之气。
姚际恒家族是清初西泠的经学世家,姚际恒及其两位侄儿姚之骃、姚炳均以治经史而闻名。姚氏家族的词作,以姚之骃的《镂空集》、姚炳的《荪溪诗余》为代表。冯景在《荪溪集序》中,明确指出姚之骃、姚炳昆仲在西泠词坛的地位:“西泠词章之盛,昔推十子,今五十年间,零落尽矣。方虞极盛之后难为继,乃今得同里二姚昆弟出,而并登风雅之坛,文章典丽,洵足鼓吹。休明彦晖,才气雄健,与其兄鲁思齐驾,固如昔人所称王元琳季琰兄弟云。”[9](卷首)
姚之骃、姚炳的词学观念与词作风格颇为相似。姚之姻《镂空集》既有婉转绵丽之作,亦有豪宕清新之风。其婉转绵丽,主要宗法晚唐五代词家温庭筠、牛峤、皇甫松,以及两宋周邦彦、李清照、黄庭坚等人;其豪宕清新,主要宗法苏轼、辛弃疾和岳飞。与兄长一样,姚炳《荪溪诗余》也是香艳与高逸并存,师法众多,温庭筠、柳永、周邦彦、黄庭坚、苏轼、岳飞、辛弃疾等晚唐、五代乃至两宋词家,均是他学习的对象。如姚之骃《沁园春·谒范忠贞公祠》:
座拥三台,城当万里,群贼胆惊。叹石头未复,不惭故节,粤王难系,空请长缨。齿嚼睢阳,血污太尉,玉帐中宵坠大星。骑箕去,作山河壮气,麟阁功成。 流芳汗简长青。对明圣恩波俎豆荣。望四贤祠畔,鸡彝同献,孤山亭外,鸟革连甍。玉简泥封,银钩彩绚,棹楔高悬日月明。抠衣拜,听祠前遗老,还载歌声。[10](卷四)
再看姚炳《沁园春·谒范忠贞公祠》:
保障江南,血食湖西,伟哉范公。想钢成百炼,吞毡肠肚,丹留一点,化碧心胸。齿砺睢阳,头轻巴汉,老子芳名万古雄。明湖上,看两高风雨,尚荷帡幪。 云霞新启祠宫。读碑版龙文篆正红。叹臣子忠贞,光悬日月,君王明圣,藻舞虬龙。祠并名贤,地邻处士,千载应看意气通。还不尽,淛东西到处,俎豆重重。[9](卷十三)
其实,姚氏昆仲在词学思想和词作风格方面的趋同,也在常理之中。相同的成长、读书、创作环境,再加上二人经常共同分韵酬唱,均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四 西泠词人的理论探讨
明末清初的西泠词人群体,相对于当时词坛其他词派或词人群体而言,在词学理论上的建树犹为卓著,对词体有着全面缜密的理性思考。其成就略可分为下面几个方面。
总体而言,西泠词人的词学理论可以概括为词体论、词风论、词法论、词选论四个方面,概论如下。
(一)追源溯流,辨体尊体
西泠词人群体对于词体推尊,主要围绕着词体的定义、词的起源与滥觞、诗词曲之辨三个层面进行展开。首先,推尊词体,必须首先明确词体的涵义。西泠词人对词体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徐士俊为代表,认为词为“诗余”;另一种以毛先舒为代表,将词定义为“填词”,认为词有别于诗,是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不是诗的附庸,更不可称其为“诗余”,实质上源于李清照《词论》。表面上看来,西泠词人群体对于词体两种不同的认识,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实质上,二者均是对词体的推尊。无论是将词定义为 “诗余 ”、“《诗三百 》之余 ”,强调词与诗、《诗三百》之间在文体上的一致性,意图将诗的雅正特质如“意内而言外”、“四始六义”、“风雅之旨”移植给词,尽最大可能将词拉入到正统文学的范畴;还是强调词本身的文体特性,别为一家,并以“填词”这一称谓对其特性加以固定,竭力反对将词视为诗的附庸,突出词在文体领域与诗并列的重要价值。所有这些努力,都说明了西泠词人群体从词的定义层面,对词体进行的理性反思,最终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词的文体地位。
其次,西泠词人群体对于词之起源的认识,既有对明人“词源于六朝乐府”观点的继承和修正,也有自己的创新。总体而言,西泠词人群体将词之本源与词之滥觞两个概念截然分开,认为本源意谓最根本的源头;滥觞意谓发端、开始。他们认为,词的本源是《诗三百》,但是,在词滥觞于何种文体的问题上,却意见不同,或认为始于六朝乐府,或认为始于汉乐府,或认为滥觞于唐。
再次,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徐士俊,率先提出“诗词曲之辩”的话题:“上不类诗,下不类曲者,词之正位也。”[11](卷下)指出词体的本质不同于诗与曲。徐士俊此论引发了明末清初词人对诗词曲之辨的一次深刻探讨,此后,不仅西泠词人沈谦、毛先舒等人加入其中。与徐士俊相比,沈谦将诗词曲之辨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诗与曲俱可入词,关键在于作者自己的把握与运用。对沈谦关于词、曲关系的看法,毛先舒颇不认同,与之商榷道:“又足下论曲与词近,法可通贯。鄙意仍谓尚有畦畛,所宜区别,兹不尽谈。”[12](卷五)的确如此,词人如何把握诗词曲之间的界限,并非易事,如王士禛说:“毎自云词曲之辨甚微 ,正不容门外汉轻道 。”[13](卷二)可见 ,明末清初词人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词与曲之间的差别甚微,非词曲均擅之人,则不能甄别。元、明以来,词的曲化现象严重,明末清初词人欲复兴词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分诗词曲之间的差别,明确辨析词体。从现存文献来看,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对于“诗词曲之辨”的讨论,在明末清初词坛的所有词派和词人群体中是最早的,具有开山之功,体现出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对词体的反思和定位。
(二)重视词律和词韵
明末清初西泠词人对于词律的重视,秉承了两宋乡贤周邦彦、杨缵、张炎等人所建立的、以音律为词体之关键的传统。他们对于词律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考订诠释词调名,如毛先舒《填词名解》;二为编撰词谱,如赖以邠《填词图谱》。西泠词人群体发展期的重要词人毛先舒《填词名解》,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考释词调调名的专书,以调名为纲目,旁征博引,逐一对调名考释。它对于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康熙二十六年所刊万树《词律》,康熙五十四年官方所编《钦定词谱》等,亦曾借鉴过《填词名解》。
在清初词坛对当下所流行的明人词谱极其不满意,亟需一部精审完备词谱的大环境下,西泠词人群体承继乡贤谢天瑞所创立的词谱编撰传统,对于词谱编撰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在清初西泠词人群体中,先后从事词谱编撰的共有两人,一为沈谦,一为赖以邠。沈谦所著词谱,未见传世,仅见于沈谦本人及好友毛先舒所述。赖以邠《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三卷,作于沈谦《词谱》之后,是一部在明代词谱和清初词谱的基础上,增益修补而成的词谱。从词谱编撰史的角度而言,它是联系明清词谱的一个桥梁,其编撰体例既继承了明代词谱的诸多优点,又对此后的清代词谱如万树《词律》和官方编撰的《钦定词谱》多有启发,促进了词谱学在清康熙中后叶的成熟。
词在与音乐分离之前,是合乐歌唱的文词,词人填词只要顺依乐律即可,不必在文字上依傍格律与韵书。宋元以后,词与音乐分离,为了保持词的文体特性,词人填词就必须在文字上讲究协律与押韵。清代以前,词韵向无专书。元明词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词人填词时,没有一部真正的词韵可以依傍。词学的振兴必须以词韵学的精审严明为基础,这是清人在词学建构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之一。
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成员多熟谙音韵,其中不乏名震一时的音韵学家,如毛先舒、沈谦、柴绍炳、仲恒等人,本身就是音韵学家,并且形成了一个音韵学研究圈。毛先舒《韵学通指序》回忆诸子的交游:“戊子岁杪,先舒撰《唐人韵四声表》及《南曲正韵》既成。适同郡柴虎臣撰《柴氏古韵通》,沈子去矜撰《沈氏词韵》,钱雍明先生撰《中原十九韵说》,其书皆综次精核,可以为辞家之宗法。”[14](卷首)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编撰的词韵专书主要有两部,分别为沈谦《词韵》和仲恒《词韵》。沈谦《词韵略》是清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词韵专书,在总结宋词用韵规律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对清代词韵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仲恒《词韵》、吴宁《榕园词韵》、谢元淮《碎金词韵》、戈载《词林正韵》等,均是在沈谦《词韵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词韵加以辨证,后出转精。而仲恒的《词韵》,则在保留了沈谦《词韵》全貌的基础上而有所订正,主要是满足自己填词所需,以适用便利为原则。
(三)对于词选的思考
选词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方面,西泠词人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在对词选学进行理性反思方面,他们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作词难,选词亦难。这一论点,明人如俞彦虽有提及,但所言甚略。直到明代末年,西泠词人群体的先驱徐士俊,不仅再次提出“选词亦难”的观点,而且还明确指出选词为何如此之难:“持衡千古,存者星星,而且日久论定。持衡于今,作者毛蝟,而且见疏闻局,其难易相去万万也。”15](P16)其后,西泠词人群体发展期的词人严沆,延续了明代词家俞彦和乡贤徐士俊的话题,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词虽小技,匪惟作者之难,而选之尤不易也。”[16](卷首)
那么,选词到底难在哪里呢?关键在于词人和词作的存留去取之难,评价一部词选是否为善本的标准:于词人而言,要博而全备;于词作而言,要精而醇雅,这就对操选政者的审美鉴赏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必须以选者之心度古今词人之腹,对所选词人的词作水平还要具有准确定位的能力。事实上,选词者在把握好对词人词作去留存取标准的前提下,往往还必须借助所编词选表达一定的词学观念,正如鲁迅在《集外集·选本》所说的“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对于操选政者而言,他所面对的难题就在于,如何把对词人词作的取舍与自己所要表达的词学思想,以最佳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以词选形式体现出来。如果偏向两者中的任何一面,要么招致“历下”、“竟陵”之嘲,要么被后人嗤以“博矣而不精”。
除了对选词之难进行理性反思之外,西泠词人群体还对当世词坛的选词之弊提出了批评。王晫在《与友论选词书》中,将明末清初词坛的选政之弊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以交情的深浅选词;二、以个人的爱憎选词;三、以刻资的厚薄选词;四、以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选词。操选政者往往为以上因素所左右,决定词的去留存删,这不仅会导致词选的鄙陋不堪,更严重的是,由于词选天生的导向作用,词坛的创作生态乃至一个时代的词风,都会因此被引入比较恶劣的环境之中。对此,王晫亦曾指出:“吾见少年以所选为羔雁之具,藉此纳交于大人;宿儒以所选为声气之媒,藉此取润于当事。有刻一封面,而其书终身不完;有偏索刻资,而其余尽充囊槖。”[17](卷五)
在意识到选词极难和选词之弊,并对之作出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西泠词人群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选词观念:一、选词应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西泠词人群体在操选政时,对词人和词作并无特殊的偏好,兼而收之,自第一部词选《古今词统》到最后一部《古今词汇》,这种选词基调自始至终被坚持。二、西泠词人群体指出,理性的选词者应遵守以下选词步骤,才能真正做到持衡古今,客观公允:首先,就选人而言,要选取海内名词家,但为数不能过多,并要豪宕与婉约兼顾。其次,尽取第一步所选中的词家全部词作,衡量定夺,抽其精华之作,还要使选中之词最有具代表性,注意勿被一己之爱憎左右。可见,作为选词者,西泠词人群体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责任,尽量完美地处理作者、选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由于西泠词人群体所编词选众多,所以,他们对于选词之难和选词之弊,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如此关注选词之难,反映出他们对唐宋以来词选学发展状况的理性反思,并走在了这一理性反思的前沿。
五 西泠词人与阳羡、浙西二派
西泠词人群体与明末清初词坛先后出现的众多流派或群体大都有交游和互动,如云间词派、柳州词派、毗陵词人群体、广陵词坛、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等。西泠词人群体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词学思想,在始终保持着“和而不同”生存状态的同时,与其他词派或词人群体以词为媒介进行交游,或唱和,或序评,或在词学问题上进行争论,或合作编选刊刻词集词选。这种词学上的大量交流和互动,使西泠词人群体的词学思想在自成体系的基础上,也时刻保持着与外界的沟通和碰撞,体现了清词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围绕西泠词人与阳羡、浙西二派之间的交游展开论述。
(一)西泠词人与阳羡词派
据严迪昌先生《阳羡词派研究》,阳羡词派以其“力尊词意的本体功能论、独崇真情的风格兼容论、情韵兼求的声律观”,而在清初词坛独领一帜。但是,这些词学观在西泠词人那里,都能找到相似之处。那么,对于早已在词坛声名鹊起的西泠词人群体,阳羡词人又持何种态度呢?陈维崧将西泠词人群体与云间词人、松陵词人、魏里词人并称为“词场卓荦者”[24](卷首),为一时之盛,欲仿效他们编撰词选;万树则对沈谦《词韵》评价甚高:“词之用韵,较宽于诗,而真侵互施,先盐并叶,虽古有然,终属不妥。沈氏去矜所辑,可谓当行,今日俱遵用之,无烦更变。”[19](P18)康熙二十六年 (1687)蒋景祁 《瑶华集》付梓,共收明末清初词人 507家,其中浙江词人有 145家,西泠词人则有 53家,占全书所收词人的十分之一之多。另外,《瑶华集》卷末附录收沈谦《词韵略》一卷,蒋景祁本人也盛赞沈氏词韵有大功于词史,极力反驳毛奇龄否定《词韵略》的言论:“去矜之书,盖重有忧也。斥去矜之书而听之时俗之揣度,譬之因噎而废食也。”还有,吴逢原与王晫也有交往,王晫有《汉宫春·题吴枚吉〈红蕉词〉》一词,评吴逢原词堪“提将秦柳,压倒苏黄”[3](P669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阳羡词人领袖陈维崧与西泠词人群体之间的交往,整整持续了近三十年,是所有与西泠词人有交往的词人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陈维崧之于西泠词人群体中的先导期、发展期和余波期词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陈维崧对于西泠词人群体的先导者如徐士俊,持以尊敬和钦慕的态度;对于以“西泠十子”为代表的发展期词人,则视为患难之交和词学良友;对于以吴仪一为代表的余波期词人,则以包容的心态,时时加以鼓励和提携。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也将西泠词人群体一直倡导的稼轩词风张扬到极致,完全打破了明代以来婉约词风一统词坛的局面,为清词的繁荣扫清了阴霾。
(二)西泠词人与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大约形成于康熙十八年的北京,其时,西泠词派群体处于余波时期,依然引领西泠一地词风。整体而言,在浙西词派以曹溶、朱彝尊为代表的前期,西泠词派和它形成南北对峙之势,由于在地域上相距遥远,词人之间的交游也非常有限,如曹溶与西泠词人的交往,有文献可查的不过四次;朱彝尊与西泠词人之间也有一些赠答之作,但是,这些交往大多限于普通的交际应酬,直至浙西词派中期厉鹗的出现,才在真正意义上对西泠词人的词学观念产生浸润。作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人物,厉鹗一登上词坛,便有主导浙西一地词风之势。而此时,西泠词人群体的主要人物,大部分已经离世,仅徐逢吉还依然健在。康熙六十年(1721),徐逢吉六十七岁,偶然得读厉鹗词作,极为叹服,遂以词与厉鹗结为忘年交,情谊甚笃,频频酬唱。自此,徐逢吉以厉鹗的引导下,以姜夔和张炎为宗,词风与浙西词派趋同。康熙六十一年(1722)徐逢吉在《秋林琴雅·题辞》中,道出自己晚年因受厉鹗影响而在词风上的变迁:“余束发喜学为词,同时有洪稗村、沈柳亭辈尝为倡和,彼皆尚《花间》、《草堂》余习,往往所论不合。未几,各为他事牵去,出处靡定,不能专工于一。……独余沉酣斯道,几五十年,未能洗净繁芜,尚存故我。以视樊榭壮年,一往奔诣,宁不有愧乎?”[20](P879)西泠词人主要活动在浙江,他们与浙西词派最终形成密切的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
六 总 结
从词学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明末清初的西泠词坛有着明显承上启下的作用。西泠词人群体兴起略早于云间词派,二者在词学理论上有相通之处,但西泠词人群体的观点更为理性客观,不偏于一隅。在此基础上,西泠词人群体尤其强调对词体本质的思辨,注重对词律词韵和创作规律的总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对清词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如稍后的阳羡词派与浙西词派词学观,均能从西泠词人群体那里找到源头。因此,西泠词人群体的词学理论,既有着明代词学思想的烙印,又孕育着新的词学思想,是明清词风嬗变的关键一环。研究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的词学理论,对于理解明清词风嬗变和清词复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陆进.西陵词选[M].清康熙十四年.
[2]丁澎.扶荔词[M].百名家词钞.清康熙绿荫堂刻本.
[3]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全清词·顺康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M].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沈谦.东江集钞[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沈丰垣.兰思词钞[M].清康熙吴山草堂刻本.
[7]沈丰垣.兰思词钞二集[M].清康熙吴山草堂刻本.
[8]毛先舒.潠书[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姚炳.荪溪集[M].清康熙刻本.
[10]姚之骃.镂空集[M.]清康熙刻本.
[11]沈雄.古今词话·词话[M].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毛先舒.毛驰黄集[M].清康熙刻本.
[13]邹祗谟.倚声初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14]毛先舒.韵学通指[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6]陆次云.见山亭古今词选[M].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17]王晫.霞举堂集[M].清康熙刻本.
[18]曹亮武.荆溪词初集[M].清康熙南耕草堂刻本.
[19]万树.词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0]厉鹗.樊榭山房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西泠六子偕友8人书法艺术展
——评《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