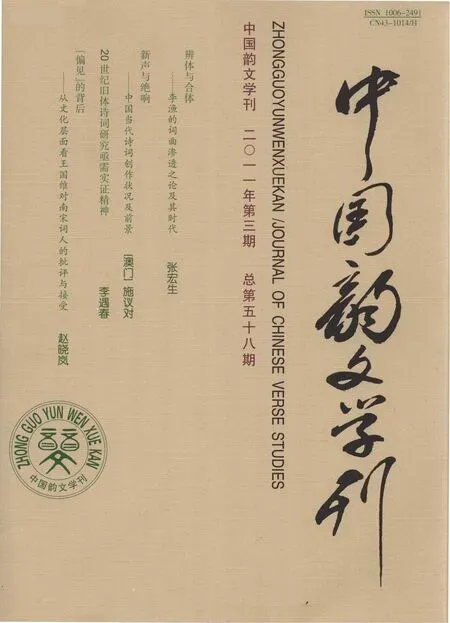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
施议对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 澳门)
一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
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经历过地覆天翻的变化。拙文《当代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载香港《镜报》一九九五年九、十月号)曾指出:胡适登场,新诗出世。原来写作旧诗的作家,多改途易辙,纷纷做起新诗来。但是,几十年过去,所谓用白话写诗,迄无成功(毛泽东语),某些原来写作新诗的作家,则转而专写旧诗或者写旧诗而兼写新诗。这就是我所说的双向流动现象。经此一变再变,中国旧体诗词“死而翻生”——胡适当时称之为“半死之诗词”(《尝试集·自序》),抡起板斧,必欲将其打杀;到了八十年代,各地诗词学会(协会)成立,旧体诗词不仅不再是一条虫,而且简直变成了一条龙。十几年来,随着开放、改革浪潮之兴起,中国旧体诗词这条龙,更是从田间飞上了天。所谓形势大好,或大好形势,诗城与诗国,经常都能感受到这一气氛。不过,如若冷静进行一番思考、反省,做到既说优点,又说缺点;既听好话,又听坏话。那么,我看,中国当代诗词创作之当前状况及前景,仍有可堪忧虑之处。
这里,着重说两个方面问题:作者问题及诗词自身问题。作者问题,即创作队伍问题。因为是一支杂牌军,人员复杂,素质较差,“诗多好少”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可忧虑之一大问题。而诗词自身,主要指其“死而翻生”后之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但其生存威胁及竞争对象,已非新诗,乃为愈演愈烈之时代流行曲。竞争得过则存,竞争不过则亡。这是可堪忧虑之另一大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下文将具体加以探讨。
一 关于作者问题
一般说来,所谓杂,不一定就不好,不杂也不一定就好。例如:有一位被称作“半路出家”的词学家,便是从副部级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才开始研治诗词的。而其进行得十分投入,十几年来出版多种著作,业绩并不比专门人才差。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但是,诗词毕竟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玩意儿的玩意儿,除了天份,尚须学识,并非个个都玩得(玩得了或玩得起)。这就是说,由于杂,大家都来玩诗词,不少人既缺乏先天禀赋,后天训练又很不足够,于是就玩出许多问题来。这是由作者问题所派生出来的问题。举其要者,大致下列数端。
(一)腐儒村叟之见,填词填字数。
以为凑上四句或八句,便可算是一首绝句或律诗,挂上一块招牌——“沁园春”、“满江红”,便可算是一首词;大量“笑掉人牙”之所谓作品,到处泛滥成灾。
“笑掉人牙”,这是湖南一位农民诗人对于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填词填字数”现象的揭露与批评。即谓某些挂着招牌的所谓作品,“仄平声韵竟全差”、“滥竽充数误童娃”、“笑掉人牙”。这一现象,在几百年前也曾出现过。例如:仇远为张炎《山中白云词》所作序即称:
……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 》、五字 《水调 》、七字 《鹧鸪天 》、《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窃笑,是岂足以言词哉。
可见,并非人心不古;某些事情,虽未必需要特别提倡,却自然流传不绝。就当前状况看,出现这一现象,除了作者主观原因——或无知或为着附庸风雅,此外,客观上或无意或有意之助长及推进,也是个重要原因。
所谓客观上的助长及推进,主要指:
第一,某些无知或附庸风雅者,并非陋邦腐儒,或者穷乡村叟,而乃有头有脸之大人物。因而,其所引纸挥笔,尽管不合格律,却仍被奉为极品,颁布天下。有关事例,相信已引起注视。不过,为尊者讳,今暂无须说明。
第二,某些不合格品,往往戴着高帽子,穿着阔衣裳,派头十足。因而,有关报刊杂志,大多照登不误。
例如,在回归倒计时那段时间里,某报所刊《念奴娇》:
香江奔腾,浪洗去,百年民族耻辱。九七回归,功劳是,一国两制构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宜国情民意。香港繁荣,港人双手创造。 追忆祖辈昔日,受殖民统治,苦不堪言;历代朝政软无能,望收复眼欲穿。喜看今朝,祖国强有力,收复失地。展望未来,明珠夺目生辉。
全篇除字数一项符合规定以外,平仄、韵部,皆十分混乱。且纯为政治术语之堆砌或胡凑。既不顺口,又不顺眼。不堪卒读。但因以“伟大构思”立题,也就不许说一个“不”字。
此类事例,屡见不鲜。尤其是各种大奖赛,运动群众,更令得诗坛、词坛,到处充塞着伟大的空话。
这是客观上的助长及推动,但与主观上的无知及附庸风雅,密切相关,都是作者自身所造成的。
(二)添足误以添手,点金而成铁。
前段授课,说学风、文风,曾揭示这么一种现象:有人语句不通,写不起整块整块文章,但做起诗来,尤其是存心让人看不懂的诗,颠倒、错落,却甚了得。与新诗界友人说及,颇有同感。但是,依我看来,旧体诗词写作,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是,新诗问题,有些也许将会留待后现代解决,而旧诗问题,却需提请留意。其具体体现,主要是组词与造句。这既是一种基本功夫,又容易受到忽略。诗国处处都有此现象。
先说组词。主要是词语配搭问题。就一般常识看,有关配搭或组合原则,最少应有二项:一、符合语法规定;二 、遵循世俗习惯。例如 “王”与“手 ”,所见棋王、蛇王、赌王以及刽子手、神枪手等,已经广泛使用,不成问题,但是,如更增添以“神钓王”或“神钓手”,我看就得费些斟酌。又如“眼”或“睛”,通常都说独具只眼与画龙点睛,如掉转过来,谓独具只睛或画龙点眼,看来就很别扭。此外,既说“开颜”,又加上个“笑”,应当也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出现于日常口语,总觉得奇怪,而见诸诗词,成为作品,却习以为常。
请看某氏所作《念奴娇》(庆祝建党七十周年):
天翻地覆,数不尽、一代风流豪杰。艰苦斗争七十载,推倒大山三迭。烽火南天,骋驰敌后,王气金陵灭。江山一统,五星红旗猎猎。 极目万里新程,送穷别白,迈步从头越。改革十年收硕果,内外交流棋活。温饱先臻,小康在望,更入高科列。卫星摇控,九天飞去邀月。
这首词与前文所谓“填词填字数”者相比,似略有进步。因为作者已注意到平仄及韵部问题。即大致能够按照词调格式规定填写。但视其对于政治术语之堆砌,同样缺欠艺术功底。诸如“送穷别白”,文理欠通,又与毛氏 “一穷二白”之原有论述相抵触,甚不足取。又,“一代风流豪杰”,重迭拼凑,亦甚牵强。这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作品选”所录作品(见《中华诗词》第三辑)。可见具有一定“水平”。
再说造句。主要是成语即现成词语及语句之入诗入词题。例如:“回眸一笑百媚生”,以之入词,成三字句,作“回眸笑”,通与不通?“发扬光大”以之入诗入词,成五字句,能否改作“发扬又光大”?等等。具体运用中,或生吞活剥,或点金成铁,经常出现差错。
请看某氏所作《采茶乐》:
雨霁山头蔚翠苍,姑娘结队采茶忙。三三五五摇摇摆,绿绿花花艳艳妆。树树株株挑剔遍,疏疏落落塞盈筐。金乌西坠呼归去,说说谈谈笑靥张。
将摇摇摆摆改为摇摇摆,将说说笑笑,换作说说谈谈,如口语中这般表述,恐怕要有相当勇气,起码应不怕“笑掉人牙”。而作为一首七律,类似“成语”,结队登场,却如此无有顾忌,其让人奈何不得。
又,某氏《江城子》(赞安源煤矿总工李敬存):
天涯何处诉衷肠。晋江旁。意绵长。不迷海外,祇爱我山乡。化作安源煤一块,燃自己,献热光。
卅年风雨费思量。不思量。志难忘。魂系华夏,岂畏履冰霜。报国常嫌时日短,明月夜,走山冈。
不仅点化成语“不思量,自难忘”,而且简直要将苏轼之整首词,剥开来,吞下去。只可惜,将其糟蹋得不成样子。
二例同见诸“会员作品选”,说明并非绝无仅有。
(三)缺少一个“观”字,依旧未入门。
以上所说,乃因观念错误及训练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一般说来,有关作者充其量都只能算是门外汉,其所谓作品,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及格线。这就是说,有关问题比较浅显,易于发现,也易于解决。但是,某些作者,既具有一定文字基础及语言表达能力,又熟悉诗词格律,却写不出好的作品来,这就比较难办。
所谓好的作品,是有一定标准的。如从诗言志的要求看,好的作品,应当是有个性、有自我的作品。这是有灵性或有灵魂的作品。相反,没有个性、没有自我,亦即没有灵性或灵魂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例如梁披云《北行杂诗》之“大明湖”曰:
老残游记尚依稀,千里初逢合有诗。几曲芙蕖万杨柳,大明湖上立多时。
诗篇写大明湖,有《老残游记》的依稀记忆,有眼前鲜明物景,但更为重要的乃有“我”——“大明湖上立多时”之诗人自我。这就是灵性的体现,就是好作品。当然,诗人之自我,并不一定非得让自己站出来直接说话不可。亦即“以我观物”,使得“物皆着我之色彩”。有时候,“以物观物”,同样有诗人自我存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观”字(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是衡量作品高下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某些作者之所以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其根本原因,我看就在于缺少一个“观”字。这是因一定的天份与学识所达致的艺术境界。
某些作者缺少“观”字,主要表现在对于两种题材的描写及反映上。
第一,对于自然物象的描写及反映。
由于缺少一个“观”字,某些作者的描写及反映,往往只侧重于物,而忽视自我;因此,虽颇为极其能事,却仍然感动不了人。类似某某八景或十景之咏以及大量模山范水之什,即属此例。
第二,对于社会事相的描写及反映。
同样,由于缺少一个“观”字,有关描写及反映,大多只是名词、术语的堆砌;因此,虽颇极堂皇富丽,却仍然吸取不了人。各地所谓大奖赛,成千上万,便是例证。
——这一些,大概就是所谓没有个性、没有自我,亦即没有灵性或灵魂的作品。这类作品,与某些摆明车马,就是要打油的“市井弹唱”相比,当有所不如。因“市井弹唱”,时有佳篇,或可让人尝一尝正牛油的滋味(打油诗另称“牛山体”),而这类作品,打的是水,又带有油味,甚是难以接受。
二 关于诗词自身问题
这里所说,主要是诗词质性以及诗词职能的变化。有关变化,既与作者问题密切相关,又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诸因素化所造成的。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雅颂多于风骚,旧经义变新经义。
讲授“古代韵文”,我曾引导学生论证这么一个题目:诗经是诗不是经。我以为,中国诗歌,就其本源看,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即使从“诗”到“诗三百”,经过孔子之正与删,也未曾将其变成为政治的附庸。现传三百零五篇,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占居大多数。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食、事以及男女间怨恨,一直是诗歌的主要咏歌对象。这是中国诗歌不断发展、不断获得成功的一个活的源头。
但是,当前创作却有掉转过来的现象。即:雅颂多于风骚。而且,所谓雅颂,大多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图解。政治,已与千百年前的经义一样,成为当今社会的新经义。因而,当前创作,使得诗词质性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当中及文化大革命之前,情况如此;文化大革命之后,也仍然继续着这种变化。
例如,郭沬若的《水调歌头》。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所作“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之所谓“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所作“粉粹`四人帮'”之所谓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以至此后所作“工业学大庆”之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凭`两论'。使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等,便是那个时代不断更换着的政治观念的图解。
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再批判,或反思、探索,原先那一套,似乎已被扬弃。例如,有一位革命家、词人,当说及自己的创作时曾指出:几首小令“反愁”,属于一种诡辩,不足为训;若干长调“批修”,现在看来,自己却修得比人家更厉害。以为平生所作,只“国庆夜纪事”之 《水调歌头》一首,较为满意。因而,极不赞成出版自己的集子。这是对于政治图解的一种自我否定。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不过,要将被掉转的现实转过来,重新确立风骚的主体地位,却并不容易。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图解的事实仍然存在。尽管其内容与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即旧经义亦即旧的政治观念,或许已经被抛弃,但新经义亦即新的政治观念层出不穷,仍然成为没完没了的图解对象。这就是促进诗词及其职能不断变化的一个外在因素。有关事例,下文另叙。
(二)立言重于学诗,旧羔雁换新羔雁。
以上所说,侧重于质性。以下着重说职能。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 ·季氏》)实际上,在此之前,所谓诗已为各诸侯国之公卿、大夫所广泛引用。不仅于祭祀、宴会、典礼,用作仪式中之一项重要程序,而且于社交场合,用作交际工具。据统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有关借赋诗以达致社交目的之事件,即有二十八例(参见袁梅《诗经译注·引言》)。这说明,所谓学诗与立言,在诗国早已形成风气。
当今世界,文明、开放,学诗立言传统,自然可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仅诗国贤俊,大多雅好讽咏,即使为蕃邦鬼佬,对此也未遑多让。比如香港回归,中英争拗,一方引用唐人李白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比喻谈判前景;一方面以美国杰克·伦敦诗句“宁化飞灰,不作浮尘”,表达最后观感,这便是典型例证。
在一般情况下,诗之用以立言,对于增添其社会职能,当颇有帮助。但是,就其自身之发展、变化看,诗之被广泛引用,却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是说,对于立言有用,起码可加强其陈志或言志之效果,而对于学诗,尤其是发挥诗之所以为诗之特有功能,则不一定有用。例如:文化大革命后,为呼应政治上需要,落实诗界、词界之“两个凡是”——凡是老干部都能够写诗填词,凡是获得平反昭雪的,都有诗词作品发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某大报,于某氏病逝不久,曾发表其遗作《金缕曲》,并附说明:“据某某同志的亲属记忆,此词写于一九六五年初。原词无标题,词牌名为编者所加。”其实,此遗作并非某氏所写,而乃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该大报之《贺新郎》,题称“新年献词”,作者赵朴初。这就是“献诗陈志”或“赋诗言志”之另一种表现方式。而此风一开,所谓学诗立言,便促使诗词职能之进一步政治化,并且使得诗词质性,也随着变化。即由某种政治观念之图解,进而蜕变为一般公卿、大夫用以礼聘应酬包括平反昭雪之羔与雁。这一变化,除了有利于某一政治目标之实现以外,相信对于诗词自身,不一定能有甚么好处。
一九八七年间,在岳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当代诗词研讨会上,有人批评诗词创作,谓其题材狭窄,存在四多四少现象:歌颂多,暴露少;自然题材多,社会题材少;应景赠答题材多,触及社会生活题材少;吟咏古迹、凭吊古人题材多,对历史作科学反思的作品少。认为,这就是平庸的表现。并指出:“平庸是旧体诗作者致命弱点,也是旧体诗振兴和繁荣的大敌。”所说甚中肯。而此四多四少,我看正是诗词之蜕变为羔雁之具的必然结果。
所以,王国维将中国文学史上诗与词这两种诗歌样式升(兴盛)与降(衰微)之关键,归结为这两种诗歌样式之是否被用作羔雁之具,其论断未必完全正确,而其所揭示现象——诗至唐中叶以后,为羔雁之具,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人间词话》)。这却是今之所谓学诗立言者,所当引起注意的现象。
三 两种系列景观
有关当前诗词创作中的问题——作者问题及诗词自身问题,已如上述。这是在横断面上所进行的分析与探讨。以下即从纵深点上,进一步加以发掘与追寻。不过,不准备说得太远,而只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所出现的两种景观:诗官与官诗相结合之系列景观及诗商与商诗相结合之系列景观。
(1)诗官与官诗。
在诗的国度里,诗与官或官与诗,本来就已结合在一起。诸如太师陈诗(《礼记·王制》)及使者采诗(刘歆《与扬雄书》)等,当是最早的一种结合形式。而且,自古以来,凡是有名有姓的诗人、词人,又几乎都当过官。这一切均说明,无论写诗当官,或者当官写诗,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事。亦即,既谓之为诗,着眼点就应放在诗上,而对于诗人之当不当官或是否当大官,则似乎不必看得太重。但是,当诗之由民间走向台阁,事情就并不那么简单。例如:一九八七年间,某诗词学会酝酿成立,有人即于北京某大报发表“杂吟”,对其结合形式提出异议,以为“一文一武两皮包”。当今世界,诗与官结合或者诗官与官诗结合,究竟好与不好?有关争议,甚少见诸报刊文字。依我看,似有重新提出讨论的必要。
首先,说好的一面。我以为,八十年代,一批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在诗词作创作杂牌军中所起领导作用,对于诗词事业之复兴及进一步发展,甚为有益,其功不可没。其主要体现,乃在于老干部之充分发挥“余热”——自身所蕴藏之剩余热量及人刚走茶未全凉,自身于官场所遗留之剩余热量。例如:筹组诗词学会(协会),要车有车,要房有房,这都不是一般弄墨舞文者所能办得到的。当然,当弄墨舞文者一旦做上了诗官,其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短短几年时间,诗词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澳门。诗词的事,已被提上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颇受重视。这当都是大好事。而且,有些老干部以诗词说政事,也时有佳作出现。例如安徽徐味所作《长征六十周年有感》二首:
一举惊天唤国魂,雪山草地忒艰辛。今宵舞困楼心月,曾照长征路上人。
鱼水情深绝对真,不真何以得生存。轻车重访长征路,怕见乡亲未脱贫。
诗篇借纪念长征以抒写观感。谓长征乃惊天动地之举,历尽艰辛,唤醒国魂;而六十年过去,国人(主要是干部)仍未醒,竟通宵沉浸于楼台歌舞,即所谓“三陪过后尽开颜”,怎么对得起长征路上人。谓六十年前,军民鱼水情,也正因为此情之真与深,军队才得以生存,长征才取得胜利;而长征胜利,夺得政权,长征路上乡亲,至今却仍未脱贫。我手写我口。既写出老干部心声,又写出老百姓心声。已完全废弃“歌德派”那一套,甚为难得。
其次,说不好的一面。这里所指乃合以后的分以及大量官诗,主要是政治顺口溜的出现。由于诗官与官诗,二者都带着一个官字,所谓分也就无法避免。尤其是某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词组织,更是一开始即蕴藏着分的危机。例如座次安排、职权分配等等,时常因此而打上官司。这都不是诗词之福。至于大量合格律或不合格律的政治顺口溜,也因作者的关系,占据重要位置,则更加造成灾难。有关事实,拙文《中国当代词坛“胡适之体”的修正与蜕变》(载香港《镜报》一九九六年二至五月号)已揭示,此不赘述。
(2)诗商与商诗。
就诗国固有传统看,诗与商或商与诗之结缘,机会似乎并不太多。但是,自从九十年代,文人“下海”,神州大地,包括港澳,却呈现另一景观,即诗商与商诗结合之景观。这是诗与商或商与诗互相需求的结果。由于步入九十年代,老干部官场余热已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社会上所谓“学而优则仕”,已逐渐变化成为“商而优则仕”,因此,某些诗人需要金钱以为雪中送炭,某些占有金钱的商人则需要诗,以为锦上添花。这便促使二者结合。而结合之后,可能两相满足,皆大欢喜。一方面,只要有钱(不一定来自赞助),就可以出书,诗集、词集大量印行;另一方面,只要有诗(不论合格与否),就有人写序、写跋,捧上殿堂。而且,各种各样的杯,各种各样的奖,大比大赛,则更加将诗坛搞得热闹非凡。这便是诗商与商诗结合之事实。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估这种结合?我看,应就具体事例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先说诗人之集子大量出版问题。诗集、词集大量出版,如从数量上看,似乎并无坏处。但是,如从质量上看,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谓诗国,时常发现一些诗词集,其中所收作品,或者徒有诗与词之外表(形式格律)而无其实,读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或者根本连外表也不要,纯粹胡诌,令人不堪入目。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一个方面,认钱不认诗。而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钱,诗写得再好,也难以出版。例如:沪上诗人富寿荪,写了一辈子诗词,及至老去,只能以若干刻油印本以示同好。比起市场上许多中看不中读的集子来,真可悲哀。前阵子,诗界前辈六楼居士(刘逸生)曾在澳门某报,就此事抒发感慨。
再说商诗问题。近代以来,以商人、实业家身份而写出好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但是,要由殷商一跃而为儒商,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位朋友,雄心勃勃,既要建造一个想赚多少钱能赚多少钱的商业王国,又要当一名能够创造历史的大诗人。我曾向其提出这么个问题:究竟赚五十六个亿容易,还是写五十六字(七律)容易。这位朋友不曾实时回答,而过后仍表示,二者都应努力做到。在此,衷心祝愿其成功。
最后,说大奖赛问题。这当也是两结合的产物。关键仍在于钱。在一般情况下,于得闲之时,凑凑热闹,也未尝不可。只是应当明白,于主事者而言,这可能是一笔一以当万的大生意,而对于诗词创作而言,相信并非正途。这一点,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每次大奖赛所布下的“天罗地网”,我看也就知道七八分了。
二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前景
一 唱衰与唱好
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看,中国当代诗词之当前状况,乃颇为复杂。尤其经历八、九十年代两个结合之后就更是杂上加杂。当前,不仅一班公卿、大夫,借重这块招牌,光宗耀祖,而且某些走卒贩夫,也扛着这块招牌,通街行走。因而,长征有诗,“三陪”亦有诗。所谓“全民皆商”,似颇有转变成为“全民皆诗”之态势。这大概就是所谓呈现出前所未有繁荣局面的一种迹象。
例如:一九九二年,中华诗词学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社在北京联合举办诗词大赛,参赛者二万有馀,参赛作品近十万,几乎有全唐诗的两倍之多。真乃空前盛举。
大家都来玩诗词、唱诗词,与上文所说两个结合一样,都具有好的一面及不好的一面,亦即有唱好与唱衰之别,同样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例如:一九九二年之北京大赛,获奖作品辑为《金榜集》出版,其中就有些少佳作。而香港回归前之另一次香港大赛,参赛作品,厚厚两大册,估计也有上千之数,但是,希望从中找出十首稍为像样的篇章来,却比沙里淘金更为艰难。
就当前状况看,所谓唱衰,大致表现在:一,社会上有些人,包括作者或非作者,利用诗词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导致诗词产生“异化”,亦即上文所说质性及职能之蜕变,令得诗不像诗,词不像词;因而,严重削弱其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朱熹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靖邃阁论诗》)之篇章,充塞诗坛。亦即“诗多好少”情况日趋严重,甚是令人缺乏信心。有关“异化”或蜕变问题,上文已述。至于信心问题,我看只要留意一下眼下之大量出版物,也就清楚了。两个问题,对于诗词现状及未来发展,都有极大影响。
这就是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见龙在田”,至八十年代中期,“飞龙在天”,诗词之社会地位已迅速提高。目前,其所面临的危机,已不再是将被人打死的问题。例如七十年前,文化革命先驱者对其批判及打击。其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自己将被自己打死。亦即,传统诗词这一条永远打不死的神蛇(某诗人语。见《中华诗词》发刊词),可能将自己“异化”为螟蚁(蝇蚁)。而且,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再是新体白话诗,而是时代流行曲。因为,经过几十年的争拗乃实践,新诗与旧诗打了个平手,至今已出现双赢局面。这一点,可以两位老诗人——臧克家及艾青的观感作见证。在为自己旧体诗稿所作序文《自道甘苦学旧诗》中,臧克家曾宣称:“我爱新诗,更爱古典诗歌。我写新诗,也写旧体诗。`我是一个两面派'。”而在为《马万祺诗词选(二集)》所作序文中,艾青则表示:“中国诗歌发展到当代,出现了双水分流的局面:多数人从事新体自由诗写作;一部份人喜欢旧体格律诗词。我主张不薄彼此,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说明,随着时势发展,旧诗已与新诗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但是,其所遭逢的新对手,却比旧对手更为强。大这对于“死而翻生”的诗词来说,无疑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二 坐井与见天
这里所说,主要是诗词的出路及前景问题。亦即,诗词之当前状况,既然如此复杂,那么,诗词之创造者,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危机,迎接挑战?这是可堪忧虑的问题,也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水平有限,见闻有限,只能就个人观察之所得,说点意见,以为进一步探讨提供参考。
第一,我以为,应当反对井蛙之见,看看井外的天。
这里所指是一种简单说“不”的观念,诸如“传统诗词永远是一条打不死的神蛇”等等。这对诗词自身发展,即如何保持其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我看并无益处。例如:唐声诗及宋歌词,二者均曾由当时流行曲,发展成为时代新声,即成为有唐一代及有宋一代之代表文学。但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时至今日,在新的流行曲已经广泛占据歌坛的情况下,唐诗宋词这一往昔流行曲,究竟能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就并非靠说一个“不”字,便可“大吉利是”(万事大吉)。尤其是台、港、澳歌坛,新的流行曲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已完全融入现代的生活。在这情况下,如简单说“不”,以为新的流行曲只追求刺激,歌词并不好,那就很危险。这是井蛙之见的一种表现。而另一种表现是,自我感觉良好。即不说 NO,而说 YES。例如某诗城,二十平方公里,四十一万人口,出了多少诗人、词人,印行多少诗集、词集,便以为世界之最。但是,就未曾检查一下,许多诗集、词集,哪一些可搬上台面,哪一些属于不合格品。时时、处处,喜欢“大阵仗”,实在不大好理解。
第二,应当提倡“无意做诗人”,防止诗词的“异化”或蜕变。
就作者与诗的关系看,“无意做诗人”,乃将诗摆在第二位,将人(作者)摆在第一位。用诗作为陶冶性灵的工具。其所为诗,亦诗亦人,乃为真诗。而非“无意做诗人”者,将诗摆在第一位,将人(作者)摆在第二位。用诗图解政治观念,用诗充当羔雁之具。其所为诗,无诗无人,乃非诗也。我想,如果明白这一道理,有关“异化”或蜕变现象,就当较少出现。
第三,爱惜资源,支持环保,扭转“诗多好少”局面。
这是编者与作者自律问题,似乎属于个人私事。因为出版自由,谁也不能干涉。但是,这又是一件关乎诗词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提请注意。因为如果任凭某些不三不四的诗词作品充塞市场,必将败坏读者的胃口。十分明显,这对于诗词之面对危机、迎接挑战,乃非常不利。所以,我曾向某大型诗词丛书之主事者建议:用控制数量的方法以保证质量。并曾在诗城所举办的一次诗词写作国际研讨会上呼吁:爱惜资源、支持环保;少出或迟出个人诗词集。我以为:没有质量,就没有出路,没有前景;没有质量,所谓新声,就将成为绝响。
附 记
本文曾以“新声与绝响”、“腐儒与村叟”、“蛇王与蛇手”、“打水与打油”、“风骚与雅颂”、“学诗与立言”、“诗官与官诗”、“诗商与商诗”、“唱好与唱衰”、“坐井与见天”为题,共十则,于“敏求居说诗”专栏发表。见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澳门《澳门日报》新园地副刊。并曾提交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十届中华诗词研讨会”。颇受关注。由于流传未广,行之不远,今谨借《中国韵文学刊》之一角,合成发表,以求正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