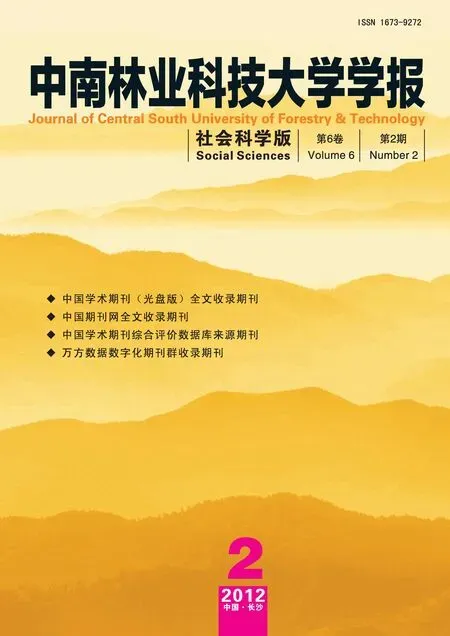目的论模式:德性正义与群体取向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简述
张 斌
(河南中医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08)
目的论模式:德性正义与群体取向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简述
张 斌
(河南中医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08)
在西方正义思想史上,“以伦理学、价值观为主题的古代正义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对古希腊传统的正义观念进行继承总结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其正义论证模式是典型的目的论,其正义实质内容是内在的德性圆满,其正义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群体本位(城邦公益)。
正义;德性;中道;价值
“粗略地看,西方正义理论主题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伦理学、价值观为主题的古代正义论、以自由平等权利为主题的近代正义论和以社会政策社会体制为主题的现代正义论。”[1]其中,“以伦理学、价值观为主题的古代正义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十多德是与柏拉图一道完成希腊古典哲学高峰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对古希腊传统的正义观念进行继承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并贯穿他的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首先,他根据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确立了自己的中道伦理观。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善”,即人作为人的功能的完满实现,也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具有,包括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而德性就是中道。中道之德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和选择,是一种把事情处理好解决好的适当的能力和方式。然后,他从作为伦理学基本原理的中道之德的出发,进入到政治领域——政治正义同样要遵循勿过勿不及的中道原则。他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如何实现小写的人——个体的善,而政治学是探讨大写的人——城邦的善,城邦政治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民个体的最高善德。他由中道之德延伸至中道之则,由个体德性过渡到城邦法律,由个体正义扩展到政治正义,从而实现了德性与规范、道德与法律、个体与城邦的统一。其正义论证模式是典型的目的论,其正义实质内容是内在的德性圆满,其正义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群体本位(城邦公益)。
一、形上根据:追求最高善——德性圆满的内在目的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是达至“至善”之学,探寻人性之优秀、灵魂之圆满即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之完善之学。这种伦理学是以目的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所谓目的论,就是用目的或目的因解释世界,认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目的性之中,目的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定性与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与柏拉图的理念目的论不同:目的存在于事物自身内部,而不是外部。在内容上具体包括“四因说”和“现实与潜能说”,它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阐释了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在诸多领域对目的论都有所讨论。而在社会领域,立足于“人”,这种目的论更多地体现在“善”的追求和实现上,“人的每种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在这种目的论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对照。”[3]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懂得如何从“偶然成为的人”进入到“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的学问,但是,伦理学探求的“个人善”如果缺少“城邦善”的支持就无法实现,人也就无法成为其所是。这样伦理学向政治学进展、个人德性生活向城邦正义原则延续成为必要。在目的论之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相对统一的,德性正义与正义规则也是趋于一致的。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门学科都属于实践科学,但是,相对来说,伦理学偏重于理论探讨,政治学偏重于现实研究,可以说伦理学为政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学为伦理学提供了应用舞台,这也体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总之,人成为其所是达至自身的德性圆满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共同主题和一致目的。
二、德性论:中道之德
亚里士多德在对前人正义思想总结、继承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中道的伦理原则。中道不仅是其德性正义论的内核,而且是其政治正义论的理论基石。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体善的,政治学是研究城邦共同善的,而个体善促进城邦共同善,城邦共同善又塑造个体善。个体的中道之德——“善行就在于行于中庸——则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行为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达到中庸”[4],从而促进城邦共同善。城邦正义反过来又塑造个体正义德性,城邦政治的目的是达致至善,它通过适宜政体和良法来造就公民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行,即善良与美好的行为。
中道原则大致蕴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中道是一种德性。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5]人“有三种性格,两种是恶的,其一是过度,另一是不及,一种则是中道”,“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5]“处在〔毋过毋不及的〕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4],德性是以理性原则为指导的,中道之德首先是理智德性,它是人们依照理性来控制、调节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使之始终保持适中的原则。如果人们按照理智德性行事并形成习惯,且促进了城邦善,那么中道之德就成为伦理德性。其二,中道是一种“相对性的中道”。这种“相对性的中道”之“德性是一种凭选择所得的习性。它的特点在于适度,或遵循适合各人的适度”[6]。“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6]其三,中道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并非全部行为和感受都可能有中间性。有些行为和感受的名称就是和罪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恶意、歹毒、无耻等,在行为方面如通奸、偷盗、杀人等,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罪过,谈不上过度和不及,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永远是罪过。”[5]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决不可用于恶的、不正当的情感和行为,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恶的性质。显然,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中道只能在德性意义上使用。
三、政治正义原则:从中道之德到中道之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和城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伦理不仅是城邦的前提,也是城邦的结果,甚至城邦本身就是以政治的方式达致自我实现的伦理实体。亚里士多德以中道之德为理想标准,希望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得以践履,这就是体现在政体选择和良法制定中的中道之则。
在国家政体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根本原则应是正义,“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中道。“一条绝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而今日正是己被许多变态政体所遗忘了的,就是‘中庸(执中)之道’。”[7]这就是说要以正义的原则即中道的原则确定国家政体。因此,他认为,富人主张的寡头政体,穷人主张的平民政体,这两种政体都趋于极端,远离中庸,悖乎正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凡是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越远的政体一定是恶劣的政体。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尊崇中道,中产阶级乃中道的化身,能顺乎理性,不走极端,是城邦正义的基石。由此,亚里士多德从中道正义观出发,主张建立由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的国家,这也是他的政治正义的现实模式。
在城邦法律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制定良法是法治的重要内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4]只有合乎正义的法律才是良法,即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良法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城邦公益为圭臬。如果法律以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为依据,则权力可能由个人或少数人掌握,而这无异于在政治中加大“兽性的因素”,显然不符合中道之则。二是以公民权利为内容。“凡自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4]这就要求法律必须成为“毫无偏私的权衡”。城邦之良法的现实意义即在于促成城邦公民都能够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四、中道之则的两种应用: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
作为正义准则的中道应用于两个不同领域,规范两种不同关系,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正义: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
普遍正义应用于一个普遍的领域——城邦秩序,它规范公民与整个城邦的关系的,要求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违犯法律的人被认为是不正义的。同样,守法的人和均等的人是正义的。因而,合法和均等当然是正义的,违法和不均是不正义的。”[5]法包括不成文法和成文法,“但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7]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也就是中道之德,成文法当然是作为中道之则的法律,中道之德在现实城邦中政治的应用就形成成文法。“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7]
特殊正义规范一个特殊的领域——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它规范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要求公民之间实现公平。特殊正义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分配正义遵循比例平等原则,其要求依据公民各自的实际价值在城邦成员之间分配财富、职位、荣耀及其它可分之物,强调分配应当因人而异,平等的人应受到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的人应受到不平等的分配,而确定公民各自实际价值应结合公民的身份、地位、财富、德性、绩效等因素综合考量。矫正正义遵循算数平等原则,其旨在维护公民经济交往中的公平,通过法律强制矫正公民之间的侵害,对受害者予以补偿。可以说分配正义是各得其所,矫正正义是各失其所。矫正正义只关注所造成的实际侵害的大小,而不管公民个体自身实际价值的大小。侵害了他人利益就破坏了正义,法律必须通过惩罚来使其恢复均等。交换正义则是对公民之间自由经济交往的要求,交换双方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即经济交换双方的所得与所失相对等。如果说矫正正义是非自愿交换中的正义即强制均等的话,那么交换正义就是自愿交换中的正义即自主的均等。[8]显然,特殊正义的再划分——比例平等、算数平等和等价交换实质上是中道之则的更为具体的现实标准。
五、价值取向:城邦公益
“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这种善对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统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5]“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善。”[5]他又在《政治学》中论述道:政治国家的目的是“至善”,城邦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优良的生活,“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了[4]”。严格说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正义的思想,实质上更多的是在阐述公共利益至上的正义思想。其经典名著《政治学》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基于又不同于伦理学的角度向人们证明:政体、法律要以人类理性选择的公共利益为正义圭臬。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实际上是以内在目的论为形而上基础,以城邦政治正义为现实目标,以城邦公益为价值取向,以行为有利于人们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为标准而建构的系统化理论。亚里士多德基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现实人性观,认为城邦应优先保护和考虑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即他所指的城邦公益,而个人利益只能在整体利益中得到实现,并且只有这样才是合法的、合理的,纯粹的个人利益是不合乎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治行为的宗旨是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指出了合法政府权能的根本目标和现实边界,也为评价政府效能提供了一个根本标准。
虽然,人类社会已跨入了新的千年,可西方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所论证的目的论德性正义理论对当代思想界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物质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可正义问题却依然困扰着人类的时代背景下。抛开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目的论这一为后世所诟病的缺陷不论,其德性正义论尽显真知灼见,特别是其将正义首先视为公民最为重要的德性的观点就被当代思想家麦金太尔所承继并加以阐发。麦金太尔提出了正义即美德的正义理论,并指出要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正义问题,就必须追寻正义之美德。他对西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自古以来关于正义概念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但又紧密联系的解释:作为美德的正义和作为规则的正义。他认为,正义首先是作为美德的概念出现的,“对于按优秀善来定义的正义来说,作为一个个体美德的正义,是在撇开并先于强制性正义规则确立的情况下被定义的。正义是给每个人——包括给予者本人——应得的本分,并且是不用一种与他们的应得不相容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人的一种品质。当正义的规则按照这种正义概念来设置而处于良好秩序中时,它们就是那些得到最佳设计来确保这一结果,包括正义和不正义的结果的规则,假如人人都遵守它们的话。”[9]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相对来说作为美德的正义要比作为规则的正义更为重要,因为不正义的人照样可以在行动上表现出遵守正义规则,可这却可能仅仅是出于害怕惩罚而遵守的,而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了解如何去应用规则。因此,“无论‘正义’还指别的什么,它都是指一种美德;而无论实践推理还要求别的什么,它都要求在那些能展示它的人身上有某种确定的美德”[9]。这就告诉我们,正义美德是遵守正义规则的内在根据,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觉遵守正义规则的品质和能力,从内心深处自觉地遵守正义规则,也只有这样的人的行为才真正具有道德价值。所以,要解决正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应该首先培养人正义之美德。
[1] 戴桂斌.西方正义论主题的历史嬗变[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49-52.
[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3] [英]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7.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4,205,199,167,81,7.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37,34,94,16.
[6] 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97,297.
[7]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273, 170,169.
[8] 马捷莎,李 祥.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J]. 学术交流,2006, (1):23-25.
[9] [英]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56,35.
The Teleology Pattern: Justice of Moral and Group Orientation——Aristotle’s View of Justice
ZHANG B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TCM, Zhengzhou 450008, Henan,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s of justice, the most famou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theory of justice on theme of ethics and values is Aristotle. He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 of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Greek traditional idea of justice. The pattern of demonstrating justice was typically teleology. The substance of justice was internal virtue satisfactor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justice was obviously featured by its group standard (public interest of city-state).
justice; virtue; mean; value
B82
A
1673-9272(2012)02-0089-03
2012-02-10
张 斌(1978-),男,河南郑州人,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伦理学。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