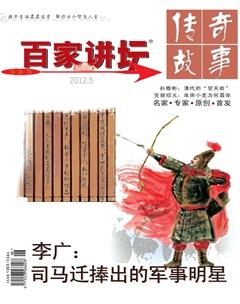消逝的锋芒:从画眉京兆到凤凰丞相
郑骁锋
这天,刚被提上丞相之位的黄霸正在府中主持工作,忽然有几十只大鸟从天而降,停在了丞相府的屋顶。黄霸出来仔细一打量,这些鸟赤颊长尾,脑后还长了一对角状的白翎,平生从未见过。他不禁又惊又喜,立马焚香净手,回到房中撰文,准备奏报给皇上。
黄霸把这群异鸟视为神雀,而“皇天报下神雀”,正是对自己辛勤工作的肯定,推而广之,更是对宣帝慧眼识人择他为相的肯定。总之,这难得的祥瑞,不仅是他同时也应该是皇上和整个帝国的荣耀,理当诏告天下,与万民分享。
报告这样的祥瑞,黄霸轻车熟路。他这辈子很有鸟缘,当地方官时,便经常上报有凤凰现身在他的辖区,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之兆,喜得皇帝再三下诏褒奖。只是这次却阴沟里翻了船:当他还在为这份喜报字斟句酌时,京兆尹张敞已经抢先送上了一封奏章,一五一十向宣帝说明了真相。
张敞说,这些鸟其实只是鹖雀。对此他有足够的证人,因为那天正值全国各地上计官员集中丞相府汇报工作,起码有几百人看到这群鸟是从丞相家里飞过来的;另外,张敞还指出,鹖雀虽然在关中稀罕,但从边郡来的官吏应该不会陌生,可那天却集体装糊涂,根子还得从黄丞相身上找。
宣帝连連称是,派人带着张敞的奏章,叫来黄霸好生训诫了一番。可怜黄丞相一团兴头,却被重重掴了一巴掌,落个老大尴尬。他只能关起门来哀叹,京城毕竟不同外郡,人心刁蛮,水深得可怕。
张敞的奏章流传开后,人们才隐约猜到,那群鸟的神秘出现不是偶然。因为那群怪鸟如果真是鹖雀,算起来和张京兆是同乡,老家都在山西。
张敞被怀疑为这起神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做出任何事,都不会有人觉得意外。
张敞的一生近乎传奇,就连走入史书的姿势都卓尔不群。后世提起此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几个香艳的成语,比如“张敞画眉”,又比如“章台走马”。然而,张敞会的不止这些。他把京师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朝会议事也总能拨云见日,一语中的,朝廷处理许多军国大事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宣帝好几次想提拔他,但总有人以其“为人轻佻,威仪不足”为由反对,宣帝只得作罢。终其一生,他与丞相、御史大夫之类的三公宰辅屡屡擦肩而过,最大的官职止步于京兆尹。
若从官场失意的角度考虑,张敞设计整蛊新任丞相黄霸,是有充分的动机的。张、黄二人的起点大致相同,治郡也都有善绩,可二人水平高下其实早有验证:任相之前,黄霸也做过京兆尹,京城剧烦纷乱,号称天下第一难治之地,黄霸很快就因不能胜任被打回了原郡,而张敞则连任八九年,是西汉最著名的两个京兆尹之一。对于黄霸的升职,张敞想来是不服气的。
然而,若真以扳倒黄霸为目的,张敞完全可以等黄霸送交喜报后再上书,那时白纸黑字存档,事情可就搞大了,弄不好黄霸会背个欺君的重罪,撤职乃至杀头都有可能。可最终,张敞只是搞了一场点到为止、要不了命的恶作剧。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张敞是个坦荡君子,觉得黄霸纵然才能有限,但终究算是个好官清官,至少非常照顾老百姓,所以,对这个自称常常能见到凤凰的老家伙,下个鸟套耍弄一把,好歹出口鸟气也就够了。不过,仔细再读那份奏章却发现,张敞此举或许还有深意。
奏章的前半部分,张敞行文看似一本正经,实则调侃戏谑无所不用,令人哭笑不得。但在后半篇,张敞却凝重而诚挚,大意为:他不敢故意诋毁丞相,是怕上行下效,破坏原本淳朴的民风,导致人心浮薄。然而堂堂京城岂能在全国带头搞欺骗?当然,地方上的弄虚作假如果超过京城,同样也不是小事。所以他呼吁,若有人敢以诡诈手段欺世盗名,必须严惩不贷。
应该说,后面这一段话更像是张敞上这份奏章的真正目的。以他的秉性,与其说他厌恶黄霸个人,不如说是厌恶某种习气。倜傥洒脱的张敞,早已经敏锐地发觉,以黄霸为代表的官员们,在庄严的光环下隐藏着一种目前还不为大众察觉的毒素,如果不及时驱除,弥漫开来很可能会导致整个大汉王朝的堕落。
在《汉书》中,黄霸被载入《循吏传》,同传的都是被朝廷表彰的郡守级地方大员,他们都温良恭俭让,爱民如子,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属于死后受得起小民烧香供猪头的大善人。然而,《汉书》在对他们赞誉之余,也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字。
据《汉书》记载,黄霸的治民诀窍依然与鸟有关。做郡守时,有次他派一名小吏外出执行秘密任务,该吏担心泄密而不敢入住官驿,便在路边吃干粮,结果被乌鸦衔走了一块干肉。这一幕刚好被一个要到官府办事的人看到了,这人后来随口告诉了黄霸。等该吏完事回来,黄霸迎上前去慰劳他说:“你此行辛苦,吃饭时都被乌鸦叼走了肉。”该吏大惊,从此办事丝毫不敢隐瞒。黄霸类似的言行还有很多,搞得属下和百姓都以为他有神通,因此坏人都不敢在他的郡内作案,纷纷离去,于是境内大治。
其他循吏也大抵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有着某种令张敞厌恶的共性—为博得好名声而不惜虚伪或者做作。不过,假如再深挖下去,虚伪做作背后,还有更令人担忧的症结。
“循者,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一个“顺”字点明了循吏的本质。两千多年后,曾国藩用“软熟”一词悲叹晚清官场朽烂不可救药,而早在黄霸等人身上,“软熟”之苗已然萌芽。黄霸的退场,证明了由“顺”到“软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黄霸官宦生涯的最后一次危机,是宣帝对他越职举荐太尉人选的严厉责问。黄霸除冠谢罪,几天后才得以免于处罚,从此至死噤口。黄霸举荐的人是史高。史高虽说为人奸邪,但他是宣帝的舅父,最为得宠。
其实,这记马屁拍得似歪非歪。宣帝死后,史高当权,甚是看顾黄霸后人,黄霸“子孙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有循吏做对比,张敞的官运坎坷多了些必然,因为在皇帝眼里,张敞欠缺一个“顺”字,甚至在很多时侯,简直就是个刺头。
张敞入仕之初便以放言直谏闻名,曾因此得罪权臣霍光,被穿了多年小鞋;而他为政也勇决自用,做事图个痛快爽气,绝不按部就班,有时甚至不惜以犯法来执法。他的这种性格,为后人留下了另一个成语“五日京兆”。
张敞的京兆尹做到第九年时走了背运,因好友杨恽犯了死罪而被牵连,遭到弹劾。虽说宣帝迟迟没有做出最终判决,但其处境之危已是世人皆知。
这天,张敞给了他属下的一个小吏絮舜一项任务,不料絮舜领命后却径直回家睡觉了。旁人问他为啥不上班,他回答:“现在张敞不过是五日京兆,威风不了几天了,还能拿我咋办?”
此人本是张敞一手提拔的心腹,张敞得知此言,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没有像一般落魄人那样只会酸溜溜地感慨世态炎凉,而是采取了非常手段—他立即发文,将絮舜缉拿归案。此时离立春只有数日,按法制入春后就不能再杀人了,张敞便命人日夜拷问,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短短几天竟将絮舜问成了死罪。行刑那天,张敞命人给絮舜带去一张字条:“‘五日京兆又怎么样?现在冬日将尽,你还能活命吗?”絮舜刚看完,就被咔嚓一声一刀两断。
因为此事,张敞被奏滥杀无辜,连皇帝都保不下来,只得缴还印绶,亡命他乡。
友以类聚,与张敞相似,他的好友严延年也相当鄙夷黄霸。有次严延年的辖区暴发蝗灾,他想起邻郡的黄霸,便不阴不阳地对人发了句牢骚:“我这里的蝗虫,大概就是他的凤凰的食物吧。”日后严延年以怨谤朝廷的罪名被处死,这句话也是罪状之一。顺便提一句,之前连累张敞的杨恽,也是由于说话皮里阳秋夹枪带棍,被宣帝判以大逆不道之罪腰斩的。
张敞结交的,大都是这些满嘴胡乱放炮的倒霉蛋。
这几桩公案隐含着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汉武帝之后,但凡如张、严之类棱角分明者,出路越来越狭窄,很少有人能得到好结局,而黄霸等循吏却开始大行其道—这是否暗示着中国历史逐渐开始消解锋芒?
数十年后,张敞的孙子张竦也做了郡守,他虽然为政不及张敞,但为人博学文雅,尤其善于自我约束。
“竦”,本意“被捆绑着站立”,引申为恭敬、肃敬。而“敞”,则开也,露也。也许只是巧合,祖孙俩的名字,从头角峥嵘到和光同尘,恰好印证了一个王朝由外向到内敛、由浪漫到拘谨的转变过程。扩而大之,这也意味着一个民族黯然挥别了激情飞扬的少年时代。
《汉书》之后,历代官史中,少有张敞这类人物,而至于《循吏传》,则每史必修。不过几千年间,循吏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把黄霸等人的事迹抹去姓名年号,随便归到哪个朝代,都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编 辑/孙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