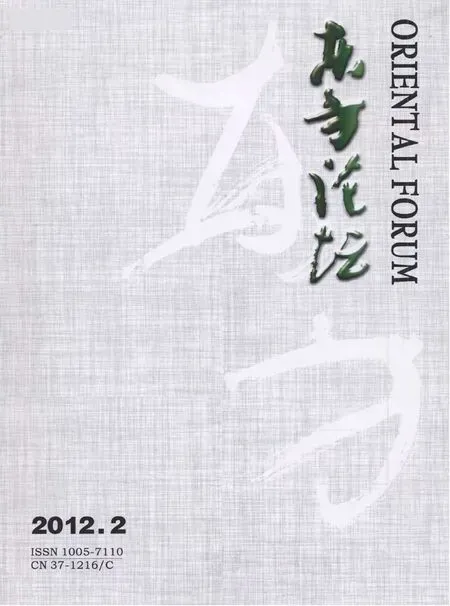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卞 修 全 肖 婧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8)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卞 修 全 肖 婧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8)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横向国家权限的规定上,虽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非均衡而带有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议会独大主要表现在国会对总统、内阁和法院的权力多所限制,而总统、内阁和法院却很难制衡议会;总统有权无责主要表现总统享受广泛的权力,包括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立法否决权等等,但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内阁替总统承担整治责任。这种做法体现了时人在议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
《中华民国宪法》; 议会独大; 总统有权无责;责任内阁
对于1923年宪法,学界已普遍承认其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宪法,认为该宪法在国家横向权限划分上坚持了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继承了“天坛宪草”的民主精神。但对于1923年宪法横向国家权限规定的深层次特征,学界缺乏探讨,本文从1923年宪法有关国家横向权限划分的条文出发,重点分析其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
一、议会独大
从国家权限的横向划分看,1923年宪法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三权分立”包含权力分立和人事分立两方面。从权力分立看,该宪法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分别交由国会、大总统和国务员、法院行使。第39条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国会行之。”第71条规定“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第97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司法权,由法院行之。”从人事分立看,该宪法严格区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制宪过程中,议员们对宪法草案第26条“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两院议员能否兼任国务员。赞成者认为两院议员兼任国务员一职可以起到沟通立法和行政的作用,反对者则认为两院议员兼任国务员严重损害了三权分立原则。如众议院议员高旭在《对于天坛宪法草案商榷书》中指出“夫立宪国之精神其主重在三权分立,议员已有立法权,若在国务院兼操行政权,一人而兼立法行政两种权限不清不第有害立法并且有防行政……如此则数十年来人民革命流血所争之三权分立不尽付诸电光石火耶。”[1](第2册P81-82)之后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在宪法二读会上删除了但书,该宪法第45条规定“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
1923年宪法虽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不均衡,立法权对行政权、司法权的限制较大,从而形成了议会独大的特征。议会独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议会对行政权的限制
(1)议会和总统。议会对总统的限制表现为议会享有选举权、弹劾权和审判权,而总统虽享有立法否决权和解散权,但立法否决权和解散权都受到很大限制,使之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抗衡议会的作用。具体分析如下:①选举权,即在人事上议会控制着总统选举。宪法第73条规定“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之。”第78条规定“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但副总统缺位时,应补选之。”可见总统要想当选必须要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②弹劾权和审判权,即议会有权对总统进行弹劾和审判。宪法第60条规定“众议院认大总统、副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得以议员总数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同意弹劾之。”第63条规定“参议院审判被弹劾之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③立法否决权,即当总统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案有异议时可要求国会进行复议的权力。宪法第105条规定“国会议定之法律案,大总统如有异议时,得于公布期内,声明理由,请求国会复议。如两院仍执前议时,应即公布之。”对于国会的议事规则,该宪法第56条规定“两院非各有议员总数过半数之列席,不得开议。”第57条规定“两院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之同意决之。可否同数,取决于议长。”可见法律案的通过需要过半数议员列席,列席的过半数同意。而根据第105条的规定当总统行使立法否决权要求国会复议时,国会仍只需要过半数列席,列席的过半数同意即可通过法律案。当时会议中也有议员认为过半数同意的要求太低,主张两院2/3同意时才能公布。但反对者认为2/3过高,有悖于议会政治,[1](第5册P432-433)后经过多次讨论出于对议会政治精神的维护还是选择了过半数通过,而没有提高复议的人数要求,从而也使这一权力流于形式,起不到制衡议会的作用。而且该宪法第107条还规定“国会议定之决议案,交复议时,适用法律案之规定。”即总统对国会通过的一般的决议也很难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④解散权。在内阁制国家中,面对国会的不信任案,内阁可以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来与之相抗衡,表面上虽仍需要国家元首的同意,但由于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没有实权,因此一般不会拒绝内阁的要求。如“在英国,解散议会女皇是必须要准许的。解散议会权,名义上虽属于君主,而实质上则已成为内阁的特权了。”[2](P152)从民国2年以来的制宪史料看,解散权经历了是否要规定有解散权到最后折中采取限制解散权的过程。反对总统有解散权的议员从民意和防止行政专制角度进行探讨,认为总统行使解散权是对民意的践踏且容易导致行政专制,如参议院议员萧辉锦在《关于宪法草案第六章规定大总统职权意见书》中认为以行政权解散民意机关不合共和之精神,他指出“夫共和国国权之行使原以民意为指归,议员代表民意监督政府,政府自无与议员意思背驰之理,且以被监督者之地位而反有解散监督者职权,理论上亦极不相容。”[1](第10册P320)而赞成者认为则既然采取议会内阁制那么总统就应有解散权,以此和议会的不信任案相抗衡,如参议院议员褚辅成认为“若欲政府趋于宪政轨道实行议会政治即罗议员所谓欲达多数政治之目的而不予以最后之监督,恐多数政治将无法以运用。……现在本宪法之全部精神在采责任内阁制度,即欲采责任内阁制度则解散权不能不与之政府。”[1](第10册P86-87)最后经过多次讨论折中选择了限制解散权,即内阁可以提请总统解散众议院,但须经参议院同意。宪法第89条规定“大总统于国务员受不信任之决议时,非免国务员之职,即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原国务员在职中或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虽然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确定了两院制,但其未区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的职权,后虽经多次修改但关于两院的职权仍只在第14条中有所规定,即“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但下列事项,两院各得专行之:一、建议;二、质问;三、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四、政府咨询之答复;五、人民请愿之受理;六、议员逮捕之许可;七、院内法规之制定。预算决算,须先经众议院之议决。”而在1923年宪法“国会”一章中也只是区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产生方式,对二者的各自权限未做具体区分。因此虽然议会采取两院制,但因众议院和参议院区别不明显,参议院很有可能为保持国会的一致性而拒绝总统解散众议院的请求,使得内阁无法与议会抗衡而只能集体辞职。
(2)议会和内阁。议会对内阁的限制主要表现为议会享有以下4种权力:同意权、预算否决权、弹劾权与不信任权,同意权和预算否决权是事前监督,而弹劾权与不信任权则为事后监督。 ①同意权,即在人事上国务总理的任命需要众议院的同意。第94条规定“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国务总理于国会闭会期内出缺时,大总统得为署理之任命;但继任之国务总理,须于次期国会开会后七日内,提出众议院同意。” ②预算否决权。根据1923年宪法众议院不仅有否决预算的权力,而且当众议院对于决算追认案予以否决时国务员还需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第112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岁出岁入,每年由政府编成预算案,于国会开会后十五日内,先提出于众议院。”第120条规定“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案,每年经审计院审定,由政府报告与国会。众议院对于决算案追认案否认时,国务员应负其责。”③弹劾权与不信任权。第61条规定“众议院认国务员有违法行为时,得以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弹劾之。”第62条规定“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弹劾是针对单个内阁成员的法律责任,由其自身承担相应的法律制裁不影响整个内阁的运作,而不信任案是针对内阁集体的政治责任,由整个内阁承担可能被倒阁的连带责任。由此可知不信任案的政治后果比弹劾要严重的多,出于政治稳定角度议会应慎用不信任案。但结合第57条“两院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之同意决之。可否同数,取决于议长。”可知,弹劾案的通过需要过半数列席,列席的三分二以上通过,而不信任案的通过只需要过半数列席,列席的过半数通过即可,因此虽然不信任案的政治后果更为严重,但1923年宪法并没有对国会通过不信任案的人数要求做特殊规定,只按照一般的议事规则通过即可,再加上第62条并没有明确限定议员在什么时候情况下可以提不信任案,这就使内阁很容易就处于被倒阁的风险中。不信任案最早起源于议会制国家英国,英国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组成,虽然英内阁也面临着被倒阁的风险,但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英国发展出了很完善的政党政治,即内阁可以通过严格的政党纪律来控制议员的行为,使议员不敢轻易提出不信任案。但反观当时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情况,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党林立,袁世凯政权建立后各政团经过分合后主要形成了共和党、民主党和国民党三大党派。当时各党派之间的政治纲领没有很大的差别,且政党之间的分散离合也没有什么根据,群众基础也不深厚,很多政党只是一些政治投机团体。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后,袁世凯一方面采取“以党制党”的方法把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成为进步党企图借此反对国民党,另一方面派人刺杀宋教仁。随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组建各种小党,通过玩弄党派迫使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国会中的政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的国会议员另组政治团体而不以原来党派身份自居。进步党变成研究系,国民党旧议员则分裂成益友社、民友社、政学会等各种小团体,段祺瑞上台后为控制国会又成立安福俱乐部作为御用政党。可见,民国初期政党政治虽曾兴盛一时,但由于各政党自身不成熟,面对军事力量的强势介入最终也只能沦为军阀政治的点缀,无法独立组阁保持议会与内阁的一致性。和不信任案一样,弹劾权也起源于英国,虽然议员们可以弹劾内阁成员,但由于议会可以对内阁提不信任案,议员们也很少使用弹劾权。“弹劾制在英国,久已废弛不用,且自1805年以来,英国议会从无行使弹劾权之事。”[3](P252)综上,根据1923年宪法议会既可弹劾国务员又可对国务员提不信任案,而其中不信任案的通过较易,没有具体情况的限定,也没有完善的政党政治能够约束议会,使内阁无力与议会抗衡。
2、议会对司法的限制
议会对司法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宪法解释权由宪法会议而非法院行使。该宪法第139条规定“宪法有疑议时,由宪法会议解释之。”第140条规定“宪法会议,由国会议员组织之。前项会议,非总员三分二以上之列席,不得开议,非列席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决议。但关于疑议之解释,得以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决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司法权是最弱的,因而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中往往赋予法院以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以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对此美国早在1787年制宪会议就有讨论,“如谓立法机关本身即为其自身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其自行制定之法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则对此当作以下答复:此种设想实属牵强附会,不能在宪法中找到任何根据。不能设想宪法的愿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远较以上设想更为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使。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4](P392-393)议员们对于宪法解释机关应为宪法会议还是大理院曾展开过激烈讨论,赞成由宪法会议解释宪法的议员认为由制宪机关解释法律可以保持宪法的一致性,而由法院解释宪法则有悖于民意。如众议院议员曹玉德在《对于宪法草案第11章第112条解释宪法权修正案》中指出“民国宪法草案从大陆派多数国先例以解释宪法权规定于宪法会议,其强健理由约有三端:首先,宪法制定即为造法机关,此后发生法律上之冲突自应由造法机关解释之,若委之于其他机关则宪法根本或有动摇。其次,制定宪法为一机关而解释宪法又为别一机关,统系不明法例紊乱而宪法精神乃蒙其影响。最后,制定宪法属之多数人民代表而解释宪法乃委之于少数任命法官揆诸定宪原则未免不合。以上三条理由为本条起草之根据。”[1](第6册P369)赞成由大理院解释宪法的则认为由同一批人解释宪法无法起到解释的作用,加上宪法会议要2/3列席,3/4同意,门槛过高且两会闭会时重新召集三分二以上议员非常困难,会造成无法解释的局面。如参议院议员王正廷指出:“试观第113条第二项非有列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之规定即可明了,加入规定为过半数之同意则尚不致发生困难,且宪法会议议员即为国会议员,以国会议员自身制定之宪法而易一名义如宪法会议者,使解释宪法上之疑义,此即为一最大值困难。况国会中均有党派之分野,以两院合组之宪法会议解释宪法上之疑义而又受总员数即列席员数种种之限制,恐难有解释之形式终难得解释之结果。”[1](第11册P156-157)最终经过投票多数通过由宪法会议解释,但通过人数从列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修减少为三分二以上。但该宪法第26条在划分国家和省立法权限时又规定“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性质关系国家者,属之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之各省,遇有争议,由最高法院裁决之。”第28条规定“省法律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省法律与国家法律发生抵触之疑义时由最高法院解释之。”由于最高法院在裁决争议、解释疑议时必然会牵涉到宪法中的具体条款或名词的解释,因此根据这两条法条最高法院在宪法具体操作层面上实际享有了解释宪法的权力。而该宪法第139、140条明确规定宪法解释权由国会议员组织的宪法会议行使,没有对国会的解释权和法院的解释权进行区分,没有划分二者的界限。因此当最高法院的裁决和解释不利于国会时,国会可以根据其享有的宪法解释权对宪法重新进行解释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和解释,从而破坏司法权的独立。
(2)诉讼范围的限制。为保持司法权的独立性,宪法都规定法院有权受理一切诉讼。但该宪法第99条规定“法院依法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但宪法及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即议会可以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二、总统有权无责
从当时宪法起草会议录上议员的发言我们可以知道议员们选择的政治体制是责任内阁制,但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让内阁替总统承担政治风险,使总统这一国家机关能够立于政潮之上,起到象征国家稳定统一的作用,同时通过其尊严地位调和国会与内阁的关系。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议员们讨论了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委员向乃祺认为“惟有两制优劣之点加以比较,简单言之内阁制似优于总统制。盖施行内阁制之国家当国内发生扰乱时大总统可以维持尊严,无论然后发生何种政潮大总统位乎政潮之上,有责任内阁担负责任。……倘使施行总统制总统任期有一定之年限,在未满任以前如国内发生政潮问题应如何解决?且一个任期之中为时甚长,政局变故如何诚不可知。是诚无良法可以解决之,势不能不起革命,革命一起革命又何能不危及国本,所以民国断乎不可施行总统制也。”[1](第3册P350-351)委员刘朝望则认为内阁制可以使总统维持尊严的地位以调和国会与内阁的关系,其在会议上指出“本席亦主张内阁制。盖民国数年以来屡次发生政变,总统地位尚不至于动摇者,因由内阁负责任也。倘施行总统制遇国内发生政变时则总统地位势必至陷于动摇,国务谁负其责?……如施行总统制恐发生种种流弊。”[1](第3册P352-353)其他赞成施行内阁制委员的原因也大体如此,可见议员们构建的民国总统类似于英国国王,但英王是虚位元首没有实权,而1923年宪法却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这也就造成了总统有权无责的局面。
具体来说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统享有广泛的权力。1923年宪法规定下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政府首脑。该宪法第79条到第88条赋予了总统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第105条赋予了大总统立法否决权。因此1923年宪法规定下的总统兼具总统制和议会制下政府首脑所具有的权力,是享有实权的国家机构而并非责任内阁制下的虚位元首。
(2)内阁替总统承担政治责任。该宪法第95条规定“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大总统所发命令及其他关系国务之文书,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但任免国务总理,不在此限。”这符合责任内阁制中内阁是政府行政领导核心的特点,但由于该宪法只规定了政府可对国务员提不信任案,对总统却未做出相应规定,因此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时,往往是由内阁而非总统承担政治责任即内阁被迫倒阁而总统却未受影响。且第81条规定“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吏;但宪法及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因此虽然国务员有副署权但总统可以凭借其人事任免权选择“听话”的国务员。
事实上总统有权无责是民国以来的宪法文本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准备按照总统制建立政府体制,后为约束袁世凯而改为内阁制,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总统类似于联邦制总统的权力,对于内阁的权力则只在第44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和第45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中做了规定。随后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在大总统原有权力基础上又增加了发布教令权,并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第17条“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解散立法院。”第20条“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害,事机紧急,不能召集立法院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发布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之教令;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第34条“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大总统否认时,得声明理由,交院复议,如立法院出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而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同时《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国务员必须在总统提出的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副署的规定。《天坛宪草》基本延续《中华民国约法》有关大总统的权力规定,但对发布教令权、停止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做了相应限制。第65条“大总统为维持公共治安,或防御非常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时,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第74条“大总统得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之会议,但每一会期,停会不得逾二次,每期间,不得逾十日。”第75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大总统解散众议院时,应即令行选举于五个月内定期继续开会。”对于内阁则恢复了《中华民国约法》废除的国务员的副署权,第81条规定“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大总统所发命令及其他国务之文书,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基本沿袭了《天坛宪草》相关规定,可见总统的权力在扩张,但内阁的权力却没有什么变化,这也是总统有权无责的表现。
三、结语
从政治心理角度看,议会权力对行政权限制过大是国会议员们出于防止行政专制的考虑所致。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经历中,行政权始终处于独大的地位,辛亥革命后中国从专制一跃变为共和,专制时期的官僚政治能否被划清依然是议员们首要防范的对象,加上袁世凯当权后解散国会,采取种种集权措施,因此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制宪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限制行政权作为防止制度专制的重心,并以此作为国会的责任。如参议院议员田桐曾在宪法会议上对制度专制问题做过发言,他指出“宪法第一之要义即在防止专制之发生,所谓专制盖有两种:一为个人之专制,一为制度上之专制……制度上之专制则立法者应负其责,宪法所固有之作用也。使一权独张而他权因之失其独立之作用,其为专制乃在制度彰彰明矣。吾国数千年来承专制之余习,所谓国家机关仅有行政一部而宪法之所认为国家之机关者则有三焉,所谓行政立法司法是也。以行政部而历史上之位置为国家唯一之机而行政权之全部者,与其今日在宪法上之位置为国家机关之一而行使政权之一部者,两相比较则虽定宪之际举行政部应有之权盖尽量以予,而论者犹以过于缩小为疑,此诚习焉不察之恒情而无足怪者。惟定宪之大业非浅识所能舆。则愿吾国人共了此义而已。”[1](第11册P30-31)虽然国会议员们在制度上避免了行政专制,但殊不知其客观上却导致了议会独大的权力分布格局。事实上议会独大的特征也是政府首脑和内阁频繁更换的原因之一,在“1916-1928年,政府首脑换了9次,平均存在时间不到16个月,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1个月,最短两天,平均存留时间3-5个月”[5](P2)。当时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议会独大的问题,如李三元曾在《宪法问题与中国》一文中指出“西方代议制的趋势之一即‘由代议民主政治趋于直接投票制度民治政治也’。新德意志共和国,为预防议会专制,及举全民政治之实,持于宪法中明文规定人民直接投票制度。德奥普三国而外,尚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亦采用国民直接投票制度,以巩固大总统之地位,而防制议员之专横。”[2](P73-74)虽然其提出了用直接投票来防止议会专制,但由于在当时的中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议会专制这一问题也并没有在体制设计上得到解决。
在制宪议员们眼中总统不仅是一国家机关,还是国家稳定统一的象征。有权无责使总统能够超然物外、不负责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虽然这有悖于责任内阁制精神,但总统地位的稳定能起到统系人心的作用,这也反映了身处军阀混战的议员们对国家稳定统一的追求。当时北洋军阀的军事实力虽然最强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袁世凯在世时凭借其政治手腕暂时维系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团结,但由于 “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6](P966)。这种基于私人情感形成的忠诚在袁世凯一死即爆发了忠诚危机,加上利害关系的权衡使得北洋军阀日益开始分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最终演化成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常年的军阀混战使议会政治不幸沦为军阀政治的点缀,在这种背景下议员们迫切希望有一稳定强有力的总统来调解争端,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在设置副总统一职的理由中,我们也能发现议员们对国家统一稳定的追求。《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即明确指出“副总统专为总统出缺时,继任而设。代理职务为第二义。……我国历来专制,骤易民主,元首地位极为重要。若总统出缺,以国务院代理,不足系全国人心,此其一;我国政治迄今未入正轨,政客扰攘于内,藩镇觊觎于外。一遇总统出缺,野心家利用时机,酿成非常变乱,亦意中事。何若预储副总统以消弭反侧于无形,此其二;反征我国事实,民国五年,项城死亡,使非黄陂继任,何能奠安时局。六年,黄陂去位,使非河间代理,更足惹起争端。揆之我国国情,副总统必须设置,可断言矣。”[7](P515)
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暴力逼走大总统黎元洪后,在三天之内快速地完成了宪法草案的二读与三读程序,并在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一职之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的颁布依靠于以曹锟为首的军事力量的推动,随着曹锟1924年的下台,这部在形式只存在了一年多的宪法也淡出人们的视野。但1923年宪法从起草到公布历经了十一年之久,其制定的过程也是人们在北洋军阀军事力量的统治下为孜孜不断追求宪政的过程。而且从内容上看,在国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也做了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不失为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
[1]李贵连主编.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M].北京:线装书局,2007.
[2]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C].程凤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萧延中,杨云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夏新华主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A Crosswise Study of the State Power Features of the 1923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IAN Xiu-quan XIAO Jing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Based on the documents of formulating the constitution since the 1912,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power features and concludes that this constitution embodies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the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But these three powers are not balanced in that the Parliament has the supreme power while the President is powerless.In spite of this problem, it still shows the restraint imposed on the executive power.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olute power of the Parliament; presidential lack of power
DF2
A
1005-7110(2012)02-0033-06
2012-02-02
张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相目“中华法制文明的传承与创新”(10JZD0028)的阶段性成果。
卞修全(1969-),男,安徽六安人,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肖婧(1989-),女,江西吉安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侯德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