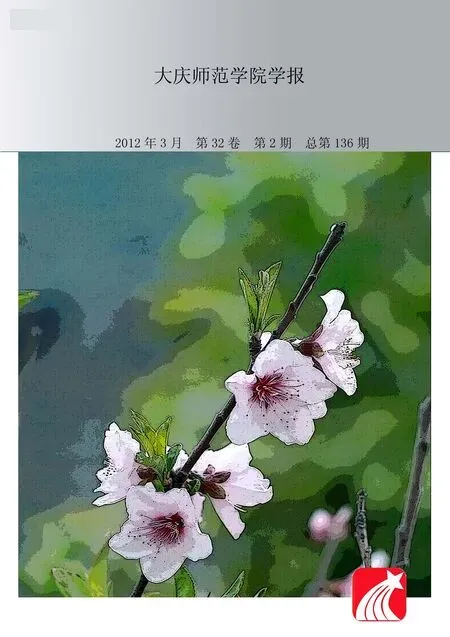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逸周书·周祝解》与“言”体文类
赵奉蓉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逸周书·周祝解》在中国文体学上是很重要的篇章,《周祝解》是早期的“言”体之作,随着其后作品的不断增加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个“言”体文类。饶龙隼在《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中指出:“‘言’,是《庄子》运用的一种特殊文学体式。”“言为一体,这个新意发明,可得到‘三言’论的支持。庄周及其后学反复申论自己的言语方式,表现出明确的创立体式的意图。”[1]他所说的“言”体,是以《庄子》的言说方式为对象。本文所说的言体,主要是以群体作品为基点,从文章体式、文学风貌等方面来加以界定。对于文体的归类,应采取“因文立体”的原则,“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2]
一“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3]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春秋至战国时代,各种文体逐渐以独特的形态登台亮相。在众多的文体中,言体作品作为当时一种新兴的文体,形成了自己的文类系统。《老子》确立了言体的原型,《逸周书·周祝解》继踵其后,与《逸周书·周祝解》大体相类似的言体作品有《文子·符言》,《商君书·壹言》,《管子》的《枢言》、《霸言》。另外《管子》一书的《王言》、《正言》已亡佚,但根据《枢言》、《霸言》可以推断,《王言》、《正言》也当属于言体作品。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言体作品的文类群,有着共同的文体特征,从而确立了“言”体这一新兴文体的地位,可以与说类、论类作品比肩而立,只是从前被忽略而已。历代论及文体的相关著作林立,但在众多的文体分类中,对于“言”这一文体均没有提及。所以,要在众多的文体论述之外独列一“言”体,必须要对“言”体的形式及文体特征有明确的界定,而且还要有自己的群体作品作为支撑。本文关于“言”类文体特征的界定也是在对相关作品共同特征的分析中得出的,“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4]。言体作品是有自己的文体特征的,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是独言体,不是对话体。从文字的字形及字源上来看,“言的本义就是讼词。讼词的特点是原告和被告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5]既然言的本义是原告和被告各自进行陈述,当然指的是个人言说,是独言。《礼记·杂记》记载:“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郑玄注曰:“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可见,“语”是两者或更多人的对话,而“言”则是单个人说的话。《论语》、《孟子》中的部分作品皆属于语类作品。语类作品通过问答者双方的对话阐明观点,这样,理论的阐发是由二者共同完成的,有一个相互依存或依次推进的关系,如《论语·八佾》中的: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通过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共同完成了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阐释,同时也使子夏对孔子的用诗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
与此不同的是,“言”体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只有一个人在阐述观点。所阐述的道理不是在对语中共同实现,而是在一人独言的过程中完成;在此过程中,不需要借助别人的提问来激发观点,是在独言自说中娓娓道来。在众多的言体文类中,独言内容的论说,有的是作者直接出面,如《管子·枢言》、《霸言》等皆是用“管子曰”来统领全篇;有的是作者不直接出面,《逸周书·周祝解》一开始就以一个“曰”字引起论述,《商君书·壹言》开篇即是论说的内容,未见叙述者的影子;还有的是假托他人,如《文子·符言》通篇皆是文子一人的言说,但是这个言说是假托老子的名义在进行。
第二,是直言体,不是辩难体。许慎《说文解字》曰:“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言,指直接言说,而不进行辩难。《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四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直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辩论之不已也。”[6]直言还是论难,是言体和语类、论类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语类、论类作品有时通过问答双方的辩难来阐述论说的观点,如《孟子·告子上》中,告子以杞柳、水作比,说明人性无所谓的善与恶,而孟子则是顺着告子的比喻反驳告子,最后通过一番辩难性的论说驳斥告子的观点,从而提出自己的“性善论”。
前面提到的那些言体作品,无一例外不是直言,是作者独自阐述所持的观点,而不是反驳别人,不是进行辩难。《老子》是言体作品的奠基之作,通篇五千言都是老子对自己的理念、主张进行阐述,没有预设论辩对象,也不是具体针对某种观点进行反驳。《老子》一书富有批判精神,但却是独言直言。《逸周书·周祝解》同样全篇都是直言,无一例外,见不到任何论辩的痕迹,如下面一段: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
这是具体说明自矜其美必有后患的道理,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理念进行阐述,没有反驳,没有辩难,采用的是直接论述的方式。春秋战国时期的言体文类,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因此,尽管对于许多道理揭示得透彻深刻,不乏犀利的言词,却见不到论辩的锋芒,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第三,是论说体,不是叙事体。先秦时期,叙事体与论说体的界限还不明显,作品中时常出现叙事性内容与论说事理的杂糅,这一特征在记言为主的《尚书》、《国语》以及记事为主的《左传》中都有所体现,《尚书》、《国语》中虽然主要是记载人物的言论,但是在其中还有一定的叙事性的语言来说明言说的背景或不同人物的形态。《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历史画卷,展示出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是作品的主体,但是历史画卷的展示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也包括人物的论说在内,有的地方还出现大段议论。这种文体的模糊现象在不同作品中程度不同。诸子散文发展的早期,如《论语》、《孟子》中也有一定的叙事成分。至于《韩非子》的《说林》、《储说》,则主要是历史传说的汇编,议论说理所占篇幅很小。言体文类则不同,它的议论在作品中起主导作用,叙事则明显处于附属地位。言体文类有的篇章纯是说理,如《管子》的《枢言》、《霸言》,《商君书·壹言》。有的虽然在议论中有叙事成分,如《老子》中某些篇章、《文子·符言》、《逸周书·周祝解》,但是,议论对叙事的统辖是强有力的,议论是作品的灵魂。所出现的叙事都极其简单,见不到连续的情节、完整的场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是采用精练的语言进行概括性显示,而不去精雕细刻,工笔描绘。如《逸周书·周祝解》下面一段文字:
故木之伐也而木为斧,贼难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术,谁昭谁瞑?二虎同穴,谁死谁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获,人之智也而陷于诈。叶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离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俨矢将至,不可以无盾。
这段文字出现的物类事象很密集,但对每类事物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进行细致的描绘。这些物类事象均服务于议论,是进行议论的依据,它们依次昭示的是防内、防外、防巧、防勇的道理。《文子·符言》也有许多类似段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言体文类的出现使议论文和叙事文的界限更加明显。
二言体作品的原型生成于春秋时期,这种文体在战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言体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种文本形态:
第一,格言警句型。此类言体作品浓缩地保留了语录体的痕迹,《老子》首开其传统,《逸周书·周祝解》和《文子·符言》则继踵其后。《老子》只有五千字而阐述了有关自然、社会、人生的众多哲理,因此言简意赅,其中有很多哲理深邃的格言。后来的言体作品继承这一传统,如《逸周书·周祝解》中的“叶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拔其本”、“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指出事物因为本身的美好而招致灾祸,因此必须要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这些都是言简意奥的人生哲理,通过韵律和谐的言说来表明垂戒之义,“古人垂戒之文不一体,此篇似箴似铭,尤为奇绝。”[7]《文子·符言》中的“羽翼美者伤其骸骨,枝叶茂者害其根”,“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多藏之家其后必殃”,则是表明“大利反为害”的观点。
此类言体作品的段落有长有短,长者已经接近常见的议论体。《逸周书·周祝解》每句的字数从二言到十言不等,据统计,比较整齐的句式有四言、七言、八言连用,还有“三——三——七”式。这样,句式的变化导致不同段落的篇幅长短不同,形成错落之美。《逸周书·周祝解》中的格言警句比较多,但长篇大论性质的段落则基本没有出现,文章主要运用由此及彼的类推方式,由自然现象推及人类事理,通过极为平常简单的事例陈列,推演出寓意深刻的道理。如“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推及到人间的灾难祸福。《文子·符言》与《逸周书·周祝解》相比,大量简短的格言警句存在的同时,在篇幅上,某些段落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集中论说某一问题,对于问题的阐发变得详尽而繁富。文中言及祸福之理的一段,洋洋洒洒几百字,已非《逸周书·周祝解》的简单言说可比,而且在言说之后还通过征用《老子》中的言语来对言说的主旨做总结。在具体的论说过程中有一定的思辨性,文中反复申言“大利为害”的道理,不仅仅是从一个方面做出说明,而是通过论说形神关系、利弊关系等,使问题阐述得更加透彻。
格言警句型的言体作品,由《老子》首开其端。老子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并且和孔子有过交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一书是他辞官退隐之前所作,是晚年所撰写。依此推断,它的成书应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关于文子其人,《汉书·艺文志》列《文子》九篇,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现代学者进一步考证,文子是楚平王时人[8],楚平王是公元前528—前516年在位,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与班固的说法相合。
关于《逸周书·周祝解》的写作时间,清人潘振《周书解义》称:“《王佩》、《殷祝》、《周祝》,疑景王时做。”[9]潘振之所以作出这种推断,因为上述三篇作品编排在《太子晋解》之后。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死于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10]1033,周景王(前544—前520年在位)是继周灵王为君,距灵王时代最近,因此,潘振推测太子晋与师旷见面的传说是在周景王时期被记录下来,《殷祝解》、《周祝解》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周景王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处于春秋后期,从实际情况考察,《周祝解》应该在这个时期写定。《战国策·秦策三》范睢引《诗》:“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引《诗》当是引《书》之误,清人丁宗洛将这两句话的出处归于《周祝解》[10]1173,从语言风格上判断,这两句话和《周祝解》的行文确实极其相似。除此之外,《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叙述蔡泽所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所用语言亦与《周祝解》相似。范睢、蔡泽是秦昭王时期人,范睢相秦是在昭王四十一年(前266),蔡泽入秦是在昭王五十年(前257)。这说明,《逸周书》包括《周祝解》在内的许多篇目,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被许多人引用。这样看来,《周祝解》写于春秋后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人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一书就认为《周祝解》的写作时间应在春秋晚期的襄、昭公时期[11]。
春秋后期是诸子学派初创阶段,儒道两家的创始人老子、孔子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这两位宗师都是哲人,他们的著作也富有哲理性,《老子》一书尤为明显。哲理往往用格言警句加以表达,从而导致言体文类的出现。言体文类的产生,老子开其先河,奠定这类作品的基础。《逸周书·周祝解》基本是沿袭《老子》的路数,没有大的突破。《文子·符言》则是首表言体之名,成为言体文类的一种范型,即格言警句型。对于格言警句型言体作品,它的产生和那个时代的风气密不可分。春秋后期是产生哲人的时代,而以哲理名言形态出现的言体文类,也就同步应运而生。
第二,专题议论型。此种类型的言体作品是比较标准的专题论文,《商君书·壹言》、《管子·枢言》、《管子·霸言》属于此类。这种专题议论型的言体作品,一方面是对前期格言警句型言体作品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超越,构成连续发展的链条。
专题议论型言体作品对前期格言警句型所作的继承,有一种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沿用《文子·符言》的标目方式,明确出示作品的体类归属,作品题目都缀以“言”字,是言体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文子·符言》文本形态的范型意义;还有一种是不易觉察、容易被人忽略的,那是论述的专门性。如《老子》八十一章,每章都专门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各章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只是没有用醒目的标题加以提示。有鉴于此,西汉河上公注《老子》,每章都拟定一个相应的标题,开篇依次是《体道》、《养身》、《安民》、《无源》、《虚用》等,共八十一个题目。河上公所作的概括未必全都正确,但他的感觉是对的,即《老子》各章均属专论,集中阐述某一方面的道理。《逸周书·周祝解》可以划分出许多段落,各段也都有专门性的论题,只是加以归纳有一定的难度。如,作品的前半部分集中论述闻道的重要性,然后依次阐明闻道与趋时的关系,道与势的关系,以道治身要防内防外、防巧防勇,以道治国要防智防谋。这样一来,作品就带有明显的专论性质,围绕闻道从各个方面进行阐发。《老子》和《逸周书》的分章专论,都没有用题目加以标示,再加上文字深奥,使得这种专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潜藏状态,具有隐蔽性。《文子·符言》和后来出现的专题言体论文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整篇而论,篇名定为《符言》,已经确定全篇论述的中心。宋人杜道坚《文子缵义》在解题时写道:
符以示信,言以达诚者也。世有谓符命符玺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达诚,此感彼应,故曰符。[12]
杜道坚的解释是合乎文本实际的。综观《文子·符言》全文,基本都是围绕着符验、征信、彼此感应立论,符是言说对象,和《管子·霸言》 言霸业、《枢言》论枢纽相似,是专题论文框架。再从具体章目来看,每章都专门论述一个问题,中心非常明确。每章没有标题,但有的章目在论述过程中或论述之后引述《老子》之语,起到点题作用。就具体章目而言,《文子·符言》与专论型的言体作品也已经很接近。
总之,《老子》、《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已经为专题议论型言体作品的出现奠定了文本基础,也预设了所应遵循的文体规范。《老子》、《逸周书·周祝解》以及《文子·符言》全篇及具体章节有着自己的固有主题,而且在主题的统领下也有较为明晰的论说,但是在具体的论说当中,由于篇幅及句式的原因,全篇未能形成严密的结构,各章节之间的联系还比较松散,甚至若断若续。《逸周书·周祝解》多并列陈说,一条条祸福论顺次罗列而下,其间缺少强有力的逻辑关系。《文子·符言》虽然某些段落在议论方式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体看来,其论说还是缺少严密的结构,完整的体系。
《商君书·壹言》、《管子·枢言》、《管子·霸言》皆是以意名篇,紧扣主题阐明事理,在《老子》、《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已经是标准的专题论文,而且在具体的论说过程当中,三者采用了不同的论说方式,体现出言体作品的多姿多彩。《商君书·壹言》围绕“专一于农战”这个主题论说,首先开宗明义,篇首点题:“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这既是对标题的回应,也是对作品主旨的揭示,下面的论说皆是围绕主旨,从治国大政方面进一步论说统一民务的缘由及其重要性,在每段的最后用总结性的字句呼应主旨,进一步强化主题。《管子·枢言》依次从七个方面来论说治国纲要,《管子·霸言》则是从五个方面来说明成就霸王之业的途径。在主题的统领下,作品依次展开述说,这是两篇作品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具体的论说方法上,二者又有着不同点,寓变化于其中。《枢言》是言国之枢纽,是治国大政,因此在文中反复出现“先王”这一词,重复频率极高,不仅每段都会出现,而且在一段中最多连续八次使用,形成气势强烈的排比句式,借用先王的权威来立论,增强论证力度,提高说服力。《霸言》是言霸业,开篇首先对成就霸王的情形有一番说明,解决“何为霸”的问题,于开篇即抓住读者的兴奋点,以一番形神俱备的描绘引起对霸王之业的向往。作品每段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成就霸王之业的途径:时机、德义、权谋、守备、地形。围绕主旨,层层剖析,于每段开头点明本段的中心观点,然后具体展开论说。由于言说主题的不同,《管子》运用不同的方式来展开议论,但都能紧扣主题,取得预想的论说效果。
综上所述,专题型言体作品都是写定于战国时期。这类言体作品虽然在文本形态上有异于《老子》、《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不是以格言警句的语式出现,但都遵循早期言体作品的基本规则:是作者独言,而不是对话体;是作者直言,没有进行辩论;是比较纯粹的议论文,而没有大量运用叙事类的历史传说。
三谢廷授《续文章缘起序》中说:“文有万变,有万体,变为常极,体为变极。变不极则体亦不工。工者,起之归而绝之会也。”[13]变化是文体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一定文体的成熟也是在相关作品的不断创新中形成的,而作品的创新最后又会导致文体的演变。
严格意义的言体作品集中存在的时间是有限性的,主要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这个历史阶段。从战国后期开始,言体文类已经出现泛化和随意化的倾向。战国后期的《韩非子·难言》、《吕氏春秋》中的《听言》、《重言》、《应言》,论述的是言之难、言之倾听、言之重要、言之应对,都以论言为中心,言已不再是作品的体类名称,而是作品内容的标示。这些作品多数带有论辩性,并且大量引用历史故事,有较多的叙事成分,有的还穿插对话,和言体文类已经相去甚远。
西汉时期,言体作品泛化,后来逐渐消融在政论文中。只有《淮南子·诠言训》基本保持了言体文类的特征。《淮南子·诠言训》中有许多文字与《文子·符言》相同,全篇皆是作者一人围绕主旨展开的的论说。《淮南子·要略》载阐明《诠言训》要义时说:“《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言,作为文体概念加以运用;诠,则是作品的主旨。这种标目方式与先秦言体文类一脉相承。至于西汉早期贾山的《至言》,多引秦朝灭亡的故事,语带锋芒,很少有言体文类的属性。《说苑·杂言》已经不像《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那样纯粹说理,而是有历史故事穿插其间,或者在论说中用一定的事例来补充说明,使得叙述更加生动、形象,这个特点在《淮南子·诠言训》中就已经出现,但多是在论说中作为典故来使用,并未对故事展开完整的描述,并未破坏说理议论的总体构架。
虽然战国诸子时代,文体的界限还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文体区分。言体作品中的《管子·枢言》、《霸言》属于典型的议论型言体作品,但是刘向在编纂《管子》一书时,将全书划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解五类,其中属于内言的《大匡》、《中匡》、《小匡》是典型的叙事文,这五类作品的划分本身就说明刘向的文体观念是模糊的,他主要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划分类别,而不是着眼于文体特征。由此而来,《说苑·杂言》中的议论说理或者与记事相互掺杂,或者直接通过大量相同主题故事的罗列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样在论述方式上就出现叙事过多,或者叙事掺杂议论的情况,从而使得言体以论为主的文体特征遭到破坏。在《说苑·杂言》中,借故事人物的言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有一种方式是由故事直接引出所要阐明的道理。因此,虽然在总的语言形式上还是一个人在说,但是在文中出现了几个言说者的角色:作者、故事中的问者和答者、故事中的独言者,从而使得言说主体的数量就变得复杂起来。扬雄的《法言》走的更远,直接脱离了一人言说的方式,采用对语,与语类作品在形式上取得了一致。这样,言体作品的另一个文体特征——独言也遭到了颠复。
任何作品的出现及消亡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言体作品在战国时期已经完成议论文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使命,这是它消融的历史必然性。汉代以“言”标目的作品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使言体作品进一步泛化,导致言体的衰微及向论体的靠拢。《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论体和阐发哲理的言体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论说’之文,或以批评对辩的方式辨别是非善恶,或以考证及说喻倡导的方式说明是非善恶,其效应在使人信从作者主观的见解。”[14]从广义上讲,言体作品开始就属于论说文的范畴,是它的一个分支,只是文体形态上与其他类别的论说文有差异而已。在论说文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各种文体形态的聚散分合经常出现,因此,言体融合于论体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129.
[2]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5.
[3]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60.
[4] 徐师曾.文体明辨[M].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3:13.
[5] 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0.
[6] 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29.
[7] 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147.
[8] 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1-13.
[9] 潘振.周书解义[M].清嘉庆刻本,卷九:11.
[10]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26.
[12] 杜道坚.文子缵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9.
[13] 陈懋仁.续文章缘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14] 蒋伯潛.文体论篡要[M].重庆:中正书局,1942:90.
——探析文类与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