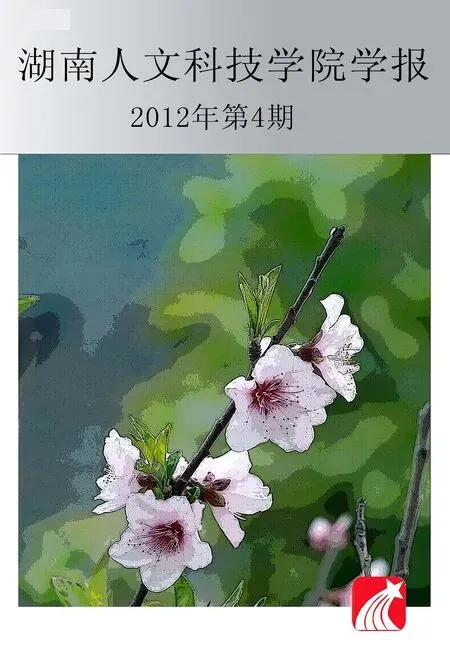两个说不尽的经典文本
——对《阿Q正传》与《边城》的比较诠释
李夫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娄底 417000)
1921年12月4日鲁迅以“巴人”的署名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阿Q正传》,而沈从文从1934年1月1日起在《国闻周报》第11卷的第1、2、4、10、16等各期发表《边城》,前者迄今已90年,后者也已77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诠释这两个经典文本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尽管如此,这两个文本的极为丰富的蕴涵迄今仍无法穷尽,真是说不尽的《阿Q正传》,说不尽的《边城》!因此,我们欲在前人评说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当然,拙文也将成为历史的“中间物”。
鲁迅与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探讨国民人性,对国人灵魂进行终极关怀的两位大师。由于二者文化的秉赋不同,所以对“人”关注的视角也不同。鲁迅从“立人”出发,通过阿Q这一艺术典型,试图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所关注的是国人灵魂的负面。自称“人性的治疗者”的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通过翠翠等艺术典型来表现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试图为湘西边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为民族魂的重铸找到一条理想的通道,他所关注的是民族魂的正面。由此可见,鲁迅与沈从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国民人性,二者互补整合,为重铸民族魂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文化—原型”批评视角考察,阿Q生活的“未庄”不仅是一个“吃人”社会制度的象征,而且是“地狱”的原型意象,而翠翠生活的“湘西”,不仅是一种理想社会体制的象征,而且是“桃源”的原型意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存在于地球人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中;而翠翠,不仅属于“湘西”,属于中国,作为“桃园”中的精神象征,则又属于全人类,具有“女神”的原型特征。
一
鲁迅的生命底蕴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入世精神的元素,同时融入了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叛逆因子。而沈从文则是一个具有“原生态”意味的楚文化的产儿,他称自己身上涌流的是“楚人的血液”,但同时也受到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学的浸染熏陶。因此,入世叛逆的鲁迅与重情重美的沈从文,虽都有启蒙思想,关注“人”,但其视角是不同的。鲁迅是从“立人”出发开始其国民性探索的,而沈从文则是从追求理想的人生形式和“爱”出发开始其国民人性探索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反帝反封建压迫屡遭失败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民族的思想素质等方面寻找原因。在这种时代影响下,鲁迅积极参与了振兴中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与探索。1902年鲁迅留日期间曾同好友许寿裳热烈讨论过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后来之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2]他认为有了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状态。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3]在这里,鲁迅提出了“立人”的思想,这种把“沙聚之邦”改造成“人国”的理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国人灵魂、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为了“立人”必须做好两件事:必须批判封建文化对“个人”的毒害;必须剔除国人灵魂中的痼疾。我们认为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针对前者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文化的要害在于“吃人”,并发出“救救孩子!”的人道主义呐喊。而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是针对后者的,即挖掘出国人灵魂中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1902年鲁迅与许寿裳所探讨的“国民性”主要是指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所谓改造国民性,就是全方位地批判我们民族灵魂中的劣根性,而这正是从“立人”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的。
在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湘西文化环境中,保留着较多的“活化石”般的远古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意识,它与湘西少数民族那种充满柔性情感和善于幻想的楚人气质结合起来,与湘西人爱美恋乡、悲天悯人、包容一切的博大精神结合起来,使他们悲悯的爱心遍及草木,从而孕育了湘西人“爱有生的一切”的强烈生命意识和博爱美德。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就是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爱有生的一切”的人道思想,就是以博爱和人道主义为基调的。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个世界上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沈从文毕生奋斗不息,将生命投注于事业,根源全在一个“爱”字。
然而现实却与他的追求相悖。沈从文在青少年时代便从湘西一带看到了太多的“人头如山,血流成河”[4]66的残酷与罪恶。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凤凰城的革命党人田应全等积极响应,但由于举事失败,几千人被屠杀:“一批血淋淋的人头垛在衙门前的平地上、衙门前口的鹿角上、辕门上,从城外缴获,用新竹做成的云梯上,也是挂着许多人头,极不甘心似的朝人瞪着眼,人头中间,夹着一大串被割下的耳朵,看的人都不大作声,脸上露出各式各样极不自然的古怪表情。”[4]58沈从文参加当地的土著部队后,又多次看到杀人:“关于杀人的记录日有所增……民三左右时一个姓黄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二千,民六黔系司令王晓珊在那里杀了三千左右,现在轮到我们的部队做这种事,前后不过杀死一千人罢了!”[5]然而,1933年当沈从文功成名就重返故乡时,看到的又是另一番令人失望与伤感的情形,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依稀看见被杀的共产党人的血迹;另一方面,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随处可见,繁重的捐税正以各种名目推行,残杀人们肉体和灵魂的鸦片明禁暗纵。这两方面的情况在腐蚀着乡村的灵魂,民风日下,传统美德丧失。
沈从文浑身涌流着“楚人血液”,楚文化根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浸染,使他把楚文化的重情重美、“爱有生的一切”的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五四运动张扬的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精神融合起来,从启蒙主义的视角历时性地观照湘西历史的诗意人生和令人伤感的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沦丧,总结出他今后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创作理念,并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性的治疗者”,用牧歌情调和诗人与画家的笔,画出了湘西理想生活的图画,其中充盈着浪漫情怀和人情美、人性美,画出了湘西“桃源”式的图景。
二
《阿Q正传》发掘出国人乃至地球人的“痼疾”——阿Q的精神胜利法,《边城》营造出以翠翠为象征的优美、健康的理想生活形式,是两位大师对国人乃至地球人灵魂反、正两面终极关怀之结晶。又因为阿Q与翠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原型与地球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遥相呼应,承继、凝聚着人类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和情感内容,从而有强旺的生命力。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指出:“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确已有了好几年。”他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任教时,有一天忽然从西门隔壁墙的缺口上跑过一个人来,原来是阿桂,这是一个流浪汉,因生活无着落作了贼。辛亥革命后活跃起来,在街上大叫:“我们的时候到了!到了明天,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另一个是没落地主阿董,极端保守而仇视劳动人民。他反对女学生穿黑袜子,卖鱼的从门前过,他把木盆掀翻,把鱼晒死。鲁迅所说的“阿Q的影像”据说就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这两个原型的。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前人已有各种探讨与说法,如孙中田引用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压抑”与“反压抑”的心理学理论,阐释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根据:“阿Q的反压抑或者成为反抗的心理,是为解读者所公认的。但是他的反压抑,时时、处处是在压抑的制约下进行的。因此,在永远的历史文化积淀中,难以寻找到正常的通道,人格与变态,在这个过程中因之而被扭曲变形。于是,‘冲突的形态’在扭曲中便形成一种防御机制,一种自然力量。‘反抗(反压抑)——防御’这时成为他的心理内核,所以精神胜利法才应运而生。”[6]在我们看来,仅仅把精神胜利法看成是个体心理压抑与反压抑的过程,还远远不够,应该把精神胜利法置于地球人阔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去观照解读。从“文化—原型”批评的角度而论,精神胜利法不仅是时代的、民族的、超民族超时代的,而且具有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特征,是人类共存的一种精神——心理现象。以前的论者把精神胜利法看成是用虚幻的胜利安慰个人失败情绪,是精神鸦片,是劣根性,这不无道理,但这仅是问题的一面。精神胜利法还有正面的功能,它至少是一种“平衡剂”——能调节失败者的心理。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柄双刃剑。它既是劣根性(负面),又是心理平衡剂和精神安慰剂(正面)[7]。
哀婉牧歌情调的抒情诗人沈从文,从探索国民人性出发,以湘西记忆和对现实社会生活感悟分析的结果为素材,用诗人与画家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浪漫的、理想社会生活的图画,用以与丑陋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照,而清纯美丽的自然之子翠翠就是这幅幽美图画的精神象征和灵魂。
沈从文在青岛教书时便开始了《边城》的写作,写作灵感虽然始于在青岛海滨所看到的一位白衣少妇,但翠翠真正的原型还是他1933年回故乡时在湘西看到的小翠:“想起刚刚起首的《边城》,主人公翠翠似乎和沪溪城绒线店里新一代的小翠融成一体。这将注于自己的笔端,喊出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苦痛,并寄待于未来。”[4]326《边城》中这样写翠翠:“翠翠在风里雨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澄明如水晶。自然既然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把亮亮的眼睛瞅着那个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便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她像山中的翠竹一样柔美,象澄碧的河水一般纯洁,她是自然之子,是“桃源”(下节展开讨论)这一理想世界的精神象征,是“桃源”之魂,有了翠翠,理想的桃源世界也就构建起来、活起来了。《边城》中的桃源世界正如前边引文所描写的那样,它是借助水建构起来的,在人类学的视界里,女性是水的推原性象征物,水与女神崇拜不可分,人类很早就认识到水是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根据原始人类的类比思维,大地上一切滋生生命的东西都与女神有关。于是,水的意象就赋予了女性意义。于是翠翠在《边城》中是水与女神的象征,是原型意象。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女神都是创世、孕育万物之母神,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最伟大的一位女神:“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8]作为创造人类、修补天地残破,使世界获得重生的大神女娲,她是诸神之母。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神话中,阿斯塔尔忒是赋予大地上的人类和一切动物以生命的女神,即万物之母。在埃及神话里,爱巴斯是伟大的母亲和富饶的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不仅司生的过程,还司死的时辰。总之,这一种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是缘于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积淀在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复活。因此我们认为,《边城》中的翠翠,既在湘西的现实社会中有原型,她就生活在沪溪城的某个绒线店里,又在人类远古的种族集体无意识中有对应的原型意象,她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地母。《边城》既写出了作家“寄待于未来”的理想人生形式,营造了一个桃源世界的图景,同时“也喊出了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苦痛”,因此作为体现着理想人生形式和人性美的翠翠,其命运也打上了挥之不去的忧伤和无奈的烙印,《边城》凄惨的收尾,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
阿Q生活的“未庄”是一个扭曲与扼杀人性的病态社会文化环境,是专制社会体制的缩影与象征,它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地狱”意象相对应。而翠翠生活的“湘西”是一个有利于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理想社会体制的写照与象征,它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世外桃源”这一原型遥相呼应。
阿Q生活的未庄是一个典型的病态社会文化环境,在这里存在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赵太爷是未庄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而地保是帮凶,阿Q等是被压迫者,小尼姑是地位最低的未庄居民。统治未庄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伦理道德,赵太爷是其执行者与维护者。阿Q由于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毒害,坚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要与吴妈“困觉”,怕断了后;他又极端瞧不起女人,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他与吴妈谈恋爱本是门当户对,却被地保罚得仅剩那条万万不能再脱的破裤子(上身已剥光了),而且被开除了未庄的庄籍。在未庄这个病态社会文化环境内,阿Q肉体受残害,灵魂被扭曲,可见未庄是精神胜利法的摇篮,是“吃人”的社会体制的缩影与象征。
在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中,都对宇宙人生进行立体的三分法:天堂、人间、地狱,由于种族和文化记忆的世代传承,天堂、人间、地狱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把未庄置于“文化—原型”批评的广阔视野来观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它是专制体制的象征与原型,而上溯到原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去探寻,它又与“地狱”这一原型意识遥相呼应。未庄即人间地狱,赵太爷就是地狱中的阎王爷,而阿Q就是被押到地狱中的冤鬼[7]。
翠翠生活的“湘西”,是一个有利于个体的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顺乎自然,有利于培养“优美、健康”的理想人生形式。翠翠生长的自然环境具有原生态特征,从未受过任何污染、任何破坏。这里“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塔,塔下住了户单独人家”,“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两岸青山滴翠,碧水如澄,正是如此幽美的天然环境养育了清纯美丽的翠翠,她成了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达到天人合一、美妙结合的境界。这里民风古朴,保持着人类的原始美德,坐摆渡过河的人每每抓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船的老船夫必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里:“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但出力不受酬不好意思,便把酬钱买来茶叶和烟叶,供渡船人享用。老船夫进城割肉,卖肉的便割一块好的扔过去,并不收钱。正是如此淳朴的民风,培养了这里人们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从神话原型的视角来看《边城》,“湘西”确实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世外桃源”。这个“桃源”在实景层面是借助于水构建起来的,而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如上所述的古朴民风,尤其是通过翠翠和老船夫以及那里的和谐质朴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来,翠翠是桃源世界的主要居民和精神象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自称“左派”“永远正确”的文人,给《边城》戴上一顶顶“反动”、抹杀阶级斗争、宣传资产阶级抽象人性和人类之爱的“帽子”,如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说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一直从事“反动”活动,企图把沈从文及其《边城》等作品一棍子打死,扫地出门。事实上,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构建的世外桃源的图画是与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苦痛”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想人生形式,这是一幅浪漫的超现实的图画,作家借这幅图画“寄待于未来”,就是说,寄托他对历史记忆中的诗意湘西和未来“湘西”的美好憧憬。因为现实中的湘西已失掉了昔日的风采与诗意,变得黑暗腐败,专制残暴,在那里不但人们的肉体被戕害,而且灵魂也被扭曲、毒化。
四
《阿Q正传》和《边城》之所以百读不厌,每次细读心灵都为之震撼,并有新的领悟与发现,虽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诠释探索都无法穷尽,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鲁迅和沈从文两位大师分别对中国社会和“湘西”社会看得透,悟得深,并用哲学和诗人的语言,画家的笔,刻画出了中国社会与“湘西”社会的灵魂。
第二,如果说《诗经》是中华文化原生态的瑰宝,唐诗、《红楼梦》是中华文化闪耀夺目的明珠的话,那么鲁迅的《野草》和《阿Q正传》就是几千年几百年后这些“瑰宝”和“明珠”的还魂再现;如果说楚文化结出的第一颗硕大灿烂、光照千古的果实是屈原的《离骚》的话,那么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说是2 000多年后《离骚》的复活再生。因此我们说,《阿Q正传》和《边城》传承和凝聚着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审美情感。
第三,《阿Q正传》和《边城》既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原型,又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中有遥相呼应的原型意象。未庄、湘西、阿Q、翠翠这些艺术典型,凝聚着人类从远古以来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其情感内涵远比个人心理经验强烈、深刻得多,其美学力量可以直逼读者灵魂的最深处。正如荣格所指出的那样,读这样的作品“会突然感到酣畅淋漓,象欣喜若狂,象排山倒海的力量席卷向前。在这时刻,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人类,全人类的声音都在我们心中共鸣”[9]。在审美共鸣和心灵震撼后,很自然地会转入形而上的反思,“认识你自己!”“我是谁?”这样的永恒主题似乎能从《阿Q正传》和《边城》中找到答案,这就是这两部经典文本的感染力之所在,无法穷尽的秘密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4.
[2]许寿裳.回忆鲁迅[M]//黄侯兴.鲁迅:民族魂的象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4.
[3]王士菁.鲁迅早年五篇论文注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111,112.
[4]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沈从文.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8.
[6]孙中田.阿Q :多元基因的艺术结晶[J].文学评论,2000(6):110-118.
[7]李玉.从“人”出发 永无穷尽:重读《阿Q正传》[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5):82-85,112.
[8]袁珂.古神话选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
[9]F·费尔达姆. 荣格心理学导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