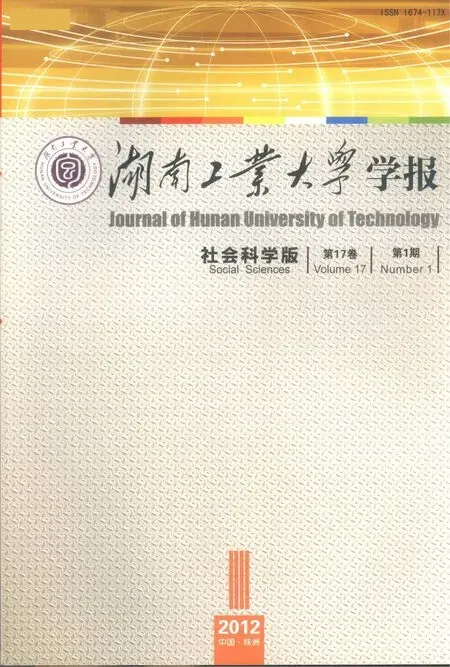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
陈润兰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主持人语】被视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标志性作家的韩少功先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出版了《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三部长篇作品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思想随笔,力图实现对自我的全方位超越,在探索现代性背景下如何变革小说诗学观念、创新小说文体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期韩少功研究专辑特邀五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转型之后的创作进行了阐释研究。《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与《从线性叙事到片断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文体探索》分别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韩少功小说叙述转向与禅宗思维的关系,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小说的叙事特点;《“八溪洞”人的合理生活与〈山南水北〉的叙事策略》与《在昆德拉与韩少功之间——兼与陈思和先生商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别从共时的角度讨论了韩少功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理论及求真文学观对其创作的影响;《<暗示>:不是说服,是聆听的开始》则剖析了韩少功的小说理念对当代阅读与批评产生的深刻影响。
庄禅智慧对韩少功后期小说的影响*
陈润兰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韩少功后期小说创作从中国庄禅哲学中获取了创旧图新、融会东西的灵感和智慧,庄禅哲学的相对主义促成了其小说观念的重新定位,禅宗的直觉思维特性改变了其小说思维模式,禅宗的神秘主义因素则为其小说表现手法注入了新质。
韩少功小说;庄禅智慧;相对主义;直觉思维;神秘主义
韩少功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表现出一种全方位的超越趋势。
与前期创作比较,韩少功后期小说具有明显的向内转的思维倾向:视点由外而内、目光由浅层向深层,重心由政治移向人性、文化。审美重心的偏移必然要求艺术表现的更新。由“问题小说”入门的韩少功面临着小说观念、小说审美思维以及小说艺术表现的巨大挑战,他在寻求蜕变,寻求突破。
钱穆先生谈到中国哲学的精神时,曾作过一番很有见地的中西比较:“西方人好言创造,而中国人则言保守。其实创造必求一成。使其有成,自当保守。……守旧即以开新,开新亦即以守旧……新旧之间,变中有化,化中有变……”[1]韩少功似乎是读过钱穆先生书的,从他的一些文艺随笔中可以看出某些精神影响的痕迹。国学热和寻根运动激活了韩少功的创造冲动与创造想象。他从中国古代的庄禅哲学智慧中获取了创旧图新、融化东西的灵感。
在考察中国新时期小说思维结构转型的缘由时,不少论者都执于一端,认定是由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和思维图式对中国作家的冲击和诱惑。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推断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完全正确,这种转型应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和思维图式冲击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图式潜在影响的共同结果。“西方现代主义的思维意识除了它对新时期小说的冲击,更主要还是诱发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思维系统的认同和重建”。[2]
韩少功多次表示过对庄禅哲学的欣赏,认为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直觉观念、相对主义、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维的财富。“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3]85那么,东方文化的优势具体指什么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举到了“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即“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是综合”,“是整体把握”;“还有思维的相对方法”,“所谓因是因非,有无齐观,物我一体”。至于审美形态方面,他认为就是朱光潜、闻一多、李泽厚等人提出的“东方偏重于主观情致说”。
人们通常把庄禅哲学指认为东方神秘主义文化。而“文学又是一个微妙的近于‘佛理’‘禅意’的‘不可说’的题目。文学的阅读,文学的欣赏,尤其是文学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精微、这样动人迷人、这样复杂、这样深邃,又是这样半自觉半不自觉,得其意几乎是忘其言。”[4]可见,禅与文学天生有不解之缘。其一,“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5]175“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同样指向生存状态与生命意识。其二,从认知方式看,无论是对宇宙还是对人生的认识,庄禅强调的最佳方式都是“开悟”,或者称“顿悟”、“直觉”。“顿悟”是“不用头脑作用来认识”,而是“用他自身之内各司看、听、觉、味的力量”来认识的,[5]179-180此所谓“直觉观念”。悟禅与思想、逻辑、概念、分析、抽象是绝缘的,“悟”的体验是一种整体的感知。所谓开悟就是认知主体从分析、抽象和概念的囚室中跳出来,在感觉的自由与解放状态中,把认知对象作为一个真实的整体来看待,这就是所谓“整体观念”。参禅悟理与学诗作诗在思维意象上都是通过情感体验达到对人生理解的真理性把握;其思维方法都采用直觉感悟、整体观照的方式。而“相对主义”是老庄哲学思想内核与佛教“缘起”论因缘和合、迁流变化观念的互渗。韩少功钟情于相对主义,不是从认识论角度而是从思维解放的角度立论的。
一 庄禅哲学的相对主义促成了韩少功小说观念的重新定位
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有一个相通之处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他们认为,万事万物不存在差别,所谓无是非、齐生死、等贵贱。尽管是片面夸大绝对运动而否定相对静止而导致最终抹煞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一种典型的怀疑主义思想。但是,其观察事物的那种因主观视角产生的模糊意向和怀疑主义气质却对韩少功的小说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其创作早期,韩少功奉行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与主题的明晰性是其主要追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韩少功的文学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有感于现代传媒对文学生存的挑战,他冷静而机智地分析了影视与文学各自的优劣短长,提出了文学必须扬长避短的战略思考。由于“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因此,“重心态甚于物像,重感悟甚于思想”就成为发展中的文学“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的合理选择。[3]69-73而写“心态”、写“感悟”,是必须强化主体性的,作为主体的作家或者作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人物,其内心感觉、情绪都是复杂而难以定性定量的。这样一来,庄禅哲学中的怀疑论色彩和相对主义、模糊性这种思维特性启迪了韩少功的小说观转向,预示了其后来的小说走向:由物象型向心态型、感悟型的转变。提出文学寻根的理论后,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道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3]108-109
这里所谓“困境”,就是一些人类无法摆脱又时刻希望求解的矛盾、悖论,例如肉身与灵魂、利己与利他、感性与理性、自由与规范、竞争与和谐等等。
二 禅宗的直觉思维特性改变了韩少功的小说思维模式
韩少功早期的问题小说表现了以人为主体审美对象,以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的运思趋向。“美善兼济”、“美从属善”的儒家审美标准派生出强化主题、伦理观照及人格理想的构思模式。中国自南北朝、唐宋乃至清代的文学家都强调“文以意为主”、“意在笔先”。不难看出,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已得到了历代作家的认同。这种模式使形象思维活动交织着清晰的逻辑推演,但同时也存在着游离感性形象的某种离心力,有导致形象思维弱化或表层化甚至失之概念与抽象的可能。韩少功早期小说就有这种思维模式的深深印记。他的创作中有一种情况是“先有意念主题”,“再找适当的材料、舞台”。相对于这类作品,其后期小说更关注人类生存之谜和内心奥秘。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的视点转变,迫使韩少功重新反思并选择自己的小说思维方式。那么,到何处去寻找改变小说思维方式的文化资源呢?有学者指出:佛文化语言“尤其是禅宗的语言,多带荒诞性、怪异性、非逻辑性和非科学性。”[6]语言的特征直接表现了思维的特征。因此韩少功指出:“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是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3]110韩少功的明智在于他不盲目排斥理性,甚至承认“有时候从理性思维中受益”,但他更明白,文学思维即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主要是直觉思维。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习惯是理性过盛,并且对形象思维造成了干扰。“既然理性存在,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决的地步,迫使理性停止功能。[7]返观韩少功1985年后的小说,它们大多带有似幻似真、云遮雾罩的神秘朦胧气息。《归去来》《蓝盖子》《爸爸爸》,乃至《马桥词典》等,无不如此。这些小说大都表现人的幽秘复杂心灵以及生存的荒诞色彩,主题幽深朦胧,情节淡化,且颇具虚幻飘忽的韵味。他大量地描写梦境、幻觉、痴呆、畸零者、精神病人,或者深入到正常人的潜意识深处。而他这样处理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现实复杂性的真实反映,更是要抵达对人性的理性把握。正像禅宗智慧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参悟,达到的却是对事物真理性的把握一样,这正是他的直觉思维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感性直觉的所在。如《归去来》在暗示黄治先自我确证的失败时,重点表现了社会文化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强大同化力;而《蓝盖子》则是在陈梦桃充满矛盾、悖反的人生戏剧中表达沉重的生存之思,重点表现了个体选择对自己命运的某种影响。二者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地方是一个从非理性到非理性,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
三 禅宗的神秘主义因素为韩少功小说表现手法注入了新质
禅宗和道家在认识宇宙和人类自身问题上都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神秘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对应,其基本特征是否认理性和知识的绝对权威,认为所有知识和理性都是有限的,人类很难通过感官、概念获得对事物和自我的真理性认识,而只能由外观转向内识,所谓“绝圣弃智”、“静观”、“坐忘”就是最基本的体悟方式。体悟是对“佛性”的明了与对“道”的彻悟。禅宗和道家都把宇宙的本质看作是动态的存在。佛教体察宇宙万物强调因缘和合,也即强调万物生灭的条件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强调万有因果律;道家的认识论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命题也指示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联与趋势。无论是禅宗还是道家学说,它们对宇宙的描绘都有混沌一体、不加分别的特征。这一特征正是世人将其归入东方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一些明智的学者开始对它们进行质疑。他们意识到东方与西方的认知传统和认知方法是不同的,不能说哪一种绝对好,哪一种绝对不好。“在西方,‘是’是‘是’,‘否’是‘否’;‘是’永不可以是‘否’。反之亦然。东方则使‘是’滑入‘否’,而‘否’滑入‘是’,在‘是’与‘否’之间,没有严谨而生硬的区分。”[5]30“科学的方法是把物体屠杀,把尸体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合并,由此想把原来活活的生命重造出来,而这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禅的方法则是把生命按它所生活的样子来感受,而不是把它劈成碎片,再企图用智力的方法拼合成它的生命,或者用抽象的方法把破碎的片断粘在一起。”[5]33韩少功对所谓“科学”、“理性”和“知识”同样怀有警觉,而且明显地受到禅宗趋近内里和整体感知的思维方法的影响。
在韩少功1985年后写作的小说中,他感悟湘楚文化的神秘魅力,直接将作品中人物意识还原到本土轮回观念和巫术思维之中。巫楚文化是一种原始、半原始文化,以湘楚大地为背景的韩氏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神秘意象。《爸爸爸》里的丙崽,《女女女》中的鼠流,《会心一笑》里受命复仇的红头蜥蜴,《鞋癖》中的亡父显灵与母亲的鞋癖,《马桥词典》中石磨石臼大战留下的斑斑血迹,被砍掉半个脑袋还依然能够行走的乡人,以及被老虎跟踪一路却还能保全性命的虎口余生者……此外还有不可胜数的神秘气氛的渲染,如某种预感、兆头,心理幻觉乃至根本无来由的诡秘生活现象,等等。所有这些超出了理性意识范围的事物,作家都想从它们当中看出某种隐秘的意义,发现某种深藏的秘密,探究某种生存的真相。《女女女》中篇末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记得幺姑临死前咕哝过一碗什么芋头,似乎在探究人生的某种疑难。这句话在我胸中梗塞多时,而现在我总算豁然彻悟,可以回答她了:吃了饭,就去洗碗。就这样。”这里化用了赵州从稔与某和尚关于自我的一段对话。这则禅宗公案故事说,赵州有一次被一个和尚问道:“我的自我是什么?”赵州说:“你吃过早粥没有?”“吃过了。”赵州又说:“那么,去洗碗吧!”言下之意是你既然在行动,在生活,那么行动主体还不能体悟到“自我”是什么吗?
《爸爸爸》中“伤痕累累的老凤”的沉重与腾空飞舞的屋檐的想象,《蓝盖子》中“停棹息桨”,又将“扬起风帆”的大小集镇的隐喻,无不化成一种意味深长的整体象征。这些象征意象,是作家直觉中的某种人生真实或者心灵真实。似有逻辑又无逻辑,似可理喻又不可理喻,似满有意义又似全无意义,似可言说又不可言说。这里直觉本身似乎又通向了理性,通向了对生命存在、宇宙存在的执着叩问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不倦探寻。
韩少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运用中国禅宗的审美思维去同化、统摄象征、荒诞、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派”技法,善于融会巫楚文化的神秘奇诡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风姿神韵,善于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熔为一炉。
《爸爸爸》《女女女》中的象征与荒诞,《归去来》《余烬》《山上的声音》《鼻血》中的神秘主义氛围,《很久以前》《雷祸》《领袖之死》中的心理分析与潜意识发掘,《空城》《人迹》《史遗三录》中朴素、简洁的现实主义白描透露出来的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领袖之死》《红苹果例外》《史遗三录》中的黑色幽默,《谋杀》《梦案》《真要出事》《归去来》中的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精神焦虑、信任危机,都非常巧妙地融会了中西古今的文化精华和审美因子,并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作家的创作追求、创作个性。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4.
[2]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三联书店,2000:78.
[3]韩少功.文学的根[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4]王蒙.维纳斯的腰带·序一[M]//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
[5]铃木大拙,佛洛姆.禅与心理分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6]杜方智.佛典语言化作诗的花朵——佛文化与《野草》研究之十[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7]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126-127.
Effect of Wisdom of Zhuangzi and Zen on Han Shaogong's Later Novels
CHEN Run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Han Shaogong acquires innovative thought,inspiration and wisdom of mel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n his later novel recreation period.Relativism of Zhangzi and Zen philosophy promotes the reposition of novel conception.Then,Zhangzi and Ze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on intuition,which influences Han's way of thinking in novel-writing.Finally,the mysticism in Zhangzi and Zen gives him new inspiration for way of expression in his novels.
Han Shaogong novels;wisdom of Zhuangzi and Zen;relativism;intuition thought;Mysticism
I207.425
A
1674-117X(2012)01-0021-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04
2011-05-15
陈润兰(1949-),女,湖南蓝山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