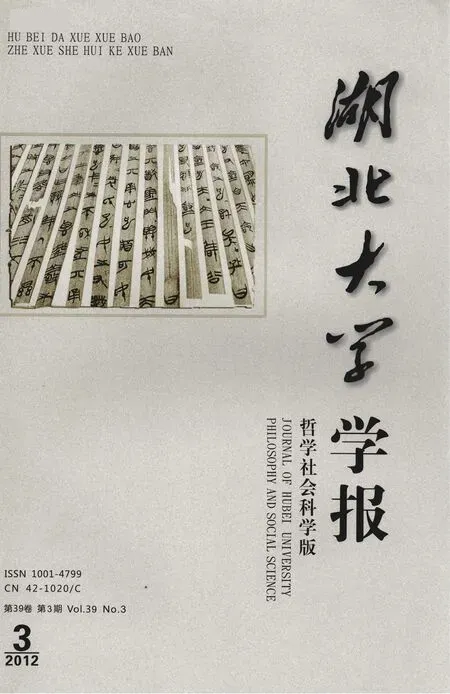聚众犯罪与聚众性之解构
邹江江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聚众犯罪与聚众性之解构
邹江江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我国刑法中,聚众犯罪的聚众性要件表述较为简单,例如聚众斗殴罪在刑法中即规定为“聚众斗殴”的客观行为,这使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以来对“聚众性”的认识存在偏差,始终将其作为一种客观的聚众行为进行处理,但在犯罪主体、犯罪形态、必要共犯等问题上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情势说成为“聚众性”合理的理论。将“聚众性”理解为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应具有的情势条件,符合必要共犯的基本原理,是聚众犯罪的应有之义。
聚众犯罪;聚众性;情势;行为
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具有聚众犯罪的特征。但在事件责任人的处理上,司法机关面临着许多难题,导致在实践中或处罚过严,将一般参与者予以定罪;或不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聚众犯罪特征因而处理失之过宽。其中法律层面的原因在于聚众性的要件并非明晰,因此有必要准确界定聚众犯罪,明晰聚众犯罪中“聚众性”的具体要件,以期司法实践准确适用。
一、聚众犯概念解析
(一)聚众犯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聚众犯的概念,学界有很多种观点,有的认为聚众犯就是一种共同犯罪,与一般的共同犯罪并无区别[1]302;有的认为聚众犯是一种以聚众为要件的共同犯罪[2]150;有的认为,聚众犯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3]123~124;还有的认为,聚众犯是法律规定的聚集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人实施犯罪,这些众多的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是由于其中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的结果[4]196。以上观点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聚众犯的涵义,各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都存在不足之处。
聚众犯这一概念乃舶来品,最初来自于德日刑法。该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就产生了理论对接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原初并无此概念,刑法条文中也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刑法中又确实规定了聚众犯这一具体的犯罪类型,有诸多条文规定了犯罪均要求聚众方能实施,例如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因此要在我国刑法中界定聚众犯的概念,一方面要结合德日刑法中聚众犯的原初概念,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予以分析。
在德日刑法中,聚众犯又称聚合犯,是必要共犯的一种。所谓必要共犯,是指依刑法分则之规定,以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构成要件之行为为必要的犯罪类型,即以多数人之参与为必要之犯罪类型[5]459。必要共犯的核心在于刑法规定之犯罪行为有赖于多数人共同实施,其又可分为两种犯罪类型,多数人同向协力实施构成“聚众犯”,相向协力实施构成“对向犯”。聚众犯与对向犯的区别在于参与犯罪的众人处于集中关系,即二人以上的行为处于同一方向,同一目标关系。
从表面上看,聚众犯与普通的多人共同犯罪并无区别,聚众犯是多人同向实施一犯罪行为,普通的多人共同犯罪也是如此,但聚众犯属于必要共犯,即刑法明文规定该类犯罪的构成必须由多数人共同实施,如果单个人实施该行为则不构成犯罪。例如,刑法规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个人无法构成该罪名。而普通的多人共同犯罪与此不同,多人所实施的犯罪一个人也可以构成,例如故意伤害罪,可以由一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多人共同实施。由此,聚众犯并非一般的共同犯罪,其核心区别在于,聚众犯是法律规定该犯罪的构成必须由多数人共同实施,一个人实施该行为是不能构成犯罪的,而一般共同犯罪则并非如此。法定性是聚众犯罪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刑法中,聚众犯均以“聚众……的”形式出现,可见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强调“聚众”性的特征。聚众,即聚集多数人,聚众一般体现为一种现实的情势,即多数人聚集一起的现实状况,聚众又体现为一种临时性,参与犯罪的多数人并非长期合作,而是临时邀集一起。聚众也是聚众犯的要件之一,当事人之间不符合聚众条件的,不能认定为聚众犯。聚众性是聚众犯罪首要的客观表现,是聚众犯罪的核心特征。
此外,我国刑法对于聚众犯罪均规定了处罚首要分子,而且从客观解释的角度,任何聚众犯罪必定有一定的召集者、发起者或指挥者,因此任何一个聚众犯都必然存在首要分子,聚众犯是在首要分子的召集、发起和指挥下开始实施犯罪的。首要分子可能不止一个,但不可或缺。首要分子的存在和处罚也是我国聚众犯的特征之一。
由此可以归纳出聚众犯的概念:所谓聚众犯,是指依据刑法分则之规定,该犯罪之成立有赖于首要分子的召集、策划和指挥,而由多人共同聚集实施者。前述前两种学术观点均未将聚众犯与普通的共同犯罪区别开来,反而认为聚众犯只是以聚众为条件的共同犯罪,没有抓住聚众犯的本质即法律规定性,一般的共同犯罪也可能出现聚众实施的情况,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也是聚众犯,无疑使这个概念丧失区分意义;第三种观点突出了刑法规定性,但将所有刑法规定的聚众实施的犯罪行为均纳入聚众犯的范畴,反而没有体现聚众的入罪条件,也有所不当。第四种观点既体现了法律规定性,也将聚众作为聚众犯成立的条件,内涵较为明确,但用语不够精炼。
(二)聚众犯的罪名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聚众犯的经典表述为:“聚众”,对法条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刑法中规定了“聚众”的罪名共有19个,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聚众是该罪名的必备条件。有学者将这一类罪名称为纯正聚众犯罪[6]184~188。就这一类罪名而言,刑法分则将聚众作为该罪名的必备条件,不具备聚众条件的不构成该罪,聚众性是法定的,不可或缺的。这一类犯罪不仅罪状上使用“聚众”的表达,罪名中也包含有“聚众”,可见聚众性是该类罪名的必备要件。该类共有11个罪名,分别是:“刑法第268条规定的聚众哄抢罪、第290条第1款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第290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第292条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第317条规定的聚众持械劫狱罪、第371条两款规定的聚众冲击军事禁区罪、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第291条规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交通要道秩序罪、第301条规定的聚众淫乱罪,第242条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
第二,聚众是该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一。有学者将其称为选择的聚众犯罪[6]184~188。这类犯罪刑法上并没有规定聚众是该犯罪的必备条件,而是这类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由于这类犯罪聚众方式实施情况十分普遍,因而刑法将其聚众的行为方式列举出来,从而成为选择的聚众犯罪。这类罪名包括:刑法第303条规定的赌博罪包含的聚众赌博行为、第309条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包含的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行为,第289条规定的聚众“打砸抢”行为等。
第三,聚众是该罪名的加重处罚条件。这类罪名刑法并未将聚众作为该类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是将其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如果行为人聚众实施该罪名的,则予以加重刑罚。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第一类罪名而言,其归属于聚合犯范畴并无太大争议,该类罪名完全符合聚合犯的要件。但对于第二三类罪名,能否归属于聚合犯的范畴,还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第三类罪名也属于聚众犯的范畴,理由是聚众犯中的聚众不仅是法定定罪情节,也可以是法定的量刑情节,只要法律对聚众作出规定的,都应当认定为聚众犯[6]184~188。笔者不能赞同这种观点,事实上,聚众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划定犯罪的合理范围,判断聚众犯的处罚模式,而这一问题是建立在聚众犯的法定性基础上的,法定性要求聚众成为定罪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聚众实施,单个人无法构成犯罪。但第三种类型的罪名,个人和聚众都可以构成犯罪,因而不合聚众犯的要件,不宜作聚众犯论处。
对于第二类罪名中的聚众行为,则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其属于聚众犯的范畴,这些学者认为,虽然这些罪名可以由单个人构成,但其行为模式与聚众的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聚众的行为模式下,单个人实施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符合聚众犯的要件[7]101~107。
笔者认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些条款中的“聚众”是拟制性规定还是注意性规定?如果这些条款中的聚众是拟制性规定,则该罪名本来并未将该聚众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而基于刑法聚众条款之特别规定才予以处罚,个人实施该类行为则不应处罚之,此种情形下,该类聚众行为应当属于聚合犯范畴;如果这些条款中的聚众是注意性规定,只不过由于这种犯罪的聚众在实践中高发,或者是该聚众情形在该类犯罪中占据重要比例,由此立法特意强调的,这种情形下该聚众犯之规定只不过是立法上的明示而已,并不具有法律区分的效果,个人实施该种犯罪行为也应当同样定罪,则该类聚众行为不应归属为聚众犯。
下面笔者逐一分析之:(1)赌博罪。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从条文可以看出,以赌博为业和聚众赌博行为互不统属,聚众赌博行为归属于赌博罪显属法律拟制之规定,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赌博行为是不能构成赌博罪的,因而赌博罪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也属于聚众犯范畴;(2)扰乱法庭秩序罪。刑法第309条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干扰法庭秩序的”,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该条文中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行为也不能为一般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所涵盖,单个人是无法形成冲击、哄闹法庭的行为的,因此该条规定的聚众冲击、哄闹法庭行为也属于聚众犯范畴;(3)聚众“打砸抢”。刑法第289条规定,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论处。本条是对聚众打砸抢行为的特殊规定,但究其本质,致人死亡、重伤的行为已经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条文所涵盖,本条只不过是对聚众“打砸抢”情形的注意性规定,并非拟制,事实上没有本条的规定,也可以援用刑法有关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条款对该类行为予以处罚,因而本条规定的行为并非聚众犯的范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有关聚众犯的罪名主要有两种类型13个罪名,一种是聚众是该罪名的必备条件,另一种是聚众是该罪名中一类犯罪情形的必备条件,但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聚众犯的特点,即聚众犯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以聚众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类型。
二、聚众性概念解析
(一)聚众性的概念
聚众性是聚众犯罪首要的客观表现,聚众犯罪如果不满足聚众性要件即为构成要件缺失,因此在认定聚众犯罪时,首先应当判定聚众性要件是否符合。刑法条文中,聚众性要件的表述较为简单,例如聚众斗殴罪刑法即规定为“聚众斗殴”的客观行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聚众斗殴”既可以理解为两个相互并列的行为,即“聚众行为”加上“斗殴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前后修饰的关系,即“聚众”是斗殴行为的一种情势和条件,而非单独的行为方式。正基于此,学理上对于聚众性的认定存在相当的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即为聚众究竟表现为一种客观的行为要件还是仅仅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情势,前者被称为行为说,后者被称为情势说。
行为说认为,聚众性是聚众犯罪的显著特征,构成聚众犯罪必须具备“聚众”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聚众行为的,则不应构成聚众犯罪[8]46~50。由于对聚众行为的性质认识不一致,行为说又可以分为预备行为说和实行行为说。实行行为说认为,聚众犯罪在客观方面往往表现为聚众行为和具体犯罪行为结合的复合行为犯,聚众犯罪主体必须同时实施了聚众行为和具体犯罪行为方可构成犯罪[6]184~188。实行行为说在行为说中占据主要地位。实行行为说的主要理由是,聚众作为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客观条件,如果不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聚众犯罪在客观方面就缺乏完整性,有损聚众与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的统一性;此外,刑法规定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系起“组织、领导、指挥”作用者,这些作用的发挥都需要通过聚众行为得以实现,而且聚众行为往往表现为对社会秩序具有直接而现实的侵害性,因此聚众行为符合实行行为的要求,也是聚众犯罪成立所必需,应当作为聚众性认定之表征。实行行为说认为通说也持该种观点,通说在解读具体的聚众罪名时,往往将聚众行为作为聚众犯罪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加以论述,例如通说在解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即指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聚众,即首要分子纠集多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聚集。所谓扰乱社会秩序,是指由于行为人之行为致使工作、生产、营业或者教学科研无法进行。”[9]544可见,通说也认为聚众犯罪的聚众表现为一种聚众的实行行为。预备行为说则认为,聚众行为是聚众犯罪的预备行为,聚众犯罪由聚众预备行为和实施的具体犯罪实行行为两部分构成,例如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是斗殴行为,聚众行为为聚众斗殴的预备行为,但仍为犯罪构成所必需。该说的基本理由是聚众行为和具体的犯罪实行行为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聚众行为并不能直接对犯罪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因而将之作为犯罪实行行为存在不妥[10]60~66。
情势说是与行为说相对应的观点,情势说认为聚众犯罪中的聚众性仅为犯罪人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时所应具有的情势条件,即犯罪人在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时,现实的具备了聚众实施的情势条件即可,这时犯罪人如果起组织、领导、指挥作用的,即为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11]65~69。根据情势说的观点,聚众犯罪并非复合行为犯,而是单独实施具体犯罪行为即可,在判断聚众犯罪是否构成时,只需判断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具备聚众的样态即可,而不需对行为人的聚众行为进行考察,行为人没有实施聚众行为,而只是利用现实的人群聚集效果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也可以构成聚众犯罪。
(二)聚众性行为
实行行为说将聚众性理解为聚众的实行行为,虽然在聚众的认定上具有相当的清晰性,但却产生了诸多的不当和困境,导致这一观点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将聚众行为作为聚众犯罪的实行行为要件,就会产生聚众犯罪构成要件难以涵盖全部聚众犯罪行为的结果,过于缩小了聚众犯罪的范围。实行行为说将聚众犯罪理解为复合行为犯,则聚众行为与后续犯罪行为之间必然存在手段目的关系,即聚众行为必须以实施后续犯罪行为为目的,二者必须保持目的的一致性,然而这显然无法涵盖所有的聚众犯罪情形。以聚众斗殴罪为例,聚众斗殴罪如果要求聚众的实行行为,则该聚众行为的目标必须是斗殴行为,非以斗殴行为为目的的聚众行为应被排除在聚众犯罪范围之外,事实上现实存在以斗殴为目的的聚集和不以斗殴为目的两种聚集状况,如果后一情形发生斗殴行为,从刑法条文规定来看并无排除罪名适用之可能,而且也符合该罪侵害公共秩序的要件,理应作为聚众斗殴罪处理,然而实行行为说即排除了该种情形适用罪名之余地。此外,复合行为犯要求行为的先后次序性,即聚众行为应当先于后续犯罪行为而实施,然而聚众犯罪中,往往存在聚众行为与具体犯罪行为同时实施的状况,实行行为说也难以解释该种情形适用聚众犯罪之理由。其次,实行行为说又会导致聚众犯罪的处罚的过于提前,处罚范围不当扩大。实行行为说将聚众犯罪认定为聚众行为和后续犯罪行为的复合行为犯,则聚众犯罪的着手应当以聚众行为着手为判断标准,行为人着手实施聚众犯罪之后,如果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完成犯罪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然而,行为人如果仅着手实施了聚众行为还未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的,一般情形下对于所保护的法益还未形成现实的侵害,以聚众斗殴罪为例,仅仅聚集而未实施斗殴行为的,社会秩序尚未遭到现实的侵害,况且即使存在斗殴的犯罪故意,聚集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斗殴行为的发生,将之作为犯罪处罚未免过于苛刻,有违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更进一步来看,实行行为说将着手实行聚众行为视为聚众犯罪的着手,然而聚众行为的着手距离法益的侵害未免过于遥远,对法益尚未形成任何现实之威胁,即使需要处罚也应当以犯罪预备论处,将之作为犯罪未遂处理明显处罚范围过宽。再次,实行行为说存在主体混乱的论证逻辑,实行行为说要求聚众犯罪以聚众行为和后续犯罪行为为行为要件,聚众行为的行为人应为聚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即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但后续犯罪行为的行为主体系全体聚众人员,一个犯罪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则该罪的犯罪主体究竟应如何认定?聚众犯罪本属必要共犯,其行为主体应当确定为全体参与人,但基于刑事司法的目的,才将处罚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的不处罚参与者,有的仅处罚首要分子,但不管怎样,聚众犯罪的行为主体仍然应确定,不可将首要分子单独作为聚众犯罪的行为主体,否则对于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与人员就会丧失处罚的根据。
正因为实行行为说存在诸多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将聚众犯罪中聚众行为作为预备行为处理,即聚众犯罪的实行行为仅为后续的具体犯罪行为,而聚众行为为犯罪预备行为,实施了聚众行为而因意志意外原因停止的,可以以聚众犯罪的预备犯处罚之[12]。预备行为说认为,聚众行为是聚众犯罪类型化的预备行为,是聚众犯罪的必备客观要件,如果不具备聚众预备行为的,则不应认定为聚众犯罪[13]68~72。预备行为说克服了实行行为说处罚过于提前的弊端,将聚众行为作为聚众犯罪的预备行为处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由于立论上的本质缺陷,导致该说也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困境。首先,预备行为说同样未能涵盖全部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在行为人没有实施聚众行为,而基于自然积聚而被行为人利用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场合,预备行为说同样无法说明处罚的根据,此外,预备行为说也无法解释不以后续犯罪为目的的聚众行为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处罚根据;其次,如果将聚众行为作为预备行为处理,则其与具体犯罪行为应当存在先后的时间顺序,毕竟预备行为应当早于实行行为实施,这在聚众犯罪中具体犯罪行为和聚众行为同时实施情形中就存在处理的难题,而且此时犯罪的停止形态的认定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后,预备行为说将聚众这一预备行为作为聚众犯罪的客观必备条件,这完全不符合罪状设置的基本原理,从未有任何罪名将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同时规定为犯罪要件,刑法要么将预备行为实行化处理,要么就是在犯罪形态中作为预备样态处罚,否则停止形态就完全丧失判断的依据。可见,预备行为说为了克服实行行为说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可行的思考方法,然而立论的错误导致预备行为说仍然存在本质的缺陷,不可适用。
情势说将聚众性视为具体犯罪行为所应具备的情势条件,认为聚众犯罪的犯罪行为仅为在聚众样态下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聚众犯罪并非复合行为犯,而是单独行为。聚众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条件,体现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之中,而非独立的行为要件。情势说回避了聚众行为的认定,避免将聚众行为作为聚众性的标准,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具体行为的样态,从而既坚持了聚众性的要件,又较好的涵盖了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因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事实上,将聚众性理解为具体犯罪行为的样态条件,是聚众性的应有之义,也是聚众犯罪的本质要求,聚众犯罪的聚众性必须依附于具体犯罪行为而存在,脱离具体犯罪行为认定聚众性无异于缘木求鱼,聚众犯罪归根结底是通过具体犯罪行为实现对于法益的侵害,因此聚众性如果离开具体犯罪行为,则丧失法益侵害的处罚根据。从另一角度来看,刑法将聚众犯罪规定为必要共同犯罪,强调的就是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时所应具备的聚众特征,这也是必要共犯的核心特征,即行为要求多人实施,可见聚众犯罪的本质即为在聚众样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因此将聚众性理解为聚众犯罪的样态,无疑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根基的合理性推导出完善的处罚范围,行为说正因为将聚众性作为一种行为,才导致其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始终未能明确,在相当多的聚众情形下丧失处罚根据,而情势说能够齐备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在临时聚众、非特定目的聚众等情形下都能够说明处罚的依据。从犯罪形态标准来看,情势说也较好的符合了犯罪形态认定的要求,将法益尚未受到直接侵害和威胁的聚众行为排除在实行行为之外,也否定聚众性的预备行为性质,而将聚众性的要件内化于具体犯罪行为的样态条件,可以有效的将法益危险与聚众性相结合,合理的认定犯罪形态①聚众性虽然不以聚众行为为要件,但存在以实施犯罪行为为目的的聚众行为时,如果因意志意外原因而终止,则仍然可以适用犯罪预备处罚之,这是基于聚众行为而产生的处罚根据,与其后的聚众性的认定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相互并不产生矛盾。。综上所述,情势说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应当成为认定聚众性的基本原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聚众犯罪中,聚众行为直接表现为法益的侵害行为,例如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聚众行为直接体现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聚众行为和具体犯罪行为发生重合,这时聚众行为也成为犯罪的实行行为,但这并非是聚众犯罪的常例,而且虽然存在聚众行为,但这时聚众行为实际上是作为具体犯罪行为而处理,因此并不可认为在此类罪名中,聚众犯罪存在复行为犯的情形。情势说仍然可以适用。
(三)聚众性的具体认定
既然将聚众性理解为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势条件,那么如何认定这一情势条件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聚众性要求行为主体数量在三人以上,这是聚众犯罪的数量基础,至于数量的上限则未有要求。对于聚众性而言,由于其仅为一种情势条件,因此不要求考察聚众情势形成的过程,如聚众到底是由首要分子组织、聚集而成,还是由参加者自发组织而成均不必严格要求。一般而言,聚众情势的形成方式包括以下几种:其一,由首要分子或骨干成员组织、指挥组成,这是聚众犯罪的基本形式,一般而言这种聚众犯罪发起容易,组织严密,危害也较大;其二,由参加者自发组织形成,这是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这种聚众犯罪日益多发,这与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存在障碍有显著的联系。就聚众情势的形成时间来看,聚众情势可以是事前形成,即参与者相互邀约,事前在特定地点集合,然后共同实施聚众犯罪行为的,聚众持械劫狱罪往往会以本种情形而实施;聚众情势也可以是临时形成,即参与者并非事前邀约参与,而是基于某一特定的场合而相互聚集,从而实施聚众犯罪,这种在扰乱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的相关犯罪中表现较为突出;聚众情势还可以是事前和临时形成相混合的状态,有的聚众犯罪往往存在核心的参与群体,在核心的参与群体引导下,其他人逐渐参与,这也是聚众情势形成的类型之一。
聚众情势的要件,要求行为人在实施具体犯罪时对聚众情势有所认识,如果行为人并不存在对聚众情势的认识则不具有犯罪故意,聚众情势系具体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行为人对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认识必然包含对于聚众情势的认识,因此不具有该种认识者,不可认定为聚众犯罪。
三、结语
将聚众犯罪的聚众性理解为情势条件,是完全符合聚众犯罪的本质特点的,这也是必要共犯的应有之义,将聚众性理解为行为,无疑是南辕北辙,只有准确的把握聚众性的情势要件,才能有效的认定聚众犯罪,进而划定聚众犯的处罚范围。长期以来,由于对于聚众性的错误认识,导致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也始终未能合理界定,因此在聚众性认定的基础上探析聚众犯罪的处罚范围,是聚众犯罪研究的必然方向。
[1]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李宇先.聚众犯罪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5]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李文凯.聚众犯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认定[J].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4).
[7]刘德法,孔德琴.论聚众犯罪的概念和法律特征[J].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3).
[8]刘德法.聚众犯罪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刘志伟.聚众犯罪若干实务问题研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6).
[11]苏雄华.不只是行为:关于聚众的另行解读[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5).
[12]刘志伟.聚众斗殴罪若干实务问题[N].法制日报,2003-12-04(14).
[13]何俊.聚众斗殴罪相关问题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2005,(5).
D924
A
1001-4799(2012)03-0085-06
2011-05-20
邹江江(1982-),男,广东广州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2011~2012年访问学者。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