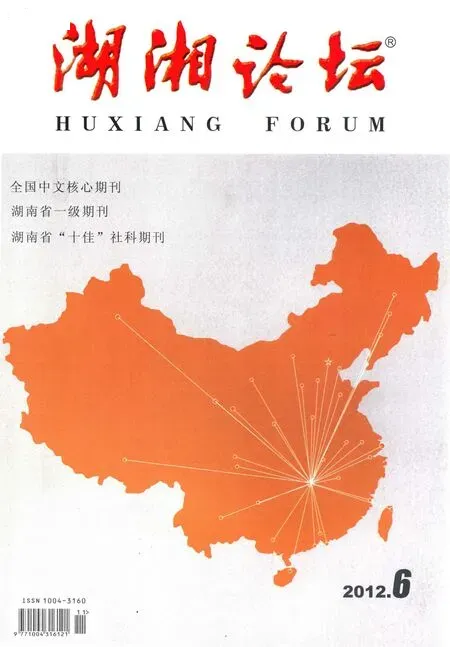奥义书与初期大乘佛教的形上学
吴学国
(南开大学,天津南开300071)
奥义书与初期大乘佛教的形上学
吴学国
(南开大学,天津南开300071)
早期佛学是实践的、宗教的,其世界观是一种经验的多元实在论,拒斥形上学和绝对主义,以此与奥义书传统有别。然而初期大乘重智的般若思想,在世界观上明确包含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形上学。这使大乘的世界观与早期佛教传统之间表现出巨大断裂,却与奥义书形上学具有实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初期大乘形上学的基本图景,即以性空如幻等解释经验存在,以非有非无、不二、无分别等描述绝对,并用二谛论把二者统一起来,都是继承、发展奥义书的形上学而来的,它的形成是奥义书思想对佛教长期渗透的结果。同时大乘佛学乃进一步破除奥义书形上学对梵作为永恒实体的执着、舍“有”入“空”,从而进入无住、无得的绝对自由之境。
奥义书;大乘佛学;形上学;空性;绝对
日本著名东方学家中村元曾说:“在印度思想中,最大正统为吠檀多,最大异端是佛教,二者的相互关系影响了印度精神史。”[1]P131吠檀多(vedanta)就是奥义书及以它为基础的吠檀多派思想。无论是吠檀多还是佛教,都是在二者的相互对话、相互渗透中成长。对于佛教来说,它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奥义书形上学的影响;而对于大乘佛学特别是其形上学,这种影响尤为根本。后者随着上世纪下半叶“批判佛教”兴起,还一度成为学界热点。佛学界和印度学界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侧面涉及过这一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见解仍较零散。如果要更深入了解这一问题,就需要从观念史层面,对于从奥义书到大乘形上学的演变作出系统化的阐明和论证,但这样的研究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仍然缺乏,而这就是本文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最早的大乘思想有重信、重悲、重智等不同倾向,大乘的形上学主要是从其中重智的般若思想发展出来,而龙树的中观学被认为是后者的最佳阐释,故我们这里讨论初期大乘的形上学,乃集中于般若——中观思想。学者指出般若思想旨在通过“空”否定经验的、相对的世界的真实性,以诠显某种超验绝对[2]P209。这种思路与排斥绝对主义且倾向于经验实在论的早期佛学判然有别,而与奥义书形上学完全一致。盖早期佛学是实践的、宗教的,它拒斥形上学,对超验的绝对保持沉默。相反奥义书作为印度哲学之渊薮,其特点是重觉证而轻践履、重形上学而轻宗教,以阐发绝对者之意义为宗旨。不过学者们发现“许多大乘经典完全是形上学的,而非宗教的。”[3]P36大乘佛学热心探讨的,恰恰是佛陀认为求道者应予回避或保持沉默的问题,它在这里表现出了明显地随顺奥义书的立场。佛学这一重大转型应当是与奥义书思想的长期影响分不开的。
以下我们试图通过观念史的阐释证明,大乘形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内容方面,即:(1)以性空如幻等解释经验存在;(2)以非有非无、不二、无分别等描述超验的绝对;(3)以二谛论作为基本框架把经验存在与绝对二者统一起来,都是奥义书的绝对主义形上学影响的结果。因此奥义书思想的渗透是促使大乘佛教形上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佛学的自我创造,而只是指出造成佛学从小乘到大乘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奥义书思想对大乘世界观的本质影响的阐明,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大乘佛教的精神是必须的,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从奥义书的“幻”到大乘佛学的“空”
首先我们试图阐明,大乘佛学解释经验世界的“性空如幻”论,就是以奥义书哲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原始佛教世界观的核心是十二支缘起论,它将世界万物,看作是因缘而生的,因而是无自性的。它所谓无自性、空,旨在于诠显一切无常生灭的有为法的时间性。把世界理解为生生不息的时间之流,乃是人类早期自然思维的共同特点。原始佛教无疑继承了这种朴素的思维。它尽管也从吠陀传统借用了“如幻”等语,但其意义朴素,并没有在存在论上斥一切法为根本虚妄之意。如《杂阿含经》说“诸行如幻、如炎,剎那时顷尽朽”(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一,《大正藏》2册,第72页),乃是用如幻等比喻有为法之变灭易逝,即阐明其时间性。早期佛学的旨趣在于依缘起的时间性开示“无我”、“苦”、“空”的道理,以达到让众生断染得净的目的。盖十二支既为缘生,故皆是时间性的或无常的,无常故无我,若住无我则离我慢、得涅盘。大概人类思想都力图超越直接、朴素的现象之流,以实现一种超时间的、永恒的意义。这种超越在印度哲学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路向:其一为绝对主义的,即构想一超验本体,与世界对立,并否定世界的实在性,这是奥义书的路向;其二为多元论的,即设想有众多超时间的实体,作为世界的基础,这是胜论、耆那教等的路向。原始佛教在世界观上是经验论的、自然主义的,但来自奥义书形上学的影响又使它力图在宗教上超越经验的、自然的存在,尽管它对任何绝对保持沉默[4]P381。而小乘有部等,由于受胜论、耆那教乃至希腊文化的影响,乃确立一种多元实体论的哲学。如有部持法体实有,把法理解为自性永远不变的、超验的实体(dravyasat)[5]P123。这些说法都与胜论一致,却严重偏离了原始佛教诸法缘生而无实体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般若标榜如幻性空,就旨在克服这种来自外来影响的实体论,回到佛教本来的无自性论。如经说:“一切法性空,一切法无我无众生,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影、如炎。”(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经》卷十,《大正藏》8册,第580页。)但般若的幻论决不是要回到《阿含》的经验的、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在于:(一)它的如幻是虚妄、性空的意思,目的不在诠显有为法的经验时间性,而是揭示有为法在存在论上的虚妄非真,因为,同缘起的法一样,生灭的时间性过程本身也是虚幻不实的,故不是般若的归宿,如般若经云诸法“无相无作无起无生”,《中论》亦云“如幻亦如梦,如乾闼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鸠摩罗什译《中论》卷二,《大正藏》30册,第12页)(二)与此相关,般若把幻的观念大为深化了。这里诸法不仅如幻,而且就是幻,色不异幻幻不异色,色即是幻幻即是色。一切诸法皆是无明所幻作,空虚无实。世界的本质就是幻有。故“幻”成为普遍的、本体论的观念。可以看出,大乘的如幻论,与原始佛教的自然实在论,和部派的多元实体论哲学,皆判然有别。
然而它与晚期奥义书——吠檀多的幻化论(māyā-vāda),却如出一辙。杜伊森说:“奥义书开示此宇宙非真我、非实有,而只是幻,一种假相或错觉。”[6]P227同般若一样,奥义书所谓幻(摩耶),也是一个真正本体论的概念。如《白骡奥义书》说:“圣者是应知,世界即是幻,自在即幻师,充满全世界,皆是彼资具。”(Svet UpⅣ·9~10[Paul Deussen:Sechzig Upanishad’s des Veda,Leipzig:F.A.Brockhaus,1921。以下所奥义书皆同此。篇名为奥义书的书名缩写加章节])幻是世界万物的本质,也是其存在的根源。幻就是无明、虚妄分别,它同时具有隐覆和生显的能力,即隐覆无差别的真如,生显差别的假有。这些观念都与大乘的说法随顺无违。其次,奥义书的幻也是对世界的真实性的否定。晚期的《光明点奥义书》和《瑜伽顶奥义书》,举阳焰、影、兔角、乾达婆城、珠母、绳蛇、石女儿等七喻以明世界虚妄,与《般若经》的五喻、十喻,具有明显的同源性。(正由于与大乘佛学的亲缘性,奥义书——吠檀多的幻化论常常受到一些印度教正统人士的斥责,比如《莲花往事书》就说幻化论“非吠陀教”[avaidika],是“伪装的佛说”,吠檀多派内部一直有人持如此责难)与大乘思想相比,奥义书的幻化论,不仅出现的年代更早,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它从吠陀自身传统发展而来的清晰线索。这两点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沿袭了佛教,而反过来的可能性更大。盖吠陀已包含幻化论的萌芽。同所有原始宗教一样,吠陀也有魔术(即“māyā”[幻]之本义)崇拜。天神、阿修罗可以通过摩耶(māyā)完成某种不可思议的工作。但吠陀晚期思想朝绝对形上学方向发展,摩耶的概念也渐被提升到本体论层面。首先,后世所谓摩耶的生显和隐覆作用,在吠陀中即有了雏形。如《黎俱吠陀》说因陀罗作为绝对、唯一者,以幻力变现为差别万有,《阿闼婆吠陀》说大梵作为万有之本源被摩耶所包裹、隐藏。一方面可以肯定奥义书——吠檀多所谓幻化的两种功能,就是以吠陀的上述说法为基础整合而成的;另一方面由于晚期吠陀的天神逐渐被去神话化,而成为与奥义书的大梵一致的宇宙精神,使摩耶从神的幻力转变为普遍的形上学原理,奥义书幻化论只是把这种发展完全确定下来了。另外,吠陀说摩耶隐藏了大梵、绝对,显现出差别世界,就暗示了世界只是相对、假立的存在。当吠陀传统的绝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大梵被确定为唯一的真理,那么摩耶作为假立的存在,就自然成为虚妄的存在。这就与奥义书的幻化论完全衔接起来了。所以随着吠陀传统自身形上学的成熟,从它原先的魔术宗教,发展到奥义书的幻化论哲学,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不是因为沿袭了外来传统。相反般若的幻论,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原理,在早期佛教中没有根源,所以它肯定是大乘沿袭奥义书思想而来的。事实上,后者对经验存在的现实性的否定,是刺激般若破解小乘的实在论的最根本原因。[7]
另外在大乘佛学中,还有无明、戏论(言说)、虚妄分别等概念,具有与“幻”同样的本体论意义,亦是经验世界产生的根源。首先虚妄分别是世界的根源,如云“诸所有色,若粗、若细、若好、若丑皆是空,是空法中忆想分别(即虚妄分别),着心取相,是名为色相”(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十四,《大正藏》8册,第398页),“有为法无为法实相无有作者,因缘和合故有,皆是虚妄,从忆想分别生”(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一,《大正藏》25册,第289页)。其次,无明、言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如般若经说一切法但假名字,一切法以言说故有,《大乘稻干经》说无明生显世界,《六十颂如理论》亦说万有从“无明种”生。般若中观思想把无明、言说、虚妄、分别、幻化当作同一原理。然而把无明、戏论、分别作为世界存在根源的观念,对于持朴素实在论世界观的早期佛教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这里它们至多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它们在大乘思想中可以说是突然出现的。这一点暗示了它们肯定来自某种外来传统影响。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传统只能是奥义书——《薄伽梵歌》的传统。在奥义书传统中,幻作为本体论的原理,也被与言说、虚妄、分别、无明等同。盖奥义书最基本的世界观,为一味、唯一、常恒、真实之绝对本体,与差别、多样、生灭、虚假之现象界的对待。故现象界之生起,乃裂一以为多、舍同而执异、失真而著妄,故为分别,为无明,言虽异而所指一;且分别必由名相,故只是戏论言说;分别等既妄,故其升起等于幻化。所以在晚期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中,分别、言说、无明与幻同义。把分别等等作为世界存在的根源,在吠陀传统中亦有悠久的历史。盖吠陀晚期就有大量关于从一味、无区分的原初之水通过分化产生世界万有的说法,或谓泰初的无相绝对以意识的分别作用为种子而产生世间万相。另外以语言为世界根源的想法,在婆罗门传统中也早已有之。《黎俱吠陀》便说语言为世界的护持、本源,在《阿闼婆吠陀》、《梵书》的时代,语言被比喻为养育万物的母牛。《百道梵书》说大梵以名、相入于世界,使其脱离一味状态而现出分别,意味着言说就是分别。这些观念在奥义书中都得到继承和发展。最早的奥义书思想完全继承晚期吠陀的宇宙论,亦认为世界乃由某种无分别的自然始基分化产生。在随后的思想发展中,这始基逐渐转化为意识、精神,且思维、言说成为存在发生的原理。在奥义书成熟的思想中,对于本体与现象的严格“形而上学区分”被确定下来,于是绝对、梵(纯粹精神)成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一切差别相都成为假相。这样,那产生假相的分别、言说,就自然被贬斥为无明、幻。总之,奥义书的无明、言说、虚妄分别等,被作为世界现象的根源,并与幻化等同,是吠陀——奥义书传统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大乘佛学的相同观念则是奥义书思想更深刻地渗透到佛教中的结果。
不过般若中观对奥义书对经验存在的看法也有实质的发展。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幻”论。盖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幻化论,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旨在遮世界为幻有,显大梵为真实,造成了本体与现象、涅盘与世间的对立。在大乘看来这仍然是“有二”、有执(对梵界、彼岸之执)。般若的精神是彻底批判性的,它讲“如幻”,最终落实到“空”,不仅要“空”掉经验的、现象的世界,而且要“空”掉超验的实在、本体。空不是与幻有相对的另一世界,空性法界就是诸法的实相,而不是离开诸法的另一种有,空与有相即不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8册,第221页)。而且不仅世界性空如幻,涅盘、佛法身亦如是,经说“我说佛法亦如幻如梦。我说涅盘亦如幻如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经》卷一,《大正藏》8册,第540页)故不应把空性、涅盘、法性当作现存的避风港,而是应当空亦复空。所以,如果说奥义书的真、幻区分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区分”,那么大乘对空、有的区分则与海德格尔(旨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对作为存在自身的本无与现存存在进行的“存在论区分”,具有相同旨趣。这一结论对于“无明”、“虚妄分别”等也同样成立。大乘以此破一切执着,实现了无所住、无所得的精神境界,此即是精神的绝对自由。但正如松本史朗指出,在奥义书形上学的进一步渗透之下,大乘佛学在其发展中,又逐渐由“空”向“有”的立场转移[8],实际上是朝奥义书——吠檀多的形上学继续靠拢。结果是如来藏思想中,空性、实相被当作一种与大梵一样的超验实在——如来藏我,名色世界则为后者的幻化,这意味着大乘的形上学在这里完全被吠檀多同化了。
二、从奥义书的梵到大乘的真如法性
接着我们也将阐明,是奥义书的渗透使大乘佛学确立了一个形上学的绝对。老一辈日本佛学家长尾雅人曾说:“当佛教徒用‘空’表达一种强烈否定时,它同时亦肯定地意指绝对的实在,因为它通过经历了否定的确认,指向对绝对的亲证。这否定只是对相对性的否定。”[9]P209台湾的印顺法师也说《般若经》论自性空,既有说世俗自性虚妄无实的方面,也有说胜义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自性涅槃的方面[10]。也有些佛教学者完全把大乘的“空”等于原始佛教的“缘起”,这等于仅仅把空当作否定而不承认其绝对意蕴,但更多者相信空论破除世俗、相对之有是为了诠显某种超越的绝对本质。
笔者认为大乘的绝对主义在般若经论中就表现得很明确了,如般若经云诸法实相是法性、涅盘、法界、法住、实际、绝对,无为无染,有佛无佛是如、法相、法性常住不生不灭,《大智度论》云“法性者,法名涅盘,不可坏,不可戏论。法性名本分种,如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如是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盘性。”(A.A.Ramanathan(Trans by),Maitreya Upanishad,III·5,Chennai: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1980.)这都是把法性当作存在之绝对真理。盖于般若思想中,空的意义逐渐从“行”的方面(无所住)扩展到“境”(胜义法性)的方面,于是空或空性就被等同于绝对、真如。大乘的绝对主义也通过它对空性的一系列表述,如真如(tathata)、法性、法住、实相(satya)、实有(bhūtatā)、实谛(tattva)、实际、胜义、涅盘、法界、不二、绝对、法身、佛性等,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们将证明大乘通过否定经验的、相对的世界来诠显超验绝对的思路,乃是来自奥义书传统的影响。盖大乘对空性、绝对的基本描述,如说它是“非有非无”(na sattanna-asat)、“无分别”(nirvikalpa)、“平等”(sama)、“不二”(advaya)、“无生”(avikāra)等,都在沙门传统中找不到根源,却都是吠陀——奥义书形上学的典型表述。这暗示了大乘形上学的绝对主义是来源于后者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典型表述的观念史追溯来阐明这一点:
第一,大乘说空、绝对为“非有非无”(na sattanna-asat)句,乃是沿袭了奥义书的传统。“空”论的渊源可追溯到印度传统中把存在的本质当作“无”(asat)的观念。《黎俱吠陀》中首先提出所谓“非有”说,认为作为存在之本原、真理的绝对者乃是“无”,后来又从“非有”说发展到“非有非无”说,如其《无所有歌》云:“彼时无有,亦无非有:无气,亦无超越于彼之天……黑暗隐蔽着黑暗,无相无表,唯有玄冥。虚空覆盖存在。”(The Sartapatatha Bratruatana X.5.3.2~3)吠陀的“无”与“非有非无”之说,都被梵书大为发扬,且最终融入奥义书的绝对证悟。奥义书云绝对者“非此,非彼”(neti neti),“离有与非有,及离诸言说,离空与非空”,“无昼亦无夜,无有亦无无,唯自我恒住。”(Svet Up IV-18)奥义书这种“非有非无”的体验,早在《阿含》时期就通过瑜伽进入佛教禅观中,但它在这里只停留于“行”(如非有想非无想处观)层面,而不涉及“境”(诸法实相)。原始佛教以“境”为生生不已的缘起法,既无实体,亦无形上学的绝对。其所谓缘起法空,指的是法的时间性或不坚住性。但小乘有部等宗,乃舍缘起法的时间性而执超时间的实体,由“空”入“有”。而般若则旨在破“有”而复入“空”。这当然离不开奥义书以名色、差别为幻的观念的感召。这从般若的以“幻”解“空”,即可了然。另外,在奥义书绝对主义的影响之下,以前局限在禅观(行)中的绝对,被般若思想释放到存在论(境)的领域,成为诸法的实相;故大乘很自然地用原本阐明实相的“空”来指称它,于是空成为绝对,故自然地融摄了对后者的全部描述。所以,前此佛教中仅系于观行的“非有”(无所有处)、“非有非无”(非想非非想处),就被用来阐明作为诸法实相的空性,如云实相“非空非不空、非相非无相、非作非无作”(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六,《大正藏》8册,第263页。),“非有非无非有无、非非有非非无、一切法不受”(鸠摩罗什译《中论》卷四,《大正藏》30册,第35页)。大乘对实相的这些描述,不见于早期佛教,在奥义书中却都曾以同样形式出现过[11],因而肯定是沿袭了后者的思想。凯思也指出般若说实相超越“有”、“非有”、“非有非非有”乃是从奥义书的“双非”(非此、非彼)之说发展而来。这种发展在于,奥义书的“非有非无”旨在描述一种形而上学的超验实体,而大乘则打破了这种对实体性的执着,超越“非有非无”,而领会“非非有非非无”,乃至“非非有非非无亦无”(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十四,《大正藏》25册,第448页)。大乘由此才实现了彻底的无着,即精神的绝对自由。
第二,大乘的形上学把绝对实相(空性或胜义有)理解为“无差别”(nirvikalpa)、“一味”的境界,也肯定是沿袭了奥义书传统。盖吠陀就开示了一个没有区分、无相无表的“唯一者”作为世界的基础。奥义书的形上学乃由此类思想发展而出。其最早的思想完全继承晚期吠陀和梵书的宇宙起源论,认为世界是由某种无分别的宇宙原质,因其自身分化欲望的促进而发展出来。奥义书在其漫长演变中,将这种宇宙起源论提炼为严格的本体论。其以为从一到多,乃是因为语言、分别心或无明、摩耶的作用覆障了绝对实相,生显出杂多的世界。如云:“信然,世界本是一味无别,彼唯因名相而被分别,如说:‘彼有如是名,如是名’。甚至现在此世界也因名色而被分别,如说:‘彼有如是名,如是名’”(Chan UpⅥ·1·4~6;Kath UpⅡ·4·10)故实相无来无差别、一味,一切有差别的存在都是虚假的。总之奥义书的无差别绝对观念是从自身传统发展来的。然而大乘佛学的相应观念则可能属于另外的情况。大乘同样以“无分别”、“一味”描述真如实性、空性,但是,一方面,“无分别”、“一味”这样的术语在早期佛教中极为罕见,且根本不具有实相或本质之义(松本史朗:《缘起与空》,第140页),因而大乘的“无分别”绝对观念在早期佛教传统中并无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类表述,如经说“当知一切法无有分别,不坏相、诸法如、法性、实际故”(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九,《大正藏》8册,第360页),与奥义书上述说法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对此唯一合理的看法,是大乘的实相“无分别”论就是汲取奥义书的绝对主义发展而来的。另外学者指出作为证悟无分别境的主体的无分别智,也是沿袭奥义书不见差别、有二相的胜义智而来[12]。佛教在这方面的发展主要在于破除了奥义书“一”、“多”对立的形而上学,“无分别”不再是对一种超验的现存实体的描述(绝对的无分别,是分别与无分别亦不分别),而就是精神的“无住”或自由。
第三,大乘说实相“平等”(sama)句,亦不属于早期佛教传统,而是源于奥义书。奥义书所谓“平等”,乃是从晚期吠陀的无分别绝对观念发挥而来。奥义书说绝对者“于草木平等、于蚊蝇平等……于三界平等,于宇宙平等”(Bri UpⅠ·3·22),“离不平等相,亦离平等相,澄明、清净”(Ramanathan(Trans by),A.A.,Maitreya Upanishad III·6,Chennai: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1980.),人若悟大梵,则“脱落善业恶业,无垢无染而得绝对平等”(Mund Up III·1·3,Svet Up II·14)。与此呼应,般若亦说平等即是恒常、超越的实相或本质:“何等是诸法平等?所谓如、不异、不诳、法相、法性、法住、法位、实际,有佛无佛法性常住,是名净”,“无有有法无有无法,亦不说诸法平等相,除平等更无余法,离一切法平等相”(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十六,《大正藏》8册,第414页)。《般若经》讲的平等包括诸法无自相故平等、无生无灭故平等,以及本来清净、离缚、离戏论、无为、非有、非无、不二故平等,如幻、如梦、如影、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化故平等。至少从文字表述上,我们看不出这些说法与奥义书有什么实质区别。反之,以诸法实相为“平等”、“似虚空”等说法,皆不见于巴利五部经中,因而这类说法出现于佛教中,只能是受到奥义书一元论影响的结果。
第四,与此相关,大乘所谓“不二”(advaya)句,也是来自奥义书传统。“不二”、“无二”(advaita)之类表述最早见于奥义书,乃是晚期吠陀作为“唯一”(ekam)的绝对者观念的自然延伸;这在于奥义书把这绝对者理解为纯粹意识、精神,一切客观对象都是它的表现,都不具有区别于或外在于它的实在,故曰“不二”。故奥义书最早所谓不二(advaita)本质上是主、客不二。书云:“当似有二相现,于是彼一者见另一者、闻另一者……知另一者。当知梵者悟一切皆我,复有何者见另一者、闻另一者……知另一者?”(Bri Up II·4·-14)知梵者乃“不知而知”,“不见而见”,“彼知者乃大海洋,不二绝对”(Bri UpⅣ·3·30-32)。晚期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乃将不二扩展为本体之泯灭一切差别、对待。如《蛙氏奥义书》说至上梵为不生、清净、不二,差别万有,皆于中泯灭。《薄伽梵歌》以“有二”或“双昧”(dvandva)统摄一切虚妄分别,世界由此显现出一多、同异、妍媸、苦乐、香臭、好恶等差别;圣者得“不二”(nirdvandva)之智,等视一切,复归于一味之自我。这些说法与大乘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了。大乘亦开示空性、绝对为“不二”:如经云诸法空性“不生、不灭、不二、无分别”(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七,《大正藏》8册,第270页。),“诸佛如来皆是一如相、不二、不别、不尽、不坏”(同上,第525页),“一切相皆是二,一切二皆是有法,适有有法便有生死”(同上,第383页)。这些说法都与奥义书的立场一致。大乘无分别智,也是同奥义书一样的“不见而见”的不二之智。但大乘的“不二”法门的出现远较奥义书为晚,它在早期佛教中并不存在,甚至在原始般若中还没有出现,故可以推测它必是奥义书传统的形上学进一步渗透到般若思想中的结果。另外大乘的不二,既是诸法不二,也是涅盘与世间、真与俗、有二与不二的不二,表明它克服了奥义书不二论仍然隐含的真、俗对立的形而上学以及对超验本体的执着,而是以破一切执、无所得为宗旨,经云“诸有二者是有所得,无有二者是无所得”,菩萨“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故无所得,而“无所得即是得,以是得无所得”(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十一,《大正藏》8册,第376页)。无所得就是无住,是精神的绝对自由。
最后般若的空性、诸法实相“无生”(avikāra,anutpāda)的观念,也是来自奥义书传统。梵语的“vikāra”意为生起差异,变化,生灭,“avikāra”则指超越生灭的绝对。晚期吠陀描述了一个非有非无、无生无灭的绝对。奥义书讲无生,乃是从这一传统发展而来,以为一切生起法皆是语言设施的名字,唯不生之大梵为真。在晚期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中,无生指神的不变易性、永恒性,一切差别、多、变易皆只是幻。大乘佛学也讲“无生”。般若中观之说“无生”,一是指诸法空、如幻,故无实在之生,“一切法中各各自相空故,言不生不灭”(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六十二,《大正藏》25册,第497页);二是指作为存在绝对本质的诸法空性、法性超越了经验的生灭,“诸法如、法相、法性、法住、法位、实际,无为法无缚无脱,无所有故,离故,寂灭故不生”(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五,《大正藏》8册,第249页)。“无生”较之“无分别”,奥义书的味道更为强烈,这尤其表现在上面第二点上。但大乘“无生”的法门,也不见于前此的佛教传统,可以肯定它是般若汲取奥义书的相应说法加以发展而来的。它对后者的发展主要在于:第一,奥义书说无生,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用以描述绝对者的超越时间、变易的永恒性,但般若说无生,则是否定性的,以有为法非实故无生,空性、法性亦非实在故无生。第二,与此相关,般若讲无生不是为了彰显某种非时间性的彼岸实在,而旨在破除一切形而上学的实在性之执,实现“无所住”、“无所得”的完全自由。
总之,大乘观绝对实相为“非有非无”等等,都不属于早期佛教传统,却是奥义书形上学的根本旨趣,因而大乘佛学在这里汲取了奥义书的绝对,是确定无疑的。这些表述是逐渐渗透到大乘佛教之中的(如原始般若可能尝无“无生”、“不二”、“法身”之类说法)。与此相关的还有法界、法身等观念,尽管不是直接来源于奥义书,但它们之被当作存在的绝对真理、本质,也是由于奥义书的影响[13]。而且在奥义书的持续渗透下,大乘佛教的立场逐渐由“空”向“有”倾斜。学者指出,像“无生”等句,直到龙树的中观学都还是否定性的,但到唯识思想中它们都被在肯定意义上使用[14]。在《辨中边论》中,这些术语全都被用来描述某种超越的实在。而当奥义书形上学的进一步渗透使得这一实在被明确等于心性、自我,就导致了如来藏佛教的产生,于是大乘形上学就被彻底吠檀多化。这种结果决定了中国佛学的基本面貌,因为如来藏思想就是中国佛学的主流。因此中国佛学与奥义书——吠檀多思想就具有本质的亲缘性。
三、二谛论:从奥义书到大乘佛学之嬗变
以上我们讨论了大乘佛学关于经验和绝对存在的观念都深受奥义书思想影响。大乘还通过二谛论的框架将这两种观念整合起来。二谛论将经验存在和绝对分别称为世俗有与胜义有,或真谛与俗谛。其立场是俗有真空,以一切由名言分别因缘安立者为世俗,虚妄不实,而唯空性真如为胜义,为实性;但不由俗有,无以显真空,故二谛论亦须肯定世俗的价值,而以真俗不离、不二为鹄的。
从大乘的“二谛”图式,同样可看到奥义书的渊源。盖《阿含》中不见有二谛之说。有部提及二谛,不过立场是实在论的,与大乘的二谛说没有实质联系。但是大乘的二谛论与奥义书对上梵与下梵的区分,却具有本质的一致性。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疏理出从奥义书的“二梵”到大乘佛学的“二谛”的演变途径。
《广林奥义书》最早区分上梵和下梵,“信然,有二种梵:有相与无相、有死与不死、固定与流转、此岸与彼岸。”(Bri UpⅡ·3·1~3)其云至上梵是实相之实相(satyasya satyam),即胜义谛;而下梵为隐藏这实相的实相,即世俗谛。奥义书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将这种区分深化为形而上学的现象、本体之分,如书云大梵“由意所成,由气息所成,由视见所成,由听闻所成,由地所成,由水所成,由风所成,由空所成,由作与非作所成……由一切存有所成”(Bri UpⅣ·4·5);同时又说它“无风、无空、无见、无嗅、无味、无眼、无耳、无声、无意、无作、无名”(Bri UpⅢ·8·8),“非此,非彼”;前者为世俗谛,后者为胜义谛。于世俗谛,大梵有差别,有杂多,有时间,有因果,有分位,可言说,为现象界之全体;而于胜义谛,大梵乃无差别,一味,无时间性,无因果,无分位,不可说,为超验之本体。晚期奥义书把这一区分转化为“实”与“幻”的区分,以世间一切为幻,唯胜义梵是实。与此呼应,《蒙查羯奥义书》还提出上智与下智之说,上智直证本体,下智但取名色。奥义书亦强调不废世俗,如《慈氏奥义书》说言说梵(俗谛)圆满,乃是得至上梵(胜义谛)的条件,并进而提出超越二与不二、空与非空、有分别与无分别。到此为止,大乘佛学的二谛论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因而其来源于奥义书是勿庸置疑的。大乘的二谛论与奥义书说的区别,在于它的胜义有,不是大梵那样的形而上学本体,而就是诸法的空性,它完全不可住、不可得,故不二乃是有执与无执之不二。于是精神的无执和自由,乃成为绝对的。但随着奥义书——吠檀多思想的进一步渗透,大乘佛学的立场逐渐由“空”向“有”转移,到《楞伽》和《起信》的如来藏思想中,空性、实相或胜义有被等同于如来藏我,而世俗有乃是此自我幻现的存在,如此理解的二谛,又完全与晚期奥义书和吠檀多不二论不分轩轾了。这种结果也决定了中国佛学的命运。
总之,大乘的形上学,就是在奥义书思想的长期渗透之下形成的。盖大乘发生之际,一方面由于婆罗门教的东扩和佛教的西进,二者流布的区域逐渐重合,且在同一时期奥义书思想的影响达到鼎盛,佛教对婆罗门文献、思想变得非常熟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婆罗门皈依了佛教,大量皈依的婆罗门势必把他们原有的思想带入佛教。这些都为奥义书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影响到大乘形上学的产生。这种渗透可能主要通过禅观的途径。盖般若思想就产生于禅观的新进展,在般若经里,空就是直接的宗教观证的对象,大乘瑜伽行派也主要是小乘瑜伽师导入了唯识观法而转化产生的。而禅的运动在大乘形上学产生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它为新的启示和觉悟提供了一个通道。”[15]175由于佛教徒对于禅定体验的信任,导致大量皈依的婆罗门把奥义书对大梵的观证带进佛教禅观,乃是极自然之事。加之佛教徒对启示(pratibhāna)说经的认可,禅观的新内容被以经的形式表述出来,也是同样自然的。
[1]Hajime Nakamura,A History of Early Vedānta Philosophy,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3.
[2]G·Nagao,Mādhyamika and Yogācār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
[3]C·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Ⅱ,Delhi:Sri Satguru Publications1988.
[4]Sarvepalli Radhakrishnan,Indian Philophy Vol.1,London:the Macmilian Company,1924.
[5]Hajime Nakamura,Indian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7.
[6]Paul Deussen,The Philosophy of the Upanishads,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ress 2000.
[7]吴学国.存在·自我·神性: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松本史朗.缘起与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G·Nagao,Mādhyamika and Yogācār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
[10]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M].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
[11]凯思·A.B.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霍巴德等(主编).修剪菩提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M].台北:正闻出版社,1994.
[14]瓜生津隆真.中观与空义[M].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
[15]P·Williams(Ed),Buddhism volⅢ,New York:Routledge,2005.
B3
A
1004-3160(2012)06-0087-08
2012-07-19
吴学国,湖北荆州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印度哲学、佛学。
责任编辑:刘剑康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