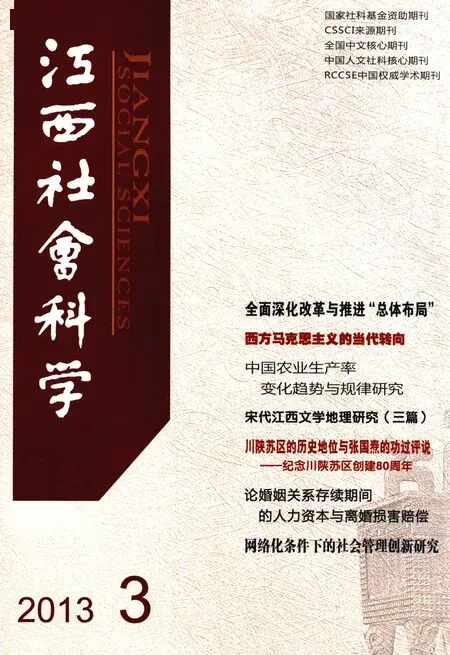川陕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张国焘的功过评说——纪念川陕苏区创建80周年
■余伯流
科学发展引领学术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特质。”研究川陕苏区,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全方位、深层次地研究川陕苏区的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川陕苏区的一些重大事件,正本清源,科学评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更好地弘扬红军精神和苏区精神,从而为推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张国焘的问题,川陕苏区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宣传,许多事情讳莫如深,未能触及,形成一个“结”。
一、川陕苏区的历史地位
川陕苏区存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零四个月 (1932年12月到1935年4月),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毛泽东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创建了13块革命根据地(苏区),其中有“六大苏区”,即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陕苏区。六大苏区中,最大的是中央苏区,“第二大区域”就是川陕苏区。这个历史定位,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央苏区二苏大会上提出的。
1934年1月24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
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1](P248-249)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很客观的。
川陕苏区的创建,源于红军入川。自古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红军入川“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1932年10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拓展发展空间,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等人率领下,离开鄂豫皖苏区,跨秦岭,走关中,渡汉水,穿越大巴山,历时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于1932年12月下旬抵达川陕边区,与陕南、川北当地革命力量相结合,一举攻下通江、南江、巴中三县。是年12月29日在通江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1933年2月,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从而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随后,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多次“围剿”,于1933年10月扩编为5个军8万余人。至1934年9月,川陕苏区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赤色县城,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红色政权。川陕苏区鼎盛时期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渠县,北至陕南,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余万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统辖下屹立在川陕边区的一个辽阔强大的革命根据地,其苏区版图仅次于中央苏区 (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为全国第二大区。川陕苏区人口超过中央苏区,为全国苏区人口第一。在全苏二大,川陕苏区进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的有14人,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光坦、熊国炳、张琴秋、李先念等。川陕苏区由此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南北“两个大本营”(中央苏区与陕甘苏区)的桥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重心从东南引向了西北,中央苏区、川陕苏区、陕甘苏区互为犄角,成为苏维埃中国的三大中流砥柱。
(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拥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其中,红一方面军10万人,红二方面军2万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红四方面军入川时13个团2万余人。据徐向前回忆:红军首次进入通江时,“石破天惊,在这座偏僻山城激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极待补给,但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军纪严明”,“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我们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2](P181、P183)
红四方面军刚入川时,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不足为虑。时四川“二刘之战”(刘湘、刘文辉)正处于火并酣斗之中。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款20万元,100万发子弹,令速“进剿”红军。红军发起“反三路围攻战役”,历时4个月,歼敌2.4万人,大获全胜,田颂尧被蒋介石免职。这时,川陕边区出现了有利于苏区发展的相对稳定局面,红军有可乘之机,有发展空间。
1933年秋,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四路军阀势力,计140个团、25万人向川陕苏区发动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与敌鏖战10个月,歼敌8万余人,战果辉煌,但红军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万余人。“反六路围攻战役”,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是“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2](P249)“经过反六路围攻,部队减员较大,仅剩六万余人。”[2](P283)但苏区红色区域迅速发展,扩展为23个县1个市,国民党报刊惊呼四川已成“江西第二”。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骁勇善战,浴血拼搏,英勇杀敌,红四方面军将领素以打大战、打硬战、打恶战著称,涌现了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秦基伟、洪学智、陈锡联、王近山等446名杰出将帅、英才,为川陕苏区的巩固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三)川陕苏区的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在川陕边区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的政治宣言
1932年12月红军一入川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就颁发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颁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这两个布告,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掀起了川陕边区的土地革命热潮。“土地革命以后,地租消灭了,租户成了自由民,封建制的经济已不存在。”“穷苦人民抬起头走上了历史舞台,做了苏维埃政府的主人。人民在欢笑中过光景了。”[3](P101)据调查,“通江、南江一带,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100斤左右。而分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收到200斤至300斤粮食,增产1至2倍。那几年是大丰收,吃干饭也吃不完,自己也可以杀猪过年”[3](P102)。毛泽东当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也曾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土地革命让广大贫苦农民有了生存之本,得到了实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纲、中共“为民谋利”的政治宣言,在川陕边区得到了辉煌的实践。
(四)川陕苏区普遍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树起了一面“赤化全川”的鲜艳红旗
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县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上,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随后,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苏区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红色政权。川陕苏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民众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开展各项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修水利,开通赤白贸易,统一金融币制,扩大红军武装,创办了工农银行、造币厂、兵工厂、子弹厂、被服厂、织布厂、制药厂、农具厂、斗笠厂、盐厂、酒厂、脚码子厂等;开设了赤色邮政、军事通讯、红色交通线;创设了红军医院、工农医院,禁烟戒烟,禁种鸦片;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出版发行《共产主义ABC》、《革命三字经》等各类政治书籍,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川陕省苏机关报《苏维埃》、西北军委机关报《赤化全川》、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军》等广为流传;红军大学、苏维埃学校、列宁学校、贫民学校、工农中学、专科学校遍布苏区;红军广场、苏维埃广场开展各项体育运动,为军民所喜爱;红军石刻标语随处可见,通江县红云崖顶部的巨型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堪称世界之最的“标语王”,豪气冲天,令人叹为观止;红军石刻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极为壮观,世所罕见。
(五)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嘉陵江战役,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作战,为策应红一、红二方面军北上提供了成功而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月20日电令红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面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4](23)根据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至4月21日,历时24天,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歼敌12个团一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纵横两三百里的广大地域。“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5](P309)
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不仅策应了红一方面军(朱毛红军)长征北上,还策应了红二方面军(贺龙部队)长征北上,对于发展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支持和掩护,没有川陕苏区的桥梁连接作用,全国三大红军主力大会师、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出现更大、更多的曲折。
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西出川康,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六)川陕苏区受到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川陕苏区的重要历史地位,除了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高度评价外,还受到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关注和好评。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川陕苏区“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6](13卷,P316;14卷,P234、P237、P238)共产国际远东局还于1933年2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不要将基地迁到大巴山,指令:“你们的基地应在南江、通江和巴中地区一带,这几座城市应该作为你们的中心和立脚点。”“要尽一切可能在居民的积极支援下保卫已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南江、通江和巴中诸城市。”[7](P156-157)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应中共中央的请求,向川陕苏区派遣了军事专家。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川陕苏区是看得很重的,是高度关注的,认同川陕苏区“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没有相当的成就和实力,共产国际是不会轻言的。当然,共产国际也指出了川陕苏区和四川红军的“弊病”:“党团组织软弱”,“苏维埃后方组织得较差”,“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
二、张国焘的功过评说
张国焘是中共党内资深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主持召开党的一大,是一大三人党中央成员,中共首任中组部长(时称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负责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曾受到列宁的召见。1931年5月,由中共中央派驻鄂豫皖苏区,为中央代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领导苏区建设。
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时,张国焘、徐向前是一、二把手,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徐向前是总指挥、军委副主席。重大问题由张国焘决策、定夺。作为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主要创始人,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曲折和撤离,都与张国焘有关。张国焘有重大贡献,也有不少失误;有大功,也有过失。但总体看来,功大于过,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贡献比在鄂豫皖苏区大得多。诚然,张国焘在长征中拥兵自重,闹分裂,后来竟而叛党,但不能以他后来的错误、罪过否定他在川陕苏区的历史功绩。张国焘在反对国民党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发展苏区经济等方面的大政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与中共中央的方略是一致的。
(一)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重要贡献
1.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通江“两河口会议”,作出了在通、南、巴“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决策
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西行5000里后,来到通江两河口约120里的苦草坝,在此,张国焘主持召开了“西行后的第一次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今后行动的方针”。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7](P156-157)随后,红四方面军4个军“以通江为指挥中枢”,分兵行动,发动群众。
在两河口,张国焘草拟了红军入川第一张布告,《红军入川十大纲领》,号召贫苦农民“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剥削与掠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大家认同张国焘提出的纲领草案,实行红军入川的“约法三章,”即“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保障人民安全”。这个布告和“约法三章”很有政策水平,受到川北人民的拥护。
2.张国焘撰写了《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一文,宣传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的政纲,统揽川陕苏区的党政军要务
在川陕苏区,张国焘“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党政军事务,纷集一身,殊感忙迫”。与此同时,张国焘还很注重党和红军的思想建设,抽空撰写了一篇短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以清晰的语言,简炼的文字,将什么是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以及他们的性质、作用、目的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党的阶级斗争、政权建设、党的领导等理论,讲得清清楚楚”。[8](P366)
3.张国焘积极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绩
张国焘利用国民党驻陕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满,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做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工作。张国焘与武志平“进行了几次交谈”,武带来了一些重要情报和军用地图,张国焘要武设法建立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等,并“专门研究对杨虎城等人的策略”。随后,张国焘委派红军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到汉中与孙蔚如进行谈判,孙表示愿意为红军提供物资,建立秘密交通线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解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而且使川陕苏区“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加以消灭的妄想”。[8](P383)
4.张国焘的“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的指导方针,鼓舞了川陕军民,成为“反刘湘六路围攻战略指导思想的蓝本”
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的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张国焘作了一个题为《为保卫赤区消灭刘湘而战》的报告。在报告中,张国焘号召“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提出了许多“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举措,如联系群众的实际利益,以宣传队、画报、演说等多种形式,“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同敌人作决死斗争”,建立群众武装,支援红军作战,扩大红军,袭扰敌人,加强党团、妇女工作,发展党团组织,组织便衣侦探等。党代会“一致接受了国焘同志的报告”,号召“动员和组织川陕千万群众,扩大五万红军主力”,“彻底消灭刘湘,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8](P391)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后取得重大胜利,川陕苏区由此进入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威名大震,张国焘也名扬川陕。
5.张国焘等部署、指挥了嘉陵江战役,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北上
张国焘根据中革军委1935年1月22日要求四方面军“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电令,在旺苍坝召开了有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执行中央指示问题。徐向前回忆说:“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2](P289)会议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艰险,中央是不会开口下令的。旺苍坝会议决定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
张国焘回忆说:“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7](P208)徐向前说:“三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2](P294)嘉陵江战役歼敌万余,威震全川,达到了预期战略目的。
(二)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过失
1.延续了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错误,错杀了旷继勋等一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
在川陕苏区,张国焘没有纠正在鄂豫皖“白雀园”错杀许继慎等2500余人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以莫须有的一些罪名,错杀了红四军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 (1933年6月),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山 (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委、赤北县委书记刘杞传(1935年冬)等一批领导人。据川陕苏区研究专家统计,川陕苏区被错杀的干部群众约2万余人。[9](P304)
2.实行了过左的土地、工商政策
张国焘在土地革命中,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查田运动中将一部分中农划成富农,将一部分富农划成地主,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主张没收中小工商业,而不是采取扶持、鼓励的政策,遏制、影响了苏区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3.轻视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
张国焘只要正规军,轻视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做扩红的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充主力红军,影响了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
4.采取了一些过火的反对宗教迷信的做法
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开展“反对宗教迷信”,打菩萨,毁庙宇,伤害了苏区一些民众的信仰和情感。
5.实行家长制,压制党内不同意见
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党内许多同志一直很有意见。徐向前、曾中生、旷继勋等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挽回过一些损失。徐向前回忆说:“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张琴秋、朱光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2](P162)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采用各种手段压制不同意见,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三、几个相关热点问题的判断与感悟
列宁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10](P492)
川陕苏区的历史是很复杂的,红四方面军的道路是很曲折的。正确和错误的东西往往交织在一起,有的问题讳莫如深,有的问题很敏感,见仁见智。这里仅说三个问题,破除三大误区。
(一)所谓“逃跑”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政界都把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说成是“右倾”、“逃跑”,现在看来这种指责是不客观、不公正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不是“逃跑”,而是“西撤”,如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一样,是“突围”,是“战略转移”。当事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军处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2](P149)。“为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保存有生力量”,红四方面军根据“黄柴畈会议”的决定,实行突围、西撤,向川陕边境退却,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种战略退却,是必须的无奈之举,是一种被迫而为的必然抉择。
(二)“放弃”川陕苏区问题
过去,学界、政界一直是指责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是“擅自放弃”。这种说法也是不客观的,实际上不是“擅自放弃”,而是事出有因。当事人徐向前分析此事时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如果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二是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导致苏区财力枯竭。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了,鱼还能活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2](P301)三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当时,中央有电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于1935年1月22日电示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2](P302)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资源枯竭的困境,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这些元素“凑到了一起”,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西路军的失败责任问题
西路军的源头在川陕苏区。西路军是从川陕苏区出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长征胜利后由中央组建的红军部队,然而兵败祁连山,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灭。长期以来,把西路军的惨败归罪为“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是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到西路军问题时,陈云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实际上,西路军的失败,张国焘没有责任,西路军从组建、渡河、转战河西走廊,重大行动都是中革军委决策的,西路军一直处于“西进”与“东返”的争论与徬徨之中,折腾了三个多月,以至多次贻误战机,被“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吃掉。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等在执行中也有一定失误,但不能将失败的责任强加在张国焘头上。张国焘一没有随军出征,二没有乱发指令,三没有参与指挥。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对张国焘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近10年多来,在一些史学专家的努力下,在陈云、李先念的干预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已开始廓清,逐渐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从而为西路军的公正评说作出了不可逆转的权威结论。
总之,研究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讲真话,写真史;一定要客观公正,功过分明,功是功,过是过,不要讲功不讲过,也不要以过否定功;一定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评价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人和事;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解说和宣传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伟大历史功勋,要拂去阴影,不要因张国焘的某些过失而失去底气,遮遮掩掩。作为史学工作者,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要恪守学者良知。
[1]苏维埃中国[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1957.
[2]徐向前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红四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资料丛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8]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9]温贤美,等.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