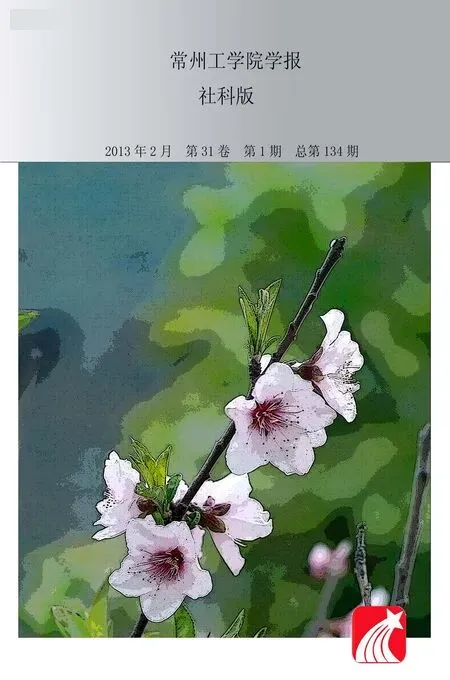后大屠杀语境下的沉思:《复仇女神》中的受难式英雄主义
李俊宇
(宁德师范学院外语系,福建 宁德 352100)
国内学者钟志清在论述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时使用了“后大屠杀”这个术语[ 1]52,“后大屠杀”即“犹太大屠杀发生后”。而“后大屠杀语境”指的是犹太大屠杀发生后人们对这次灾难的探讨、认识与反思所形成的话语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的一段时期,许多幸存者都不愿提及那段惨痛的历史。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沉默后,后大屠杀话语以各种形式使人们回视那段历史,而且这种话语随着《安妮日记》的出版和在以色列举行的艾哈曼审判逐渐变得强势起来,“突然大量关于犹太大屠杀的书籍、文章、会议、电影等出现在美国”[2]127。诚然,正视与反省这段历史,惩罚落网的法西斯分子乃天经地义。然而,这种后大屠杀话语被掺进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在后现代语境中,西奈山最终被奥斯威辛所替代,犹太身份认同直接建立在大屠杀记忆或‘后记忆’的基础上。”[3]110犹太身份中被铸进了受难者的内涵,犹太人与受难者如影随形。这样,后大屠杀话语赋予全世界的犹太人受难者形象。这种受难者形象之所以容易被建立,是与犹太文化本身存在的受难意识或受难精神有关,犹太宗教认为,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要受难的,“受难精神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一种文化密码或思维方式”[4]57。受难精神中并非只是单纯地接受受难,而是要主动地去承担责任,并最终获得救赎。与之相呼应的是,二战后犹太领导人倡导一种“英雄主义”,在以色列的复国运动中,“历史创伤就这样被铸造成了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以适应新的社会与政治需要”[1]54。这种英雄主义在受难意识的沃土之中得以催生。因此,可以说,英雄主义在以色列犹太人中的复活是后大屠杀语境下的产物,它与受难精神相勾连,并借犹太大屠杀话语扩散并植根在部分美国犹太人的思想意识中。
菲利普·罗斯在作品中并不回避犹太大屠杀这个令许多作家难以表述的沉重的话题,他不仅多次暗示了犹太大屠杀在犹太人意识中的存在,并且在《夏洛克在行动》(Shylock Operation,1993)等作品中直接探讨了犹太大屠杀问题,这说明他在创作中有一种后大屠杀意识,这种后大屠杀意识与后大屠杀语境息息相关。那么,他与后大屠杀主流话语是否一致呢?他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后大屠杀语境下的英雄主义呢?本文通过细读其新作《复仇女神》(Nemesis,2010)加以探讨。
一、《复仇女神》中的受难式英雄主义
《复仇女神》是一部虚构性很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纽瓦克地区流行小儿麻痹症疫,体育教师布奇·坎特带领学生们与瘟疫抗争,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但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小儿麻痹症病毒携带者,坎特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并从此一蹶不振。彼得·海勒格指出,“小儿麻痹症疫与大屠杀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类比关系。”[5]31小儿麻痹症疫发生在犹太人社区,与犹太大屠杀同为犹太人的灾难,所以海勒格的这个说法颇有道理。在《复仇女神》中,纽瓦克犹太人社区与“印第安山”分别喻指发生大屠杀灾难的欧洲、以色列或美国,而坎特的“逃离”喻意为犹太人从欧洲流落到以色列或美国。
在小说中,犹太小孩遭到了小儿麻痹症疫的袭击,对犹太人来说这场灾难是一个悲剧性事件。而以坎特为代表的一代犹太人最终的一蹶不振更是一场悲剧,抑或是悲剧的延续。造成坎特悲剧的因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更多的是后者。尽管他患上小儿麻痹症,身体落下残疾,然而坎特最终被击倒却是因为其精神世界的崩塌。而支撑他精神世界的是受难式英雄主义。坎特式英雄主义的基础是其祖父所培养的男子汉气概。在《复仇女神》中,当坎特来到“印第安夏令营”布罗姆柏克先生住处时,布给他介绍汤普森·西顿及其著作。“一个伟大而有影响力的导师。‘男子汉气概,’西顿说,‘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他们一直坚持英雄主义的人类理想。……他们认为所有力量的基础是自控。‘最重要的是,’西顿说,‘英雄主义’。”“坎特点点头,同意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即使他以前从没听说过西顿这个人。”[6]146-147这说明坎特很容易认同西顿的英雄主义观,因为西顿所说的男子汉气概恰好与坎特从其祖父那里承继下来的相吻合。
坎特式的英雄主义是一种耶稣受难式的英雄主义。坎特有一种强烈的罪责意识,一种受难心理,并将这种受难意识转化为受难精神,这种受难精神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变成了受难式英雄主义。这种受难式英雄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过分的内省与自责,并因此而背负起沉重的心理和精神包袱,然而,这些本不应由他来背负。当他因为视力很差没有能像儿时好伙伴一样奔赴欧洲战场时,他不断地责备自己;当他因为恋人的“怂恿”而“逃离”纽瓦克犹太社区来到“印第安山”时,他又责备自己,并给自己判了“背叛”罪,尤其是在小儿麻痹症疫的传播这件事上,他竟认为自己应该对瘟疫的传播负责。总之,坎特将外在的责任内置于自己,承担起“错置的责任”[7]124,并“转化为内疚与自责”[6]265。坎特是部分犹太人的一个典型例子。罗斯的好友,著名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作家阿哈龙·阿帕菲尔德曾在与罗斯的对话中提到,“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对那些不自卫的大屠杀牺牲者作出苛刻而严厉的评价。而犹太人将这些责难与谴责的言论内化,这种内化的能力真是人类本性的一大奇迹。”[8]37
在坎特受难式英雄主义过分的内省与自责中,责备的对象指向的是自身。在整个小说中,表面看来,坎特责备的对象除了他自身,还有一个是上帝:当坎特因为瘟疫无情地夺去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的生命而陷入精神上的痛苦时,和许多犹太民众一样,对上帝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其实,坎特对上帝的责难与对自身的责备是一致的。在该小说中,我们并不清楚坎特具体的宗教信仰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但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上帝与人都是紧密联系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对上帝的信仰其实是对人自身的肯定,在走向世俗化的基督教中更是如此。那么,质疑上帝就是质疑自己,责难上帝就是责难自己。在小说中,从表层逻辑上看,坎特因多次抱怨上帝并责问上帝,因而受到了上帝的严厉惩罚,因为上帝是个强大的力量。其实,罗斯从深层意义上表明,坎特是在惩罚自己。受难式英雄主义者过分地内省与自责,不断地惩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虐待。这种自我虐待是对自身的残酷,这种残酷虽针对的是自己,但在客观上也伤害了他人,尤其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而且,具有受难式英雄主义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往往残忍地割舍亲情、友情和爱情。《复仇女神》中坎特残忍断绝与未婚妻玛西娅的关系就是例证。而这种对自我的残酷与客观上对他人的残酷是与人本关怀相对立的。显然,受难式英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人本关怀,尤其是对自身的人本关怀。这是受难式英雄主义的又一特点。
二、受难式英雄主义的局限性
诚然,英雄主义有它积极的一面。坎特的祖父是犹太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英雄式人物,他无所畏惧地反抗法西斯势力,并将这种反抗精神传给了坎特。从罗斯对坎特祖父高大形象的描述和对坎特在运动场非暴力赶走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勇敢行为的叙述来看,罗斯肯定了坎特祖孙俩的抗争精神,也就是肯定了英雄主义积极的一面。但受难式英雄主义有其局限性。首先,英雄主义在某种历史环境中往往是最容易被击倒的,因为它忽视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忽视了人性中的弱点;它挑战并试图越出人承受能力的极限;英雄主义极易将血肉之躯的人神化。英雄主义者在认同别人对自身的神化时,也下意识地将自身神化,把自己当作拯救他人的救星,为自己叠加了过高的期望。而当现实打碎这种期望时,英雄主义者会无法接受所谓的“失败”,也无法接受自身的缺陷。《复仇女神》中的坎特就是一个典型,他一心要阻止病毒的传播,而当他发现自己也是病毒的携带者时,他整个精神世界都坍塌了。其次,如上文所述,受难式英雄主义的一大特点是过分的内省与自责,过分的内省与自责会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巨大包袱,以致于“头重脚轻”, 而“头重脚轻”的东西往往极易坍塌;金字塔之所以坚固,乃是因为它“头轻脚重”。同样,一个背着沉重包袱踉跄而行的人,是极容易跌倒的;而且一旦倒地,身上的包袱会将他彻底压垮;反之,一个没有精神包袱的人能够以较为轻松的心情坦然面对现实,即使偶尔“绊倒”,也能迅速“爬起来”,重新开始生活。在《复仇女神》中,与坎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虽同样遭受了瘟疫的打击,但“我”却能够正视身体残疾的现实,重新“站立”起来,并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另外,过分的内省与自责会直接打击一个人的信心,导致其不断地怀疑自己,并从精神上击垮自己。这是受难式英雄主义的局限性。
受难式英雄主义的另一大局限性是,它无法真正抵挡恐惧这种“病毒”的攻击。在该小说中,罗斯将“恐惧”比喻为“病毒”,即病毒式的恐惧。病理学上的病毒会直接摧垮一个人的肌体,而精神病毒“恐惧”则会击垮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亚瑟·本森的研究表明,“恐惧具有使人瘫痪的力量”[9]6。而且恐惧可以传染,正如病毒可以传染一样。在疫病流行初期,坎特耐心安慰孩子们惊慌的家长并提醒道:“重要的是不要让孩子们感染恐惧的病毒。”[6]38“不要让孩子们感染恐惧的病毒”,也就是不要让美国犹太孩子感染犹太大屠杀的恐惧。在这里,罗斯以意大利反犹分子指代大屠杀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以病毒来隐喻法西斯分子给犹太人造成的恐惧。一开始坎特在灾难面前还能保持镇定,并试图减少恐惧对体育场上孩子们的影响,但实质上他自己很快被恐惧所控制并击倒了。受难式英雄主义者希望别人不要受恐惧的影响,但由于受难式英雄主义总将责任指向自己,因此英雄本身往往被恐惧这种“病毒”所摧垮。在小说中,罗斯并未给出造成体育场的犹太小孩感染小儿麻痹症疫的真正原因,意大利人故意到操场吐唾沫并宣称是散布病毒的根本目的是传播恐怖。其结果是,恐惧使得坎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动摇,坎特狠心与未婚妻断绝了关系,其实是深深地伤害了对方,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意大利反犹分子完全达到了他们邪恶的目的。
而且,受难式英雄主义并不能带领人们走出灾难的阴影,因为如前所述,受难式英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人本关怀。在小说中,主人公坎特与“我”之所以在灾难后有那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我”对生活、对人类包括对自己一直充满了爱。爱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爱体现出强烈的人本关怀;而坎特却因为一心要做一个受难式的英雄,排除了这种对自己的人本关怀。他用自责与内疚的利剑无情地刺向自己的心灵,当他在伤害自身的时候,也同时伤害了他所爱的人。在小说中,坎特与其未婚妻玛西娅之间原本有着纯真美好的爱情,但坎特却让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和内疚感扼杀了这种爱情。事实上,坎特的行为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都是残酷的。玛西娅是位能在灾难中保持镇定的坚强女性,她非常希望坎特能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她在1944年7月给坎特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了四行“我的男人(man),我的男人,……”[6]151“我的男人”重复了二十次,这是玛西娅发自内心深处爱的呼喊。而且,my man一词也可以理解为“我的人类啊!”在这里,罗斯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女性,并在她身上倾注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罗斯意在表明:尽管发生了悲剧,但是人们如果正确看待,仍然可以活得很好。灾祸本已经是悲剧,如果还要延续这个悲剧的负面影响,这不正是法西斯分子在制造恐惧的病毒时所希望看到的吗?以色列政府倡导英雄主义,使得部分大屠杀幸存者心怀内疚,因为他们在灾难发生时并非“英雄”;而且受难式英雄主义以残酷对待残酷,就是延续了残酷,以色列建国后与周边阿拉伯国家流血冲突不断,这不也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怀吗?因此,受难式英雄主义在解决如何应对灾难、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因为受难式英雄主义的这些局限性,所以罗斯借坎特的例子对这种在后大屠杀语境下复活的英雄主义话语予以反拨。
三、结语
总之,在《复仇女神》中,坎特奉行的是一种受难式英雄主义,过分的内省与自责是其最大特点,而且它拒斥了人本关怀。坎特在灾难的打击下一蹶不振的悲剧性结局表明了受难式英雄主义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无法真正抵挡恐惧这种“病毒”的攻击,也并不能带领人们走出灾难、重新创造美好生活。受难式英雄主义是后大屠杀主流话语中的一部分,罗斯对此进行的反拨表明了他与主流话语并不一致。其实,罗斯在以前的创作中一直试图远离后大屠杀的主流话语,譬如他一直反对将犹太身份的建构与大屠杀相连,“罗斯一以贯之地讽刺这种身份政治”[10]54。罗斯在被掺进了意识形态的后大屠杀语境中坚持的是一种独立、务实的立场。他在作品中认为,大屠杀对幸存的犹太人的影响与对年轻一代犹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一直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与有过欧洲生活经历的犹太人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大屠杀,罗斯在其作品中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经历与美国经历的区别上。”[10]54在《乳房》中,主人公开普什对犹太大屠杀的恐惧是外部世界强加给他的,并“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焦虑”[ 11]34。年轻的美国犹太人更多地是受到后大屠杀话语的影响,这种话语让他们背上历史包袱,并获得“受难者”形象。而罗斯用《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1979)对《安妮日记》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后大屠杀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受难者形象”[ 12]59,从而试图使犹太人摆脱这种“受难者”形象的束缚。罗斯通过其作品表明:美国犹太人不应该背负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包袱,也不应该生活在犹太大屠杀的阴影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的创作往往突破了犹太文学的阈限,其作品的主题上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思考的高度。在这部作品中,罗斯描述了人在遇到灾难时的内心想法与精神抗争,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如何应对灾难、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作品也可归入后灾难文学范畴。
[参考文献]
[1]钟志清.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4):52-54.
[2] Hasia R D.A New Promised Land:A History of Jews in America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7.
[3]林斌.“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J].外国文学,2009(1):110.
[4]季水河,陈娜.《裸者与死者》中的犹太身份意识解析[J].外国文学研究,2012(1):57.
[5]Peter Heinegg.Tragedy Without a Hero [J].America,2011(4):31.
[6] Roth Philip.Nemesis [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38-273.
[7]金万锋,邹云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耻”——评菲利普·罗斯新作《复仇女神》[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23-124.
[8] Philip Roth.Shop Talk [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7:37.
[9] Arthur C B.Where No Fear Was[M].Montana USA:Kessinger Publishing,2009:6-58.
[10]Rothberg Michael.“Roth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M].Timothy Parrish,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53-60.
[11]李俊宇.历史的阴霾,现实的震颤,未来的茫然——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的恐惧主题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34.
[12]刘文松.《鬼作家》对《安妮日记》的后现代改写与困惑[J].当代外国文学,200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