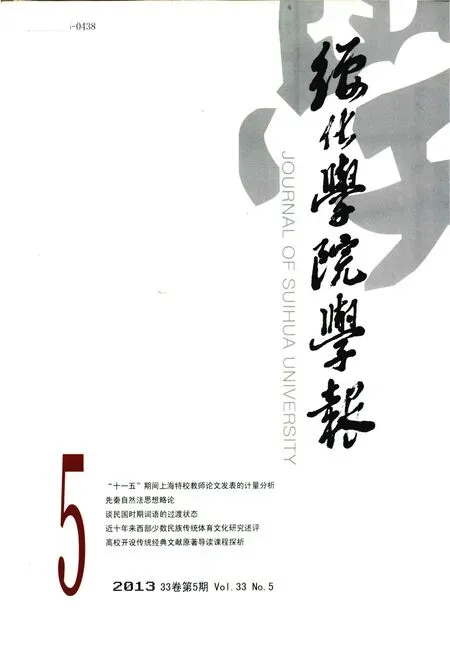寻梦于神性世界:论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与理性文学思想
李修元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铜陵 244000)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这一个”,又是一个寻梦于神性世界的理性存在。沈从文从荒蛮、偏僻的湘西走进了都市,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都市文化圈。因此,他便立足于湘西世界,用一种“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都市世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赞美人性、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以诗意来展示湘西神奇优美的民俗风情画卷而在文坛上奠定了不朽的地位。“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关键”。[1]可以说,沈从文在寻梦于神性世界的心灵深处隐含着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体现为一种自我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性人格。这或许是进一步深入探讨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把钥匙,同时,研究沈从文生命哲学的理性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也极富启示意义。
一、生命哲学:人性与神性
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明确提出“美在生命”这一人生命题。他在《水云》中说过:“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由作家的“生命信仰”再延伸到他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在沈从文看来,人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必须自我超脱的“生活形式”,即人的生存及生理需求;另一种是人生的精神境界即“生命形式”,它不仅表现着自然人的“本性”,还蕴含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充满爱与美的生命形式的“神性”即人生理想。在沈从文看来,神性与人性的自然融合,是人生追求之最高理想标准,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创造上更应完美体现。因此,沈从文在繁华的都市世界中寻梦于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湘西世界,以犀利的秉性反抗并批判国人对现代物质主义倾向的同时,追寻超越世俗的人生价值。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沈从文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学上创造了理想的生命哲学,以爱和美唤起国民“人性”中的“神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便是一个典型的令人神往的“神性”世界,是用“爱”和“美”构筑的一个世外桃源。因此可以看出,沈从文崇尚的生命哲学是寻梦于以人性为内涵的神性世界。
二、文学追求:批判与重造
民族灵魂的重铸和深掘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动荡的时代和现代人性堕落的现实促使沈从文极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他对文学追求的强大动力正是源于对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深忧患。他执著于文学创造来张扬理想的生命形态,以实现文化的变革与民族人格的重构,他倾注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捕捉与思考,体现出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文学追求赋寓深沉的现代性品格。实际上,沈从文倡导的民众和民族的文化改造,在本质上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主流文学提出的社会革命,但在“人性的解放”,“精神重造”及改造“国民灵魂”的基本主题上又与“五四”启蒙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因受现代性与局限性的双重影响,使他的文化思想难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也因此而形成了风格独特而内蕴丰富的“沈从文现象”,彰显了作家的创作理想和艺术品位。
沈从文笔下的城乡呈现着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道德与审美视角,乌托邦式的理想,民族重造的希望,病态人性的批判及现实生存的困境等,构成了二元框架里五彩缤纷的内容。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明显呈现着两极形态:乡村的美丽、静穆与城市的堕落、混沌。这也是他们在多重文化冲突中作出的文化选择。正如凌宇所说:“沈从文是从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道德的退步,即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角度透视都市病态的。这类作品主要有《萧萧》、《柏子》等。汪曾祺说过:“《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是与现实中丑恶虚伪作对比。所以有论者说:“它有文化批判的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的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3]沈从文企图以生命的强力来滋养文明侵蚀下的人性的枯萎,抗拒人性的扭曲和病态,当然也不乏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和不健全人性的反思。沈从文希望回复“童心”,以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青春活力。
三、创作风格:诗化与神蕴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一类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而其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构了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描写了湘西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颂了人性美。“在他成熟的时期,他对几种不同文体的运用,可以说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计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4]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同时还供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不仅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而且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作品用散文的笔调和诗歌的意境淡淡写来,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只有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情不自禁的感情流动。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融合在“水”做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画”,也是“诗”。
沈从文的乡土题材小说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很诗意地讲述他年轻时节经历见识过的人和事,将生命挣扎的粗犷同生存泥涂的险恶,皆用小说形态作诗意的抒写。在短篇小说《柏子》中,沈从文写到湘西,写到他记忆中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到他熟悉且关怀的那些在社会底层顽强挣扎的人物命运,他的笔好像具有了一种魔力,字里行间便充满温情的缅想和悲悯的情绪,那些山光水色,平常人事,只要轻轻点染勾勒,便发出一种美的光辉
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萧萧》就是作家最富有写实意味的作品之一。作品以小说联结着风俗散文与爱情歌谣,自由结构使小说融入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
除了小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司马长风说过:“沈从文的笔是彩笔,写出来的文章像画出来的画。画的是写意画,只几笔就点出韵味和神髓、轻妙而空灵。……沈从文的散文,则像顺流而下的船,不着一点气力,‘舟已过万重山’”。[5]其散文那种诗化的文体与诗意的抒情带有牧歌的特征,他常常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娓娓道来,真切而富有历史感,饱蕴作者的故乡情思与现实思考。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从水手与妓女的缠绵相恋中进行着爱欲即为生命、生命契全自然的人性的哲理思考,这种违背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原始主义的人性理想。地域性、民族性及人性仍是沈从文散文着力表现的主要方面。
在文体结构上沈从文善于追求千变万化,形态各异,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几乎不找不出两篇结构完全雷同的作品来,堪称可贵。如《八骏图》是橘瓣绽开式结构;《大小阮》是双线结构;《月下小景》是连环套式结构等等。
四、独立品格:自觉与理性
沈从文从艺术创作、文学理想及自身生活实践对文化人政治与人格的理性自觉与自省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刻反思。鉴于政治、商业文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奴役与侵蚀的社会环境,对于文化人独立自由人格的坚守,沈从文始终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惕。
首先表现的是现代的忏悔精神与理性的深沉反思。对于人格奴化的警醒,沈从文通过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他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应该具有独立的个性人格和独特的创作思想,所有艺术创作都需要有个性,都必须渗透作家的人格、感情和思想。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由此可见沈从文作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的深一层意义和原因,这“深一层意义”就是沈从文现代的忏悔精神与理性的深沉反思的最好体现。
其次是高扬学术本位与理性的审美精神。他的许多朋友加入了党派,而他自己却从未加入何类政党,这是他自觉意识的理性表现。沈从文认为,文学家应高于政治家,这便是他理性的批判精神的突出体现。他倡导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6]他主张政治与文学之间应该建立一种较为理性的关系,可见,对于作家主体的自我塑造来说,宣扬本位与理性的审美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坦诚和正直是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独立品格,沈从文一直反对文学被沦为金钱的娼妓,更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重,却是始终如一坚持文学家的人格和艺术至上的创作观点。身在大都市,商业宣传与活动难免时有发生,但沈从文一贯保持警醒的头脑,以免丧失文化人独有的个性品格而陷入低级趣味,如若那样,所谓的作家,也只能创作出敷衍、世俗的“白相文学”,相对于学术本位而言,那就是一种艺术堕落。他在批评左翼文艺运动时说过:“并不在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宣传革命的政治观点,而是集中在一部分作家只要‘思想’,不要艺术,空有血和泪,而无实在深入的人生描写,以至宣传思想而不注重艺术所导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化”。“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却‘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7]沈从文的审美思维具有理性精神,而其人性品格则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惟其是理性的,他对生命哲学的追求才凸现了永恒的理想主义情怀;惟其是浪漫的,他的文学思想才蕴含着坚韧不拨的理性主义光辉。
[1]何小平.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46-50.
[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1):45.
[3]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9.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家史[M].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11.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6]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J].文艺先锋,1942(2).
[7]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