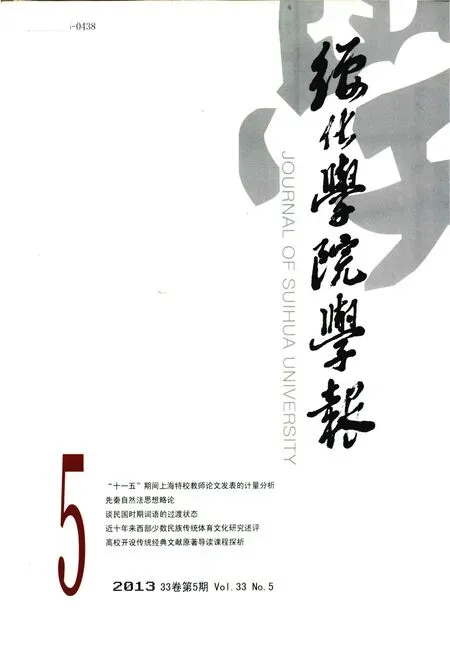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死亡”叙写中的三种关系——《生死百年》与《活着》比较
罗兴国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生死百年》是2011年出版的闵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是1993年出版的余华在小说创作转型期中的长篇力作。从小说创作时间上来看,虽然两部小说大致相差十七八年的时间,但从小说的内容上来看,两部小说却十分相近。可以说两部小说讲的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关于死亡的故事。《生死百年》讲闵家族人及与其有关的人在历史莫测的长河中艰难的挣扎,终一个个地死去。《活着》讲徐富贵的亲人在苦涩的历史中,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一个个地死去。“死亡”是贯穿两部小说的主线、主题,也是两部小说中人物的终极命运,死去的人已经死去,而活着的人也终将死去。当面对死亡时,由最初情感的剧烈震荡,到最终情感的平淡、释然。在小说中刻意去遮蔽、隐去这种情感也好,释放、表现这种情感也好,“死亡”对人们情感的冲击永远是最犀利而深透的。《生死百年》与《活着》就是围绕以下三种关系,对“死亡”进行冷静而透彻的叙写的。
一、人与历史
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写了在中国曲折历史中人不断死去的命运。很显然,在人与历史之间,历史对人的决定性是更大的、更有力的、更普遍的。两部小说共同涉及到的历史背景有土改、大跃进、三年饥荒灾害、文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经历着共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命运,有人生存下来,有人死去。《生死百年》中的闵少卿和《活着》中的富贵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在土改的历史浪潮中,他们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曾经都是地主,都是靠剥削贫下中农过自己好日子的人,而他们又都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嗜赌如命。闵少卿在赌场中把家底输个净光,富贵也把百亩田地、家中宅子等家财都输给了龙二,结果两人都因输光家产而由地主落为了贫农,而特殊的历史却给予了他们非常态的命运。土改中,他们因为是贫农不但得以活命,而且还受到了一定的照顾。反而是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的、赢了钱的人一命呜呼了。所以在两部小说中,同样的历史赋予了他们同样戏剧化的命运,而最终他们的命运却又是不同的。在土改的浪潮中,闵少卿虽然输了家产,顺风顺水地活了下来,但到了大饥荒的年代,历史就没有再次眷顾这个曾被认为是举人湾最幸运的人,在自己和家人被饥饿重压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在夜晚偷偷去打渔时命丧青衣江。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挣扎,在岸上两个儿子默默的注视中消逝于江雾中。历史决定了他的饥饿,他没有能力去反抗历史,但他有权利反抗饥饿,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再看《活着》中的富贵,他和闵少卿在土前土改中都有着同样的命运,但在大饥荒时期两个人的命运就分道而各异了。富贵也是因输光家产,使得赢了他的钱的龙儿替他去死了,他在土改中得以活命,可以说他也是幸运的。如果说在土改中这是他的幸运,那么他在大饥荒年代得以继续存活下去,那就是他生命的韧劲了。在一家人的共同忍受与扶持下他们度过了大饥荒年代,使生命得以继续向前艰难延续。在他个体弱小的生命与历史大饥荒的对抗中,他胜利了,他仍然活着。所以可以看出,如果说闵少卿和富贵输光家产而在土改中的得以活下来是一种历史的不经意偶然的话,那么在历史的下一道沟壑——大饥荒当中闵少卿因饥饿而死去,富贵经历饥饿仍然活着,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历史对生命的严酷考验下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死亡,一是活着。历史在冥冥中注定了一些人的命运,无论你如何挣扎你都不能逃脱,在历史面前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卑微的弱者,无意识的消亡者。
在人与历史这一层面,从两部小说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两部小说虽然同写历史、同写历史中人的命运,但最终的落脚点却不同,《生死百年》写一个家族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生生死死,而其最终的落脚点是“百年”,即百年中国历史,而“死亡”只是构成这历史苦涩风景的色彩之一。如作者所说:“所以,我从故乡的小山写起,一路寻找百年中国之足迹,述之为文,与大家分享我在这种寻找中的感动与思索,也算为这段澎湃的历史作个小注。”而《活着》写以富贵为中心的一家人在近半个世纪历史风雨里的生死,其最后的落脚点是“活着”。所以在人与历史这一层面,《生死百年》更注重的是历史,写死亡也是为了历史,而《活着》更注重的是人,写死亡时为了活着。也因此,《生死百年》中对于历史的涵盖,包括其所涉及的人物都要比《活着》丰富些。那么从反面来说,越是着力于历史与人物的丰富性、涵盖的广泛性上,那么相对一般其深入性与穿透性就薄弱些。而其薄弱处正在《活着》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弥补。即《活着》中对于历史的苦难、对于人的苦难的超越性。“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作的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人活着只为活着本身的存在,而不是为了历史或为了苦难或是为了自己等其他事物。这是《活着》最真实的力量。
二、人与人
无论在任何历史境况下,历史对人的命运的决定性都是不容否定的,当然这命运中也包含着人的生死。而在大的客观历史下,对人的命运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的,还有另一因素,那就是人。与历史对人的绝对客观影响不同,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与决定多是带有主观刻意性的,当然也有些是主观无意识的。但人对人的命运的决定性无疑是存在的。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生死的决定。尤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相对立的两种人之间。在两部小说中,在共同的死亡的命运下,人与人之间简单而直接的关系却体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在《生死百年》中两个革命小将来到举人湾,在天龙寺中打砸烧毁“封建余孽”,而寺中的两个和尚延均和延平在一旁平静地为革命小将端茶倒水,没有丝毫伤心和异样,结果,两位革命小将门牙黑了一半,被两个和尚给毒死。显然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在这个事情中,革命小将是批判者,是强者,两位和尚是被批判的对象,是弱者,革命小将“理应”去扫除他们眼中的“封建欲孽”,而两位和尚“理应”检讨自己,承认过错。但结果却是两个和尚在两位革命小将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毒死。两位革命小将死于非命,而两位和尚继续生活下去。而《活着》中文革时期春生被打为走资派,被红卫兵抓去批斗,挂牌游街,大喊毛主席万岁,又被红卫兵骂,“这是你喊的吗?他娘的走资派”[2]之后被打倒在地,脑袋被踢得咚的一声响,之后整个人趴倒在地。一个多月后春生便上吊死了。革命卫士们在斗争中胜利了,他们的批判让“敌人”最终一败涂地,自杀认罪。作为被批判对象的春生则在斗争中默然死去。春生的死在他们来看是罪有应得。红卫兵继续以他们狂热的生命来不断冲击那些的将被打垮的生命,而春生生命的消逝只是对红卫兵们的批斗的一个没人在意的“正确”的回应而已。、
所以可见在两部小说中,同样是写文革时期的两种人的关系,即批判者红卫兵与被批判者两个和尚及春生的关系,他们的关系都是单向对立的,即红卫兵把他们看成对立的批判的对象,而他们却不得而知这是为什么。但这相同的关系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在《生死百年》中这种人与人之间单向对立关系的最终结果是主动的批判者、相对的强者的红卫兵的死亡。而在《活着》则是被动的被批判者,弱者的春生的死亡。所以可以看出两部小说中的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实际是一种相互的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生命形态,展现了生命的两种必然——生或死!这是这两部小说在共同的“死亡”的主题下,所展现出人与人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偶然与宿命。
另外,在另一个层面,如果将小说的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也视为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在《生死百年》与《活着》中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是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在《生死百年》中作者闵良与小说中的人物的距离拉开的比较大,其关系比较疏远。而在《活着》中余华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实际是很近的,其关系也是比较近切的。所以从直观感觉上看两部作品,《生死百年》中闵良写人物的死亡与种种艰难命运,他始终是保持了客观的、旁观的、冷静的创作者的身份的。而《活着》中余华写人物的死亡与困苦命运,他表面虽然也是冷静、客观、旁观,但其实际对作品中的人物投注了太多的主观情感,其内心中对作品中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说又难以回避、难以割舍的悲悯思绪与情感。“不论善恶,他都要保持一种理解后的超然,并由之产生一种悲悯心,这也导致了他进入90年代之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风格转变:这些小说在描写底层生活的血泪时仍保持了冷静的笔触,但更为明显地加入了别天悯人的因素。”[3]这就使得作品在对极端生命形态冷静抒写的同时呈现出了一种默默的温情。“重视写作的余华自然要将‘为内心写作’当作自己最高的艺术原则,《活着》出版后,人们从活着中读出了种种意义,余华却只认同‘让内心真实作主’的说法,不是毫无道理。”[4]这回答了《活着》中温情来自哪里,即来自内心。
三、人与自身
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应该是最近的,但也是自己最容易在无意识中忽略掉的。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死的决定,除了历史因素、其他人的因素之外,自身因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人对自己的生命具有一定的决定权,这种决定就必然会包含不平衡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一方面是死。而不平衡则是人不一定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但人绝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当然这其中还包含了一层无意识的、偶然的因素,使得自己的生死具有了一种不可测的、冥冥注定的色彩。在《生死百年》与《活着》中都有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走向死亡。而这种自杀也既是可以与历史因素有关的,也可以是与历史因素无关的。《生死百年》中四爷爷投水自杀,《活着》中春生上吊自杀。他们都已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式选择死亡。但明显《活着》中春生的自杀是带有直接的历史因素的,而《生死百年》中四爷爷的自杀其历史因素很为淡薄。主要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扭曲而导致的四爷爷自杀。但从另一方面说春生完全可以选择活下去,虽然这种存活是非常态的,是艰难的、屈辱的。但最终他仍然选择自我了解。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就在于他自身对他的阻挡,他无法越过;自身给他的重压感,他无法继续负担;他自身给他带来的绝望,他无法回避、更无法超越现实自身悲苦的存在。所以春生选择自杀,结束自己难以承受的生命之悲苦。而四爷爷戒男女之礼,一辈子未娶,一心只读他那几本圣贤书,三次跳水都被人救下,没死。第四次终于如愿,淹死于犀牛塘。其实四爷爷也可以选择继续安静地活下去,其自杀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缘由,但最终四爷爷选择自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厌弃、一种孤独的冷漠、一种偏执的解脱。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四爷爷被自身所围困,而且这种自身的围困越缩越紧,四爷爷无法挣脱,终选择一了百了的方式,使这自身的围困与自己的生命同时消尽。所以小说中两人共同的选择自杀,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其背后其实都是自己与自身之间裂变却又难以维持或调和这种裂变的结果。
有些时候,有些人的“死亡”呈现出一种自身的无意识状态。即他并不是要刻意自杀、也根本没想自杀,而结果却又自己杀死了自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人与自身之间突然的接近,近到无法看清自身;是一种人对自身异常的清醒,清醒到完全忽略了自身;是一种对于自身太想生存,以至于最终死亡的至极而反的关系。《生死百年》中的黑豆和《活着》中的苦根就是如此。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可以说是几乎完全相同,《生死百年》中黑豆的父亲汪武上山挖洋芋时,摔断腿,被冻死在山上。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掉进青衣江淹死。只剩下黑豆继续活着,而最后黑豆却吃了太多生肉而把自己撑死了。《活着》中苦根的父亲二喜干搬运时被两块水泥板夹死,母亲凤霞在生产后大出血而死。只剩下苦根跟着富贵,但最终苦根却吃豆子把自己撑死了。两个孩子都以自己的双手把自己送上死亡之路。而这一切对于他们自己却又是无意识的。他们的想法很纯粹、很简单,在本能的驱使下,他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无懈可击的对自身的谋杀。这种“死亡”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在不经意中笑着拥抱自身时用力过大而把自身勒死的悲剧。这种悲剧的呈现使得小说中的“死亡”在带上了一层荒诞色彩的同时,也显得更为单纯、深沉。“从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内心中,发现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4]。这是这两部小说在文本背后要表达的中心内涵。
上述《生死百年》与《活着》中的关于“死亡”叙写之中的三种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也是包含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只是它更近切、本真些。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包含在大的人与历史的关系中的,只是它更具体些。所以总归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人与历史,更具体的说是苦难的历史与苦难的人生,而这些苦难的历史与苦难的人生终归是该有个结果的,对于一些人,这个结果就是死亡!这种死亡在小说中是冰冷的,但穿过死亡之后却是温暖的。
[1]闵良.生死百年[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2]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