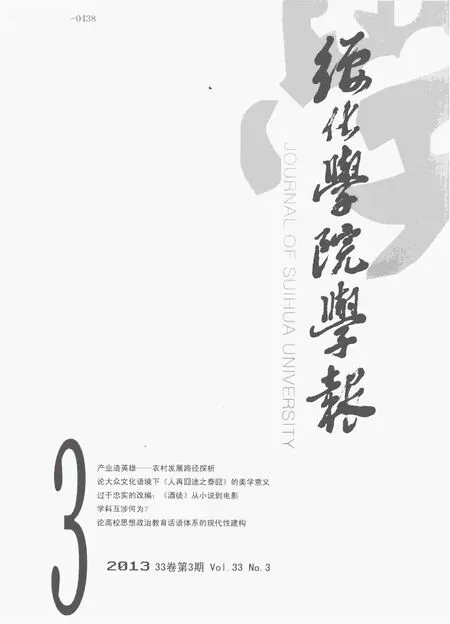从金甡诗歌的意象特征看清代康乾诗坛的宗韩风气
龚慧兰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衢州 324000)
金甡,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字雨叔,号海住。生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乾隆七年中进士后,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授职修撰。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多次主管各地科举考试,选拔有才之士,替清政府施行文政教化。在文学创作上,金甡以时文名重当时。乾隆二十三年(1758)戊寅年编写完成试帖诗诗集《金状元诗墨》(又称《今雨堂诗墨》),一时艺林争相传阅,奉为圭臬。作品有《静廉斋诗集》。
清代杭世骏在《词科余话》中认为金甡“诗宗韩、杜,骈体得南宋二李之遗”[1],这句评价不能概括金甡诗歌的所有特征,尤其在师法前人的问题上。但是在《静廉斋诗集》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与杜甫、韩愈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杜甫的诗歌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创作为后人提供了创作诗歌的范本。康乾时期学杜诗、学韩文的现象较为普遍,如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说“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2],但是在创作中学习韩愈诗歌的现象并不普遍。而金甡对韩愈之诗似乎有特别的关注,虽然在唐代诗歌史上,韩愈还称不上最优秀的诗人,但韩愈在中唐地崛起以及在诗歌创作方面独特的手法的确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打开韩愈诗集和金甡的《静廉斋诗集》,人们不免看到两者意象选择方面都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前人时的取舍。
一、诗中山水有奇景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意象的选择可以看出诗人的审美倾向。金甡在一些意象的选择上追求“奇”象。如《清凉寺双桧》中描写其中一株柏树:
潜虬惊飞老蛟舞,千古突兀撑乾坤”,柏树盘根错节,破空直上云霄,撑起乾坤,潜虬老蛟惊而起舞。
“元驹”“潜虬”“老蛟”等意象怪诞奇特。又如《东阿阻雨》中写骤然而至的暴雨:
回头直北望,疾雨乘横风。黑蜧吐昏雾,连鼓雷公攻。奔腾破空至,尽掩青芙蓉。白弩势斜注,旋转随西东。始知山川气,呼吸通鸿蒙。
暴雨来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似有黑蜧飞腾、雷公击鼓,雨注如剑弩势如破竹。此诗借鉴韩愈《龙移》一诗:
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隋。清泉百丈化为吐,鱼鳖枯死吁可悲。
又如《龙窝寺》一诗先写龙窝寺的险恶地势:
羊肠百折行逶迤,土囊张口吞茹多。千年神物此潜蛰,陆海岂必无蛟龟。疾雷破山扫腥秽,漂残龙蜕留龙窝。
羊肠小道、疾雷破山、神龙留蜕等意象都带上一种超现实色彩。这种想象在山水诗中尤为表现突出,为突出山水的恢宏气势,诗人常以神话、神怪、龙蛇等意象营造出奇特的诗歌意境。如《磨盘山》:
帝遣夸娥蹙地脉,突起弹厌于其中。土龙百万睡不动,蛇蚓盘结纷纵横。云蒸雾涌引而上,鼇背贔屓摩苍穹。
天帝、夸娥、大鼇、赑屃都是远古传说中的人或物,诗人在描写磨盘山的地形时运用神话故事,展现出磨盘山的高耸险峻,颇具韩诗风范。金甡在《静廉斋诗集》中几乎没有专门论述他诗学倾向的篇章,但在一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的诗学倾向。他在《陈开周煌乡荐戏柬》中赞扬陈煌的诗文非常奇妙“奇文发光怪,丽藻炫丹雘”,“奇文”既是对他人诗歌的评价,也是他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标准,尤其在山水诗这类题材的诗歌中,金甡较为注重“奇境”的创作。从意象到整个诗歌的整体意境,都力求雄奇之风。如《识舟亭》中“旅泊凭高一散愁,孤亭遥控大江流”孤亭遥看,大江日夜奔流不息,境界宏阔,颇有苍凉之感。《阜口渡江后行乱山中经五眼桥福子坳下分水岭赴赣县》:
赣山斗拔藏回溪,我行升降百折梯。高出云表云莫齐,下临无地穿重闺。顽石塞道缩殼蠵,危桥架壑饮涧霓。粗砂细砾布蒺藜,藤梢竹刺胜磨筓。
此诗穷形尽相的描写了山势的崎岖,山比云高,顽石塞道,桥梁横跨在山涧之间犹如长虹饮涧。极尽夸张之能是。在山水诗中,金甡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气势,如《银山》一诗“银山高出蒜山巅,补救东南半壁天。淮海片帆通远势,金焦两点护中坚”,银山山之高大,几乎可以填补东南的半壁天,地理位置也十分突出,粗线条的表现立体感极强,给人一种雄壮的感觉。如《登光岳楼》中描写光岳楼所见之景“飞楼飘渺倚天开,百尺丹梯独上来。终古浮云封岱岳,祉今弱水接蓬莱”,光岳楼高接浮云,可比岱岳。金甡为了追求诗文创作中的“奇境”,往往通过选择带有神话色彩的意象,营造出气势宏大、充满奇诞色彩的诗歌世界。
韩愈的诗歌创作在中唐可谓是当时之奇,尤其是在一些意象地选择上,较为怪诞生僻。唐代司空图曾说:“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白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拄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3],此句意指韩愈诗歌在中唐时期具有独创性,诗歌充满了雄奇怪异之美,韩愈自己也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在此诗中韩愈认为自己与李杜的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而“拔鲸牙”、“酌天浆”表现出的是对这种雄奇怪异之美的推崇。这种审美趣味最明显体现在了意象地选择上。贞元、元和之际韩愈被贬阳山,南方地区温热多湿。
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县斋读书》)
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答张十一》)
下床畏食蛇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环境的不适应使得诗人在这一时期所写《宿龙宫滩》、《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岳阳楼别窦司直》等诗歌,较多使用了凶险、幽奇的词语,如“激电”、“惊雷”、“蛟龙”、“怪鸟”等意象令人惊心动魄,营造出奇特、怪诞的诗境。他在《醉赠张秘书》一诗中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歌是“险语破鬼胆、高祖媲皇坟”,表现在他诗歌中便是对新奇险怪意象的偏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拥有巨大神力的巨兽、面目狰狞的龙蛇等常被诗人纳入他独特的诗歌王国中,并被诗人赋予强大的诗歌张力。如《赤藤杖歌》中写赤藤杖:
共传滇神出火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
一根赤藤杖,被世人幻化出赤龙拔须、羲和操鞭的神奇景象,显示出诗人对生命张力的一种追求。又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光华闪壁见鬼神,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赤虬卵。魂翻眼倒忘所处,赤气冲融无间断。
此段描写青龙寺壁画,唐代壁画内容多源自佛经,这些壁画谈鬼言神恰恰成了诗人的关注点。使得诗歌呈现出怪异的奇幻色彩。《苦寒》中为了表现严寒之苦。诗人先云:
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太昊驰维纲,畏避但守谦。遂令黄泉下,萌芽夭勾尖。草木不复抽,百味失苦甜。凶飚搅宇宙,铓刃甚割贬。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
冬帝颛顼、春帝太昊、羲和、炎帝祝融等神话意象更突出了韩愈诗中奇幻的特点。
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金甡与韩愈有着共同的美学好尚。偏爱选择上古神话人物、怪诞意象来表现自然山水的神秘、奇特。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金甡注重学习了韩诗中“奇”一面,避免其“丑”的一面,韩愈为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在意象的选择上注重“奇丑”二字,如《孟东野失子》中用“鸱鸟啄母脑,坼裂肠与肝”,《苦寒》中“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归彭城》“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等用语多狠、重。甚至到后来“丑”倾向尤为突出,如“昼蝇食案蚋,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灵虱撮狗虱,村稚啼禽猩”(《城南联句》)等,这些诗句用语艰涩难懂,意象怪诞血腥。元和元年之后的韩愈由贬所回到京城,他的诗歌创作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这类毫无美感之事。但在金甡诗中这样狰狞、血腥、狠重之词很少见。金甡在《玉偶亭元礼自登州归谈蓬莱阁之胜且录长公海市诗见示同用其韵》中写道:“名章俊句涌泉出,势与溟渤争豪雄”,雄奇之风是他所追求的一种风格,而险怪之风则是他所摒弃的一类。
可见金甡在诗歌创作中借鉴韩诗,但并不一味模拟,这与他的诗学观念有很大关系。他对诗歌创作有自己的见解,从现存资料无法看到他对诗歌创作的具体理论论述,但从其五千多首诗中可大致看出他的诗歌主张,在《家诫五十首》中他写到:
言者心之声,诗文寻正脉。险怪与酸寒,屏弃不足惜。岂徒失体制,应亦少福泽。夫惟大雅才,诵法永不易。
分析此诗诗意,金甡认为写诗应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在师法前人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博取大家之精华,摒弃险怪寒酸之风。他还曾在《书四溟山人集后》一诗中评价明代谢榛,他说“先生起清渊,风雅倾当时。论诗揭三要,允为百世师。”谢榛喜好唐诗,重视诗歌的格律音调。在《四溟诗话》中谢榛回忆当年七子论诗,说:“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舆、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模?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4]谢榛认为学习唐音在诗歌的取法对象上无特别要求,但是应采唐诗诸家之长,然后找出精华之处,仔细玩味,为我所用。金甡对谢榛以高度赞赏,认为他:“评诗观大体”。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金甡在学习前人的问题上持论与谢榛相同,所以在学韩的过程中,他是有意识的吸收韩诗的精华之处,对韩愈诗歌有着深层的认识。
二、清代康乾诗坛的宗韩之风
美国的本尼迪克说:“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5]。个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历史文化环境与个人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康乾时期的诗坛,各种流派此消彼长,宗宋宗唐纷争不休,但是对韩愈都有较深的认识。清初叶燮等人对韩诗提出了精僻的见解,尤其是叶燮他在《原诗》中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雄思,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6],“韩愈为唐诗一大变”[6]的看法,看到了韩愈在中唐的独特之处,在叶燮看来,韩愈品格高尚,爱才若渴,嫉恶如仇,并且在诗歌创作上是“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6]。薛雪作为叶燮的弟子,持论与叶燮较相似,推崇韩愈的才学、品格,肯定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并对韩诗的某些具体细节进行了评论。韩诗中的体貌、造境都得到了较多的阐释,可见在金甡之前诗坛对韩愈的研究特别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就已经表现出一定的规模。大凡诗评家在评论韩愈作品时,以褒为主,如果没有对韩愈诗歌的精深研究,是不可能出现如此广泛而细致的评论。特别是王士祯、叶燮等人的诗论对金甡学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诗歌的创作关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前代诗学的积淀。乾隆时期是清代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金甡学韩是当时的一种诗歌现象。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欧公学韩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公学韩诗,而所作诗颇似韩:此宋诗中所以不能独成一家也”袁枚在这段话中肯定了欧阳修学韩愈文的成功在于学韩不似韩,欧阳修学韩诗似韩诗,没有自家风貌,不算成功。金甡学韩在取法对象上在当时显得独特,而且他学韩较为成功的一面应该是借鉴了韩诗奇崛的一面,在山水纪行诗这类题材中较好的体现了“奇”的风貌,这点也补充了当时的诗坛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韩愈诗歌奇崛的一面,更加肯定,如晚于金甡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韩昌黎生平,所心摩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僻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虚见定,欲从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7]赵翼在这段话中就认为韩诗在奇险这点上得益于杜甫,但是他以自己的学识将奇险的诗风发扬光大,最终自成面目,其实在雍乾时期金甡就认识到了韩愈奇崛诗风的价值。
从金甡学韩可以看出,从清初到清代中期人们对韩愈的诗歌认识已经逐渐从理论转向了具体的诗歌实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学习更为全面。与金甡同时期的就有杭世骏、胡天游等人在诗歌创作中学韩愈。金甡之后这种研究似乎更为精深全面,较为突出的著作便是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以方东树为例,在《昭昧詹言》卷九论及韩愈诗,他说“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试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8],此段评论显示出对韩愈的推崇,包括了意象、字句、诗境、气势等多方面,而早于赵翼的康乾诗人金甡则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推动了清代中后期学韩风气的形成。
[1]四库未收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M].北京出版社,2000:731。
[2]王英志随园诗话[M].凤凰出版社,2000:1999.
[3]王济亨、高仲章选注.司空图选集注[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32.
[4]谢榛.宛平校点·四溟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80.
[5]露斯·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三联书店,1988:231.
[6]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8,51.
[7]赵翼.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
[8]方东树.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