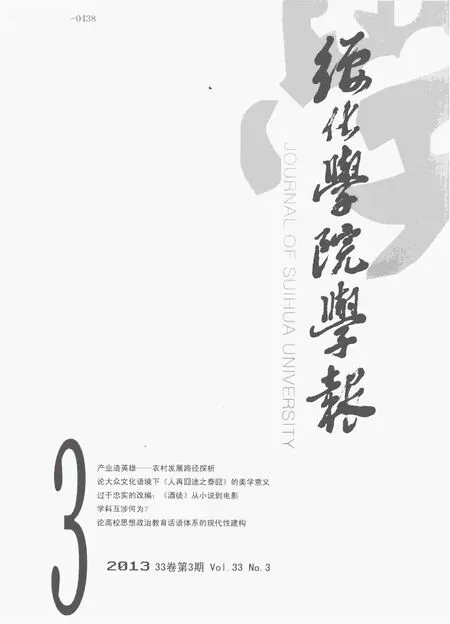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列仙传》赞文考论
施 健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赞文又称颂赞,最早可以追溯到诗《诗经》中颂诗。姚鼐《古文辞类纂》说:“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1]吴曾祺《文体刍言》认为:“颂为四诗之一,盖揄扬功德之词。”“赞亦颂类,古者宾主相见则有赞,互相称誉以致亲厚之意,故文之称人善者,亦以赞为名。”[2]可见此类文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他人进行歌颂、赞誉。在赞文创作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对人物事件品评的“太史公曰”式样的赞文,这种的赞文往往有很大的主观性,有的是直接评论,有的是间接的评论,这是传记文学赞文书写的一个先例,同时也是较早的一个古代文学赞文的一个蓝本。
无独有偶,题为西汉代刘向的《列仙传》也成为了一些文人作赞的对象。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在于,《史记》是作者自己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发表看法,而在《列仙传》这书上,是先有刘向的本子,然后才有的后人的赞文。纵观早期小说,像《列仙传》那样有后人作赞文的是很少见的,其他作品较多是模仿司马迁在文中略有评价,但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价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赞文。
一、《列仙传》赞文的缘起及作者
在历史上,到底是谁为这部道教小说作了赞文是模糊的。但通过查考文献,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有两个人曾做过尝试。一个是孙绰,一个是郭元祖。《列仙传》在唐前曾有两种赞,《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了《列仙传赞》二种。一为三卷本,刘向撰,孙绰赞文;一为二卷,刘向撰,郭元祖赞文。当今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列仙传》版本应是晋代郭元祖的本子,而孙绰的赞文遗失的较多,仅存一部分。《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孙绰的《商丘子赞》八句中仅有二句相近,可见今本非孙绰所作,而是郭元祖所作。而在《文选?西京赋》及《游天台山赋》注引《列仙传赞》二段中,又没有与今本相同的部分,可见那些又的确是孙绰所写的赞文。《初学记》卷二三引用孙绰的《老子赞》与今天的本子不同,再按两人生活年代来考察,孙绰(公元314-371),为东晋人,而郭元祖也提及为晋人,但缺乏生卒年资料,据这几条资料姑且判断为郭元祖的赞文是作于孙赞之后的,而且多少是有对孙赞的借鉴的。当然,郭元祖的赞文也曾脱离过孙绰赞文而单行,《隋志》杂传类就著录了一卷《列仙传赞序》,郭元祖撰。除了孙绰和郭元祖为《列仙传》做过赞文之外,历史记载北魏安丰王拓跋延明曾为其作注,但流传不广,鲜有人知道。《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列仙传》二卷,未言作赞者,当为郭赞。《中兴馆阁书目》《宋氏艺文志》道家神仙类著录三卷,皆附有郭赞。《通志艺文略》著录有郭赞二卷,孙赞三卷。以上为《列仙传》赞文的文献查考,对于我们认识其赞文的来源还是有帮助的。
二、《列仙传》赞文艺术特色
(一)赞文的诗化,押韵易诵读
翻看《列仙传》赞文,会发现其最大的特色是评论赞文的诗化。无论先前的论述或是神仙故事怎么样,赞文的作者都可以用诗文的形式表达对神仙人物故事的理解。例如第一篇《赤松子篇》: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是焉。[1]
眇眇赤松,飘飘少女。接手翻飞,泠然双举。纵身长风,俄翼玄圃。妙达巽坎,作范司雨。[2]
在这里,赞文用简短的四字句,就概括了对于赤松子的评价,但如“飘飘”,“泠然”,“纵身”等词语的使用,又是的赞文的叙述毫不逊色于原文。“作范司雨”更是点出了赤松子雨师之本事,精炼而恰当。再来看《老子篇》: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函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3]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道一生死,迹入灵奇。塞兑内镜,冥神绝涯。德合元气,寿同两仪。[4]
在赞文里,老子的生死境界全出,无为而又无不为,那种遁于世俗的神情让人印象深刻。生与死的顿悟,超脱神灵获得生命的延伸,使得那种老子那种道家的神仙感通过赞文也得到了升华。
《列仙传》赞文艺术性很高,在诗句的安排上用韵现象很明显,琅琅上口。我们来看《偓佺》一文:
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也。松者,简松也。时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岁焉。[1]
偓佺饵松,体逸眸方。足蹑鸾凤,走超腾骧。遗赠尧门,贻此神方。尽性可辞,中智宜将。[1]
这里的“方”,“骧”,“将”也做到了较对称的押韵。读来比较顺畅,仙气十足。接下来的一篇《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辅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发白更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也。[3]
亹亹容成,专气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独游。道贯黄庭,伯阳仰俦。玄牝之门,庶几可求。[4]
这里句尾的“柔”,“游”,“俦”,“求”更是严谨的押韵。这种自然而有序的押韵诗文读来琅琅上口,易于赞文的传播。同时也说明这些赞文出自魏晋六朝文人之手。虽说诗文押韵由来已久,但这种较严格的押韵诗文的出现是魏晋六朝时期典型的特征,后来永明体的出现,对于诗作格律的严格要求是当时的文坛主导,从此处不仅可以见出赞文的文学性,也可以觉察出赞文深深的时代变革的印记,这也是我们分析这些文人赞文时应当察觉到的东西。
(二)忠实于原文与传神再叙相结合
在这些文人赞文中有很多是对原文的概括,有时候是捡取了原文的字句来形成四字句,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内容,起到的是一个总结的作用。举两篇为例:
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闾士,炼食云母,亦与民人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士,为人所劫,闭之室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丸泥涂门,户终不可开。[5]
方回颐生,隐身五柞。咀嚼云英,栖心隙漠。劫闭幽室。重关自廓。印改掩封,终焉不落。[6]
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着《天人经》四十八篇。后钓于菏泽。得鲤鱼腹中有符,隐于宕山,能致风雨。受伯阳《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7]
涓老饵术,享兹遐纪。九仙既传,三才乃理。赤鲤投符,风雨是使。拊琴幽岩,高栖遐峙。[8]
第一篇《方回篇》的赞文与原文的大部分字句是相同的,顺序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只是作者将其四字化了而已。再如《涓子篇》的赞文的作者叙写的是涓子作为神人,他所精通的神仙饵术,所以赞文也较大程度上遵循了原文的叙述结构,较为一致。可以想见这些赞文是极附有魅力的,文人只有忠实于原文才能表达出其独特的意味。
但这并不意味着,《列仙传》的赞文都是绝对忠实于原文的,也有相当一部分赞文是作者对其原文的演化和诗意的再造,这不是一种曲解,反而体现了文人的一种对著作的敬意。如下面的两篇:
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不食五谷,而噉百草花。至尧帝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时于市中卖缴,亦谓之缴父云。[1]
蒸民粒食,熟享遐祚。子舆拔俗,餐葩饮露。托身风雨,遥然矫步。云中可游,性命可度。[2]
黄帝者,号曰轩辕。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圣而预知,知物之纪。自以为云师,有龙形。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唯剑舄在焉。仙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群臣百僚悉持龙髯,从帝而升,攀帝弓及龙髯,拔而弓坠,群臣不得从,望帝而悲号。故后世以其处为鼎湖,名其弓为乌号焉。[3]
神圣渊玄,邈哉帝皇。蹔莅万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数通无方。假葬桥山,超升昊苍。[4]
在《赤将子舆》这一篇中,尽管大体上仍保持一致,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原文中提到了其在尧帝时为木工,而下面的赞文中却省去了这一个重要的信息,转而叙述他的神奇本领和事迹,可见这是文人在叙写赞文时做的一种艺术上的取舍。在《黄帝》篇中,原文用大量的笔墨塑造了其神奇的故事,自知天命,悄然尸解,由神龙驮负,携大臣升天,这些事迹都渲染上了浓厚的仙家色彩,文学性已经很强,但在文人的赞文中,却淡化了皇帝仙化的过程,甚至连一些具体的细节也省去了,这你虽然使得赞诗能较为流畅的表达,但也稍微失去了原文的魅力。
(三)《列仙传》赞文的灵动美
除前述两个特点外,《列仙传》的赞文也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深刻的启发意义,例如《江妃二女篇》: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彩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彩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1]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盻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2]
在这段赞文中,不在一味的叙述故事,而是将凡人的奇特经历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出来。“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盻生姿。”这四句写出了江妃二女绝美的身姿,灵动的身影。而后两句凡人的经历“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却又充满了浓浓的遗憾,美好的事物一旦逝去就不再回来,又有什么必要去追寻呢?这样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又回味无穷。再如《东方朔篇》:
东方朔者,平原厌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为郎。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诙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3]
东方奇达,混同时俗。一龙一蛇,岂豫荣辱?高韵冲霄,不羁不束。沉迹五湖,腾影旸谷。[4]
对于东方朔的赞文同样用较高的艺术手法,奇达之人混迹于世俗之中,犹如龙游蛇穴,鹤立鸡群。但东方朔的归宿在于“高韵冲霄,沉迹五胡”,写出了其奇特的生命指向,同时也展示了了东方朔与俗不同的神仙气息,那种无拘无束畅游五湖四海的旷达情怀。
三、《列仙传》赞文的意义与启发
谈及《列仙传》赞文的意义,我们首先得了解后人为何会为其作赞文。《列仙传》是我国最早且系统的叙述神仙故事的的著作,记载了从赤松子(神农时雨师)至玄俗(西汉成帝时仙人)七十一位仙家,形成的是一个神谱样的仙人故事系列。在《列仙传》中,七十余位仙人或有神奇的本领,或有超凡的能力,或有与众不同的经历,或有让人羡慕的神仙气质,这些都是深深吸引道家追随者的。《列仙传》作为一部宣扬道家观念的作品,其观点是明确的,想宣传的是道家神仙之术和升仙之奇。正因为《列仙传》这一重要的地位,后代文人为其写评论性的赞文,那也便不为过了。《列仙传》的赞文一般都是采用四字句的形式,这或许也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四字句押韵和谐,读来琅琅上口,使人印象深刻,同时这些赞文又并不拘泥于固有文本的规矩,依照仙人故事来安排,自然而不拖沓,显得较为顺畅。《列仙传》的赞文在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仅有的,纵观其他类似的志怪小说,都没有这样独立的赞文,这一点在文学性上就使得《列仙传》有了更近一步的表现。我们说葛洪的《神仙传》比《列仙传》的叙述神仙人物的内容和方式上有了较大的改进,但《神仙传》并没有赞文,这或许后代文人更喜欢《列仙传》的古朴表述,而舍去了葛洪更多的添加的神仙道教因素。
《列仙传》赞文是对于司马迁《史记》中“太史公曰”式评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对于后代文学又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尽管在后代文学中,那种独立成段的或是诗歌式样的赞文已经不多见,但类似的穿插在文学作品中的赞文却有很多。其实赞文的启发意义最大的地方在于其对于消息评论或者说是新闻评论的意义。怎样用简短而有效的文字对故事或是新闻做出合理而精当的评论,那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当考虑的问题。《列仙传》成书的年代久远,版本也几经变迁。后世孙绰,郭元祖等文人作的赞文也是很久的事情了,但作为一种典型的评论性的文章,尤其对于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或新闻工作者是有启发意义的。
[1]王叔岷.列仙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严可均辑.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姚圣良.史传体例 寓言笔法—《列仙传 》.《神仙传》叙述模式探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2):18—21.
[4]谭敏.《列仙传》叙述模式探析—与史传之比较[J].宗教学研究,2004(1):128—132.
[5]刘涛.试论南朝颂赞文[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81—84.
[6]李秀花.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122—126.
[7]王建国.论孙绰的文学贡献[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50—54.
[8]刘猛.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9]冯万里.《史记 》中“太史公曰”史评形式初探[J].绥化师专学报,2004(3):6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