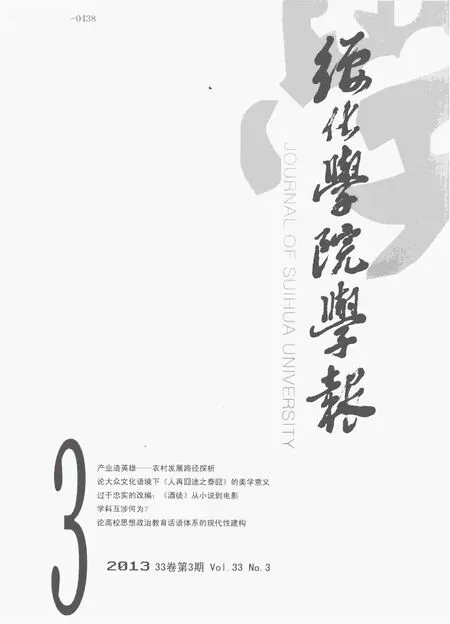过于忠实的改编:《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丁 婕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46)
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酒徒》是华文世界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1962年10月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一年后由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出版,1979年台湾远景事业出版公司出版台湾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这部小说。其实作家刘以鬯及其小说《酒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均十分重要,但限于大陆文坛长久以来对香港文学的陌生与偏见,包括文学爱好者在内的大陆读者和影迷大都是通过王家卫的电影认识刘以鬯的:2000年拍摄的《花样年华》从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对倒》获得灵感,2004年上映的《2046》中周慕云以《酒徒》中的老刘为原型,只是王家卫极端个人化的语言系统、拍摄方式和叙事手段使他从刘以鬯那里借来的胚胎,生出了更像王家卫的小孩。2010年,香港资深影评人黄国兆在买下小说影视改编权十年之后,身兼编剧、导演、监制数职,自筹资金还拿出自己和朋友的积蓄,加上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小额资助,终于将文字变为光影,引起影视及文学界等多方关注。
一
影片序场即是主人公刘先生的背影,他手夹香烟坐在椅上,面前案几正中一尊白色鲁迅全身像,旁边一瓶开始凋谢的红玫瑰。镜头缓缓向后拉,画面渐渐朦胧,字幕插入:“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接下来一组蒙太奇,节奏明快,配乐令人陶醉,片名字幕淡出。这短短的一个序场已经为影片奠下了文艺腔的基调,唯美的画面风格与六十年代特定的生活场景图片展示,将电影与小说模糊成一体,用影像重述故事。
电影抽出小说原本游散的故事情节加以整合,以不同人物身处的几个场景作布景切换,串起了主人公刘先生的生活:他向深爱的舞女张丽丽求婚遭婉拒,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物质现实。文学青年麦荷门向他抱怨“现在的流行文章篇篇都差不多”,他淡定的指出原因“理由有很多,编剧的生活不安定,观众的水平太低,政府没有办法保障编剧的权益,真正的影评也没有,整个环境不好,奸商盗版成风,编剧收入太低……”房东十七岁的女儿司马莉几番引诱刘先生,他被迫搬家,同时为糊口开始写黄色小说。偶遇之前老友莫雨,却被骗走辛苦写成的剧本。新房东王太太是个寂寞深闺、风韵犹存的海员妻子,一次酒醉承欢之后对刘先生动了真情,最后更因他饮滴露寻死。麦荷门约刘先生一同办纯文学杂志《前卫文学》,最终在现实面前认输。再次搬家的刘先生被新房东的老母错认作战时被炸死的儿子,给他久违的真情呵护。张丽丽嫁人后刘先生喜欢上清纯的舞女杨露,只是杨露最终也嫁做富人妇。刘先生不堪生活困苦寻死未果,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却因为酒醉误使雷老太割腕自杀。
女性形象是电影《酒徒》所着力刻画的,但不同于许多影片将女性作为美好、诗意、甚至伟大的象征,《酒徒》将女性作为都市人性堕落与丑恶的代表展示出来:虚荣空洞的张丽丽凭借年轻貌美的身体将自己作为商品卖给纱厂老板,毫不顾惜与刘先生的感情;还是中学生的司马莉在香港这个西化开放的国际都市过早成熟,丧失了少女的清纯与美好;而为生计所迫沦为舞女的杨露从被迫堕落到自甘麻木沉沦,还有出卖亲生女儿身体换的一点点钞票的无情老妇……这简直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甚至远远比鲁迅刻画的“狂人”那个在封建礼教侵害下不自知的吃人社会更可怖,这是在物欲纵横的麻木侵蚀中自觉“食人”与“自食”,并以此为乐,而这一个个纸醉金迷、丑恶颓败的故事以电影镜头的方式呈现,观感比小说更加触目惊心。
但是电影《酒徒》过于忠实原著,不但故事情节基本完全照搬,人物名字未做任何改动,导演甚至将小说中许多细小的场景都在大荧幕上影像化,比如最后一章第43章中刘先生的依稀回忆:“有人曾经用木屐打死墙上的蟑螂”,“阳光极好,几个学童在对面天台上放纸鸢”,“窗槛上摆着一只瓷花瓶,瓶里有一朵萎谢的玫瑰花”,“麻雀在窗槛上啄食”等一一还原于镜头之下。忠于原著或许是出于导演对小说的热爱,这在不破坏影片艺术感觉的前提下是无碍的,但该片在转换场景时总要借用小说原有的语句作隔断,对影片叙事的流畅性是种明显的伤害,也给观众带来与影片生硬分离的感觉。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酒徒》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整个文本充斥着“我”的意识流动和情感直抒,着力表现的是“我”在酒醉和清醒两种状态下的徘徊与沉浮,借助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将一个文人纷乱的思绪和细腻的情感以一泻千里的方式描写出来,使今日的读者也能更切身体悟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人的生存困境。这种直抒胸怀、思绪纷飞、情到浓处回环往复的文字没有得到恰当的影像化表现,导致整部电影在表现有志文人在当时香港这个物质空间中的困苦挣扎的力度都被削弱。另一方面,小说的精华部分是主人公老刘借恣意汪洋的意识流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精到品评,他的真知灼见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常常产生阅读半个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名家史著的错觉,但在电影中,刘先生虽然也是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但更侧重他的西方文学修养,诸如海明威、普鲁斯特、乔伊斯等分别在片首那段书本特写镜头,以及刘先生卖书换钱中加以表现。这或许是影片考虑到观众的知识构成不便于过多展示乏味的五四文学知识,也或许是电影要参加西方影展为了评奖而有所侧重,但如此一来,电影中的酒徒喝酒醉酒就仅仅成为逃避现实的手段,而少了酒后吐真言,发表对现代中国文学卓越见识的一面,这对于老刘形象的塑造无疑是一种较大的损伤。
二
电影《酒徒》的最大成功在于一干演员的出色表演,剧中各色人物塑造异常突出,主角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互动都对“酒徒”刘先生这一角色的塑造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老戏骨张国柱,还是一人分饰两角的蒋祖曼等,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影片序场主人公刘先生坐在桌前写稿,一尊白色鲁迅全身像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点,这尊鲁迅像后来在片中多次出现,随着刘先生从司马莉家搬到王太太家,又搬到雷老太家都始终放在他的桌头正中,这个细节无疑暗示了鲁迅在刘先生心中的地位,也就是文学于他的重要性。虽然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总是骨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是个现代化、国际化、一切以利益最大化的大都市,市民们的头脑里充斥着股票、马经,逐利的生活不需要纯文艺的烦扰,读者的缺乏导致纯文艺报刊没有销路,为了生存文人必然转行写作满足大众需求的色情作品,而刘先生正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戏骨张国柱一手夹着骆驼香烟,一手握着钢笔却无从下笔,加上那看透前路的无奈眼神,联想到当下的社会依然无改六十年前的物质本性,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而刘先生何尝没有过追求?他曾经深爱着舞女张丽丽,作为一个文人为了她可以去做“捉黄脚鸡”的勾当,而假扮丽丽的丈夫或许是刘先生明知无法得到丽丽而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吧。爱一个人却无法和她在一起是异常痛苦的事情,而热爱文学却不能从事纯文学创作,对于文人来说也是同样难耐。但讽刺的是,为着钱,张丽丽抛弃了刘先生,而刘先生也放弃了文学!如果说张丽丽嫁给曾经打伤刘先生的纱厂老板是为生计所迫,但刘先生改写《潘金莲作包租婆》实属自我放弃,电影中有多处暗示刘先生并非走投无路而写黄色小说,如文学青年麦荷门付给他三百块钱办《前卫文学》时说“不算多,只要不喝酒,不会不够的。”再如雷老太将三千元体己钱送给他,他却出门先买了瓶威士忌喝。演员在表现刘先生一步步滑向自我放逐和堕落的境地时表演极其自如,虽然张国柱已经六十有二,但他身上兼具的文人和浪子的双重气质,依然入骨的刻画了刘先生这个中年落魄文人形象。
一人兼饰两角不是电影《酒徒》首创,但蒋祖曼一人扮演文学青年麦荷门和舞女杨露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麦荷门第一次出场是他请教刘先生对五四文学的看法,尽管刘先生总以“这问题好伤脑筋,还是聊聊女人经吧”避而不谈,但麦荷门放光的眼睛,急迫而充满期待的语气已然把一个求知欲强,热爱文学的形象勾勒出来。后来刘先生放弃办《前卫文学》改写黄色小说,他读着麦荷门的来信时,电影画面只有他一个人的背影,信的内容由画外音读出,结尾麦荷门说:“这些都是你说给我听的。”此时的画面和声音让观众感觉到刘先生内心仍有一丝挣扎,这丝丝缕缕的纠结借着麦荷门的嘴讲出来,其实讲的是刘先生的心里话。年轻的麦荷门与中年的刘先生好像一体两面的双子星,前者是对于理想,对于文学的孜孜求索,后者则看透世事,自甘堕落。演员精到的演技让人不自觉在心里默默追问:若干年后变成中年人的麦荷门还会如今日般讲出“只要还有一个忠实读者,《前卫文学》绝对继续出版”的豪言么?
如果说麦荷门象征着刘先生内心对于文学和理想的不懈追求,那么舞女杨露则象征着刘先生在这个物质社会谋生不得不放弃尊严的妥协。与房东十七岁的女儿司马莉出于无聊和好奇勾引男人不同,同样十七岁的杨露作舞女是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赌债,供养半身不遂的妈妈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为了家人的温饱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这和刘先生为了一百块钱去写黄色小说何其相似。杨露媚人的眼风流转让人心生怜惜,与老刘的轻歌曼舞仿若巴黎最后的探戈,舞女用她柔弱的身体和坚强的内心昭示出在这个逐利社会里,单纯的道德评判是多么武断和残忍。
1960年代的香港在物欲中陷落了,1960年代的香港文化也随着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愈加边缘化。而文化的堕落又反过来毒化、催化着城市的堕落。《酒徒》实际上将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香港无情的变成了荒凉的文化废墟。在这片废墟上,人们日复一日按照消费游戏的的谋生规则构筑着日益高耸云霄的大楼,而将书店从门面房挤到二楼,三楼甚至更高,以致最终一间间消失。导演黄国兆在接受采访时说 “近50年前的故事与现今香港社会并不脱节,60年代初香港一般人讲钱,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人人都挣钱维生,人际关系往往建基于金钱之上;50年后,香港社会依然不脱金钱挂帅观念,凡事以经济利益主导,功利思想盛行,这套电影反映现实,使人思考社会问题。”可见他将《酒徒》搬上大荧幕不仅仅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追求,更多的是实践一个电影人的社会理想,这种尝试在当今社会异常宝贵,也异常艰难,作为一个香港文学研究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我必须向黄国兆的勇气和努力致敬!
——兼谈民国时期上海舞女的职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