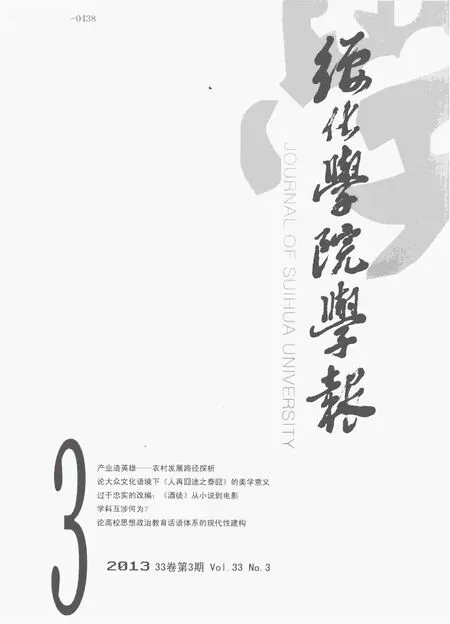童年经验和陈染的文学创作
刁蒙蒙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陈染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中以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和性别经验,书写着女性内心的情感世界,从身体上以及心理上表达着女性成长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男权制下被忽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而陈染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本人认为童年生活对其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童年作为生命个体的开端,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作家来说更是如此。童年的记忆像血液一般流淌在陈染的体内,支配着她的文学创作。童庆炳先生曾说“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的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1]
一、音乐的感知与色彩的运用
陈染的母亲酷爱音乐和绘画,而这也在潜移默化着陈染,小的时候,母亲就为陈染找老师学习音乐,学习作曲和手风琴,因此陈染受到了良好的音乐熏陶和系统的音乐训练。陈染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着音乐。“当时我的生命里只有两样:音乐和妈妈的爱。”[2]虽然后来陈染选择了放弃音乐而从事文学道路,但是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又充满了音乐的气息,陈染创造性的赋予了文学作品音乐性。在音乐的世界中,作曲家意味着要自由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感受突出自我,因而陈染的小说被评论界称为 “私小说”,“个人化写作”,在陈染的小说中,内心的真情实感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在她婉转优美的语言下流转着天赋的诗情与奥妙的旋律。“我渴望着不能令我满足的世界,越来越沉浸在远离现实的梦幻之中,在音乐里寻求安慰。”[2]例如在《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中“她感到自己攀登在石阶上的脚,似乎是踏在扩音器上,扩音器模糊地发出吱吱嘎嘎的交流声。她定睛一看,原来那石阶都是一排排堆起来的走不完的死人肋骨,吱吱嘎嘎声就是它们发出的。”作者把石阶比喻成死人肋骨,而石阶又好比是钢琴的键盘,钢琴的声音是美妙动听的,但是作者此时确认为它发出的是“吱吱嘎嘎”的声音,一种阴郁忧伤的感觉油然而生感染着读者,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最后到读者的心灵,无一进行了洗礼。
陈染幼时学习音乐的经历,又使得她比常人更加对于声音敏感,多思。也许在我们常人看来无谓的声音而到了作者耳中确是别有内涵,幻化成一串串不同的音符,表达着别样的情思。例如在《饥饿的口袋》中的“窗外雨脚密布,滴到她的心田里变成一串又一串浓郁又凄凉的词汇。”《破开》中“她说,穿透它的外表,你所想象的是那里边迷宫似的莫测的走廊、呆滞的门窗以及有回纹装饰的天花板上余音袅袅地渗透下来的惨淡的乐声。”
童年家庭生活关系的紧张,父亲的漠然,政治环境的局势都对幼小的陈染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加剧了她性格的敏感,忧虑,谨慎多思,陈染母亲酷爱绘画的品性,又使得陈染对颜色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反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陈染常以超然的主观感受,去感知世界,在她笔下,色彩便是感受,便是心情,极富作家自己的感情色彩。她所选择的色彩并不是热情洋溢的大红大绿而大部分都是暗色系的。“用颜色来阐释生命的色调纯粹是感觉化的比拟,而不是科学的界定。”[3]如《破开》中“天空灰中透出一股脏兮兮的黯淡”。《与往事干杯》“我看到一个十七岁少女的乳房正悬挂在黑褐色的树杆上,它银亮灿白,含苞待放。”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她的影子渐渐扩展,挡住了户外稀稀落落的几株黑树枝桠以及远处苍凉非凡的景观。”透过“天空灰”、“黯淡”、“黑褐色”、“苍凉”这些字眼,我们仿佛看到美丽忧伤的女子在心理成长历程中所遭遇的困惑,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之痛,现实生活冲刷不掉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忧伤。
二、孤独——由内而生的气质,尼姑庵——寻求精神故土
小的时候,陈染父母感情不和,又伴随着“反右”政治运动,陈染家庭氛围压抑、紧张、沉闷,陈染一方面羡慕别的小朋友家庭的和睦美好,另一方面她只能孤零零的躲在房间里练琴,自卑使她不敢出去和伙伴玩,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陈染也是自闭,敏感,多愁善感。戴锦华指出“对于陈染,童年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底景,远不及父母间的婚变、破败的尼姑庵中的夏日,更为巨大、真切地横亘在她的人生之旅上。”作品中的人物即便她们年龄、职业,习性不同,也都感染了陈染的孤独气息,她们幽闭,落寞,忧郁,感伤,病态地沉湎于自己的感情世界。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她们反复吟唱着“孤独”之歌,她们或自觉的生活在孤立的空间中,如《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我是那么的忧郁、多思、瘦弱而且胆怯。”或生命个体之间的零交流,如《潜性逸事》说雨子“她努力呼吸着夜晚,以埋没和消释白天的孤单。”或是母女之间的窥视,压迫。如《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母亲时时刻刻监视着女儿,“家”似乎只是牢笼。如果说小时候的孤独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而成年之后陈染在接受西方女权思想后,在寻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未果后,越来越脱离现实,试图营造想象中的世界,这又注定了是孤独的道路。“许多年过去了,转来转去,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家居动物,发现我其实并不想摆脱那种被称之为“孤独”的东西,而是那样地喜欢与它相依相伴,那样刻骨铭心地依赖它。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人的智力生活或精神生活得以进行。”[4]
1979年陈染父母婚姻破裂,陈染跟随母亲离开了家,居住在尼姑庵,这是陈染一生中重要的居住地点,在这里,陈染开始自己新的人生之路,弃音乐从文,在其作品中尼姑庵的意象反复出现,是陈染许多小说发生故事的源头,它是不幸的开始,总是夹杂着作者童年的记忆,也许在这样的记忆中,在尼姑庵的氛围下,作者才能找寻到抒发或者叙事故事的完美适合点,一个现实与幻想的世界便轻松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与往事干杯》中的尼姑庵是一切故事发生的起点。尼姑庵又是作者眼中的“故土”,童年时期的“家”对于陈染来说并不是浪漫温馨的避风港湾,父母感情的梳离,使幼小的陈染觉得“家”是情感的束缚之地,当遭遇了现实生活中的磨难,作者便寻求尼姑庵作为一方净土。《另一只耳朵的敲门声》中尼姑庵情结在她童年时期就已经深埋在她老人般顽固的心灵里。当黛二发现现实与想象世界的疏离,母亲与其感情世界的隔膜,她想逃离尼姑庵,可是却又无处可逃。
三、家庭外的男人和女人
陈染的父亲和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感情不和,“父亲是个性情古怪的学者,终日埋头书海,著书立说,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顽强精神,母亲与父亲性情趣味上差距很大,她温良优雅,是个作家。”[2]父母不和谐的感情生活对陈染的影响很大,而父亲对于陈染是严厉苛刻的,父女俩几乎很少交流,父爱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陈染很渴望得到父亲的关注以及疼爱。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是她的“恋父”与“弑父”情结。陈染曾经说过:“我热爱父亲般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的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5]在陈染的大部分作品中,父亲这一角色是缺席的,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死亡的,这和她的缺失性的童年经验密切相关。而作品中的人物对于“父亲”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功能更多的从爱情中获得。《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与比她大将近二十岁的男人发生关系,《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和T老师暧昧不清。这些女孩子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获得父亲般的感觉。陈染的“弑父”情结,也是她“恋父”的一种方式,当你想获得某种渴望的爱而不得,便产生了 “恨意”,正如伏波娃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以后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或是敌视的态度。”[6]这也足以说明父爱的缺失在她童年时期产生的莫大影响。她童年时期渴望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得到父爱,但是她却从内心惧怕父亲。因此作者在作品中便选择了消解父亲这个角色。《私人生活》中的父亲是个狂暴、自私、专横的男人,“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他其实不关心母亲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倪拗拗拿起剪刀对着父亲的裤子就是一剪子,在她的思想中,裤子便代表了父亲,代表了男权社会。“仿佛那不是一条裤子,而是一条活的腿,剪开的裂缝正在突突的向外奔涌着鲜血。”陈染作为女性文学作家代表,在其小说中作者不仅对“父亲”这一角色进行了消解,解构,对于男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来说,作者也打破了传统的“历史主体”本位说,怀疑男性的存在价值,在她的小说中男性很少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涉及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T老师,大树枝,父亲,气功师,医生等,但是他们要么只是代表着性动物,要么是自私庸俗之徒,毫无优点可循。
陈染幼时的生活是和母亲相依为命朝夕相处的,少女时期父母离异,又和母亲单独的居住在尼姑庵中,可见母亲对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本属于“父亲”角色的爱也由母亲一人给予,对于陈染来说,母亲便是自己的守护神,是温暖的臂膀,是感情的慰藉。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便可解释陈染小说中的“恋母”情结。“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跟妈妈走街串巷……我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2]陈染作品中描述了较多的母女之情,有母女之间病态扭曲的感情纠葛,例如《另一只耳朵的敲门声》中的黛二母女,有母女之间的相濡以沫,似朋友样的相处。例如《世纪病》中的姐妈关系……而母女之情的牢固使她对于同性之间的爱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破开》中作者直说:“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别,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认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一种生命力潜能”,在作品中,女主人公把自己的感情更多的倾注于同性,这不外乎是母女之爱的一种延伸,一种缺离以“父亲”为首的男人世界的同性之间的情谊,对于陈染来说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衍化。在《潜性逸事》中的李眉与雨子,《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与禾寡妇,《另一只耳朵敲门声》的黛二与伊堕人,她们之间似知己,似爱情,似母女,是纷繁多乱的感情纠葛,陈染在传统文化所默认的单纯的异性恋之外发掘了人类更为复杂的“姐妹情谊”,而这对新时期女权运动文化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由此可见,童年经验与作家的创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童年经验在人成年后并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它只是通过不断的整合,渗透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影响着作家人格形象的塑造。透过陈染的小说创作,和她的童年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童年生活对于陈染小说中的主题的选择,人物的设定,多重意象的重复,色彩的渲染等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对于陈染本人的性格形成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染在自己的成长经验世界里,去找寻人类的共同生存之痛,去探询在男权压制下女性意识的萌发,缺失性的童年经验对于陈染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之路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笔财富。
[1]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
[2]陈染.我的人生旅途[J].散文百家,2003,(20).
[3]陈染.色调的哲学[J].悦读,Happy Reading,2007,(12).
[4]陈染.谁掠夺了我们的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5).
[5]陈染.不可言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