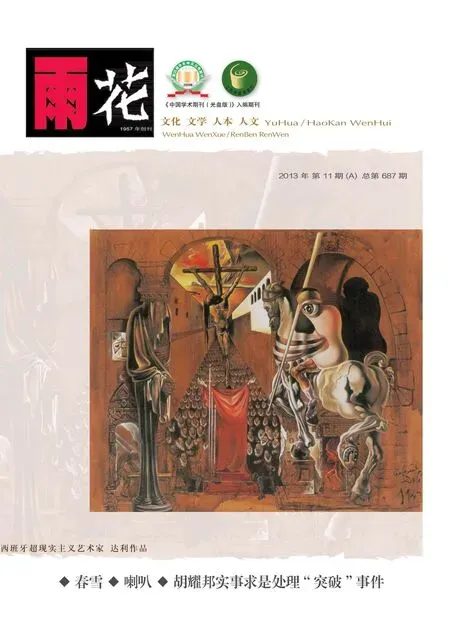春雪
●朱庆和
春雪
●朱庆和
黑暗中,春雪就看到那个女人拿着枕头一心求死的样子,那眼神要穿透她。

人间的收成一半属于勤劳,一半属于爱情
——《乡村》
一
17路公交车停了下来,几个男人苍蝇一样扑到“蛋糕”上去,纷纷拽着从车上下来的人,要他们坐三轮车,不停地问,上哪去上哪去。一会儿,“蛋糕”被瓜分掉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似从外地来的,被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拖着走了很远,可死活就是不答应。这是一场毅力的较量,双方一拉一扯,一时难以决出胜负。结果眼镜站定了,拿松山话厉声呵斥对方,天黑了吗?这句话把胡子拉碴镇住了,后者不情愿地松了手,回应说,没黑,亮着呢。
从大地方来的人,不喜欢被强迫,喜欢自由选择。眼镜看到了站在街边的春雪,拎着旅行包来到跟前,说了个地名,后者立即报上价格,眼镜就拎着包上了她的三轮车。这是中午时分,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眼镜叮嘱春雪,开慢点,别撞上了。春雪连连说,没事,没事,你坐好了。过了路口,春雪问道,看你戴着眼镜就知道你怪有学问的,考学出去的吧?眼镜谦虚地说,哪有什么学问,猪鼻子插葱,也就在外边瞎混日子。眼镜接着问道,路口怎么不装个红绿灯啊?春雪回答说,装过一次,结果时间不长,出了条人命,就又拆掉了。眼镜很奇怪,有了红绿灯,怎么会出人命呢?春雪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装上有什么用,谁都不习惯,不出人命才怪,没有红绿灯,从来没出过事。眼镜无语了,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到了目的地,眼镜说春雪做生意很地道,坚持要多付两块钱给她,后者却执意给退了回去。于是,眼镜要了春雪的手机号,说回去还坐她的车。这没问题。春雪觉得眼镜真是个可爱的有趣的书呆子。
回到镇上,春雪来到街边的饭店,那是她一个远房亲戚开的。每天早上她从家里带来盒饭,放在笼屉里热着,到了午饭时拿出来。此时,饭厅里有两三桌人正在喝酒,师傅在厨房忙着炒菜,烟雾缭绕,喧哗有声。春雪站在笼屉边,看着烧得正旺的炉火,却觉得很安静。那火苗,让她想起了三年前死去的丈夫。他是个煤矿工人,在一次窑底事故中死掉了,是几个工友一起给扒出来的,尸体从底下拖上来的时候,春雪看到丈夫已是血肉模糊,上面裹着煤屑,就像烧得正旺的炭火,火苗子直朝上蹿。突然间她的脸被舔了一下,她知道那是丈夫的魂儿。
春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拿了盒饭到车上吃。这样既不打扰亲戚做生意,又好照顾自己的生意,有人坐车的话,扣上饭盒就走。
不久前,春雪在一个叫破桥的地方拉人,那儿因为不通公交车,生意赶上门,钱来得特别快。自从入秋儿子洋洋上了小学,才挪到松山镇上,一来接送洋洋方便,二来离家很近,开车就五、六分钟的时间。可是这里的生意却很难做,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指甲盖小的行当,就有十几个人来抢。虽然同是一个镇上的人,乡里乡亲的,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却相互攻击暗算,有时甚至大打出手。她亲眼看见一个人拿着尖锥朝一辆拉着客人的车轮子上狠命地扎去,一直追赶着,直到扎破胎为止。她的车胎就被扎过两次,开始怀疑是那个人所为,可是后来她却发现,几乎每个人手里都藏有一把锥子,于是春雪离他们远远的。
女人往往给客人一种安全感,她们待人热情,而且不会宰人。所以主动找春雪载客的人也不少,可有一次,那帮人中有两、三个挑头,硬是起哄把客人给赶跑了。春雪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骂起来。他们觉得好玩,跟她对骂,带着挑逗,很色情的样子。这时一个外号叫长眼皮的男人给她解了围。春雪觉得这人还不错,两人话语逐渐多起来。
吃过中饭,长眼皮就凑过来,坐到春雪的车上,说找个地方歇歇吧。春雪还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看见一百块钱塞到了她手上。春雪气得浑身哆嗦,一把把长眼皮扯下来,滚,快滚,什么东西!
春雪把自己锁在车里,黯然地看着街上过往的行人。不远处,又一辆公交车停下,车上的人陆续走了下来。春雪心里一直有个隐秘的想法,她始终觉得丈夫没死,而是离开松山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多么期待有一天,他也从公交车上走下来。
二
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已西斜,哑巴牵着牛去村外吃草。现在,整个村子就只有这么一头牛,也只有一个哑巴,哑巴牵着牛走在路上,像是从远古走来的两件古董,锈迹斑斑,沉默相望。
谁都知道,哑巴天生是干农活的料,以前农闲的时候,他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和泥、运石料,有一次脚手架上掉下来一块砖头,旁边的人喊破了喉咙他也听不到,结果那块砖头毫不客气地把他拍晕了过去,从此谁也不敢叫他去做工了。所以他只能下地,地里的庄稼都听他使唤。现在人们变懒了,收麦子、割稻子都用机器,花钱图省事,哑巴却还撅着屁股、操起镰刀,在地里挥汗如雨。一到地里,哑巴插秧、割稻子比谁都快,他就是机器,想停都停不下来。的确,他种的粮食比谁家的都好,根粗苗壮,颗粒饱满。他是光棍,但人们却都感觉他伺候的那几亩地就是他老婆,地里的庄稼就是他的孩子。
经过村口时,一帮人正抽着烟聊着什么。二富拦住了哑巴,要跟他推掌比定力。有什么好比的呢?哑巴打着手势,意思是,你根本就不是对手。但二富却坚持不让他走。哑巴只好把牛撇在一边,拉好架势。两人一交手,结果二富又输掉了,众人都嘲笑他,想跟哑巴比,你还是回家再吃两年饭吧,哑巴都是很有劲的。哑巴看着众人张着嘴笑,他也觉得挺兴奋的,暂时忘了放牛那一茬。
谁都想跟哑巴说上两句话,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哑巴不会哑语,只是用最土最直接的手势搭着模糊不清的话说,他们有时不懂,意思难免会南辕北辙,但看着哑巴手舞足蹈的样子,大家也就像被抹了脖子扔在地上的鸡一样。
二富抽了口烟,指着哑巴的裤裆问道,哑巴你攒这么多劲,有什么鸟用?你说你不是白攒了吗?哑巴看了看自己的下身,大家都笑了。
国庆对哑巴说,好白菜不能叫猪拱了,你别让二富鸟人占你家春雪便宜啊。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模仿性交的动作。
众人也在帮腔,对,肥水不流外人田,那话怎么说的?小叔子睡嫂子,就好比吃个枣子,那是天经地义。
二富截住众人的话头说,谁说他没老婆,他种的那二亩三分地就是他老婆,我亲眼看见他在八亩半跟他家的地搞。大家一听都很惊奇,来了兴致,纷纷问道,跟地怎么个搞法?你搞过?于是二富现身说法,双手撑在地上,上下运动着。哑巴以为二富要比俯卧撑,也开始趴到地上,做起了俯卧撑。这时,哑巴的手机掉到了地上,国庆捡起来,但不知藏哪儿好。有人指了指边上的牛。国庆就把手机系到了牛尾巴上。众人都笑起来,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笑破了肚皮,有的笑得脖子转了筋。哑巴感觉不对,抬头看见他们的脸都扭曲得变了形,就立即站起来,牵上牛走了。
哑巴拐到了右边的田间小路,看见牛一直在甩着尾巴,左右一扫一扫的。原来刚才不知谁把他的手机系到了牛尾巴上,哑巴不跟他们计较。他们曾经把哑巴的手机抢走,并且取笑他,你要个手机有什么用,打不出去接不进来的,跟你的鸡巴一样,摆设。他们懂个鸡巴,他买手机自然有用。
牛尾巴上的手机被解下来,牛就觉得好受多了,一边走一边吃着草,样子很安逸,哑巴跟在牛后面,也显得轻松自在。牛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哑巴觉得这样安安静静地呆着挺好,他觉得这头牛就像是他的兄弟,自从哥哥走了后,这头牛就成了他惟一的兄弟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哑巴的手机震动起来,来了一条短信。是长眼皮发的,说是晚上七点在好再来饭店等他,有事情说。
三
当然,这帮男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好人,春雪觉得来自沟角的小马就不错,温和,懦弱,忍让。他靠主,信耶稣,是真信,年轻时受了不少苦,现在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他觉得有神在护佑着他。他劝春雪也去靠主,这样苦难就到头了。也许是跟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春雪不相信世间会有什么神,如果真有的话,她觉得她的洋洋就是她的神。为了儿子,她可以像狗一样活着。春雪这么认为。
下午乘车的人少了,春雪就和街边摆水果摊的刘凤梅聊天。刘凤梅准备在她村里买一套楼房,给儿子结婚用。眼下每个村子都在建小区,楼房一盖起来,就跟魔术一样,村庄立马摇身一变成了城市,自来水,暖气片,管道煤气,抽水马桶,真正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刘凤梅劝春雪也买一套,钱不能存着,存着存着就存没了,比魔术变得还快。春雪当然知道这一点。但那五十万块钱,是春雪跑了半个多月从矿上争取到的,一拿到就攥到了婆婆手里。当时婆婆对她说,这是青山的人命钱,可不能随便花,存起来给洋洋上学用。刘凤梅说,你傻呀,那是你婆婆怕你跑了,想拴住你。春雪想对刘凤梅说,为了儿子,我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但她欲言又止,想起这句话就觉得心里酸酸的,她怕说出来会掉眼泪。这时,那个男人过来了。刘凤梅捅了捅春雪,找你的。
那个男人坐上车,春雪发动了车子,开着出了小镇,一直向北而去。路边是一条河,河水跟老人的尿一样,在河底窄窄的一道,乳白色,似流非流的样子。靠近路边的田地有的建起了工厂,有的被砖墙圈了起来,其间夹杂着稻田,间或种着玉米,现在已是收获时节,却给人一种很荒芜的感觉。他们一路无话。
早在两个月前,那个男人就搭她的车回家。她看着他从公交车上下来,高大,但背微微驼着,眼神忧郁,手里提着黑皮包。他四处找他的自行车,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男人只好问一旁的春雪,到晏驾墩多少钱。春雪说,五块钱。于是那个男人就上了车,给春雪五块钱。春雪推给他,说,到了地头再给。在车上,春雪想跟他说说话,但他始终不作声,也许是那辆丢失的自行车让他很郁闷。过了几天,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眼神。两个人只有两句简单的对话。晏驾墩。五块钱。春雪就带着他一路北去。春雪是个外向的人,什么人都能聊得来。但是很奇怪,碰上他,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耳边只有马达声,似乎静得出奇,春雪甚至以为自己开了辆空车,那个男人根本就不在车上。回头看了看,他正闭着眼。也许是他太累了。春雪觉得车上的人是青山,在外漂泊了三年,甚至更久,有一肚子的话憋在心里,等回家跟她慢慢细说。她被自己突然跳出来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以后每次那个男人都主动坐春雪的车,春雪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载他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一看到他,她的心里竟有些慌慌的。但她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刚才刘凤梅说话的腔调,叫她不高兴。今天她不想载他,但他已经坐在车上了。
到了那个男人的家门口,春雪把车子停稳了。那个男人下车,掏了掏口袋,说,不好意思,钱不够,你等一下。说着,就回了家。院门被他习惯性地带了回去,但没关严,虚掩着。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什么意思?春雪对着院门自言自语。难道这五块钱不想给了?可是也没有这样赖账的,就在自家的门口。算了,下次再问他要也不迟。春雪左右思忖着。可他为什么不出来呢?那个虚掩的院门是不是他设的一个陷阱?是不是想引诱人进去,然后谋财害命?一连串的疑问包围着春雪。虚掩的院门是个秘密。院门里面的那个男人是个秘密。
春雪推开了院门。院子中间堆满了玉米,还没有剥皮,小山一样,空气中飘着中药味。春雪屏住呼吸,绕过小山来到了屋门口。春雪不知怎么称呼那个男人,就“哎”了一声,小心翼翼的。屋里没有回声,那个男人却从院子东边的锅屋走出来,手里端着碗。看到春雪,他连连抱歉,真是对不起,忘了,全忘了。他碗里的东西随之漫了出来,看颜色像是汤药。
那个男人来到屋里,春雪也随之跟了进来。一股味道扑面而来,中药味都盖不住。适应了屋里的光线,春雪看清了堂屋里的摆设,那些家具应该是他结婚时置下的,当时很流行,跟春雪家的一样,但现在看上去很陈旧。春雪猜测,他家的孩子也应该跟洋洋差不多大。这时他拿了五块钱给春雪,然后转身到了西间里屋。
里屋的床头坐着一个女人,在小声地呻吟。那个男人开始喂她药,喝两口吐一口,一会儿她胸前的毛巾就黑了,大概喝了半碗的样子,女人把碗推开了。那个男人起身,站在一旁,垂着头,像是在为那个女人默哀。春雪看清了女人的模样,脸很瘦,因为瘦而显得惨白。女人似乎刚刚意识到有人来,脸色立即变得明亮起来。她费力地抽出枕头,递给春雪,又做了个捂嘴的动作。春雪不解,那个男人小声解释说,她是想叫你,叫你捂死她。春雪被吓得一激灵,像是一股阴风吹进了她的身体。那个男人把枕头拿到手上,重新垫到了她的背后。女人明亮的脸上突然断了电,重新黯淡了下来。春雪终于闻出来,屋里弥漫的那股味道,是死亡的味道。她在等死,可是现在却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
透过这张脸,春雪还原了女人年轻时的样子。如果没有猜错,女人应该是春雪中学时同一届的同学,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也没说过话,但春雪认识她,记得她的样子。多么残酷啊,春雪感觉,她和眼前的这个女人就像开在乡间的两朵野花,也曾有小小的灿烂,但悄无生息,一朵就要凋谢了,她这一朵也必然是同样的命运,只是时间的早晚,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知如何用言语去安慰那个男人,春雪就帮着在厨房烧了饭,炒了菜,似乎是本能地尽到一个女人的责任。他的孩子放学了,果然跟洋洋差不多大,一进门就哭着喊着要钱买校服。那个男人晚上要到钢铁厂上夜班,他答应孩子,明早一准把钱给他借到,但条件是今晚他要把院子里的玉米剥出来。孩子很听话,蹲到一边开始剥了。
春雪临走前,把身上的两百块钱悄悄地压在了那只盛汤药的碗底下。秋天的傍晚,天气有些凉了,春雪却觉得脸上热热的,她把马力加到最大,她想一直开,开到命运的尽头。
四
餐桌上摆着猪头肉,油炸花生米,几道热菜也陆续上来了。哑巴和长眼皮分坐两边,边喝边聊,在切入正题之前,他们照例要谈谈国际形势。
长眼皮说,萨达姆死了你知道吗?哑巴跟他碰了碰杯,意思是,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还用你说?长眼皮接着说,卡扎菲被干掉了你知道吗?哑巴就接着跟他碰杯。长眼皮继续说,下一个是谁你知道吗?哑巴打着手势回答道,下一个是谁关你鸟事,喝吧。于是两个人同饮而尽。
拿了纸和笔,长眼皮开始跟哑巴说正事。长眼皮写道,下午春雪又带那男的去了他家里,很长时间才回来。为了确保自己说的是实话,长眼皮又加了一句,我要是扒瞎话,把眼珠子抠下来安到屁股上。哑巴写到,狗日的我相信你,那人是不是晏驾墩的,你上次带我去看的那家?长眼皮点点头,说,你他妈的听得到呀。
长眼皮和哑巴不是一个村的,两个人能走到一起,自然有相同的地方,那是因为孤独,当然他们也有所不同,那就是长眼皮尝过女人味,哑巴却没尝过。有人说,看见长眼皮在村里偷了鸡到镇上卖,卖了钱就在镇上找鸡。听话的人随口问道,那鸡不会是我们家的吧?说话的人就问,你指的是前面那只还是后面那只?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已说明人们都觉得长眼皮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都得提防着他。但哑巴始终觉得跟长眼皮很亲,好像几辈子的老伙计。
长眼皮打着手势问哑巴,你有没有日过你嫂子?
哑巴脸红了一下,但酒把脸盖住了,没看出来变化。
长眼皮说,鸟人,就知道你没有,你没那个胆量。
哑巴害羞地笑了笑。
一瓶酒不知不觉被干掉了,长眼皮酒量有限,估计哑巴喝了小七两,可他还想喝,长眼皮担心他喝醉了付不了钱,就及时制止住了。哑巴结了账,另外给了长眼皮五十块钱,这是他们俩讲好了的。
走出餐馆,长眼皮一头扎进了洗脚房,熟门熟路,临走前对哑巴说,家去吧,今天你要不把你嫂子给办了,你狗日的就不是哑巴。
哑巴看着长眼皮消失的背影,抽了支烟,然后骑上车出了镇子,却没有回家,而是朝北而去。他要去晏驾墩,教训教训那男的,叫他离春雪远一点,不然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天上的月亮,明亮而孤独,照得万物清晰可见,照得哑巴的愤怒也清晰可见。哑巴骑得飞快,感觉他和他的影子在赛跑。
在晏驾墩村头,哑巴把车子锁好,藏在麦穰垛里。到了那男的家门口,透过门缝朝里看了看,院子里的玉米堆挡住了视线。哑巴在犹豫,如果春雪在的话怎么办?哑巴想好了,就对她说,洋洋叫我喊你回家吃饭。哑巴决定爬进去,院墙很矮,没费事就翻过去了。他转身要把院门打开,留好后路,却发现门根本就没上闩。
三间主屋,西边的一间亮着灯,透着微黄的光。
屋里的女人坐了起来,她听到了推门声,就像她一直想像的那样,那人真的带她来了。她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己面前,嘴里还透着一股酒气,真是香啊。她多么欣喜,“快带我走吧!”她的苦痛就要结束了,她的灵魂就要随着黑影飞出她的院子,飞出这个小村庄,到一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但她不知道黑影怎么带她走,她看到他空着手。黑影说了一句话,但她没听懂。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听不懂是很自然的。女人就问道,现在就上路吗?我的孩子正在院子里剥玉米,那么一大堆玉米,他怎么剥得完啊,可是他剥不完的话,他爸爸就不给他钱买校服。
黑影伸出了手,布口袋一般,看来要收她进去了。女人流着泪说,我想把我的孩子喊进来,他可能是睡着了,我要嘱咐他两句,我喊他,他就是听不到……这时黑影张开了布口袋,女人顿时被黑暗吞噬了。
五
在回家的路上,春雪突然意识到,洋洋早已经放学了,她却忘得一干二净。该死!春雪狠狠地骂着自己,假如儿子出现什么差池,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到了学校,找遍了教室,也没见到儿子的影子。春雪吓得一下子瘫到了地上。门卫老头连忙扶起她,先别哭,说不定你儿子已经回家了,快回家看看去。
一进家门,春雪看见洋洋正坐在板凳上看动画片,一动不动,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婆婆埋怨道,这么晚了,到哪儿去送客了,幸好洋洋识路,不然叫人给拐跑了,看你怎么办。公公不让老婆子再说下去,安慰春雪说,没出事就好,先吃饭吧。春雪知道婆婆本来就不支持她开三轮车,怕她带上洋洋一溜烟跑了。她站起身,忍住了,今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大悲大喜,起起落落的,她要好好梳理一下。
青山的父亲年轻时就干了一件事,盖了六间大瓦房,之后迅速老了下去。东头三间给老大,西头三间给老二,中间一道院墙隔开来,老两口一直住在老二这边。自从青山出事后,晚上婆婆就到东头来陪春雪。于是婆婆不由分说就叫哑巴在中间院墙上刨了个月门,这样两家就成了一家了,有什么事也方便来回,不必经过大门。开始,春雪以为婆婆是真心为她着想,怕她想不开,后来发觉不对劲,婆婆晚上不来陪的时候就把屋门从外面锁上,白天她要去哪儿婆婆就跟到哪儿。她看出了端倪,婆婆把这笔钱捏在了手上,假如春雪改嫁,是可以答应的,但钱不能走,五岁的洋洋也不能走。甚至婆婆哭着对她说,你看青山走了,你和洋洋要是再离开,哑巴又是个残废,这家可真就破了。春雪听着心酸,就把话挑明了,说她不会离开这个家的,洋洋是她的命根子。
春雪穿过月门,头顶上是月亮,茧丝一样的月光罩在她纷乱的心口上。进了屋,春雪把屋门反锁上,这样谁也不能来打扰她,包括月光。黑暗中,春雪就看到那个女人拿着枕头一心求死的样子,那眼神要穿透她。
春雪想,其实现在自己也跟死了差不多。青山的突然离去给春雪打击太大,如果不是为了洋洋,她早就想一死了之了。有时她真想狠狠心,带着洋洋偷偷离开这个家。婆婆从一开始就给她下了个套,叫她把脖子伸进去,她挣扎越厉害就会被勒得越紧。青山去世一年后,他们开始给她说上门女婿。相了几回,公婆都没看上。倒是有一个山区的,条件还不错,春雪看上了,可婆婆死活不愿意,说不知根知底,怕是坑钱的主。此后,春雪就不再提倒插门的事。他们最初和最终的想法都是,要她跟了哑巴,用婆婆的话说,“也不是什么丑事”。所以前面张罗入赘实际上只是个幌子。有一次春雪听到婆婆跟哑巴讲,不要跟死驴一样,就知道蒙眼拉磨,要跟洋洋妈多接触,多说说话。公公问道,一个哑巴,你叫他怎么说?你叫他说什么?婆婆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点破了,嘴巴不能说,就用身子说。
有一天婆婆弄了一桌子菜,把她和洋洋叫过去,公婆和哑巴已经在等着了。春雪问,也不过年过节的,这是要干什么?婆婆说,自从青山走了后,我们一家人还没好好地吃上一顿。说着,给春雪倒了酒。婆婆硬劝着让她喝了两杯,而且婆婆说了些回忆青山的话,弄得她泪光闪闪。等春雪回过神来,发现公婆和洋洋不见了,只见哑巴在朝自己碗里夹菜,这一定是婆婆教的。春雪起身去拉屋门,外面已经锁上了。春雪觉得很可笑,问哑巴要钥匙,哑巴摇摇头。春雪坐下不说话,看着哑巴,看看他想干什么。哑巴却低下头去,像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春雪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就起身给他盛了饭,也给自己盛了一碗。哑巴没吃,站起来去开门。婆婆没走多远,她听到哑巴在一个劲地晃门,嘴里还在“啊、啊”地叫着。婆婆把门打开了,上前给了哑巴一巴掌,你个驴日的,整个巷子都是你的声。
春雪和青山是经人介绍的,他们不是金童玉女,也非相见恨晚,相互看着顺眼就算把亲事定了下来。相识一年多结婚,两个人有没有爱情,这谁说得清楚?他们就好比一根筷子碰到了另一根筷子,凑成了一双筷子,一起吃饭过日子。特别是有了孩子,她觉得青山成了她的亲人,主心骨,家里的支撑。所以,青山一死感觉房子塌了一样,把自己埋在了底下。
她知道青山再也不会回来了,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那个男人不是青山,他有他的生活,她和他只是两个不幸的家庭的偶然相遇,他们的不幸却不能嫁接在一起。她的不幸已经过去,自己还健康地活着,她的洋洋还健康地活着,她庆幸今天在那个男人面前没有慌乱,表现得恰如其分。
还有哑巴。哑巴是多么单纯啊,即使在婆婆的教唆下,也做不出一件坏事。哑巴除了不会说话,看上去就像是青山的翻版,只是脸略黑一些,但那双眼睛却更为清澈。有一次,春雪进屋,看到哑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硬是给吓了一跳,她以为是青山回来了。去年夏天,春雪在田里拔草,被包石灰窑的刘三拦住了,他突然甩出五百块来,说要包她一晚,还动手动脚的。春雪回到家一直哭,婆婆追问,才知道事情经过。哑巴知道后,在街上碰见刘三就追打,一直追到他家,拿刀砍烂了他家的大门,算是给春雪出了口气。
春雪摸摸脸颊上的泪水,什么时候流下来的都不知道。
春雪来到婆婆这边,洋洋已经在哑巴的床上睡了。婆婆连忙给她道歉说,我老糊涂了,说话没个分寸,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春雪说,我饿了。算是原谅了婆婆。婆婆连忙给她盛饭,春雪说,我自己来。她边吃边问道,他叔呢?婆婆说,到镇上跟谁喝酒去了,别管他。
吃完饭,春雪来到哑巴的房间,把已经睡着的洋洋抱了起来。
六
哑巴把自行车一摔,几乎是同时也把自己摔进了屋里。父母已经睡下了,他们听到哑巴“嗷、嗷”地叫着,跟狼发情了一样。母亲披上衣服,骂了一句哑巴,这么晚,到哪儿杀人去了!
只见哑巴张着两只青筋暴露的胳膊,在空中胡乱挥舞着。父亲也起来了,扶着哑巴坐到了椅子上,哑巴一身的汗水,还满嘴的酒气。父亲了解他的心事,就说,我知道你是一肚子的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边说边拿毛巾给他擦汗。
母亲问他,峰啊,你有什么苦,趁着酒劲全倒出来。
哑巴就打着手势说了一通。父亲翻译道,他说他不能跟洋洋妈结婚。
母亲问道,为什么?
哑巴又打着手势说了一通。他说他杀人了,跟洋洋妈结婚会害了她的。
母亲猛然一惊,上下打量着哑巴,看到他浑身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血迹。母亲对着哑巴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耳性变好了,刚才是不是听到我说的话了?
这时,哑巴突然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意思是,求求你们,放了嫂子吧,叫她带着洋洋走吧。
母亲明白他的意思,不再需要父亲翻译。母亲骂道,你懂个屁,两杯狗尿就烧坏你个猪脑子了。
父亲安慰说,傻儿子你喝醉了,快上床睡吧。哑巴却赖在地上,像一摊烂泥,死活拽不动。母亲说,要不要把春雪喊来,抬他到床上去。父亲说,这么晚了,别喊她了,先叫他坐着醒醒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哑巴茫然地坐在地上。
以前的生活是多么平静啊,哥哥到葫芦头去采煤,嫂子在白瓷厂捆扎碗碟,父母在家养猪、喂兔子,而他在地里忙活。忙得不能再忙的时候,父母兄嫂还有洋洋都赶来了,笑容洋溢在他们的脸上,他能清晰地闻到田里散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气息。春去秋来,寒暑交替,一年年地这样过着。直到哥哥死后,哑巴才闻出来,那气息是幸福。幸福被无情地夺走了,也把日子打乱了,结果是越来越乱。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掉进了罪恶的泥潭里,不但不能自拔,反而越陷越深。
有一次,哑巴在春雪屋里看电视,就是不走。春雪实在太困了,说你回去吧。哑巴却一把抱住她,然后摁倒在地上,嘴巴拱啊拱的,像头猪在啃白菜。春雪也不喊,只是拼命挣扎,但怎么也挣脱不开,哑巴那两只胳膊,像螃蟹的两只铁钳子,死死地钳住她,使她动弹不得。春雪眼睛一闭,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哑巴被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春雪趁机爬起来,径直来到哑巴屋里,在枕头底下翻出一张照片,当着哑巴的面撕掉了。照片是洋洋四岁那年青山带母子俩去日照海边照的,照片上春雪抱着洋洋,海风吹得她的头发飘了起来。
看到哑巴醉眼迷离的样子,母亲晃晃他。突然,哑巴“哇”的一声,所有的伤心、愧疚和绝望都从嘴里喷了出来。吐完,两位老人觉得哑巴醉得轻了不少。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把他搬到了床上去,给他喂了红糖水解酒。哑巴身体不动了,正慢慢地睡去,身上的薄被子在微微起伏。
哑巴的枕头底下有一张照片。那是晚上春雪来抱洋洋时放进去的。已露出了一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