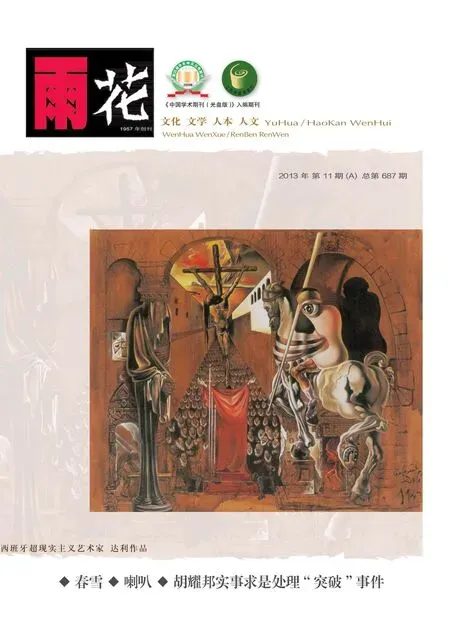满宽的心愿
●王成祥
满宽的心愿
●王成祥

几天之后,满宽成了个瞎子。只见他戴着墨镜、手握竹竿,每天都要在村路上走一趟。他的不幸,很快被村民传扬开来。
满宽一夜之间成了个瞎子。
这天上午,他戴着副墨镜,手握一根竹竽,一步一步走出了家门。
正是桃红柳绿的大好春天,天空有片片白云在悠闲散步,四周有不知名的鸟儿在婉转啁啾,附近的河塘里,一条大鱼快乐地跃出水面,随后“啪”的一声,身体又重重地落入水中……可这些对满宽来说已显多余,因为他成了瞎子,只能靠想像去感受一切,无奈满宽已认定想象一类的事儿不大靠谱。比如他曾想像过三个儿子全部成家后,一个大家庭能够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他和老伴过着子孙绕膝的幸福生活,可大儿子成家不到半年,就另起了炉灶。二儿子虽然脾气好,可结婚一年后,禁不住媳妇的再三捣鼓,也和他们分开。满宽只好将惟一的希望放在小儿子身上,但小儿子却被附近一个全是姑娘的人家看中,结果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操办完小儿的婚事后,满宽手中已空无分文。好在一开始,他和老伴还有一些田地可以侍弄,日子还能勉强应付,可随着年岁渐高,对于继续从事农活已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正在这时,老二家因为要扩大苗木生意,将他的田地一下子收了过去,说是每年补贴五百元。虽然有了这五百元,加上村上每月给两位老人分别发放一百元养老金,可满宽和老伴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紧巴,因为从口粮到油盐姜醋菜,甚至水电等,几乎样样都要开销。至于另外两个儿子,理应也有赡养的义务,可自从老二家收了两位老人的田地后,相互间的关系一下子陷入从未有过的僵局。满宽是个有骨气的老汉,他从不张口主动向下辈们要这要那,倒是老伴时常会在他耳边发出这样的抱怨:“父母再穷,也能将一窝子下代养得胖乎乎的,没想到有再多的下代,父母仍被养得瘦骨嶙峋。都说养儿是图防老,简直是鬼话哩!”每逢这时,满宽总是无言以对。
满宽走在村路上,一颗不安的心跳得十分厉害,如同手中竹竿每次敲在水泥地面所发出的声音,这使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异常难看。好在一路上他都没碰到任何行人。有一刻,他让脚步停了下来,似乎在调整着什么,当感到心脏跳动得不再那么厉害,并且脸上的表情有所缓和,这才用竹竿轻轻敲击着水泥路面,继续慢悠悠地朝前挪动。其实,对于脚下这条村路,他已走过七十多年光景,即使闭着双眼,也能照直不打弯地一气走到底。更何况,原先高低不平的土路,如今已被修成光滑崭新的水泥道。虽是这么想,可他不愿丢掉手中的竹竿,他感到有竹竿与没有竹竿在别人眼里意义定会大不一样。可别人在哪儿?此刻怎么连个人声都没有?难道连老人和小孩也像年轻人一样,一夜之间纷纷前往城里打工了?抑或是人们见了他这副奇特的装扮故意敬而远之?这么一想,他刚刚恢复的那点自信,顷刻间又荡然无存。
终于有人迎面而来,远远就冲他打起了招呼。满宽一听,知道是村上的五保户来福,便一时装作没有听见,继续用手中竹竿敲击着水泥路面朝前缓缓走动。满宽知道,来福年轻时父母就双双过世,一直未能讨到媳妇,如今已六十出头,依然过着光棍生活。没想到他因祸得福,充分享受了公家的种种好处,先是被列入低保户,如今又成了五保户。就在不久前,他那曾见证近半个世纪的两间土坯老屋被拆了,由公家出资在原地盖了一幢漂漂亮亮的“蒙古包”,“蒙古包”不仅内外粉刷一新,屋顶还盖上了琉璃瓦。满宽看在眼里,顿生羡慕。他和老伴现在住的也是“蒙古包”,里面有一间堂屋、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这房子还是十多年前造的,供他们住到老死应该不成问题。可问题是,当年建造时,由于缺钱,里外都没粉刷,如今已十分陈旧,尤其和左邻右舍的楼房比起来,更是不堪入目。满宽虽然年纪大了,也懂得好个面子,他一心想将房子的里外粉刷一遍,最好还能像别人家一样,将房顶也换成琉璃瓦。可他找一位瓦匠来看时,得知连材料和工钱在内,需要八千元费用,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目。“那如果只里外粉刷不换瓦呢?”瓦匠又重新算了算,然后告诉他:“那也至少三千块。”那位瓦匠和他小儿子是小学同学,见满宽仍然拿不定主意的样子,便安慰道:“老人家,你一时拿不出钱来没有关系,等事情做好后,我会找你三个儿子去结账,让他们平均分摊。”满宽听后,连连摇着头,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当儿,来福已经走近,看到满宽有点奇特的装扮,一时不解地问:“老满,你这是怎么啦?”满宽收住脚,朝四周茫然地瞅了瞅,先是拖着长长的语调轻轻问了声:“你是来福吧?”而后才回答道:“我的眼睛……瞎啦!”来福大吃一惊,伸出右手在他墨镜前使劲挥了挥,并用近乎哀伤的语气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反正今天一早醒来,就什么也看不清了。”说到这儿,满宽有气无力地反问道:“你这是从哪儿来?”
来福于是告诉他,端午快到了,他刚去村部领了一笔过节费,还有鱼呀、肉呀、粽子之类的物品。似乎为了让对方相信,他还特意将左边肩膀上那只鼓鼓的蛇皮口袋放了下来,然后打开袋口,让满宽的手伸进去摸了一番。
“嗨,想不到你的日子过得比我自在多啦!”满宽摸完后不由得感叹道。
“嘞,这个你拿回去当下酒菜。”来福顺手从蛇皮口袋里拎出一只咸鸭朝他递去。
满宽摆摆手,又连连摇着头说:“我不要。”
“老哥,别客气!我来福光蛋一个,生是公家人,死是公家鬼。只要在这世上多活一天,公家就得多养我一天。等哪天被阎王招去了,连丧葬费也是公家的。”
听来福这么一说,满宽只好将那只咸鸭拎在了手中。两人沿着村路开始慢慢往回走,一边不停地说着话。满宽手中的竹竿似乎成了多余,因为他的手始终被来福牵着。每当在路上碰到行人,来福总会主动作出一番解释,而满宽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对方,神情显得异常凄凉。临分手时,来福突然提醒道:“老哥,既然你的眼睛出了问题,公家不会不管的。”
满宽一时没有应答,他摇摇头,用手中的竹竿轻轻敲击着路面,心事重重地进了自家的“蒙古包”。但来福的话,让满宽想了很多。他知道,这几年由于搞征地拆迁,村上一下子富得流油。来福那次亲口告诉他说,通过征地拆迁,村上一下子有了五百万。那些钱呀,其实都是从被征地拆迁的老百姓身上刮下的。
满宽知道,因为国家在当地要建一个大厂,前年村上就有一半农户家被拆迁了,那些被拆迁的农户,家家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经济赔偿,可是村上怎么还会有五百万?那该是个怎样巨大的数目?
来福见满宽一脸惊讶,便继续说:“拆迁里面有很多的鬼名堂。要知道,国家给老百姓的赔偿款其实很高,可到了镇上,就变少了一部分,到了村上,又会少一部分,这叫做层层扒皮。更可恨的是,拆迁公司和地方政府有时会联合起来欺骗老百姓,比方说,如果遇到一些钉子户,镇里和村上的干部就会充当说客,反复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软硬兼施,直到对方败下阵来。”来福说到这儿,似乎意犹未尽,他咽了口唾沫,又继续说开来:“但他们也会遇到个别不买帐的主儿,我就亲眼见过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因嫌赔偿款过低,要求再增加十万元,谈判多次都没成功。后来,赔偿款在原来基础上已增加了八万,可他仍然寸步不让,一口咬定要十万。后来,果然就分文不少地增加了十万。因为那个不怕死的家伙身上居然绑满了雷管,手中始终捏着一只打火机,扬言死了也要拉个公家人来垫背。”
“想不到,公家也会干出这种操蛋事儿。”满宽不满地说。
“更可笑的是,双方签字是在夜晚进行的。公家有位管事的家伙说这是特事特办,末了还要求那户人家千万别声张出去。”
满宽又问了个“为什么”,来福这回压低嗓门,有点神秘地说:“这还用问?当然是担心会引出更多麻烦事。老满,你想想,一户头上就有十万块的水分,那一百户是个什么概念?不信的话,村部大楼已经造好了,你有空过去看看。”
那天,为了“蒙古包”能够内外粉刷的事,老满真的去了趟村部。在一幢十分气派的崭新办公楼里,他战战兢兢地找到一位管事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谁知话音刚落,对方就问:“老大爷,你家儿子是不是不赡养你?”他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
“大爷,别怕,有什么麻烦尽管说。赡养老人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受国家法律保护。你如果有什么担心,村上可以出面帮你解决。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申请补助金一事,我们实在难办。因为补助金发放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标准,况且你有下代,生理上又没有任何缺陷。”听年轻人这么一说,满宽只得悻悻地退了出来。但他显然不大甘心,一时在楼下一座十分漂亮的水池旁站定,目光时而对着从几道水管里喷出的好看水雾不断张望,时而又注视着水池内几条正自由自在游动的金鱼。“不行,我得再上去找找那个年轻人,就问他村部原先只有几间不起眼的平房,如今建成这幢豪华气派的大楼,钱是从哪儿来的?”主意已定,他正欲转身,却被一阵响亮的喇叭声给吓了一跳。当抬起头时,他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随着电动门的徐徐拉开正缓缓驶近水池,然后轻轻拐了个弯,最后稳稳停靠在村部那扇偌大的玻璃门前。几乎与此同时,刚才那位年轻人已从楼道里快步走出,热情地将一位刚从小车里钻出的中年人引往楼上。目睹这一幕,满宽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顷刻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来的路上,心事重重的满宽反复琢磨着刚才那位年轻人所说的话。“况且你有下代,生理上又没有任何缺陷。”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听上去有点像骂人?没有下代可以得到公家救济,这话他信,因为来福就属于这样的人。难道自己想要点补助,非得让下代消失不可?妈的,这是什么话!再说,我身体各方面还挺硬朗,难道非让我变成一个聋子、哑巴或痴呆的老汉?满宽越想越生气,越想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后来,当他抬起头时,从远处又看到了自家的“蒙古包”。那“蒙古包”夹在一排高大的楼房间,又旧又矮又丑,有点像只死去的癞蛤蟆常年趴在那儿,显得毫无生机。满宽的脸不由得红了起来,同时,一个荒唐的想法不觉涌上心头。
满宽将那个荒唐的念头牢牢地压在心底,不肯让它轻易冒出。没想到,每次当觉得快要被压住时,它却在不经意间又十分顽强地冒了出来。满宽同自己较量着,一连几天里,他感到心烦意乱、寝食难安,直至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于是,他只好将那个荒唐的念头如实向老伴说了一通。老伴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妈的,老百姓的钱,每天不知被乱花多少!”满宽语气不平地大声嚷道。老伴终于不再言语。
于是,几天之后,满宽成了个瞎子。只见他戴着墨镜、手握竹竿,每天都要在村路上走一趟。他的不幸,很快被村民传扬开来。
满宽再次来到村部是在一个“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午后。这回,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在老伴的陪同下前往的。一路上,有人清晰地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有位老太婆在前面引路,后面跟着个佩戴墨镜的老头,连接他们的是一根细细的竹竿。他们走过一片青青的麦田,走过油菜花盛开的菜地,在阵阵布谷鸟的高歌中,步履蹒跚地朝不远处一幢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大楼而去。而在那幢大楼不远处,呈现的乃是青山含黛、碧峰染翠的更美春色……
满宽终于如愿以偿,只是从此足不出户。
面对已被粉刷一新的“蒙古包”,人们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要是他老人家能够亲眼看到,那该多好!”
满宽不久后生了场大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老伴。
人们感到有点奇怪:他死的时候,双眼居然睁得老大。更令人痛心的是,他的老伴呼天抢地痛哭了几天几夜,结果竟将一双好端端的眼睛给哭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