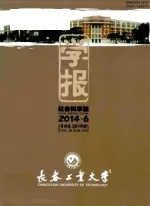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赫克利益法学综评
薛 姣
(浙江警察学院 法律系,浙江 杭州 310053)
一、利益法学发展的轨迹
利益法学作为服务于法学实务的一种规范解释方法论源起德国,执其牛耳者当属“利益法学之父”赫克(Philipp Heck),他认为“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是人们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1](P255)概念法学独领风骚的19世纪德国,利益法学的提出无疑是颠覆性的,是“哥白尼革命式”的转折点。利益法学揭露了概念法学的先天缺陷,即“逻辑的优先地位被对生活的研究和评价所排斥”,[2]打破了法律无漏洞和法律逻辑自足的神话,其子嗣“价值法学”又延续了“利益法学”的香火,在汇并、融合中逐渐发展为当今法学方法论的主流思潮。但因为一些历史上的原因,赫克利益法学宝石般的价值却被各种尘埃掩去了风华,未被正确地重视,不免令人扼腕。
二、赫克的利益论:最广意义上的利益
既然称之为利益法学,“利益”的概念自然成为理解利益法学思想绕不开的门槛石,而赫克利益法学又是继承了耶林关于利益的思想后发展出来的。在对何谓利益的解答中,耶林在此对利益一词的广义用法——利益不仅限于经济上的利益——深深影响了赫克对“利益”的看法,他的利益界定也是划括在最广意义上的,非仅指物理的存在,也包括非感官的、理想上的利益与享受,并强调任何一种对这个词所做的质的限制都必然会造成而且也已经造成了对这个方法的彻底误解。①参见Philipp Heck“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Magdalena Schoc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p130,p133.
三、赫克利益法学的研究方法:评价地形成诫命
“利益法学之父”赫克批判地接受耶林“目的方法论”后,提出他的“利益冲突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并非平行和谐的,而是往往处于相互冲突对峙的状态,这样状态的出现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可能满足所有存在的欲望,法律在这些欲望中必须有所择取,正是这些利益的冲突形成了法律上的诫命。他强调解释的出发点是:法官应受制定法的拘束。在对法官与立法者的关系上,赫克使用著名的“主人与仆人”的比喻:法官是立法者的助手和仆人,但法官不应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考虑到法律的精神与意义,为主人利益状态“设身处地的思考”的“思考式服从”,要“评价地形成诫命”。对如何“评价地形成诫命”的问题,赫克的回答是:“按照利益法学的原则,评价地形成诫命是这样进行的:必须要由法官先掌握到与该判决相关的利益,然后对这些利益加以比较,并且根据他从制定法或其他地方得出的价值判断,对这些利益加以衡量,然后决定较受该价值判断标准偏爱的利益获胜。”[3]
通观赫克的作品,笔者总结了赫克利益法学方法论的逻辑,其可从四个设问中得以体现:(1)该案的事实是什么?(2)该案的事实是否均可以找到法律构成要件的概念特征?(3)是否可以通过对法律利益的探究工作,考虑矛盾双方各自利益优先性是否已经为制定法所决定?(4)若不能从制定法中得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出现法律漏洞时,如何处理?最后这个问题恰恰反映的是利益法学在漏洞填补时分歧产生的关键点,即评判标准和价值序列问题。
步骤一:确定事实。在步骤一中,法官需认清某一具体案件中相关者是谁,案件事实特征是什么。
步骤二:逻辑推演。在步骤二中,解决的是该案中事实是否可以包摄于某具体条文的问题。若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出现了赫克所谓的“简单的情况”。在此情形之下,法官只要逻辑地进行“规范+事实=判决”的三段论演绎即可得出正确的判决,并不需要作利益的检验,因为立法者对此问题已有明确的判断,法律事实已逻辑地包摄在法条之中。法官的工作至此基本可以告一段落。
步骤三:利益探究。若在步骤二中回答是否定的,则需继续移步到步骤三——探究相关利益。实际上是探知制定法的价值判断的环节,赫克也认为,利益法学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利益探究的问题。法官到这个步骤需要去发现规范中所包含的立法者的利益判断(Interessenentscheidung des Gesetzgebers),并且需要受到“从制定法得出的价值判断”的拘束。立法者意思的探究就成为利益法学规范解释的重点,赫克坚持的是“历史的解释的方法”,但他的历史解释并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学上的“意思论证”,而是对形成这种价值判断原因的究问与续造式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他并不只是主张进行立法目的探究,还主张随时代变化而调整,且不仅要探究“得胜的利益”,也要探究参加这场角力的其他利益,包括“战败的利益”,这就是赫克所谓的“利益细分原则”(Maxime der Interessengliederung)。
赫克利益探究的结果,会有三种情形出现:“通常情形”、“授权情形”和“漏洞情形”。“通常情形”下,立法者已形成并说出了诫命,法官只需将法律事实逻辑地包摄于法律概念之下,符合法律之意图,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判决。第二和第三种属于广义上的漏洞,不同的是“授权情形”下的漏洞是“有意的漏洞”,而狭义的漏洞就是“非有意的”。在立法者没有进一步确定概念内容,而允许、委托法官进行符合利益的补充时,如法律中关于“合理期间”、“重大事由”等不确定概念,赫克认为法官应该注意到“法律整体结构”、整个制定法法律秩序的评价结构,符合“法律秩序”地形成诫命。对狭义的漏洞赫克再细分为“第一次漏洞”、“第二次漏洞”和“碰撞漏洞”:在法律产生时就存在的漏洞,是第一次漏洞;生活关系因时间经过而产生的漏洞,是第二次漏洞;碰撞漏洞源自法律诫命与评价矛盾的碰撞,在这种情形下,历史的事实没有一致性的诫命与一致性的价值体系。相对应的填补方式分别是“执行”(Ausführung)、“事件经过上的调适”(zeitliche Anpassung)和“调和”(Ausgleichung)。
步骤四:漏洞填补。在出现漏洞、无法从制定法的价值中找到明确指向时,就出现漏洞填补的问题。赫克既反对“概念法学”刻板的“包摄”,在找不到法律规范时,要么拒绝裁判要么将漏洞忽略掉的做法,也反对“自由法学”个人式的、完全不考虑法律一般规定情形的处理方式,他认为法官应该符合目的地、依赖式地去进行法律补充,进行很好的折衷,既避免拒绝填补漏洞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发生,也要确保法的安定性不受过分的危害。而赫克折衷方式的具体运用,可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制定法的远距作用”概念,也可以说是其方法论精髓所在,其重要性也是赫克再三强调的。“制定法的远距作用”在现代方法论上仍被采用,与类推较为相似,只不过“制定法价值判断的远距作用”更强调的是具体案件中的利益冲突状态和一个制定法业已形成的利益冲突选择结果的联系。赫克以死因的利他合同为例展示了制定法远距作用是如何具体运用的。他通过比较利他合同①案情大致是这样的:某退休者有多位侄女。在遗嘱中,他赠与侄女们同等份额的财产,却因无心之失而遗漏了一位侄女。他没有更改遗嘱把这位侄女加进去,而是在某银行存了一笔相当的钱款并与银行约定,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自由、排他地处分这笔款项。如果该款项未被处分,就在他死后归那位侄女所有。在这位退休者生前,那位侄女的法律地位是很清楚的:她还未获得对钱款的权利,而只有一种针对其伯父(被继承人)的不受保护的期待(《德国民法典》第331条)。假设伯父死亡,其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破产程序启动,谁能对存在银行的那笔款项主张权利?是那位侄女,还是遗产债权人?参见吴从周著:《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中的受益第三人和其他遗嘱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定法上已经对债权人的利益优于受遗赠的人的利益做出价值判断,而利他合同(利益第三人契约)中的受益人在地位上和应受保护的程度上与受遗赠者并无不同,通过制定法关于遗嘱继承中的法条的“远距作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同样的利益冲突下,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也应优于利益第三人的利益。这个结论与当时严格秉持概念法学立场的帝国法院的判决截然不同,因为帝国法院套用《德国民法典》第328条的规定,公式化地进行概念的推导,其结果就是作出严重违背生活的需要和法感的结论。赫克认为,只有对利益状况进行考察,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合理处理制定法刻板过时的疆线。
如果法官缺少可以取向的制定法远距作用,此时赫克认为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得出价值判断,按他的解释,“其他地方”指的是“法律共同体的价值判断”和“法官的价值判断”。若“法律共同体内共同的价值判断”也缺失的话,法官可以自己的评价填补漏洞,尤其在立法者授权情形下的漏洞填补时,法官自己的评价十分重要。当然,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法官价值判断的标准——赫克并没能正面回答法官是适用何种标准去界定或衡量利益冲突的问题。赫克也并非对这种“缺憾”浑然不知,但他以利益法学研究目标的局限性为由作推诿,将研究的包袱甩给哲学,因为他认为,利益法学的服务对象并非立法者的工作或社会上的世界观,而是法官,且法官只需要在现有的法律秩序中实现公认的理念就算完成职责。
尽管缺失具体衡量标准,赫克还是“不甘落寞”地进行了一番作为,指出了法官漏洞填补的界限,亦即所谓法官“评价地形成诫命”的范围,他认为法官应该在实现个案实质适当性的利益法律安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利益之间不断衡量,对于这两种利益孰先孰后,正是法官是否可以类推或造法的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赫克的利益法学非常强调“法律感觉”、“判决感”、“直觉”、“情绪”等感性因素,他甚至并不讳言利益法学多少是种感觉论。法官活动的论理,不属于认识思维的论理,利益法学的理想,不在于各种思维结果的真实性,而在于思维结果的生活价值或利益价值。[4]在赫克“灯笼的比喻”中,他说理性就像灯笼一样,给判断者所到之处撒下光点,但他背后的黑暗城墙,更多混沌不清处是非理性的生活。只不过,在利益衡量时,理性衡量和法律感觉应该是交融的、协力的。如果对这个比喻的理解正确的话,似乎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利益法学真正的法源其实是各人内心的“法感”,而非衡量的理性。“理性考量之光”只是对根据感性作出的判决加以把关,来弥补仅凭法律感觉却无法验证的缺憾。在这里,“法律的感觉”作为一个机关,安置成为利益保护的预警机制:当法律规范不符合法官对法律规范期待的普遍要求时,例如相同案件未作相同处理,“法律感觉”就会作出反应。
四、关于赫克利益法学的评价:感性与理性间的方法改变
卢埃林说:“方法的改变才是最大的改变”。利益法学作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的确是一次意义深刻改变。拉伦茨都不得不承认:“20世纪之初,菲利普·赫克所倡导的‘利益法学’至少在私法领域上获得不凡的成就。”[5]如果说耶林的“目的法学”结束了当时德国法学沉迷于概念天堂“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的计算时代,那么赫克的“利益法学”则启示了法律人如何用“利益”的棱镜正确折射出真理的方法。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利益法学这种方法就在于它对教义论的宣战,也就是它是一种决疑论。
批评赫克的声音,一是质疑他的利益观包容过度,二是质疑他评价标准缺失而沦为“感觉论”。[6]赫克的利益法学也曾受到拉伦茨、Isay等人的笔伐,甚至被贬伐为“根本算不上一种方法”。笔者认为,耶林也好、赫克也好,后起之秀 Müller、庞德也好,尽管他们的“利益观”往往因过于宽泛受到诟病,但也不妨视此为利益法学的特色所在——因为“无所不包,所以无所不能”,也正是这种广义的利益观,才能让我们不受局限地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利益冲突问题。另外,即使认为利益法学是一种感觉论,也未尝就是一件坏事。至少在形成法的判断力方面,利益法学对法学教育方面是有帮助的,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法律,尤其是民法所体现的价值判断。而评判标准上,赫克也并非如批评者声讨的付诸阙如、毫无作为,至少在历史的解释、制定法过度老化、调和相冲突的价值判断问题等部分,利益法学都进行了价值探究。
赫克的利益法学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做评价:在宏观(立法)层面上,赫克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法学方法的问题是宪法问题的人,认为法官解释法律需符合法治国家权力分立的要求,其方法论的基础就是主张:“法官应受制定法的拘束”;在微观(个案)层面,利益法学方法也能做到兼顾法律安定性和个案判决适当性的平衡,是一种通过个别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法律外在整体价值的同时生成判决的方法。赫克的利益法学可分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在理性部分,如探求制定法价值判断的认识过程,进而适用“制定法的远距作用”于相关案件,这是理性衡量可以办到的;在感性部分,法官直觉的法律发现和下意识的利益衡量形成一种报警机制,当法律包摄的结果违反利益时,警报就会拉响,提供了新的司法观察方式。因此,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赫克利益法学的主张确有可取之处,甚至可能是最佳的解释学了。他所提出的“制定法远距作用”是他最大的亮点。
在漏洞填补过程中,赫克的利益法学通过交替地站在各个当事人的视角上分析其利益,复合地、衡平地解决,可以更为灵活、公正地实现个案妥当性。需知社会中的法律,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表层往往是不固定的,如流沙般或快或慢地流动着和变化着,作为高度经济成长、社会发生剧变之时期的方法论,利益法学在某种意义上能很好应对这种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当然,赫克的利益法学默认的前提是,法律相当多部分是稳定的,并且要尊重制定法的权威,不能轻视暂定的法律秩序所具有的固定性。
可惜赫克终没能解决价值位阶问题,对“价值变迁”、“利益优先顺位”等难题不置可否,而将这个法律哲学的问题与其方法论断然切割开来,的确是会影响到利益法学作为方法论的周延性和科学性。可也正是这样的弱点,才给了他的衔续——价值法学壮大的空间。因此,所谓瑕不掩瑜,赫克从实务的角度出发,在符合宪政的要求下,创新性地提出了其考量的理论,在实践运用中也被验证为有效,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最适合多元民主国家法学方法论的任务。
作为复合着理性与感性之光的方法论,作为衡平的技法,利益法学或者利益衡量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呢?更为理想化的设想是,我们是否可以以及如何用它来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实践,作为一种可以有效规范法官或是过于恣意或是过于机械的司法审判活动法律解释方法呢?殊知“不患概念法学,患没有概念”的贫瘠时代早已过去,中国目前的法治难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如何依”的问题。只是利益法学的方法能否担当此重任,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借用利益法学的光点,让它成为探照黑暗迷雾的一个工具,成为法官形成更具说服力、符合法治要求的裁判的一种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司法困境,还是极具探讨的现实意义。
[1]何勤华.西方法律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陈林林.方法论上之盲目飞行——利益法学方法之评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