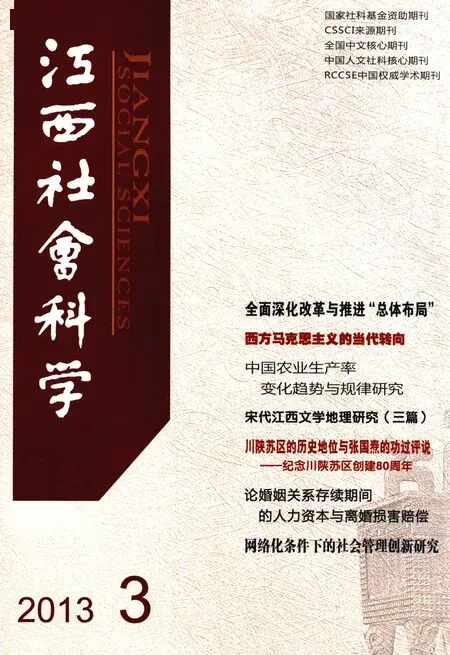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视角下的“诺思第二悖论”分析
■胡 晶
一、对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的零交易费用,即价格机制的运转不存在成本,可以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科斯却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既然价格机制如此完美,那么企业内部交易这种方式为什么还会存在?这样,科斯就发现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他同时提出:价格机制的运转是存在成本的,企业代替市场是就为了节约这种成本。因此,在科斯看来,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1]。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例如,威廉姆森提出,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的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费用”[2];诺思提出“交易成本是实施和规定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3]
制度是约束个人或组织的行为的一个规则集,其内部的各种规则可以改变个人或组织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向他们提供一种激励或约束,改变他们的行为与决策。由于制度是过去变迁过程的产物,是适用于过去的环境的[4],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制度会逐渐变得不再符合现在的需要,人们对现行的制度就有一种变革的需求,这就是制度的非均衡。在制度出现非均衡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种新的制度可以用更小的成本提供更大的收益,一般而言,人们会积极的实现旧的制度向该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制度变迁的方向是降低交易费用。
二、“诺思第二悖论”的产生
诺思指出,制度规定了一种能够影响私人收益的产权界定方式,从而向人提供一种从事合乎社会需要活动的刺激与激励。由于制度也存在效率递减的规律,随着人类交易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交易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现行的制度安排便逐渐不再符合交易行为的需求,甚至可能会限制交易的发展,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更富有效率,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他进一步强调,在这种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人们存在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制度变迁调整的方向是节约交易费用。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制度随之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会逐渐提高,而交易费用则会不断地下降。于是,诺思得到了一个结论:随着制度的变迁不断进行,交易费用会持续的下降。这是诺思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5]。
然而,在考察总量交易费用的过程中,诺思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衡量:1870—1970》中指出,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6]此外,在另一篇文章中,诺思估计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50%,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却要小很多。[7]因此,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整个社会的总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的,这又为诺思解释经济停滞提供了理由。
这样,悖论就出现了: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变迁,制度变得更加富有效率,这在很大程度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根据诺思对美国经济的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社会的总量交易费用又在不断的上升。我们把诺思体系中出现的这一矛盾叫做“诺思第二悖论”,以区别于“诺思悖论”(国家悖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领袖人物一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向、组织选择的标准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例如,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是存在成本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也提出,组织的治理结构必须与交易类型相匹配以节约交易费用[8]。然而,诺思1986年对美国经济的考查却明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交易费用却越来越高。于是,我们便产生种种疑问: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诺思第二悖论”能不能得到顺利解决?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破解“诺思第二悖论”。
三、对有关“诺思第二悖论”解释的评述
很多的制度经济学家对“诺思第二悖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解释,虽然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也加深了我们对“诺思第二悖论”的理解,但是他们的观点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笔者尝试在此进行分析。
袁庆明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出这么一种观点:由于人力因素的限制,人们不能够测量到所有的交易费用。因此他把总量交易费用划分为理论上的总交易费用与测量到的总交易费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潜在的交易转化为现实的交易的数量增多,人们所能够测量到的总交易费用占理论上的总交易费用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虽然制度变迁导致总交易费用降低,但是,由于可测量到的总交易费用快速增加,人们所测量到的总交易费用还是在增加。[9]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根据交易费用的定义,在交易不存在的情况下,经济系统中并没有该种交易行为的进行,经济系统的运转自然也不包括该种交易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一种还没有产生的交易行为存在交易费用么?这并不符合我们对交易费用的认知,缺乏任何的基础。
杨小凯强调,随着分工组织结构的演进,单位交易费用下降,但是总的交易费用却可能上升,而且一般情况下总交易费用是上升的。因为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使得人们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次数也增加了,甚至分工合作交易次数增加得更多,这将导致总交易费用的增加。那么,为什么社会能够接受总交易费用增加的情况呢?这根源于交易费用增加的成本收益分析——专业化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随着分工演进,虽然总交易费用在增加,但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增加得更多,因此社会仍然愿意以不断增加总交易费用的方式来伴随专业化分工的发展。[10]显然,杨小凯的理论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讲述的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随着制度变迁的变化状况,这一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是逐渐下降的。但是杨小凯没有考虑到建立制度所需要的费用,也没有给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为什么会上升一个合理的解释。
李建标、曹利群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的细化,交易规模的扩大,交易费用必然会攀升,制度变迁的方向只是对日益复杂的交易提供支撑,而非一定需要降低交易费用。[11]显然,他们放弃了制度变迁的方向是降低交易费用这一观点,只是选择了诺思的第二个观点,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交易费用逐渐增加。这显然是他们在无法使用有效的方法来包容两种观点的情况下选择的一条道路:选择其中一种观点。然而,放弃许多制度经济学家都认同的观点未免有失草率。
总之,学术界目前对“诺思第二悖论”的解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是都存在着些微的缺陷,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建立一种对“诺思第二悖论”的新的解释,能够稍稍弥补这些缺陷。
四、基本的前提与假设
为了解决“诺思第二悖论”,我们首先提出一些必要的假设与前提,作为我们所构造的理论的基础。
首先,我们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发生。由于劳动分工深化与广化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交易规模,因此我们可以把劳动分工定义为生产力的范畴,并用劳动分工深化和广化的程度来衡量一个社会中交易的总数量。此外,由于制度是对个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约束,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制度定义为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制度变迁就是生产关系的转变。[12]这样,当制度对劳动分工产生很大的束缚,限制了社会进步和交易规模的时候,制度变迁就会最终发生。
其次,我们认为一个既定的制度所能包容的交易的规模是有限度的。因为制度是对个人或组织行为的一个约束集,它自然也约束了人们的交易行为。在对交易行为的约束下,交易的形式和规模也有一个上限,因此,制度制约了劳动分工深化和广化的程度,制约了交易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交易费用。而制度变迁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这种制约,促进了劳动分工和交易规模的扩大。
再次,我们把一个社会总的交易费用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和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一个较为主流的说法是:“经济系统的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费用。”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健康的运转,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可以支撑其正常运转的框架,这就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此外,在基本的制度框架搭建完成以后,为了保证经济系统运转可以持续下去,也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这就是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
最后,我们采用交易费用占总交易额(GDP)的比例来衡量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显然,这部分交易费用随着制度变迁的进行持续降低。以购买100棵白菜为例,在物物交换制度下,需要很高的搜寻成本找到白菜有剩余的人进行交易,交易成本是30%的白菜总额(30棵);在菜市场购买的时候只需要跑到菜市场寻找价位相对较低的卖家,交易成本显然会降低,譬如20%的白菜总额(20棵);在网上交易的情况下,只需在网上查询价格较低的卖家,成本会更低,比如10%的白菜总额(10棵)。其实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随制度变迁逐渐降低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购买白菜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就不会有制度的变迁 (新的交易市场的出现),也不会有白菜交易规模的扩大。
五、对“诺思第二悖论”的破解
利用前面的前提与假设,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制度变迁前后交易费用的变化来得出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并进而破解“诺思第二悖论”。
在此,我们设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为C,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为M,单位交易费用为m,交易次数为n,总交易费用为TC。
根据前面的分析,总交易费用是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和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之和。在旧制度下,制度所能包容的劳动分工的程度较低,交易规模较小,因此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C1)较少;但由于旧制度对交易行为的限制,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1)较高,交易次数(n1)(用于衡量交易规模)较少,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M1)为M1=m1×n1。因此,旧制度下总交易费用(TC1)为:

在制度变迁发生以后,新制度所能包容的劳动分工程度较高,交易规模大,庞大复杂的分工导致了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C2)较高,但是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2)较低,而且新制度下的交易次数(n2)也较高,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为M2=m2×n2。因此,新制度下总交易费用为TC2,根据之前的假设可以得出:

制度变迁导致了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降低,其缓慢递减而且逐渐趋于平缓。劳动分工的深化,不但导致交易的种类增多,而且导致了每一种类交易的数量增加,这样制度变迁导致交易规模急剧扩大,交易次数快速增加。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与交易次数n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单位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变化趋势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呈缓慢下降趋势,而交易次数n呈指数式增长,也就是说单位交易费用m下降的幅度远不如交易次数n增加的幅度。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相对于制度变迁即将发生时,制度变迁以后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C)升高,同时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M)也随之上升,这时可以得出:

我们同样可以计算交易费用占GDP的百分比。根据前面的假设与前提,我们用交易费用占交易额度的比例来衡量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这一费用是随着制度变迁而逐渐降低的。假设旧制度下每一笔交易中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占该笔交易额的比例为P1,制度变迁后每一笔交易中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占该笔交易额的比例为P2,那么,
旧制度下总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R1为:

制度变迁后总交易费用占GDP比例R2为:

比较式(5)、(6),我们发现虽然P1>P2,但是由于C1<C2,因此R1和R2大小关系未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首先可以得到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制度变迁会导致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增加,对于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虽然每一笔交易费用都降低,然而由于交易规模的急剧扩大,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仍然会增加,因此,制度变迁导致了总量交易费用的增加。在总量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上,制度变迁导致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在GDP中的占比减少,而建立制度的交易费用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因此总效果未知。
此外,我们还可以应用上面的分析来考察“诺思第二悖论”。诺思在讨论制度变迁导致交易费用下降的时候指的是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即维持制度运行的单位交易费用(m),它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渐减少。但是,诺思在统计美国的总交易费用的时候却显然只能够计算宏观层面的,总的交易费用(TC),它必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增加,虽然其占GDP的比例未必会增加。这样,诺思对于交易费用的考察就不再存在悖论了。
既然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未必会增加,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这一现象呢?这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劳动分工的深化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日益繁杂的交易种类和急剧膨胀的交易规模使得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所需要的交易费用呈指数式上升,即从C1到C2的急剧膨胀导致建立一个制度的费用占GDP的比例逐渐上升,而且大大超过了维持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占GDP比例的下降,这才导致了总交易费用占GDP比例的上升。因此,未来总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这还要依赖于未来的技术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
本文中提出的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的关系以及对“诺思第二悖论”的解释也只是在当前制度下对该问题的一家之言,希望可以得到其他关注该问题的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1](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美)道格拉斯·C.诺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J].经济译文,1994,(2).
[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美)道格拉斯·C.诺思.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衡量:1870—1970[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6.
[7](美)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8](美)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10]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李建标,曹利群.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J].财经研究,2003,(10).
[12]马克思.资本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