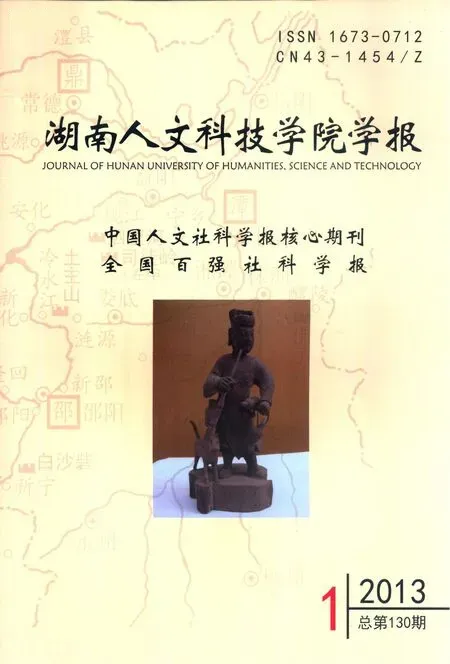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李敦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分裂、大融合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以分裂为主要特点,但在思想文化上却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大解放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重要思想。这一时期的儒学表现出了“中衰”的的特点[1]。《三国志·王朗传附王肃传》:“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2]420此时朝代频繁更替,在政权的交接上体现出“禅代”的特点,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并没有衰退,反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使其在论证政权合法性及为取得帝位提供依据等方面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
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礼学家: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对这一时期郊祀礼制制定的影响表现为: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郊祀礼制上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非儒家因素也被逐渐排除在郊祀之外,但郑说与王说的并存使得这一时期的郊祀礼制并没有成为定制,统治者在郑、王学说之间徘徊,采取有利于统治的部分施用于郊祀,体现出“师古、适用”的特点[3]。
一 郑玄、王肃在郊祀礼说上的异同
郑玄、王肃是汉末魏晋时期著名的儒者,二人的郊祀礼说见于其对儒家经典礼书的阐释,这些阐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郊祀礼制的制定、实行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此以后,各政权所用郊祀礼基本是在二家礼说的规范下进行的。郑、王二人的郊祀礼说继承了汉代匡衡郊祀复古以来于国都之南北郊祭祀的基本格局,但也有明显差异。
二人对郊祀礼制的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郊祀对象与郊祀地点上,而其争论的中心则是位于国都南郊的圜丘祭与南郊祭,对于北郊的方泽祭与北郊祭则不甚关注。首先是祭祀地点。《礼记·祭法》云:“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郑玄注曰:“禘、祫、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郊谓之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孔颖达《正义》:“有虞氏禘黄帝者,谓虞氏冬至祭昊天于圜丘,大禘之时,以黄帝配祭,而郊喾者,谓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以喾配也。”[4]1587从郑玄对《礼记·祭法》的注及孔颖达的疏中可以看出,在祭祀地点上,他认为南郊与圜丘是不同的祭天场所,圜丘所祭为昊天上帝,南郊所祭为感生帝,祭圜丘在冬至,祭南郊在夏正建寅之月,即正月。而关于北郊的祭祀,郑玄注《周礼·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而对《大司乐》:“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郑玄注:“地示所祭于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4]790与郊、圜丘分别祭祀相对应,北郊、方丘也分开祭祀,北郊所祭为神州地祇,方丘所祭为昆仑地示。
下面再看一下王肃关于郊祀的论述。《南齐书·礼仪志》中有王俭引王肃关于郊天场所的记载:“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于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泰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5]122孔颖达在《礼记·祭法》疏中对此概括为:“肃又以郊与丘是一,郊即圜丘。”[4]788-789在这里,王肃将郑玄的郊祀礼仪大大减省,只保留圜丘以祭天,取消了祭昊天上帝与祭感生帝的区别,只以“天”代之,对北郊祭则没有论述。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看出,郑玄、王肃在祭天场所上之所以会形成差异,其源在于二人天神观的不同,郑玄的天神系统是“将《月令》到王莽以及纬书的五帝说来了一番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一套更为完整的复杂的宗教神学体系。”[6]顾颉刚将郑玄的天神系统列为表1:

表1 郑玄观念中的天神系统
正是有此天神系统才会出现圜丘祭昊天上帝、南郊祭五精之帝的郊祀方式。由此图来看,郑玄用圜丘祭昊天上帝,南郊祭五精之帝,那么在郑玄那里圜丘之祭地位要高于南郊。
王肃主“一天”说,是对郑玄学说的反动,《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附王肃传》:“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2]419因此,王肃在郊祀学说上与郑玄必定有背离之处。这与王肃所属重义理、重抽象的荆州学派研经风气是相一致的[7],王肃的“一天说”将郑玄的“六天”说大大简化,表现在郊祀地点上就是郊与丘的合并,将天与五帝等同。王肃说与郑玄说在魏晋南北朝郊祀礼制的建设中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但此时制定郊祀礼制并非纯取一人之说,而是对各种观点有所取舍。此外,后世礼学家的创造使得郊祀礼制不断丰富完善,使得不同朝代的郊祀礼制体现出各自的风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着郑玄与王肃两家郊祀礼说,从西晋到陈,在南朝政权中,王肃学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由王肃礼说更加符合这一时代政权更替的现实决定的。在郑玄郊祀礼说中存在“禘郊祖宗”之说,即在郊祀之时以祖先配祭的礼法,以周为例,禘为祭圜丘时以帝喾配食,郊为祭祀南郊时以后稷配食。因此,如果要以郑玄礼说来制定郊祀礼制的话,统治者必须要找到能够配食的祖先,这些祖先应该像帝喾、后稷一样具有卓著的功勋,或者像文王、武王一样具有开国之功绩,且必须同时具备二人。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政权更替频繁的时代,其政权获得者多“起自匹夫”,要找到两位功勋卓著的祖先着实困难。因此,在魏晋时期各政权郊祀礼制的建立中,祖配问题的解决也要等到第二代皇帝,这种政权获得方式的改变导致了郑玄礼说的不切实用。
二 郑玄礼说下的曹魏郊祀礼制
三国是儒学发展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为了在割据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大量延揽人才,不能为统治者带来实际利益的儒学则不受重视,统治者所重视者为“刑名之学”。诸葛亮、曹操等在治理国家之时多是如此,刘师培曾说:“魏武治邦,喜览申韩法术,以陈群、钟繇为辅弼,诸葛亮治蜀,亦尚刑名。”[8]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的区别》中分析曹氏家风“并不以儒学为务,与豪族的服膺儒教不同。”其具体表现为在文化上尚文辞、轻儒学;在行为上“为人佻易无威重”;在婚姻上因爱立后,“自好立贱”,同族通婚等[9]。儒学发展在三国时期一度衰落。《三国志》引《魏略》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2]420但儒学的发展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而有所改善。在这种对峙中,各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儒学发展有所促进:“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2]420儒学的复兴为三国尤其是魏国郊祀礼制的建立提供了保障。
三国时期郊祀礼制的建立以曹魏最具代表性,虽然这一时期的郊祀无论从群臣对郊祀礼说的议论还是郊祀仪式的复杂程度上看都无法与后世相比,但曹魏将郑玄礼说第一次运用到实际之中,很有代表性。
曹魏郊祀礼制并没有在受汉禅后立即确立,在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后,直到魏明帝景初元年才最终定型。魏文帝曹丕受汉禅后曾举行过祭天仪式,《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曰:“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2]75在曹丕在位期间曾经下过关于郊祀、宗庙等国家重大礼仪的诏令:“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祀,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2]84规定了祭祀的对象,将非儒家因素清除出国家郊祀体系。在曹魏正式确立郊祀礼制之前,其所采用多绍东汉之余绪,《宋书·礼制三》:“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邑,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湮之礼具存,魏之损益可知也。”[10]419-420因此,曹魏在建立郊祀礼制初期无论是祭祀对象还是祭坛形制上都是对汉代郊祀礼制的继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由于儒学的荒废,曹魏要建立自己的郊祀礼制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此外,政局不稳,朝臣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也是重要原因。曹魏郊祀礼制的最终确立在魏明帝景初元年,《宋书·礼三》记载:“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栗山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10]420正式将郑玄礼经注中的郊祀理想付诸实践。关于曹魏采用郑玄说作为其郊祀礼制制定的理论依据,马端临认为:“时康成所著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11]631《三国志集解》也认为:“是时王学尚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庙之大礼皆从郑义。”[12]126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在此之前,曹魏已经采用了东汉郊祀礼制,而明帝时又改用郑玄学说。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郑玄学说可以为曹魏代汉提供合法的依据。
曹魏代汉是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的,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12]80将曹魏视为舜后,其实曹操家世,难以追溯曾祖以上历代祖先的名讳,“莫能审其生出本末”[2]1,曹氏以其卑贱的出身而禅汉为帝,于礼不合,必须用高贵的出身为其家世披上高贵的光环。曹丕即位以谶纬思想为依据,正如前面所引。卢弼《三国志集解》引《西汉金石记》云:“东汉之儒竞言谶纬,卒致三分之际,曹魏受禅,孙吴封山,皆托谶以为文。”[12]85《三国志》裴松之注:“蒋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书》述曹氏胤绪亦如之。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曰:‘于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后,后魏为《禅晋文》,称‘昔我皇祖有虞’,则其异弥甚。寻济难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文多不载。济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谓‘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然于时竟莫能正。”[2]455-456因此曹魏在郊祀中将其“始祖”舜配至上神“皇皇帝天”,以舜妃伊氏配皇皇后地,将虚构中的氏族在郊祀中表现出来。进一步证明其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如果在郊祀中采用郊丘合并的方法则无天神与曹操相配,魏之开创者曹操将得不到祭祀,郑玄的礼说恰与曹魏祭祀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关于蜀国和吴国的郊祀礼制情况,《宋书》记载较为详细,其使用何种礼仪来祭祀则于史有阙,其中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时曾经祭南郊告天,后因孙权以为居非中土而不设郊祀,其末年也曾郊天,以孙坚配,后终吴世无郊祀。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郊社”条称:“终吴之世,未暇礼文,宗庙社稷,不见于史。”[13]王永平《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一文中认为这与孙权的轻视儒学和崇信巫术有重要的关系[14]。
刘备以汉之苗裔自居,在登上帝位后也行过郊天礼,因其享国祚短,并没有亲自主持过郊祀大礼,章武二年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其形制如何,实行与否则不得而知。
三国时期尽管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各国为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都举行了郊祀上天的仪式,这说明郊祀作为国家宗教的重要部分在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
三 王肃郊祀礼说影响下的两晋郊祀礼制
西晋政权是司马氏通过残酷的手段剪除异己而取得的,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在国内镇压反抗者,在国外相继灭蜀国、吴国,最终完成了统一。伴随残酷政治斗争的是思想领域的较量,阮籍、嵇康等人都以“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态度与司马氏相对抗,在儒学内部也有明显的体现,王肃以与司马氏联姻的地位而使其礼说大畅,司马氏以王肃学说来对抗曹魏所采用的郑玄礼说,使王说与郑说本是比较纯粹的学术之争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15]。
这首先反映在郊祀宗庙礼制的制定时对王肃说的采用上,司马氏在建立政权后改变了郑玄礼说在宗庙、郊祀等礼制中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全面采用了王肃礼说。事实上,在司马炎称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以王肃说为基础的《新礼》:“及晋国建,文帝有命荀觊因魏代前事,纂为《新礼》,参考古今,更其节文,羊祜、任恺,虞峻、应贞等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16]581此《新礼》在郊祀上多依据王肃的建议,《晋书·礼上》引挚虞议:“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16]587《庚午诏书》及《新礼》中体现出的天神观正是王肃与郑玄“六天说”相对抗的“一天说”。很明显,在西晋建立之前就已经将王肃郊祀礼说作为其郊祀礼制的蓝本。《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17]《文献通考》:“以圜丘即郊,五帝即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11]631因此在西晋建国后基本上采用了王肃的礼说。
在泰始二年的改革中,是年正月群臣议明堂、南郊废除五帝祭祀,只祭昊天上帝,这是在王肃“一天说”影响下的改革,这年十一月群臣又议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有司又奏,古者郊丘不异,亦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16]584这是王肃“郊丘不异”观点的实行。在这一年的冬至,郊丘合一的祀礼终于得到了实施:“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自是后圜丘方丘不别立。”[16]584将圜丘、方丘与南北郊别立改为设圜丘、方丘于南北郊,在冬至日于南郊圜丘祭天,夏至日于北郊方泽祭地。(西晋不见北郊祭地的记载)金子修一认为:“‘古者郊丘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就是废除圜丘、方泽,只置南北郊坛的意思。”[18]但在《晋书·礼上》中有:“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的记载,则冬至祭祀圜丘的礼制在改革后仍然得到保留。我认为对这句话应该作如下理解:将圜丘祭祀转移到南郊的位置,将南郊坛废除而“更修立坛兆”,保留了冬至圜丘祭祀的传统,将改革后的祭祀称为南郊。因此,上述所说“南郊”一为地名,一为祭名,即王肃所说:“以所在言之谓之郊,以所祭言之谓之圜丘。”[11]621《南齐书》中有尚书王俭引王肃关于郊祀的论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于正月又祭天以祈谷。”[5]122则王肃认为祭天应于圜丘,而泰始二年的改革是“一如宣王所用王肃议也。”因此在西晋圜丘并没有废除,只是用圜丘坛代替了南郊坛,“祠圜丘于南郊”是武帝完全按照王肃礼说建立的。
晋武帝用王肃礼说对抗郑玄说,体现了此时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王肃反郑学,实际上反映了司马氏的兴起和代魏所必须要进行的学术上的更新与礼仪典章的相应变换。”[19]以此确立学术权威,以助于确立晋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泰始二年的郊祀改革在持续一段时间后便恢复了旧貌。太康十年十月,恢复了郊祀五帝于南郊的礼制,这次恢复源于王肃礼说在祖配问题上的缺陷,王肃以五帝同为天,在郊祀及明堂祭祀中废除五帝而只保留昊天上帝一神,这就导致了远祖配与近考配的矛盾,《孝经》中有:“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4]2553远祖(创业祖先)与近考的地位不同,如果同以之配天则导致对远祖的不尊,与儒家经典相违背。故泰始十年的诏书中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以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16]584由此看来在祭天与祭祖问题上发生矛盾时只有调整前者以适应后者。因为祖先为既定的,而天神的布置可以按统治者的需求安排,即钱钟书所谓“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各以为代兴张本。”[20]武帝之后不见有郊祀的记载。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之后,依然举行郊祀礼:“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循依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一依武帝始郊故事。”[10]424所谓武帝始郊故事即在泰始二年二月丁丑举行的五帝废除之后,郊丘合并之前的祭祀。因此,东晋的祭祀基本上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但当时并无北郊祭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直到晋明帝太宁三年七月才下诏设立北郊,明帝未及建而崩。北郊真正设立在咸和八年正月,至此确立了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祀制度,形成了各自的配神体系: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 、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 。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16]584-585。
需要注意的是,晋室南迁之后就以正月上辛作为郊祀的日期,这是对王肃说的重大改变,《宋书·礼三》:“江左以来皆以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不以冬至,皆以上辛。”[10]424由此可知,东晋祭祀是在正月上辛。另外,东晋郊祀还采用先后配祀的方法,是对汉魏郊祀旧制的继承。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晋南迁后,在郊祀礼制上已经逐渐开始脱离王肃礼说,体现出依据儒经改革的趋势。
郑玄与王肃的郊祀礼说对魏晋时期郊祀礼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魏晋的统治者们正是在这种权衡中对这两种礼说进行取舍,采取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方面加以实施。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1.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J].中国史研究,2001(4):27-52.
[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李延寿.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顾颉刚.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J].史学论丛,1935(2):33-54.
[7]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76-179.
[8]刘师培.国学发微[M]//邬国义,吴修艺.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3.
[9]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8-12.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4.
[14]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
[15]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5.
[1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495.
[18]金子修一.魏晋南北朝的宗庙郊祀制度[M]//刘俊文.日本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79.
[19]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1.
[20]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