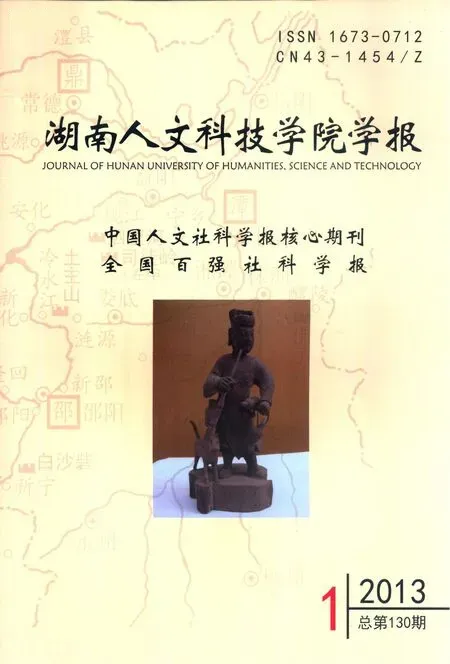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研究概述
徐 伟,刘智莹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也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方法选择上,从理论研究扩展到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研究角度选择上,从单纯的心理学范畴深入到结合社会学、教育学、精神病学展开多视角融合研究;研究侧重点选择上,由起初对网络成瘾概念、理论模型的争论,发展到重视网络成瘾的测量及治疗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们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网络成瘾概念
“网络成瘾”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Goldberg于1994年发现并提出。随后Young博士对于这一类过度依赖互联网的行为障碍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证实了这一类行为障碍的存在[1]。但是目前学界对于网络成瘾的命名和界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名称,诸如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网络行为依赖(internet behavior dependence,IBD)、病态计算机使用(pathological computer use,PCU)以及成问题的互联网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等等。这些名称都是对于不当的互联网使用现象的描述。对这一概念名称进行逐一梳理,可大致分为两类。
第1类提出用“成瘾”来命名。这类命名通俗易懂,较易被普通人群接受和认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患有网络成瘾的人群,与药物成瘾一样,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他们的痛苦真实且深刻。患有这种障碍的人群离不开网络,并将过多的行为表现与心理关注投入其中,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生活。而当主动或被动的与这一行为隔绝后,又会出现一定的戒断反应,表现出诸多不适和焦燥,这些特征和药物成瘾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第2类主张用“依赖”或者“病态的使用”这样的称呼。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此种行为障碍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强调此种行为障碍若以“成瘾 ”来命名缺乏一个条件,即行为过程的物质摄入。换而言之,“依赖”或者“病态的使用”的整个过程只涉及到上网行为,人的身体并没有确切的摄入一些化学物质,并不能称之为“成瘾”。因此,学者建议以“不合理的网络使用”来命名。
就其本质来说,网络成瘾是一种过度依赖互联网,严重损害个体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行为障碍。
二 网络成瘾的理论模型
根据网络成瘾的定义,可以明确的是此类行为障碍并不依赖于化学物质的摄入,这就使得关于网络成瘾心理机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致力于探讨网络成瘾的成因和作用机制,并探讨是什么使得人们能够做到牺牲健康,付出生命,疯狂地沉迷于网络世界。美国心理学会(APA)于1997年正式承认“网络成瘾”研究的学术价值,学术界亦有众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揭示网络成瘾的形成过程,探究网络成瘾的原因。归纳起来,这些理论一般从4个角度出发。
(一)从互联网自身的特点阐释网络成瘾
这种观点的代表理论是Young提出的关于网络成瘾的ACE模型,在这个模型中,A代表Anonymity(匿名性),C代表 Convenience(便利性),E指代Escape(逃避现实),她指出互联网的这三个特性是导致网络成瘾的主要特征[2]。具体来说,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环境,人们可以使用虚拟的身份进行交流互动,不用担心此种交流互动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甚至后果,并安心地表达一些平时压抑的想法;加之,这种双向的交流和互动非常的便利和便捷,而不受时空的限制;此外,互联网的平台给予人们一个改变自身形象的机会,使得人们能够在虚拟的空间得到满足与放松,暂时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生活情境。毋庸置疑,正是互联网的这三大特征的存在,导致了网络成瘾的发生。
(二)从易患人群的个体特征解释网络成瘾的形成
Kan-dell从网络成瘾的高发群体大学生出发,挖掘网络成瘾的原因[3]。他发现,此类人群的网络依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导致:大学生网络的易于获得性;该年龄群体的发展需求使大学生有强烈的社会交往需要,而现实的限制使得一部分大学生将此种需要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上来;自我同一性的建立的问题是这个年龄阶段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网络的匿名性以及信息量的爆炸性迎合了某些学生寻求自我,追求自信的迫切需要。正是大学生群体的这些特征,促使了网络成瘾的发生。
(三)从认知——行为的角度出发解释网络成瘾的形成
R.A.Davis提出了“病态因特网的认知行为模型”[4](如图1),该理论区分出了两种 PIU的模型,特定PIU指因为网络拍卖或者网络财务交易等具有特殊目的的原因而形成病理性的互联网使用;而一般类化PIU则是指没有特殊目的,或者特殊行为指向的互联网依赖,通常是与网上交友、网络聊天联系比较紧密。根据这种理论,病态互联网使用的近端原因是非适应性的认知,也就是说该理论强调的个体负面的自我观念以及歪曲的认知是引发PIU(特别是特定PIU)的主要直接原因。此外,个体非良性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是引发一般类化PIU的直接原因之一。相对的,因特网的特点、生活环境中的压力困境以及个体抑郁或者焦虑情绪等精神病理学因素则是导致PIU的必要条件,属于远端原因。远端原因也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近端原因影响力没那么大。这种理论比较强调认知及社会支持系统这两方面的因素。

图1 病态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
(四)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揭示网络成瘾的形成过程
国内研究者高文斌提出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失补偿假说[5](如图2)。该理论认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发展阻力,此时,如若采取建设性补偿手段,会激发个体的心理自修复,从而形成常态发展,这样的循环发展引发的是健康的、正常的上网行为;反之,若采取病理性的补偿行为,则会使心理无法自修复,进而导致网络成瘾行为的发生。

图2 失补偿假说
三 网络成瘾的诊断
其实,对于网络成瘾的诊断,社会大众仍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误区。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在网络上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或者精力就是网络成瘾,这样贴标签的说法是极其武断的。笔者认为,网络成瘾需要科学的诊断标准,而目前存在的一些诊断量表则为其提供了一定的诊断依据。
在1996和1997年,学者们针对这个问题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进行了讨论,并最终确认了一套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这套标准列出了7种网络成瘾症状:①耐受性增强;②退瘾症状;③上网频率总是高出计划,上网时间总是超出计划时间;④有缩短上网时间的尝试,但皆以失败告终;⑤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或其相关活动上;⑥上网严重影响个体学习、工作、社交及家庭;⑦能够意识到上网行为的危害,但无力做出变化。标准规定,如果个体在12个月时间内的任何时间段出现以上症状中的任意3项,即可确认为网络成瘾。这是心理学界最早的关于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
Young博士由于好友的丈夫沉迷于计算机操作而对这类问题行为产生了关注,她是网络成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Young参照《美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SM-Ⅳ)关于赌博成瘾的诊断标准,制定出了网络成瘾的测量问卷[1]237。其问卷对于网络成瘾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它因简易和科学被广大研究者接受,并成为了相关研究的工具。但这个简易问卷的问题多是关于症状行为的直接描述,仍存在着信度与效度指标不甚明确的弊端。
正是因为存在着不足,Davis根据他提出的认知——行为模型编制了《Davis在线认知量表》(Davis Online Cognition Scale,DOCS)[6],该量表属于7级自陈量表,共36题。此量表相对于Young的网络成瘾量表而言,不仅仅是对病理性行为症状的简单罗列,还相应增加了个体认知观念,这种个体认知观念的相关体现具有一定的预测性,经过研究者的初步检验有较好的效度。
除此之外,很多其他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网络成瘾诊断的相关研究成果。Brenner提出了网络相关成瘾行为调查表(Internet-Related Addictive Behavior Inventory,IRABI)[7],该量表包含了32个是非判断题;Caplan编制了一般问题网络使用量表(Generalize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Scale,GPIUS)[8],该量表经过验证有较好的信效度。
在国内,也陆续有一批学者编制了相关的测验量表。台湾学者陈淑慧以大学生为样本,根据DSM-Ⅳ的成瘾诊断标准,以及临床案例的表现,在侧重心理层面因素的基础上,自编了一个4级自陈量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该量表共26题[9],经验证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是筛查与研究网络成瘾的较好工具之一。随后内地的白羽、樊富珉等也以大学生为对象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包括19个题目的修订版的内地大学生中文网络成瘾量表[10]。华东师范大学的崔丽娟等结合DSM-Ⅳ的成瘾诊断标准,参照国内外经典的网瘾量表,自行编制了12个项目的网瘾量表,他们结合Angoff的标准设定方法将界定分数定义在7,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有7个或者7个以上的肯定回答,就可以判定他为网络成瘾者[11]。
目前,网络成瘾的研究仍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但不可否认,已存在的量表为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工具条件,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网络成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网络成瘾的治疗研究
一般来讲,研究者提出的网络成瘾的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CBT提议建立新的适应性行为来代替旧的问题行为。Young根据她的研究提出了一套针对网瘾患者的CBT方法,其中包括:反向实践,外部阻止物,制定目标,节制,提醒卡,个人目录,支持小组,家庭治疗。Young提倡通过这些手段建立个体新的应对系统,希望能以新的适应性行为代替问题行为[12]。此外,Hall等的研究证实,CBT对于网络成瘾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13]。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也从治疗的角度入手做了许多努力,如杨放如、郝伟等采用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辅以家庭治疗的方式对52例网络成瘾患者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综合干预,显著减少了被试的上网时间,并改善了被试的情绪和心理功能[14]。于衍治2005年的研究则肯定了团体心理干预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成效,证实团体干预能够改善青少年网瘾个体的人际关系、心理防御机制以及生活无序感[15]。张海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团体辅导的过程中,除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因素外,注入情感的因素对于矫正大学生的网瘾也是有效的,实验组的网络成瘾大学生被证实在认知情绪调节、自尊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和提高[16]。张兰君的研究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加入了体育运动的新元素,在12周的干预之后,这种综合的干预模式被证实是有效的,结合体育运动的团辅干预确实对网络成瘾大学生起到了一定的矫治效果[17]。
五 小结
从网络成瘾的提出到网络成瘾的焦点关注只有短暂的十几年时间。然而在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网络成瘾的研究在成瘾的界定、理论模型、测量和诊断、治疗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存在诸多不足,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改进和深化。同时,鉴于我国的网络研究和国外的较大差距以及我中国的现有国情,国内心理学研究者需要在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中国本土领域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特色研究,以期更好地为我国2 000多万网瘾青少年提供积极的指导、帮助和治疗。
[1]YOUNG K S.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J].Cyberpsychol Behavior,1998,1:237-244.
[2]YOUNG K S.Internet addiction:symptoms,evaluation and treatment[M]//VANDECREEK L,JACKSON T.Innov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asource book.Sarasota FL:Professional Resource Press,1999:19-31.
[3]KAN DELL J J.Internet addiction on campus:the vulner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J].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1998(1).
[4]DAVIS R A.A congnitive-behavior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J].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2001,17:187-195.
[5]高文斌、陈祉妍.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96-603.
[6]DAVIS R A.Internet addicts think differently:An inventory of online cognitions[J/OL].http://www.internet addiction.ca/scale.html.
[7]BRENNER V.Psychology of computer use:XLVII.Parameters of internet use,abuse and addiction:the first 90 days of the internet usage survey[J].Psychological Reports,1997,80:879-882.
[8]CAPLAN S E.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development of a theory-based cognitive-behavioral measurement instrument[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2,18(5):553-575.
[9]Cheng S H,W.L.J,Su Y,et al.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and it’s psychometric study[J].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Taiwan),2003,45:279-294.
[10]白羽,樊富珉.大学生网络依赖测量工具的修订与应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4:99-104.
[11]崔丽娟.用安戈夫(Angoff)方法对网络成瘾的标准设定[J].心理科学,2004,27(3):721-723.
[12]Young K S.Internet addiction:symptoms,evaluation,and treatmen[M]//VANDECREEK L,JACKSON TL.Innov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Volume 17.Sarasota FL:Professional Resource Press,1997:19-31.
[13]江楠楠,郭培芳.国外对因特网成瘾障碍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3,26(1):178-180.
[14]杨放如.52例网络成瘾青少年心理社会综合干预的疗效观察[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3):343-345.
[15]于衍治.团体心理干预方式改善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可行性[J].中国临床康复,2005,9(20):81-83.
[16]张海文,卢家媚.对网络成瘾大学生注入情感因素的团体辅导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3):525-527.
[17]张兰君.团体心理治疗和体育运动处方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干预[J].心理科学,2009,32(3):738-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