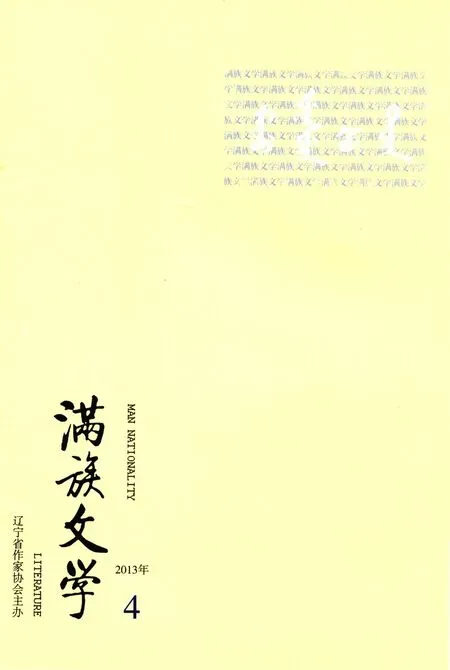陈州笔记五题
孙方友
吕公馆
吕公馆坐落在城内大十字街南边路东,其主人叫吕光第,清光绪年间拔贡出身,西华县清河义村人,民初曾任柘城县知县,后任郑州知州。当时赵倜为河南督军兼省长,一次赵倜的母亲生日,吕光第前去祝寿,特派人从北京请来一班马戏团来开封,在赵倜公馆门前搭台表演三日,很是轰动古城。赵倜的母亲对马戏团表演的杂技特别喜欢,得知是郑州知州所送,对吕光第特别有好感,连在儿子面前为吕光第邀功。赵倜是个孝子,看吕光第能让母亲高兴,便调其为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级别虽没变,但毕竟成了省府大员,权力大,又是“财神爷”,可谓是一肥缺。
吕光第虽系西华人,然清河村距陈州城较近,故在陈州营建府宅。吕公馆门楼高大,大门上方挂有黑漆金字长方形大匾一块,上写篆书“方伯第”三个大字。所谓方伯第多指地方长官的府第门宅。方伯是过去对诸侯首位的称谓,也是唐代以后对地方的统称。吕光第此时高为省财政厅厅长,相当于专任一方的地方长官,所以陈州人就对他家的大门以“方伯第”称颂之。
吕家公馆为三进院,院内有大过厅,再进为楼院,有堂楼和东楼,整个院落全为砖木瓦房结构,布局严谨,宽敞阔气,实为陈州豪宅之一。也就是说,比较上品位。
民国时期,军阀部队调动频繁,驻军一到当地,就向地方要钱、要粮、要草料,开拔时要车、要民夫。那时候,县城商户各种税捐多如牛毛,乡镇派款名目繁多,百姓们苦不堪言。县政府为应付这种杂捐,特成立了支应局(专理支应过往驻军招待、应酬、支款、支物等事务)。凡部队到来向地方要粮要钱,均要找支应局解决。这虽然是个肥缺,也是个苦差,而当这个局长的人选,更需慎重,最好要挑选有后台的人来担任。因为吕光第时任省财政厅厅长,所以陈州城的参议员们就荐了吕光第的侄子吕锡钟。县长一听,当即答应,于是,吕锡钟就一跃当上了支应局局长。
吕家公馆从此更加热闹起来。
民国十六年,豫西镇嵩军刘振华部的一个旅驻防陈州,旅长姓施,叫施大炮。施大炮是土匪出身,很霸道。他仗着刘振华的势力,根本不把吕公馆放在眼中,对吕锡钟任意支使,今天要粮,明天要款,忙得吕锡钟焦头烂额。
吕锡钟架不住了,就跑到县府向县长提出辞职。当时的陈州县长姓梁,叫梁照煜。梁县长自然知道个中因由,劝吕锡钟说:“施大炮只是暂住,总归要换防的。锡钟兄只要顶过这一阵,梁某定当为你邀功请赏!”吕锡钟诉苦道:“县长大人不知,那施大炮蛮横不讲理,贪得无厌,看我连狗都不如!”梁县长笑道:“常言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锡钟兄还需再忍耐。”看辞不掉职,吕锡钟只好又硬着头皮往下撑。
大概就在这时候,其叔吕光第要路过陈州,趁机回乡省亲。梁县长闻之,自然不会放过巴结财政厅长的好机会,就决定在吕公馆大摆宴席,请党政要员、豪绅名士赴宴。当然,也有驻军头目施大炮。
为使宴席上档次,梁县长特请了陈州饭庄最好的大厨来吕公馆掌勺,并提前订购了陈州几家名吃。如方家烧鸡、施家酱蒲菜、段家小笼包子、陈家烤野鸭、邵家枣泥藕什么的,应有尽有。当然,梁县长也不放过这个要钱的机会,让下属准备了好几个批件,争取为本县多要点儿经费。
吕锡钟深怕施大炮也借机向叔父提出无理要求,悄悄向梁县长建议,不让施大炮前来赴宴。梁县长思索片刻说:“这样怕不妥。他是驻军头目,如不请他来,礼仪上不到不说,怕是让他知晓后他会报复的。”吕锡钟说:“若万一他向我家叔父狮子大张口,怕是也不妥。我叔若是不批,日后我与那施大炮更难处。若是我叔批给了他钱,那梁兄你的批件肯定会受影响!属下还是请县长大人三思。”梁县长一想也是,禁不住锁紧了眉头。可如何能不让施大炮赴宴又不让他知道这件事呢?他让吕锡钟帮助想办法,说是最好两全齐美为上策。吕锡钟想了想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不能来!”梁县长问:“那如何能让他自己不能来呢?”吕锡钟沉思片刻说:“通常情况下,唯有这几种原因他不能来,一是他自己不愿意,二是有病,三是军务缠身走不开,四是正巧赶上他的上峰召见他。可现在看来,这四种原因前三种都不可能发生,唯有第四种情况是未知数。”梁县长点头称是,望了吕锡钟一眼,说:“看来,锡钟兄早已胸有成竹了,不妨说出来让我听听!”吕锡钟看了看梁县长说:“我也没考虑成熟。”梁县长有点儿迫不及待,很急地问:“成熟不成熟只管说!”吕锡钟说:“我是想你该通知他赴宴尽管通知,然后再阻止他前来。”梁县长说:“怎么阻止?”吕锡钟说:“最好的办法是在他来的路上制造障碍,延误他的时间。”梁县长一听这话,怔了一下,问道:“你是说,用人佯装搞暗杀制造混乱?”说完,梁县长停顿片刻才又说道:“那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再说,有省府官员前来,影响不太好。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吕锡钟摇了摇头说:“没有了。”梁县长望了望吕锡钟,好一时才说:“这样吧,为缓和关系,我把人情送给你,由你去请他前去吕公馆赴宴如何?”吕锡钟一听让他去请施大炮,颇为不解,怔怔地问:“那样会合适?”梁县长笑了笑,说:“由你去请,规格比我高,因为吕厅长是你叔父,你代表的是吕厅长,算是给足了他面子。但是,有一条你记住,要悄悄告知他千万别当面让梁厅长批钱,就说你叔父最忌讳这个!”吕锡钟听到这里,才明白梁县长的真正用意。他佩服地望了望梁照煜,赞叹道:“还是县长大人计高一筹呀!”言毕,便告辞了梁县长径直去了驻军指挥部。
第二天,吕公馆里张灯结彩,陈州党政官员地方名流皆来拜望吕光第。可令人奇怪的是,驻军头目施大炮却未前来。吕锡钟深感不解,悄悄向梁县长说:“施大炮说好要来,怎么没来呢?”梁县长神秘地笑笑,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已没油水可捞,他来干什么?”
由于没有施大炮的干扰,梁县长的几个批件全都获批。吕光第签过字,笑道:“吕某人回乡一次,要给家乡的父母官批三十万大洋,看来光宗耀祖也不是一句话哟!”
梁县长的批条中,有一张是修葺一座古庙的,需资十万元。不久,这笔钱便转到了吕光第账下。
又过了不久,施大炮带护兵去了吕公馆,他与吕锡钟在密室中说了好长时间的话,看样子很投机。
据说是聪明的吕锡钟借去通知施大炮赴宴的机会,特让他以地方军需为由写了一张十万元批件,事成之后,二人各五万大洋。
花 杀
覃怀公馆,又名四圣会馆——是周家口的著名公馆,名就名在清同治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钦差大臣李鸿章为镇压捻军,曾先后进驻过这个地方。
据考,覃怀公馆在周家口颍河北岸迎水寺。占地约三十余亩。寺内建有山门、东西配房,东偏院有僧室、禅堂九间,大殿为悬山式,内塑岳飞、张显、汤怀、王贵四公像。四人皆怀庆府人,同拜周侗为师,皆宋之名将,精忠报国。在周家口经商的覃怀人以有此同乡引以为豪,捐钱建馆,尊称四圣,作为流落他乡的精神支柱。
周家口就是现在的周口市,位于淮河上游,颍水、沙河、贾鲁河在境内交汇,不但是商贸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曾国藩两次来周家口,一次是路过,一次是驻防。路过的时间大概是1840年,他从湖南赴北京任职时,曾小住了几日。他第二次来周家口是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当时捻军在皖北、豫东一带活动频繁,他是奉命来“剿匪”的。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活动在苏、鲁、豫、皖广大地区。1864年,捻军主要领袖张乐行牺牲后,1865年便分两路开展活动:一路由赖文光率领转战鄂、豫、皖、鲁之间;一路由张宗禹率领进入秦、晋地区,准备配合西北的回民作战。
当时清军有四个驻防地点:徐州、济宁、归德、周家口。曾国藩于同治四年五月初五接到朝廷快信,命他督师“剿贼”。开初他以徐州为驻地进行指挥,后根据形势发展,方决定移驻周家口。
据《曾国藩家书》所载,曾国藩于1866年农历八月初九到周家口,即以周家口为老营,坐镇指挥“剿灭捻军”的军事活动。在周家口期间,曾文公就住在这覃怀公馆里。
住在覃怀公馆里的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除办公批阅文件和会见客人外,每天读书、写字,并坚持散步、下围棋,同时每月三次写家书,专差送达。对每月初一、十五的“贺朔”、“贺望”之客一律谢绝。十月十一是曾国藩的五十六岁生日,宾客一概不见,只接见了好友彭玉麟,并与之同吃早饭。
直到傍晚时分,曾国藩才走出书房,在公馆院里散步。时至初冬,一切萧条,公馆前庭两旁却菊花盛开,养花人是个年近七旬的老者,姓胡,是公馆内的守门人。两江总督住进公馆,自然是岗哨森严,再用不着他守门户。没事干,他就每天扫扫院子,摆弄各种花卉。当初曾国藩进驻公馆时,要求庙院内所有闲杂人等扫地出门,一个不留,不想总督大人进院第一眼就见到了庭前的各种花草,问是何人种栽。陈州府役急忙派人查询,找到胡老汉,通过一番“政审”之类的调查,见胡老汉并不是“长毛”、“捻军”之余党,便破例留下了这位老花匠。也就是说,这军事要地,胡老汉可随便出入。
事实上,这胡老汉从小就是孤儿,是跟随覃怀公馆里的老和尚长大的。令人奇怪的是,他在这座庙内住了几十年,却一直没剃度出家。据说那位老和尚就是养花高手,一段时间里,庙内的给养就全靠卖花支撑。当初老和尚不让胡老汉出家的目的是想让他为胡家续一脉香火,不想胡老汉养花弄草着了迷,一生未娶。后来老和尚圆寂,公馆里香火日衰,胡老汉便利用卖花收入,修葺破庙,塑神真身,并给公馆请来了两个和尚,原想再复当年鼎盛,不料曾总督看中了覃怀公馆的整洁和宁静,便在此挂印升帐了。
那时候曾国藩已来周家口两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和胡老汉见面,自然已经相熟,开初,胡老汉有点儿“怯”总督大人,后见曾国藩和蔼可亲,满腹经纶,便慢慢自然了。更令胡老汉佩服的是:这曾大人虽官至极品,却也爱摆花弄草,尤其念起花经来,一套一套的,听得胡老汉瞠目结舌。因为他一生只重实践,凭经验弄花,而曾文公却从理论上讲起,一说一个透亮,使得胡老汉豁然开朗,禁不住五体投地,连连地说:“没想到您这般大学问!真没想到!”
九月菊开,十月正旺。胡老汉为让曾大人散步时赏花悦心,调情养性,便把盛开的菊花摆得错落有致,满院飘香。曾国藩走到花前,很悦心地赏花,时而弯腰闻闻这一朵儿又闻闻那一盆儿,最后禁不住伸手要抚摸,不想手到半路突然意识到什么,笑着对胡老汉说:“只顾醉花,差点儿让污气浊了圣洁!”
胡老汉望了曾大人一眼,恭敬地说:“大人,一般人摸花,使花沾染浊气;而大人若抚摸一下,能使花儿现出灵气!”
“此话怎讲?”曾国藩好奇地问。
胡老汉说:“师傅在世时,每培出一种新品种,必请少女抚花,只有沾了少女的灵气,才会越开越艳。”
曾国藩大笑说:“胡师傅真会开玩笑,少女抚花花开更艳,可我一个半百老头子能给花儿带来什么呢?”
“大人,话不能那样说。”胡老汉说:“我师傅说,花开平常人家,只是图个好看;花开富贵人家,花随人高贵;花开古庙寺院,就含着某种禅机;花开官宦之家,自然也就有了品位。帝王家的花匠也是六品官哩!”
曾国藩又大笑,说:“胡师傅,这么多天只见你弄花养草,听我瞎叨叨,却不曾听到你有如此高论。今听你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我问你,这与我抚花有什么联系呢?”
“小人不敢讲!”胡老汉望了一眼曾国藩说。
“恕你无罪!”
“我师傅临终时对我说,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覃怀公馆,并要我好生养花,说是有朝一日将得到一位贵人的赏识,这贵人将带我离开这里。但有一条,那贵人必须抚花以后才能答应带我走!”
曾国藩怔了一下,思忖良久方问道:“为什么要那贵人抚花以后才答应呢?”
“小人不解禅机!”胡老汉说。
“我现在确实没带你走的意思!”曾国藩说,“如果你师傅说的那人是我,那就不妨一试!”言毕,曾国藩伸手抚了一下盛开的菊花。
不想一瞬间,那菊花竟突然枯萎了!
曾国藩目瞪口呆!
胡老汉也目瞪口呆!
曾国藩扬起手很认真地看了又看,最后长长地“噢”了一声,说:“怪不得我养不得花,可能是因为我杀气太重之故吧?”
……
不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来周家口时,曾文公果真让儿子带胡老汉去了南京。
放 足
当年在陈州城第一个提出妇女放足的,叫龙言公。
龙言公,字又謇,乳名贵秋,陈州颍河人。他幼年聪慧,就读私塾,考中秀才。1905年3月,曾在北关小学堂任教,同年5月,考入中州师范深造,在学校加入了同盟会,化名龙言公。
1907年龙言公在陈州创办北关小学堂,秘密进行反清活动。这一年,清廷又行科举,龙先生赴省城应试,擢为拔贡。
同年,龙言公再次应聘到北关小学堂任教。他与堂长崔峨亲密合作,以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编写教材,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民主意识,发动爱国青年,开展反清活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校办得朝气蓬勃,学生经常走上街头宣传放足,破除迷信,很是得人心。
不想这时,清巡防营换了个新管带,姓赵,叫赵胜宝。赵管带热衷迷信,一来陈州就到处烧香拜佛,尤其对放足运动,更是反对。据说这赵管带有种“金莲癖”,所娶五房太太全是“三寸金莲”。一听说要放足,五个小脚女人怕得要死,一起跪在赵胜宝面前,要他赶快惩罚宣传“放足”的人。因为她们从四五岁起就被大人用白布条把双脚缠得紧紧的,肌肉被勒瘪,血管被压缩,骨头被折弯,一直缠到长大成人,脚成了马蹄形,走路扭扭捏捏,如果不打上裹脚布,几乎走不成路,而且要用白酒、醋水天天浴洗才能以解缠足之苦。也就是说,当初裹脚时受苦,现在放足也要受苦。如此之苦不但赵管带的五位姨太太不干,连他的老母亲也极力反对。赵管带的母亲听说要放足,拄着拐杖到前庭,对赵胜宝说:“儿啊,当年娘才五岁,你外婆就把我关在房内,两只脚留在门外,用白布狠缠,疼得我脚肿腿肿不能走路,好不容易裹成了,你怎能再让娘受放足之苦?”面对娘和五位姨太太的强烈抗议,赵管带决定抓几个宣传革命提倡放足的反清分子,当然,第一个就是龙言公。
因为龙言公有功名,欲抓必须有罪名,想来想去,赵管带就想到了龙言公的母亲。因为他断定龙言公的母亲也是小脚,如果龙母也反对“放足”,就可以以不孝之罪把龙言公抓起来。
派人暗暗一打听,龙母果然是小脚。据说龙老太太的小脚在颍河周围是出了名的。如此脚小而赢得声誉的老太婆肯定是反对“放足”的。当然赵胜宝虽是行武出身,但并不是鲁莽之辈。为拿到确凿的证据,他先让人请来龙言公,得意万分地说:“龙先生,听说你提倡放足,连令堂大人都反对,不知你如何对待这件事?”
龙言公知道是赵管带故意找茬儿,想从放足下手查找自己的反清事实,然后再下毒手。他冷笑了一声,侃侃地说:“大人,现在世上流行一首《缠足痛》,你可有所耳闻?”
赵管带摇了摇头。
龙言公说:“既然大人不曾耳闻,鄙人就给你念上一遍:
女子可怜真可怜,
可怜把足缠。
三岁女孩正发育,
好不该足用白布缠。
小脚一双,
血泪两行,
唉!凄惨!凄惨!
同胞姊妹们,
快快放足见青天!
念完,龙言公接着说:“实不相瞒,这首歌词就是我母亲编写的!”
赵管带一听,笑了,说:“怕是先生假借令堂之名自己编写的吧?”
龙言公也笑了笑,说:“如若大人不信,你我可同去颍河或派人请来我母亲,当面一试便知真假。”
赵管带听得龙言公如此说,正中下怀,忙派人去颍河请来了龙老太太。
赵管带对龙老太太说:“久闻您老人家编了一首《缠足痛》,可否让晚生一饱耳福?”
龙老太太望了一眼赵管带,戴上老花镜,说:“我嗓子不好,笔墨侍候!”
赵管带急忙派人端上笔墨纸砚,放得规规正正。龙老太太手持毛笔,很认真地写了《缠足痛》,让人转给赵胜宝。赵胜宝一看,果然与龙言公背诵的一字不差。
万般无奈,赵管带只得放了龙家母子。
路上,龙老太太对儿子说:“这赵某一心要找你的错,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先躲避一时为好!”
龙言公沉吟片刻,对娘说:“娘,如果孩儿今日一躲,就不会有明日的扬眉吐气!娘今日为儿受了委屈,是孩儿的不孝。但请娘放心,此仇非报不可!”
果然,辛亥革命胜利后,龙言公当上了陈州县长,而赵管带却成了阶下囚。一日,审讯赵管带时,龙言公不但请来了自己的母亲,也请来了赵胜宝的娘亲。龙言公让两位小脚老太太坐在一起,端上水果茶水,然后才让人带上赵胜宝。赵胜宝饱受监牢之苦,满身伤痕,面色苍白,步履艰难地走进大堂。赵老太太一见儿子,一下就扑了上去,抱着儿子痛哭不止。赵胜宝做梦也没想到娘能来这里与自己见面,禁不住泪流满面。
没想到此时,龙老太太凶凶地走到儿子面前,很响亮地给了龙言公两个耳光,说道:“如果辛亥革命不胜利,我将是赵老太太的下场!你这是替我出气还是刺我的心?如果赵管带事儿不大,就赶快把他放了!”
因为赵管带刚调来不久,罪恶不大,又因为他刚提管带没几年,以前的问题也能说得清。龙言公就尊重母亲的意见,放了赵胜宝。
赵胜宝出狱之后,决定回山西老家当百姓。临走之时,遵照母亲的意思,备下厚礼去看望龙老太太。龙老太太对赵胜宝说:“如若我儿犯到你手中,不知你母亲能否像我一样替他着想?”
这话不知怎么传了出去,赵胜宝的母亲听到之后,想起自己为一双小脚而要挟儿子去抓人,很是羞愧,竟上吊自杀了。
茗香楼
茗香楼是一座藏书楼,为李云灿所建。李云灿字修敏,号暗斋,陈州人。清光绪九年(1885年)举人,光绪十六年(1892年)进士。历任登封嵩阳书院、武陟致用精舍、禹县颍滨经舍山长,河南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入民国后任河南教育司司长、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等职。平生无他嗜好,独喜购书。一生购置约三万卷,藏于家。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灵鹣图》、《四部备要》、《清通典》、《清通考》、《经籍篡诂》、《皇清经解》、《十一经音训》等重要图书均盖有“毋自欺斋珍藏”篆文长方小印,一般图书只盖有“茗香楼收藏书”石章和其他图章。李老先生年老居家,深入浅出,很少与外界联系。李府在陈州城尚武前街,阔阔一宅,三进深。茗香楼在李府后花园东侧,紧靠城湖,算是那条街较高的建筑。楼内有专制的书橱,各种书籍分类储藏,甚为整齐;并编有《茗香楼藏书目录》,红格抄本,便于查找。后来李先生还拟定条例,拟在陈州开设群众图书馆,以会同好,也算是为家乡做些薄力之献。不料计划还未实施,日寇入侵,为躲战祸,携全眷避于项城。
李云灿带全家逃至项城后,心中一直惦记藏书楼,整天精神不振,日渐瘦弱。家人见他身体将垮,便请名医诊断。李云灿说:“我病在心中,能治我病者,非茗香楼不可也!”言毕,便说自己要回陈州。家人听之大惊,轮流相劝,不行,且病情越发严重,万般无奈,只得让他回陈州。
那时候国统区与沦陷区的防线在陈州南姚路口一带。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以后,这里沦为黄泛区。水冲的地方就形成了小黄河,两岸都有岗哨,盘查很严。因为李老先生当时已年过古稀,身体又虚弱,过渡口时就省去了不少麻烦。家人为他备的是辆胶轮马车,车夫姓黄,叫黄天,是李府的老佣人。另外,为照顾老人起居,还随车回去了一个厨娘和一个大脚丫头。也就是说,因为家人都怕日本人,随李老先生回去的没一个亲属,而只有三个佣人。不想李老先生为此很高兴,说这样好,我一人独来独往,没亲人相随,省得有牵挂。我也怕日本人,但我更怕身边无书。若不让我回陈州我会死得快一些,只要让我天天坐在茗香楼里,死而无憾!家人看他爱书如命,也只好随他了。
姚路口距陈州城还有三十华里,临近中午时,李云灿的胶轮马车到了南城门,不想过城门时遭了点麻烦。因为查岗的是日本人,他们看李云灿一派儒家打扮,又坐着在当时算是较豪华的胶轮马车,便误以为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或其他抗日武装搞的化装侦察。当然,岗哨里也有伪军,他们都认得李老太爷,忙让翻译给日本人讲了。日本人一听是李云灿回了,就拿出一个小本本儿查了查——上面果然有李云灿的名字,就急忙给总部打了电话,经过总部同意,急忙放行。
原来日本人也搞统战,每侵占一个城市,就对地方名流进行拉拢纳降,然后帮他们搞什么皇道乐土东亚共荣一体的把戏。李云灿官至省教育厅长,又是省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自然是他们劝降的对象。日本驻陈州长官叫川原一弘,为能争取李云灿,不但没破坏茗香楼,而且还特意让人保护了起来。
这是李云灿做梦也未想到的。
李云灿回到府邸,见日本人非但未动茗香楼,连宅院也没遭到破坏,寂静的大院里,只留下他的两个老佣人,各厅房里的摆设一动未动,还是原旧一般。李云灿简直像走进了梦里,虽然还是那个家,虽然日本人什么也没动,却使他产生了某种陌生感。因为回来之前,他脑子里充满了战争的疮痍,现实与想象的反差如此之大,真让他有点儿始料不及。定神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另一种恐怖——他顿时感到这个平静的宅院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他一步跳了进来,说不清等待他的是福还是祸。
他知道,自己既然回来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他。
果然,第二天,川原一弘就登门拜访了。
川原一弘年不过四十,个子很矮,他像许多矮个子日本人一样爱挺背扛胸,而且由于发育不成比例,头颅就显得过大。这种形象很像屠夫,再加上他那很浓的仁丹胡,更给人某种凶残手辣的感觉。
川原一弘见到李云灿,显得很高兴,说:“我就知道先生会回来的!”
李云灿此时感到自己已走进一个阴谋,心想既回之则安之,很冷地说:“你猜得很对。”
川原一弘笑了笑,说:“我很理解先生的心情。先生虽然暂时走了,但魂一直就没离开茗香楼。一个人有体无魂,那只是一个躯壳儿。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先生。你大概已经看到了,你的宅院可以说是陈州城目前最干净的一座宅院,茗香楼的书籍更是安然无恙。”
李云灿这才看了川原一弘一眼,问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川原一弘又笑了笑,去了手上的白手套,说:“先生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请您出山,为皇军推行皇道乐土,让其在贵国的土地上施行得更圆满一些而已!”
李云灿深思了良久,问道:“我要不答应呢?”
川原一弘的蛇眼里闪出一丝冷笑,说:“我知道先生要这样回答,与我们配合的社会名流一开始都是你这种声音,但最后他们还是答应了。不过,你若不答应我也不强求,只是我将要把茗香楼里的这些书全部取出来!”说完,从袖筒里抽出一沓儿书目单,递给了李云灿。
李云灿接过书目单一看,双目顿然睁大,惊怒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原来书目上全是自己收藏的孤本!他颤抖着手又将书目翻看了一遍,最后长叹一声,对川原一弘说:“你们先拴了我的灵魂,然后让我就范!”
川原一弘“呵呵”干笑了两声,说:“话不可那般说,这只不过是咱们合作的一种方式!”
李云灿怔怔地盯着书单,盯了许久,最后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对川原一弘说:“这种事情非同小可,是出卖灵魂的大事!你要容我想一想!”
川原一弘一听李云灿说这话,也很长地呼出一口气,说:“好吧,我恭候先生的抉择!只是不过要有个时限,这样吧,我限你三日,三日后我希望能听到先生的佳音!因为我不愿听到任何与我相左的消息!”
李云灿双目仍在打直,一天茶水未进。
第二天,仍是茶水未进。
第三天,李云灿走出了卧房,他命家人买来几十丈白绫,给茗香楼全楼挂白。接着,自己也一身重孝,在楼前摆上香案,开始焚香祭楼。他燃上一炉香,然后长跪于地,很静地等着川原一弘。
川原一弘来了。
川原一弘一看茗香楼全楼挂白,李云灿也一身重孝,很是不解,问道:“李先生,这是为何?”
李云灿双目微闭,很平静地说:“想我李某,一介书生,一不能保家,二不能卫国,平生也就这么点嗜好,为我们大汉民族收藏点书籍。可惜,现在也保不住了。为不让国宝落入你们这群倭寇手中,我只好亲自送它们上西天!”言毕,抬眼看了立在楼前的车夫黄天一眼。黄天立刻点燃火把扔入楼内。因楼内泼满了汽油,顿时,一片火光。
李云灿站起身,一步步向火海走去。
川原一弘看得呆了,许久才高喊道:“拉住他,快拉住他!”
此时李云灿已走到楼门口,扭脸对着川原大笑三声,然后就从容地走进了火海里。
李家的佣人一片哭声。
川原一弘气极败坏,将李府佣人都捆绑了起来,审问李云灿是否转移了那些孤本。因为他坚信李云灿爱书如命,决不会将那些国宝级藏书随他火葬。很可能他烧的只是一座空楼,重要书籍肯定暗地转移了。果然,李家车夫黄天就站了出来,对他说:“转移书籍是我一个人按老爷的指示办的,你放了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些书藏在何处。”
川原一弘看了看黄天,信了他的话,便放了其他人,要黄天带他去找书。黄天跪在楼前,磕了三个响头,哭着说:“老爷,恕小的不孝,为救众人,我也只好如此了。”说完,抹了一把泪水,站起身领日本人去了后进院的一座小楼里。
小木楼是李府的储藏室,里边全是破旧的家具和一些坛坛罐罐。黄天领川原一弘和几个日本人上了三楼。里面果然有几橱旧书,但更多的却是李府储存的老酒,黄天走上楼,突然就举起一把铁锤挨个儿砸烂了十几个大酒坛,然后堵了下楼口,大笑着对川原一弘说:“老爷命我藏的那些孤本,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了!我今天就是要为老爷报仇才领你们来这里!你们上当了。谁也别想下楼了!”说完,就从怀中取出火柴,一下划着了四五根,扔到了楼板上,顿时,火光四起,小木楼成了一片火海……
据年过九旬的一位李府老佣人回忆,那一天的大火几乎使李府全部化为灰烬,共烧死包括川原一弘在内的六个日本人。
鸟 女
画卦台为陈州七台八景第一台,位于伏羲陵东南一里许的城湖中,占地十亩。四面环水,台高出水面六尺有余。原《一统志》称此台为“揲蓍台”,意说伏羲曾在此揲蓍画八卦。《寰宇记》中也说画卦台乃“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可见其非凡了。
画卦台是后人为纪念伏羲画卦之功绩而修建的,始建何时,已失考。经宋、明、清各代多次增建修葺,台上建筑颇具规模。到了万历之年,陈州知府洪蒸增建卷棚五间,黄瓦八角亭一座,内奉宋代铸造的伏羲铜像一尊。立一碑,高广各五尺盈,上刻“先天图”。传说此图蕴藏天机,凡人不得解。台上苍松挺拔,虬枝繁密。每当月明星稀,满湖浮光跃金,静听蛙鸣鹤唳,如入蓬莱。
画卦台一隅,住着一户姓于的人家。父女二人,以打鱼为生。于老汉年近古稀,但身板硬朗,能天天下湖。女儿于莲,年方十九,质丽聪颖,能歌善舞。城里城外,颇有些名声。
日寇侵华第二年,陈州沦陷。于老汉怕女儿遭不幸,便把她藏匿在深湖中,白天送饭,夜里陪女儿在湖中过夜。于莲整日躲在芦苇深处,非常寂寞。无事可干,便做芦笛儿,学各种鸟叫。时间长了,于莲竟悟出了不少鸟语。于是人鸟开始相熟。每每听得哨音,百鸟如朝凤般聚集在于莲周围,喋喋不休,诉说衷肠。
到了严冬,芦苇被割,湖水结冰,一片凄凉。于莲湖中不可藏身,只得回到家中。鸟儿像是舍不得于莲,每天早晨或黄昏时分,总有成群结队的鸟儿在于家小院儿的上空盘旋,叽叽喳喳,向于莲问好。于莲心喜,取些谷物,让鸟们吃。事情传开来,人们便称于莲为鸟女——并说她是湖中一只丽鸟转变而成。
消息传来传去,就被日军驻陈州城的中队长田中角荣知道了。田中角荣很想见一见鸟女。
这一天,田中饭后无事,便自个儿到了画卦台处,见到落满小鸟的院子,他就走了进去。
那时刻于莲正在喂鸟,听到柴门响,抬头一看,见来了个日本鬼子,禁不住面色灰白,惊恐地叫了一声。于老汉闻之惶惶出门,一见田中,急忙护住了女儿。
田中会讲华语,笑笑,说:“惊慌的不要,我只是想看看鸟女!”说着,掏出烟来,递给于老汉一支。于老汉怒目相待,只是紧紧地护住女儿。田中尴尬地回了手,自个燃了,看了看于莲,问道:“你就是鸟女吗?”
“她叫于莲!”于老汉替女儿回答。
“你怎么能懂得鸟语呢?”田中平静地问。
于莲望望田中,见他没有恶意,便怯怯地说:“听得多了,也就懂了一些!”
“小时候,我家喂了好多鸟!各种各样的都有。我每天都是在鸟的叫声中睡去,又在鸟的叫声中醒来……”田中满脸稚气,沉浸在童年的往事里。
于家父女不解地互望一眼,说不清这个日本鬼子给他们唠叨这些干什么。
“我母亲是位研究鸟的专家,可她却不懂得鸟语!记得母亲常说:‘我要是懂得鸟语该多好呀!’可惜,她老人家已不在人世了!”田中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了于莲。
照片上是一个身穿日本和服的女人,端庄漂亮,双目间透出善良和慈祥。她的身上落满了鸟。
于莲很是好奇,看看田中,又看看照片,悄声问,“她是你娘吗?”
“是的!”田中痛苦地说,“母亲死于昭和十一年秋天。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埋葬她的那一天,墓地的上空全是鸟!”田中抹了一把泪水,停了片刻又说:“如果母亲活着,我一定写信告诉她这里有一个鸟女,让她聘请你当助手!”
一阵沉默。
“我能给你照张相吗?”田中突然取出照相机问道。
于老汉急忙用身体遮住女儿,对田中说:“俺不照相!你走吧!”
田中遗憾地收了相机,深情地望了望于莲,长叹一声,郁郁地走了。
这以后,于家父女开始提心吊胆地熬日子,深怕田中来这里无事生非,给他们带来祸端。等湖里的芦苇半人高的时候,于老汉就匆匆把女儿嫁了人。
可是,田中一直没来。
日寇投降那一年,于老汉已下不得湖。孤独一人,靠编蒲包度日月。一天午后,他正破蒲草,突然听得叫门声,抬头望去,禁不住吃了一惊。
门外站着田中角荣。
那时候的田中面目灰灰,已显得老相。他对于老汉说:“日本已宣布投降,临走之前,我想见见鸟女。”
“鸟女?”于老汉梦呓般地问道,“啥鸟女?”
“就是您的女儿!”
“噢!”于老汉望了望田中,怅然地说:“她出阁了!早就出阁了!”
田中惊诧如痴,双目里透出遗憾,好一时才说:“那时候我知道你们怕我,所以一直没敢来打扰!现在我们不可怕了,可她却……”田中显得很惋惜。
“你找她作甚?”
“想给她照一张相!”
“为了你娘吗?”
“是的!”
于老汉望了田中一眼,沉思片刻,突然放下手中的活计,对田中说:“走,我领你去见她!”
于莲的婆家也在湖边,距画卦台有五里水路。于老汉用船把田中送到的时候,已是半下午时分。
小院很破旧,到处散发着鱼腥气。田中蹙着眉头走进院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听到响动,房门洞开,一下子涌出两三个娃娃,看到田中,同时惊叫一声,扭头就朝屋里跑,许久,又簇拥着一个女人走出来。
走出来的女人又黑又瘦,衣服褴褛,蓬乱的头发上系着孝布,眼睛的周围萦绕着操劳过度的青丝……
几个娃头上也戴着孝布。
几个娃娃好奇地望着田中。
突然,那女人叫了一声,像是拾起一个遥远的梦幻,眼睛里透出惊讶和疑惑,最后咬了一下嘴唇儿,平静地把目光伸向远处。
这时候,于老汉从湖边走过来,对田中说:“她就是我的女儿!你原来见过的!”
田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得目瞪口呆。他望着当年如花似玉浑身充满大自然魅力的鸟女,禁不住颓丧地垂下了脑袋……
远处,是一只弹痕累累的木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