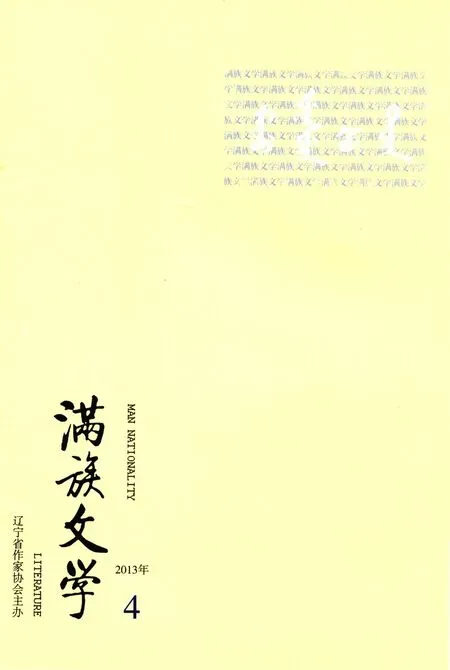四季轮转
苍 耳
三月下旬对樟树的一点观察
我自以为对我的邻居——樟树——了解最多,其实不然。我是按常绿乔木的一般习性来理解樟树的。比如常绿乔木的叶子渐生渐落,故不易发觉其新陈代谢。樟树似乎也是如此。但自三月下旬以来,我早上注意到地上铺满了樟叶,有的淡黄,有的酡红,有的兼色,还有的竟是青碧。看起来,它的换叶季大致集中在春天了。
近几日气候变化颇不稳定,忽雨忽晴,乍暖还寒,极敏感的樟树就喜欢在这间隙悄悄换装,却一不留神被我撞见了。仅一夜工夫,地上就铺了薄薄的一层。我当然不希望清道工来扫它们,就让它们一层层地覆盖下去吧,厚厚的,踩上去有一种清寂而幽深的感觉。
这时你若留意观察它们,就发觉樟树之冠的色彩分布得颇有层次:顶部外缘呈鹅黄色,蛋青般透明,嫩尖部分微微有点酱红,似栖停着万千的蝴蝶;中间部分以暗绿色为主,泼墨似地洇成一团,蓬勃而不失冷静,沉着而毫不浅浮;内里底层则有或黄或红之色斑衬缀着,仔细看去大都形单影只,也有三五一簇的,清清寥寥,静静地悬停在那儿,但整个树冠却被皴染得很有点斑斓雍容的韵致了。比如居委会门前那高大的一株,它的红叶像不像秋风吹燃的枣儿在绿叶中隐现?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樟树,其呈露的色泽和姿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远观和俯瞰,涌动着的樟树冠便很有些烂漫、放浪的风姿;而近看和仰视,其葱郁之气便混和着几分箫索和清峻,不能不令你停下脚步,感受它们内在的驳杂与犹疑,将洒落的叶子视为它们的一种言说。
但我还是搞不懂,樟树落叶的颜色何以如此繁复?它几乎没有什么定准,到了这个节气想落就落,不必顾忌什么色调该落,什么色调不该落。比如,绿叶子在其中就占了不小的比例。这就很让人费解。不像那些梧桐叶和枫叶,落下来都是清一色的。所以当我踩在它上面时,只能对这种驳杂不一、深浅不一暗自惊讶。
经过比较,我发觉樟树的老幼或高矮的差别,都会造成落叶颜色的不同。尤其是,樟树对周围环境的嗅觉特敏感。因而长在不同小环境的樟树,自然会因“感觉”不同而呈现相异的“面色”来。在街道两旁,车辆的噪音和带起的灰尘使落叶大都呈枯蛾色;而在居民区的桥边附近,因那儿开着不少小吃部,樟树的落叶似更早一些,红叶也比较少;间距较密、且被楼影遮阳的樟树,落下来的绿叶、半黄叶似更多。而水边的香樟树的特点是:树冠垂向水上的那一半枝条,红叶挂在那儿能坚持得更久,并以背面淡绯色朝向我。
近几日,在校园进门旁的一棵高大樟树下,我开自行车锁时,常被一堆红得鲜亮、堪称绚烂如火的叶子所吸引。它令我停顿、注目,为之一醉。这棵香樟,至少有二十年以上树龄,生得高大而挺拔,绿髯浓密,像古代齐国的那个美男子。如此英俊不凡的樟树,无遮无拦地向天空腾展,老叶才能获得足够春气的熏染而泛酡晕。
不瞒你说,有一次在三楼上课时我开了小差。原因是,我突然瞥见窗外春天的樟树被八点左右的阳光斜穿而过,树冠内部顿时灿亮无比,其间有疏疏的几片红叶,风情万种,如神来之笔。这时我恍然置身于清秋氛围的晕染之中。
有个在树叶上写书的古人,我很羡慕他。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避乱于江华亭,每天下田干活,累了就在大树下读书,没有纸,就随手把心得记在树叶上,回家后把“树叶笔记”放进瓦盆里,埋在树下。十多年后“树叶笔记”竟有数缸之多,经整理就成了《南村辍耕录》一书,长达三十卷。他真是因祸得福。这种得天地之灵气的写作行为本身,就足以让人回味不尽了。只是我还想知道那都是些什么树的叶子?
写作这篇短文时,三月已临近结束。樟树不久就要清馨四溢了,绽出那极细极细的白蕊儿。那么樟叶究竟然要落到何时呢?还是静静地等着瞧吧。
夏日防线
当连日的暴雨在接近中午还不曾止息时,它已强有力地涂改了我周围的事物和景观:仿佛史前的淫雨与当下的垃圾、尘灰混成一片浊水,使偌大的排水沟满溢不堪,所有的下水道都开始回流;而城北这片最大的居民区已成岛礁群,靠近东南角的居民楼最下层已大半沦陷,洪水依次向北涨,底楼几乎家家都进了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熟人家淹了水,一只拖鞋从前门漂出来,一天后竟然奇异地从窗口漂了回去。与此同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另一个潜在的事实,即人与鱼在这个泛滥的季节形成极为有趣的对比:当院中花草们最先忍受被淹的苦楚,而我步步退守地在居所的三道门仓惶垒起积木般的防线时,鱼们正狂欢着越过人们精心构筑的坚固堤岸,漫游在它们不曾也无法游及的广大世界。事实上,柔韧无比、细尖无比的水,已从我们无法看见的墙脚裂纹渗入了客厅和卧室,而鱼们也随之悄悄侵入我们自以为是的、绝对的日常统治区域:当我冒着细雨一路趟水,经过停车场那片靠近排水沟的低洼区时,我的腿肚毫无准备地被擦击了一下:哪来这个神秘的家伙!
我怔在那儿,思维出现短路:这是怎么了?难道这儿有……
但在靠近桥边收费站的地方,青灰色的、约有尺把长的鱼脊,确凿无疑地从水中浮现出来。在这一瞬间,二十多年前的摸鱼动作在我的筋骨脉络中苏醒了过来。我试图逮住它,但很快遭到它冰凉而有力的甩击——它成功地逃之夭夭!哦,这儿有鱼!我几乎本能地叫起来(与白日梦有点相似吗?)。它带给我的快感是如此突然而强烈,以至于我发觉了肉体的另一种颤栗。这惊动了商店门口站着的几个妇女。她们先是一怔:什么,这儿有鱼?接着就不屑一顾地笑起来。我不理会她们。我赶紧回去,拿来菜篮子,用它作捕鱼的工具,同时又伪装成上街买菜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在这儿趟了两圈,但半个鱼影也没有见到。心里想:这回碰上了,看你往哪跑。但我又意识到此处不宜久留。我似乎已被人注意并不断被路人问及菜市场可有菜卖的问题。我支支吾吾,眼角还不停地瞟着水里。
事情竟是如此简单:防线不过被喜剧性地挪移了一下,规则遭到了一点戏弄,于是一切随之改观。到了傍晚时,排水沟(它约有二十米宽)中出现了戏剧性场面: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三五成群的鲢鱼。它们浮在水面并不断飞起,划出银色的弧。当我吃过晚饭来到这儿,一些人手里已经提着活蹦乱摆的白鲢子。他们居然能用手在沟边将鱼逮住。我在这儿住了十年,碰上这等事,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正当我搜索目标时,一条大鱼竟飞落在距我不远的岸沿。一个拿长竿网兜的和一个纯粹的观望者,同时作出迅疾反应,但前者被栏杆挡了一下,后者则抢先一步按住它,整个脸也随之兴奋得变了形。天上真的掉馅饼了!但上游那边的一阵阵欢呼,吸引我来到桥上。桥栏边已围了两层人,沟沿上也挤满了人,个个脖子伸得像老鸭。档次最高的要数居民楼的窗口、晒台,它们此时类似于大戏院的包厢。欢呼、惜叹的声浪此起彼伏。但鱼们没有听觉,它们不断跃出水面,也不断被网兜网住。
想来这是否有点“濠上观鱼”的味道?只是现在还有谁争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一妙问呢?显然,庄子所谓的“鱼之乐”,是一种“出游从容”的姿态,一种自在自由的悠然状态。然而,现代人之“乐”,已很少有庄惠观鱼那样的纯粹之乐了,因为现代人之“乐”必须添加强烈的功利性和刺激性作为燃料,当然也就越来越看不见“鱼之乐”了。然而,当我看见鱼们快活地飞起之时,可能正是它们不堪忍受之时,它们被尘世的混浊呛得够呛,水面上漂浮着人类丢弃的日常杂碎以及意淫的泡沫。突破防线而泛滥的鱼们也未必幸福,这世界到哪儿找庄子所惊叹的“秋水”?鱼们大约想不到,它们梦想的“乐园”竟是如此糟糕,如同一座更大的牢狱。
不过,对现代观鱼者而言,他们毕竟“看见”了闯入野水中的活生生的鱼。这跟在市场上日日所见的、经过精确计量与讨价还价后的鱼有本质的不同。对后者而言,“鱼”永远处在缺席状态。这难道也是一种“水至清则无鱼”?可见擅长筑堤的人们也未必快乐,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几乎是必然的,第二天沟边来了个带电瓶的男人,他用电击的方法捕获深水的鱼,使那些携篮带杆的相形见绌。再后来,又来了个更具专业性的扳大罾的家伙。他在沟边稳稳当当地守着,嘴里叼着烟,几乎网网都不空。岸边的塑料盆和桶里都装满了鱼,他的婆娘拿着秤忙不迭地卖鱼。但来沟边看热闹的人已经不多,稀稀拉拉的几个孩子和老头。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傍晚,我用篮子总算在沟边兜住一条大鲢子,但不知可是在停车场溜之大吉的那一条。结果让家人着实大吃一惊,以至于父亲撂下酒杯,跨过堤防,兴冲冲地奔出门去。
一棵树的霜降
这是一棵寻常的落叶树。只要我站在五楼的窗前就能瞥见它。秋凉渐渐深了。在大毛小毛周岁后的某个下午,我发现它冠面的叶子微微有点黄,但一经偏西阳光的照耀(它恰好站在路边楼角),却自下而上地由灰绿转明艳,一直灿烂到冠顶,清冽而温煦,颇有几分动人的韵致。
这似乎是这儿唯一的落木。人们喜爱常绿乔木的原因不言自明。但我反而觉得落叶树可爱,仿佛它们都是过敏体质和感伤主义者,承受不了一丁点刺激,便唏嘘叹啘,让人也跟着叹息一番。当然,这不符合市政领导们的想法,他们抱怨落叶树会给城市带来垃圾,使街面显得不宽敞,也不明洁,尤其是落叶会给创建工作惹麻烦。因此定常绿乔木为“市树”也不言而喻。
江城实际的霜降比日历上要迟滞近一个月,并且清霜降下后消融得也快。我发现大地上的落木都有自已的速度,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小节气。比如,我把这棵树叶子黄透之日称为它的“霜降”。所谓黄透,其实不含一点枯色,灿丽,素洁,轻飏。这是它自己的生命物语,或者抒情方式。至于注视它的人,也因此领受了大地轮转的微妙重量。
我时常带着大毛小毛在树下玩,我指着它的脸,它的头发,教她们发“树”和“树叶”的音。可是我够不到最上面的粗壮枝桠,否则我会让大毛小毛轮流骑在上面,让她俩在比我高的地方看我,看世界。当然,它的下面有一个石凳,大毛小毛就在石凳上玩,有时看树,有时看行人。后来有一天,大毛指着树说,“是妈妈”。还有一次,小毛在树下跌倒了,她哭了,一连说:“树打我,树打我。”
也就在去年,我目睹了满树的黄叶渐渐落稀,以至于剩下最后几片叶子,在常绿乔木中显得特别孤零,仿佛初冬残剩的几只蝴蝶。虽然我没看见它们如何飞走,但我想它们飞离的间隔不过几分钟,而且是在朔风野大的深夜时分。记得有一次跟父亲聊天。父亲说有个老战友“走”了。我随口说,人上了年纪,就象树上的叶子,说落就落了。父亲无语,只是望着窗外的树。
想想看,每一轮叶子不都是这样慢慢变黄,变稀,然后消失的么?
但对这棵树而言,每年它都要经历自己的“大雪”时分。这正是它突然打动我的原因。想一想吧,纷纷扬扬的树叶悉数飘落的时刻,人们正在暖被窝里做着春梦。事实上,暖冬时代的“大雪”已形同虚设。早晨起床,我看见它站在自己落下的“大雪”——那黄灿灿的一圈叶子中间,有一种特别清亮、疏淡的韵味。人们为什么要过多忌惮岁月的凛冽呢?你究竟留下过什么东西来见证这飘零的年华?
这与春天是不同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它那光秃秃的树桠上便睁开许多细小芽苞,几阵暖风吹过后,它就丰满、绚烂得恰到好处,像年轻时出现在梦中的青葱少女。因此,我把它长出第一片叶子的日子叫作“立春”。
雪后之夜
半夜里,一个男人凄惶的叫声惊醒了我。如果不是这个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后的冻夜,我或许会误认为那是谁在“吊嗓子”。那低沉的声音抖颤着发出来,缓慢地扬上去,麻花一般扭着,然后突然凝止在空中,仿佛被更高处的雪冻结;随之而来的无边寂静又将它碾碎,没有激起任何回声,只是被他稍息后再次发出的叫声,应答着,证实着。
大约是个流浪人,无家可归,蜷缩在屋檐下或楼道里,被提前来到的酷冷冻得叫起来。我心里这样想,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深切体验。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挨冻时,向着天空叫喊是否能暖和身子。当然,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在表达一种祈求、绝望、无奈、愤怒、恐惧相混和的情绪。但那叫声听上去绝不惨烈、尖厉,而只是凄惶、孤单,甚至在人与野生灵声音的边缘滑动、模糊。我感到几分惊悚和不安。尽管人是动物的一种,但一个人何以又回复到发出类似史前动物时代那样的叫声?
显然,他十有八九是个精神病患者,按通常的说法,他是一个孬子。这或许可以让听见这种叫声的人,包括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和无聊。不过是一个孬子而已。但问题是,在寒冷驱使他发出本能的叫声这一点上,他与任何陷于类似困境的正常人相同。当一个人的自我丧失干净,包括思想、奢望、情感乃至语言都丧失干净,而只能退守到本能,并本能地发出叫喊,那么这样的时刻是怎样的时刻?比如溺水者,祈雨者,遭遇猛兽者,比如那些与洪水搏斗的先民,甚至包括钉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喉咙里模糊不清的“哦哦,咿咿、啊啊”的叫声,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这种本能潜存的力量一旦爆发出来,常常能超过他平时力量的好多倍。
一首描述与洪水搏斗的诗这样写道:“那为漩涡所困的船不过是堕水的鸟/每分钟都是它最后的时刻/只有人,早已与兽揖别的人/此时重又焕发出兽的野性/发出‘啊啊’的不成语言的呼喊/……/--在这样的时刻/谁敢想到自己一定会活下去?/天空已不存在/时间已不存在/无数个自我也消失干净/只有人的疯狂七月之潮的疯狂”。
不幸的是,有的时候,人连本能或本能的叫声也被封杀了。记得有部当代小说,写到一个人被剥夺结婚权时,那个人只丢下一句话:“还得像牲口一样活着。”人落到这种地步,当然还可以选择更干净、更自尊的解决方式,至少“死亡”的本能是任何力量也难以剥夺的。但“活着”的本能毕竟更顽强些,甚至“死亡”的选择也是为了“活着”,人之为人的一点尊严。
我觉得,应该将“只剩下本能”与“退守到本能”加以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放纵行为,一种物化状态。后者恰恰是严峻的、“不得不”意义上的生存处境,它意味着一个人,乃至作为集体的人的根本处境遭到了致命的危机。我曾在报纸上读到有关考察古楼兰国遗址的报道。在苍凉的西域戈壁,古楼兰国那无声无息的消亡已成为流沙中的千古之迷。但不管怎样,它肯定有最后离去的一群人,或者坚守在那儿的最后一个人。当他承受不了倾圯王国的荒凉,那一轮被流沙焚烧的悲怆的落日,难道他不会仰对目击过王朝自戕的大漠虚空,像沙狐一样“噢噢”地叫上几声?但那叫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听到了,尽管我们仍能听见那叫喊消失后无边无沿的死静。
沿着这样的思路,“最后一个”,“最后一地”,以及“最后一天”,这些词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距日常的沉沦状态确乎太远,否则人群中的倾轧、使绊是否会少些呢?
当然,这些与那个叫喊的家伙并无什么关系。他是一个个体,一个当下的偶然,一个被寒冻剌痛肉体的人,一个逃离并丧失了对家的记忆的人。
我感觉他的方位在发生变化,好象已移向排水沟,徘徊于架设十几根油管的桥边一带。他的叫声也比先前微弱,甚至好久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在居民区,还有什么障碍物能遮住他的声音?那些前呼后应的人群已在夜色中消遁、沉入梦乡,只剩下一片冰碴般的真实:被群体遮掩又被群体悄悄抛离。小小的隐秘的命运,在空旷的寒夜来得过于迅速!
不妨说,这仅仅是一个暗示,一个在冻结的反面滚动的暗示。在随后而至的白日里,它肯定将被谈论、被遗忘以及被过多的阳光温馨地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