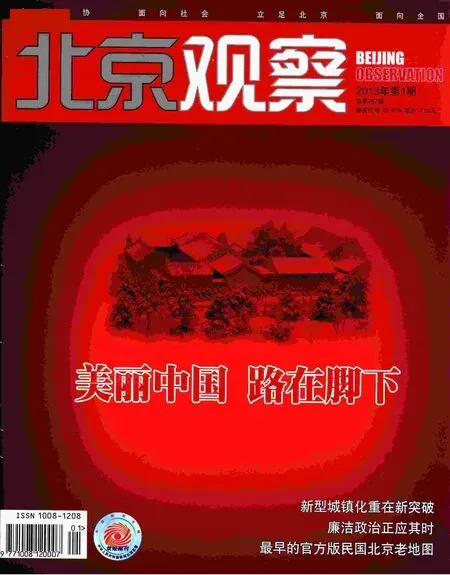活水活心的新城镇化
文/毛大庆
作者系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镇”字的巧妙绝非文字游戏,是针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定国情并切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确概括,可以说如同沙漠里一汪碧水中的泉眼,活水,更活心。
“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却是国家发展观念的飞跃。首先,从行政区划来看,“镇”囊括了更加广袤的地区,关注了更加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次,从人口组成来看,“镇”更加关注农村人口向非农业方式变迁的过程,更加侧重解决农民的问题;第三,从城市发展历程来看,“镇”更加注重片区经济的和谐均衡,规避资源过度集中的大城市弊病。而“镇”字的巧妙也绝非文字游戏,是针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定国情并切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确概括,可以说如同沙漠里一汪碧水中的泉眼,活水,更活心。
我国城镇化率的现状有两个特点,一是较其他国家同一发展阶段要低10-20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化率同农村人口在统计学上存在差异。按照2011年51.27%的城镇化率计算,城镇人口理应达到6.9亿,而当年的农村户籍人口是9.3亿,也就是说城镇人口仅为4.2亿,近三分之一的差距更加真实地提醒我们,在看到国内外城镇化率差距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和机遇的同时,需要更加紧迫地落实城镇化人口的质量提升。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总结内在规律,有利于城镇化过程中的科学推进和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美国、德国、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在上世纪20年代末、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达到我国目前水平,并分别通过31年、20年和14年实现了收入倍增。其城镇化的发展存在明显共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新兴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是收入倍增过程中主要产业特征。城镇化不是简单转换农民身份,进行城市建设,其发展必须以非农就业增加为基础。各国数据都显示,制造业是容纳非农就业的第一大行业。从结构看,以纺织、钢铁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就业数量下降,以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半导体、电子电器等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就业大量增加。
较低的运输成本决定了海岸线和重要内河沿岸是制造业转移和分散的主要区域,其他内陆地区机会较少。美国、德国这些陆地型国家,沿海岸线或河道发生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和新兴制造业分散。日本作为海岛型国家,制造业始终集中在东京-阪神都市圈,没有发生转移和分散。
人口分布跟随制造业布局,出现新的聚集点。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加州,南部墨西哥湾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德国新兴地区黑森、巴登-符腾堡州;日本的东京-阪神都市圈都是很好的例证。
通过卫星城建设,在核心城市周边发展100万—500万人的中型城市更符合城市管理效率的需要。德国77%的城镇人口分布在小于50万人的城市,没有出现过度拥挤的问题,但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高昂。目前,德国中部地区、前东德地区的许多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已很难继续维持。日本将近一半人口集中在超过1000万人的大都市圈。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政府向全国进行产业分散的政策努力均告失败。最终,依托制造业和居住地向核心城市周边县市迁移,才使得东京都、大阪府人口密度得以稳定下来。美国以大中型城市搭配为主,100万—500万人的中型城市人口占比34%,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人口占13%。城市管理问题相对没有德国、日本突出。
而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像墨西哥城、孟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世界级大城市中大量的贫民窟成为了快速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后遗症。比如孟买,全市1300多万人口的60%住在贫民窟,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8平方米。究其根本是没有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很快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然而激烈的竞争导致制造业远离城市追求低成本;农民失去了土地却又找不到工作,大量贫民窟必然成为他们蜗居的场所。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与重视并引以为戒。
大步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
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主要有如下特征:制造业转型和服务业发展刚刚起步;小城市数量较多,人口占比偏高,规模效应不足;大城市开发不足,导致“大都市病”过早出现。参考国际经验,下一阶段推进城镇化的策略应该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由偏重基础建设和投资向更加注重产业升级、乡镇企业扶持等内驱力的打造转变。
发挥水路、铁路运输优势,继续发展沿海、沿江、沿铁路地区制造业。水路运输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铁路的1/3,且无需前期大量投资,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和长江沿岸区域,发展制造业和新城镇。特别是应支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新兴制造业发展。在这些地区开展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吸引欠发达地区人口。
在教育资源发达地区鼓励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建议重点支持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等教育资源集中地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创造中国的“硅谷奇迹”。
降低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展的行政门槛,引导人口在特大城市周边的城市群内分散。应下放审批权力,允许东部特大城市的周边城市自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跨行政区域和级别的城市间协调机制,避免断头路等公共设施不兼容的情况发生。通过融资渠道创新、省管县等财税分配改革措施,支持100万-500万人符合规模经济的城市财政资金实力。
在确保耕地保护和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提高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占比,解决特大城市过度拥挤问题。要按常住人口规模,重新确定城市建设用地人均标准,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应控制特大城市工业用地占比,防止利用较低土地价格吸引工业项目的做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例如建立存量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已有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打破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的“玻璃门”、“弹簧门”。要减少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的行政审批,简化行政管理流程。理顺民营教育、医疗机构与公共教育、医疗制度的对接机制。完善法律环境,为民营服务机构提供公平待遇。